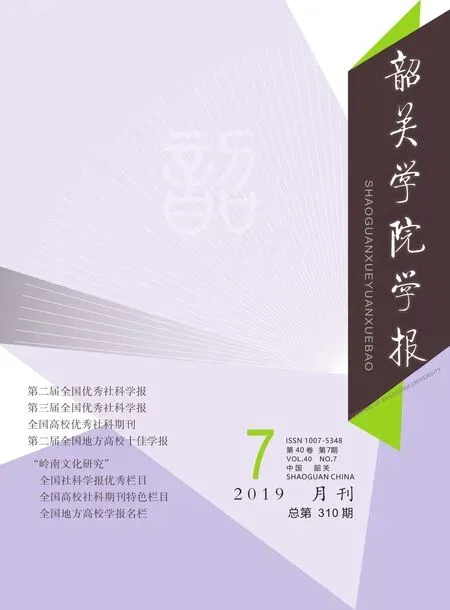方言学视域下汉族民间歌谣的记录与保护
——以仁化石塘“月姐歌”为例
李冬香,毛俊杰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510665)
“月姐歌”是流传于仁化县石塘村女性中的古老民歌。相传是唐朝宫女月莲逃至石塘后用石塘方言传授给当地妇女的宫中歌曲。“月姐歌”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是姐妹、婆媳间口传心授,并以清唱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开坛”至八月十五“收坛”,期间每天晚上全村妇女不分老幼,分别聚集在几个最会唱歌的“歌首”家开设歌坛。据传,鼎盛时期,全村设有11个歌坛,每个坛的主要成员有30多人[1]。现在,石塘“月姐歌”仅剩2个歌坛,共60余人。
“月姐歌”作为一种民间活动,其发展并不顺利。20世纪60-7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几近失传;80年代后,渐渐活跃起来。2007年,“月姐歌”被列入韶关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月姐歌”走出深闺被人识,有关“月姐歌”的记录和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
据笔者搜集到的材料,记录“月姐歌”的歌词和曲谱的有饶纪洲整理的《粤北采茶戏音乐》(下文简称《采茶戏音乐》)中的“灯调”,《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编辑委员会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广东卷)(下文简称《歌曲集成》),韶关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的《中国歌谣集成》广东卷韶关分卷——《韶关歌谣集成》(下文简称《歌谣集成》),以及李招环的《仁化月姐歌集》(未公开出版)。从学术角度研究“月姐歌”的有宗江、战勇的《广东民间的“月姐歌堂”》、熊茵的《论客家情歌之情感堂会——月姐歌》、杨韶军的《石塘“月姐歌”的特色及其价值》、王群英的《粤北仁化县石塘古村“月姐歌”的艺术特征》和《石塘月姐歌探骊》、张鸿舜的《音乐形态学视野下的粤北山区村落民谣——以广东仁化石塘“月姐歌”为例》和《〈石塘月姐歌〉的音乐特征》、李暑红的《仁化石塘村月姐歌研究状况述评》。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月姐歌”是用石塘方言演唱的,但专门从石塘方言本体来研究“月姐歌”的成果尚未见到,因此,本文拟根据已有的“月姐歌”的歌词和笔者的实地调查,从石塘方言本体的角度探讨“月姐歌”歌词的记录情况,进而讨论汉民族民间歌谣的保护问题。
一、“月姐歌”歌词记录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月姐歌”是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录的,因此,不同的传承人口中的歌词会有所不同,不同的记录人所记录的情况也会有出入。下面我们根据已有的材料阐述“月姐歌”歌词记录中存在的五方面问题。
(一)用来自其他方言或官话的词语进行记录
用来自其他方言或官话的词语记录“月姐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伍巍指出:“当然,中国民歌也有被文字记录的历史,记录民间歌曲如果没有方言的专门知识,不能按方言的原貌处理,反映地方土语的用词习惯,即使记录下来,也往往会失真,或多或少地渗入某些书面语的痕迹。”[2]下面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歌谣集成》中《私求姐》记录表示引进、给予对象的词用的是“给”,如“私求姐来私求姐,买条头绳送给你。”[3]115-117但石塘方言“(借)给(我)、给(他)、被(他吃了)”都用“俵”。如:钱俵渠用了了钱被他花掉了。|俵本书在渠给他一本书。[4]353-355在《歌谣集成》和《歌曲集成》中,《私求姐》中问物的疑问代词都写作“什么”。如“多谢哥来多谢哥,要你梳子做什么?”[3]115其实,石塘话不说“什么”,而说“□sɿ45□ma45”。如:渠在做□sɿ45□ma45呢他在干什么?|你去做□sɿ45□ma45呢你干什么去?[4]361-363这里的“给”和“什么”明显来自官话。
另外,否定词的记录也存在问题。普通话的“不”石塘话说“唔”,但是,有些把“唔”记为“不”。如:“一转来到罗一一罗行呀,不生不熟罗哎依哟初相交罗哎。”[5]147“八月采茶茶打花,风吹茶花不成双,八十婆婆摘朵插,新茶不当老茶香。”[6]487-488“九月香包绣九行,九月九日是重阳,旁人话我绣得好,不晓老人在何方?”[6]498
此外,有时候记录人还会用自己的方言或周边强势的方言来记录“月姐歌”。如《私求姐》表示引进给予对象的词“俵”在《歌曲集成》中记为“畀”,如“私求姐来私求姐,买把梳子送畀你。”[6]490-491这个“畀”来自当地的粤语。另外如《十二月歌》中把母猪、母牛记为“猪嫲、牛嫲”[6]492,这明显是来自周边的客家方言。石塘话母猪、母牛不说“猪嫲、牛嫲”,而说“猪婆、牛婆”[4]211。
总之,由于记录者经常用官话或者其他方言来记录“月姐歌”的歌词,使得“月姐歌”的地域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
(二)同音替代
《接月姐》是“月姐歌”歌坛中最重要的一首歌,可是流传下来的这首歌词由于用同音字来记录而使人无法理解。如第一句《歌曲集成》记为“赏高月,高云青,高云修个春千间”[6]486。赏月一般赏的是“皎洁”的明月,而不是“高高”的明月。其实,这里“月”前面的修饰成分“高”应为“皎”。在石塘方言中,“皎”与“高”是同音字,都读为“kau44”[4]94-95。
在“月姐歌”中,多次出现“郎子”这个词。如“四月里四月花,四月滩头如朵花,过路郎子莫要拗(呀),留出细妹做一扎(嘿呀个嘿),做一扎”[6]492。“悠悠慢慢(啰)锣合鼓(啊),有钱难买学唱(呀)歌。有钱郎子(哩)唱得好(啊),没钱郎子鼓吹(呀)迎。”[6]489-490据笔者调查,“郎”在石塘话中是“女婿”的意思,“子”是一个非常用词的词缀。根据歌词上下文的内容,此处“郎子”不应是“女婿”之意。原来,石塘话“郎”与“男”同音,都读 loŋ22,上述歌词中的“郎”应为“男”;“子”应为“仔”,是一个常用词的表示小称的词缀。“郎子”实为“男仔”,是“年轻男孩”的意思[4]265。这样一来,歌词的意思就很容易理解了。
(三)对衬字的认识有偏误
在《歌曲集成》中,衬字一般加圆括号。该书在《凡例》部分指出:民歌的衬词,如啊、哎、哟等多数是虚词,但也有的是实词,如“刘三妹”“刁嫂子”“我是心想妹”“黄草帽娇髻妹”等;有的民歌虚词、实词夹杂其间。为了区分主词、衬词,特将所有衬词一律用圆括号括起来[6]10。这个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认识不够准确,以致有时把非衬字当作衬字,最典型的是“个”字。如《竹叶歌》:“……姐妹大家看龙灯(呀),多看(个)花灯赛赢人,多看(个)花灯赛赢人。……姐妹上岭看种子(呀),多看(个)种子赛赢人,多看(个)种子赛赢人。”[6]488-489还有如《私求姐》:“要亻厓梳子就想梳(呀),梳起(个)头个靓嗬嗬。梳起(个)头上靓嗬嗬。……要亻厓头绳就想扎(呀),扎起(个)头个靓嗬嗬。扎起(个)头上靓嗬嗬。……”[6]490-491其实,这个“个”不是衬字,而是指示代词,相当于普通话的“这”。为区别于量词“个”,我们把指示代词“个”写为“個”。如:個个系渠哩书这是他的书。[4]346试比较:
(1)姐妹大家看龙灯(呀),多看个这花灯赛赢人,多看个这花灯赛赢人。
(2)姐妹大家看龙灯(呀),多看(个)花灯赛赢人,多看(个)花灯赛赢人。
很明显,(1)句由于指示代词“个”的使用,整首歌的歌词语意顺畅连贯,情感丰富。(2)句理解为衬字的话,虽然歌词内容基本不变,但语意的顺畅和情感的丰富明显要弱一些。
(四)书写形式不一
同一个读音,同一个意思,用不同的字形来书写。如“月姐歌”中的“我”,在不同的记录中就有不同的写法。《采茶戏音乐》写作“涯”,如:“一轮丝片官家哩知呀,以前拿涯红花女呀,如今拿涯在官家呀,身边眼泪抹唔干。”[5]142《歌谣集成》写作“亻厓”。如“要亻厓梳子就想梳呀,梳起头上靓嗬嗬”[3]115。在《歌曲集成》中,有时写作“亻厓”,有时写作“我”。《私求姐》写作“亻厓”的如:“(男)要亻厓梳子就想梳(呀),梳起(个)头个靓嗬嗬。”写作“我”的如:“(男)要我衣裳就想穿(呀),穿起(个)身上靓嗬嗬。”[6]490-491在上述三个字形中,“亻厓”是当地方言俗字,“我”是本字,而“涯”则是一个同音字。
表示“没有”的否定词,《歌曲集成》写作“没”,《采茶戏音乐》则写作“冇”。如《悠悠慢慢》的后两句前者记为“没有人家(啰)养老女(啊),只有单身没老(呀)婆”[6]489-490。后者记为“冇有人家养老女呀,只有单身冇老呀婆”[5]136。很明显,“没”写的是官话,“冇”写的是方言俗字。
书写形式不一,不利于“月姐歌”的保护,进而会影响到相关的研究。
(五)缺乏必要的注释
汉语方言非常丰富,内部差别很大,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方言区有可能意思完全不同。因此,为了既保持方言特色,又便于不同方言区的读者理解,适当的注释是非常必要的。如《一轮丝片》:“一轮丝片我儿哩知呀丢了。涯儿叫哀哀呀,日头时辰冇娘痛呀,日落未时冇娘想。”[5]142这里的“叫”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叫喊”,因而就很难理解后面两句“日头时辰冇娘痛呀,日落未时冇娘想”。事实上,石塘话的“叫”是“哭”的意思。解释为“哭”后,后面两句与前文的语意衔接就很顺畅了。
《歌曲集成》对部分歌词加以注释,如《十二月歌》中解释了“牛嫲母牛”“鸡嫲母鸡”“猪牯公猪”,但还是有一些应该解释的地方没有解释。同是这首歌中出现的“笠嫲”就没有解释[6]492。读者如果根据“牛嫲母牛”“鸡嫲母鸡”中的“嫲”去类推“笠嫲”表示雌性的动物就大错特错了。其实,这里的“嫲”并不表示雄雌,只是一个词缀而已,相当于普通话的后缀“子”“儿”。“笠嫲”就是“斗笠”的意思。
2017年中秋节期间,笔者实地走访了“月姐歌”歌坛,亲耳听到当地村民演唱《私求姐》《竹叶歌》《悠悠慢慢》等歌曲,演唱的方言是非常地道的石塘话,与我们上文对“月姐歌”歌词的认识一致。
二、“月姐歌”歌词记录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对方言词语的价值认识不够
由于“月姐歌”是用方言演唱的,方言是一地之音,因此,有些调查记录者或许是为了让外地人能看懂歌词,就用官话或者周边强势方言如粤语等来转写。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就使得“月姐歌”不能以原生态的面貌展示出来。作为民间歌谣的记录,首要的是如实、准确。因为:
第一,方言词语是地方文化特色的载体之一。简其华在谈到关于少数民族民歌歌词的记录和翻译时指出:“我们都知道,词和曲是构成民歌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民歌的思想内容不但表现在曲调上,而且表现在歌词上,后者还往往占有更重要的地位。”[7]歌词是一地地方特色文化的载体之一,失去了地方特色,其音乐的地方特色就大为降低。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客家话的俗名。客家话又叫“麻介话”,“麻介”的得名就是源于其“什么”的说法。如果我们用“什么”来记录这个词,其方言特色就显著降低。
以“月姐歌”来说,表示“看”的动词,石塘话用“望”,但《竹叶歌》记作“看”。如“正月好唱竹叶新,门前花灯闹沉沉。姐妹大家看龙灯(呀),多看(个)花灯赛赢人,多看(个)花灯赛赢人。二月好唱竹叶新,门前种子闹沉沉。姐妹上岭看种子(呀),多看(个)种子赛赢人,多看(个)种子赛赢人”[6]488-489。由于“看”的使用,“月姐歌”的地方特色受到了影响。
第二,方言词语有利于准确表达歌谣的思想情感。魏建功指出:“我们要建设有活力的新的中国文学,活语言的词类不能不充实,我们要充实文学的活语言,方言词不能不尽量采用。”[8]方言中的很多词包含了丰富的思想感情,用普通话很难生动地再现出来。如《竹叶歌》描写了十二个月的自然景观以及每个月姐妹们的活动。其中每一个月相应的景观后都用“闹沉沉”一词来描写,如:正月“门前花灯闹沉沉”,二月“门前种子闹沉沉”,三月“门前笋芽闹沉沉”,四月“门前莲花闹沉沉”,五月“门前龙船闹沉沉”等等[6]488-489。“闹沉沉”是形容热闹、充满活力的样子,其使用范围非常广。通过“闹沉沉”的反复使用,渲染了一年四季充满生机的画面,烘托了姐妹们愉快的心情。如果换作普通话中相应的说法,就失去了这种修辞效果。
第三,如实记录方言词语有利于学界利用这些材料开展相关的研究。周作人指出:“其次,我觉得歌谣上也颇有修改过的痕迹。本来纪录方言是很困难的事情,在非拼音的汉字里自当更是困难,然而修改也不能算是正当的办法。上边所说《拜菩萨》一首里,便改了好几处,如‘这样小官人’原本是‘ㄍㄚㄍㄜ小官人’——范氏写作‘概个’,意云这样的一个童男,经集里改作国语,口气上就很不同了。……虽然说这些书或者原为公众或儿童而编的,未始不可以作为辩解,但在学术的搜集者看来不能不说是缺点,因为他们不能成为完整的材料,只可同《演小儿语》仿佛,供检査比较的备考罢了。”[9]
如普通话的“的”,石塘话说“哩”,如:個个熟哩这个是熟的。[4]349但是,在“月姐歌”的记录中,几乎都把这个“哩”记为“的”。如:“正月风吹海棠花呀,新官上呀任坐旧的衙。大小官员来恭贺哩,开怀畅饮穷人的膏。”[5]137“新打的龙船呀十二哩座。初三哩初四哩睇龙呀船。”[5]167-168如有学者利用这些材料来讨论石塘方言的结构助词,就会得出错误的认识。
(二)缺乏相关的方言学专业知识
当然,“月姐歌”歌词记录的问题除了源于记录者没有认识到方言词语的价值以外,也有相当部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不太熟悉一些方言区俗字的写法,不会探求方言的本字。如前文把“唔”记为“不”、“冇”记为“没”就是由于不熟悉方言俗字所致,把“皎”写为“高”则源于没有掌握方言学的专业知识。还有如《怨爷娘》中的“妈妈”一词在《歌谣集成》中写作“亚娘”[3]137,《采茶戏音乐》写作“妈娘”[5]145。石塘话中妈妈有“阿娘”一说,“亚”与“阿”同音[4]68。记为“亚娘”让人费解,记为“妈娘”大概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所致。
由于缺乏方言学专业知识,有些比较土俗的方言词语,其记录就很不准确。如《季节歌》中有三句这样的歌词实在让人费解:“正月钉波潭(□□叮),二月透皮烂(啊)……十一月婆婆新遂新(□□叮)……。”[6]495根据笔者实地调查核实,这三句应为“正月钉陂□tεŋ314(□□叮),二月斗陂塘(啊)……十一月婆婆请新酒(□□叮)……”。意即:正月筑陂基,二月筑陂头……十一月婆婆办酒……。
三、从“月姐歌”歌词记录看汉族民间歌谣的记录与保护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重视与高度关注,有关的科研成果丰硕。但是,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是讨论非遗保护的数字化建设问题,甚少涉及如何开展调查和进行记录。我们认为,数字化是非遗保护的技术手段。在进行数字化保护之前,首先应该进行如实、准确的记录,这是做好非遗保护的前提和保证,尤其是像这种没有文字记载的、靠世代口耳相传遗留下来的汉民族民间歌谣。
在民间歌谣的记录与保护中,少数民族的相关研究一般都有语言学专业人士的参与。可是,汉族的民间歌谣,除了早期有很多语言学家参与并非常重视它的记录以外,后来的歌谣记录不太重视方言词语。我们实地调查中,有村民提供了《一条禾秆》的歌词,歌词是:“一条禾秆双条心,我爷养女二号心。大女放在高粱屋呀,细女放在田中心。六月校田水六脚,头戴笠帽日晒身。……”其中的“六月校田水六脚”让人很费解。根据她们的现场吟唱和我们此前对石塘方言的调查,方才明白此处用的是同音字,“校”应为“薅”,“六”应为“渌”。“六月校田水六脚”实为“六月薅田水渌脚”,意思是“六月耘田水烫脚”,这样才与下句“头戴笠帽日晒身”语意连贯了。把“薅”写作“校”,把“渌”写作“六”,这样的记录明显不利于我们对“月姐歌”的理解和保护。还有如《歌曲集成》把《竹叶歌》和《私求姐》中的“个”理解为衬字,影响了对整首歌的意思和情感的把握。正如沈兼士所说:“……歌谣是一种方言的文学,歌谣里所用的词语,多少是带有地域性的,倘使研究歌谣而忽略了方言,歌谣中的意思、情趣、音调,至少有一部分的损失,所以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工夫。”[10]
“月姐歌”只是汉族歌谣中的一支,有关它的记录中存在的问题看似是一个个小问题,但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损害了“月姐歌”的地方特色,丧失了其包含的诸多信息,从而影响到它的保护和传承。如果这些问题在汉族歌谣乃至其他口传文化的保护工作中普遍存在,积少成多,会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失,因此,我们必须予以重视。
四、结语
以上根据现有材料讨论了“月姐歌”歌词的记录问题,其中相当部分问题是由于记录人对方言词语的价值认识不够引起的,也有的是由于缺乏方言学专业知识造成的。“月姐歌”歌词的记录情况启示我们,要做好汉族民间歌谣的保护工作,离不开对方言词语的重视和相关的方言学专业知识。实际上,在记录这些民间歌谣时,如果能进一步记录歌词的读音,就会使歌谣的分析研究更上一个台阶,因为方言特色最显著的载体是语音。魏建功很早就指出,搜集歌谣应全注音并标语调[11]。可惜,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目前的记录绝大部分未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