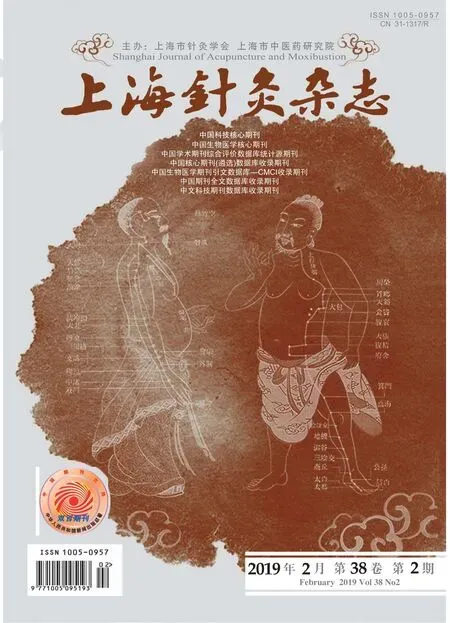针刺胃肠俞募穴对卒中后便秘的随机对照研究
冷孟桐,王剑,刘韬,吴坤朋,张洪伟,孙晓伟
针刺胃肠俞募穴对卒中后便秘的随机对照研究
冷孟桐1,王剑1,刘韬1,吴坤朋1,张洪伟1,孙晓伟2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哈尔滨 150040;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哈尔滨 150040)
观察针刺胃肠俞募穴治疗卒中后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疗效。将66例卒中后功能性便秘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33例。治疗组采用胃肠俞募配穴针刺治疗,取胃俞、大肠俞、小肠俞及中脘、天枢、关元;对照组口服中药六磨汤原方。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并在基线期、治疗期以及随访期对患者CCS和大便性状进行评分。治疗组和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90.9%、42.4%,两组治疗后CCS评分与大便性状评分均低于治疗前(<0.05),且治疗组疗效更为显著(<0.05)。随访期两组患者CCS评分和大便性状评分都有上升,但治疗组上升幅度明显低于对照组(<0.05)。俞募配穴针刺能明显缓解卒中后功能性便秘症状以及改变大便性状,优于单纯中药治疗。
穴,背俞;穴,募;针刺疗法;中风后遗症;便秘
功能性便秘不存在器质性病因,且为非肠易激综合征型便秘,患者排便不通畅,便质干结如羊屎,或便质不干但排除不能,并伴有焦虑、烦躁等神经系统症状,对患者心理、生理都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1]。据流行病学调查统计,卒中后4周便秘发生的几率高达50%以上,通常以卒中急性期多见[2]。功能性便秘的发病机制至今未得到确切的说法,目前已知的发病机制有脑-长轴异常、肠道菌群失调、肠道运动相关神经递质异常、肌肉功能障碍等。卒中后出现便秘的患者多数心烦焦虑精神压力大、食量减少饮食结构改变、后遗症偏瘫患者长期卧床体力活动减少,致使胃肠蠕动减慢,腹肌、膈肌、肛门括约肌肌力减弱均可诱发此病。且患者排便时不能用力过猛,否则会增加腹腔压力和心脏收缩力,使颅内压及动脉血压急速升高[3-4],诱发颅内二次出血,甚至猝死。因此,对卒中后功能性便秘的治疗不能忽视,本研究采用俞募配穴针刺法,与单纯口服中药对比,采取随机对照研究,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试验选取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科住院部卒中恢复期后首次出现功能性便秘的66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33例,卒中病程控制在10个月以上。入组前分别对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卒中病程、基础疾病类型、BMI以及美国国立卫生院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SS)进行评估,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0.05),详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1.2 诊断标准
1.2.1 西医诊断标准
卒中的诊断标准参照《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5]。
功能性便秘的诊断标准参照RomeⅢ诊断标准[6]。
1.2.2 中医诊断标准
中风病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科研协作组制定的《中风病诊断疗效评定标准》(试行)[7]。
便秘参照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8]。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以上诊断标准;②卒中病程控制在10个月以上,发病前无便秘病史;③患者意识清楚,生命体征正常,能够配合治疗;④签署知情同意书;⑤参加本研究期间不能参与其他研究。
1.4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以上纳入标准;②患有严重心血管、肝脏、肾脏疾病;③腹主动脉瘤或肝脾肿大;④凝血功能障碍者;⑤生命体征不平稳者;⑥肠道内发生器质性病变者;⑦拒绝针刺者。
1.5 剔除及脱落标准
①治疗期间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及并发症者;②不能遵循医嘱者;③自愿退出本试验者。
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都依照卒中单元模式治疗,连续治疗4周,随访4周。治疗前1周为基线周,此期间嘱患者清淡饮食多饮水,忌服其他有助于排泄的药物;针对基础疾病根据个体差异予以相应的药物治疗。
2.1 治疗组
2.1.1 取穴与刺法
采取俞募配穴,背俞穴选用小肠俞(双)、胃俞(双)、大肠俞(双);募穴选关元、中脘、天枢(双)。针刺处皮肤用乙醇棉球常规消毒后,使用0.35 mm×60 mm针灸针,小肠俞直刺25~30 mm,胃俞斜刺15~25 mm,大肠俞直刺25~30 mm;腹部穴位采用0.35 mm×40 mm针灸针,天枢直刺20~30 mm,中脘直刺15~20 mm,关元直刺15~20 mm,以穴位处有触电样感觉为度,留针50 min。每日1次,7 d为1个疗程(连续针刺5 d,休息2 d),连续治疗4个疗程。
2.1.2 针刺异常处理
晕针:马上中止针刺,迅速起针,去枕平卧,松开衣带,可饮适量温开水或糖水以缓解不适。若上述方法无效可采取急救措施。
滞针:安抚患者以消除其紧张不安情绪,可循按针刺穴位附近皮肤,或弹叩针柄以缓解肌肉痉挛状态。
血肿:若微量出血可自行吸收;若局部肿胀或出血面积较大,用乙醇棉球按压3~5 min即可。
2.2 对照组
予中药六磨汤原方治疗,药物组成为乌药10 g,大黄10 g,木香10 g,沉香10 g(后下),枳壳10 g,槟榔10 g。每日1剂,于早饭前30 min和晚饭后30 min各温服150 mL。7 d为1个疗程,连续治疗4个疗程。
3 治疗效果
3.1 观察指标
3.1.1 便秘临床评分量表(CCS)
便秘临床评分量表(CCS)通过对患者排便频率、排便困难程度、排便不尽感、腹痛、排便时间、排便不成功次数、协助排便、便秘病程这8个方面,分别进行评分,评分最低0分,最高30分,评分越高表示便秘越严重,在治疗前、治疗结束后以及随访期最后一天分别进行评分。
3.1.2 布里斯托(Bristol)粪便性状评分[9]
治疗前、治疗结束与随访期间,观察患者每周的大便性状,依照标准表进行评分,并由专人记录。计算方法为7 d内每次评分和除以排便次数。在治疗开始前对患者前1周的大便性状进行评分。
3.2 疗效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0]中相关标准。
痊愈:排便基本通畅,排便时间正常,2 d内可排便1次,大便表面光滑质软,解便通畅,无排便障碍及其他不适感,或便秘积分减少大于95%。
显效:便秘症状减轻,排便时间较长,2~3 d内可排便1次,便质较干,接近正常,表面略有裂痕,排便略困难,或便秘积分减少大于2/3。
有效:便秘症状减轻不明显,3~4 d可行1次排便,便质较之前略有松散,解便不通畅,便秘积分降低大于1/3不超过2/3。
无效:便秘症状未见减轻,便秘积分减少小于1/3。
3.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24.0统计软件,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4 治疗结果
3.4.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由表2可见,治疗组和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90.9%、4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05),且治疗组疗效更为显著。

表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注:与对照组比较1)<0.05
3.4.2 两组治疗前后CCS评分以及各因素评分比较
两组治疗后CCS评分均降低(<0.05),且治疗组治疗后CCS评分低于对照组(<0.05)。随访期间两组CCS评分均较之前小幅度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0.01),表明两组方案均能有效改善卒中后功能性便秘的症状,且治疗组更加明显。详见表3。

表3 两组治疗前后及随访期各因素评分比较 (±s,分)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1)<0.05;与对照组比较2)<0.05;与同组治疗后比较3)<0.01
3.4.3 两组治疗前后及随访期间布里斯托大便性状评分比较
在基线周、治疗期以及随访期对患者大便性状每周进行评分,治疗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两组在随访期评分稳定、反弹较小,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详见图1。

图1 两组治疗前后及随访期间布里斯托大便性状评分比较
4 讨论
卒中,中医学称之为“脑中风”,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第二致残和死亡的原因[11],其发病率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而在卒中的众多并发症中,单单功能性便秘的发病几率就高达30%~60%[12]。功能性便秘的中医学称谓较多,常见有“肠结”“脾约”之称,如今统称“便秘”。中医学认为,便秘的病因很多,归结起来不外乎饮食不节、外邪侵袭、年老体虚以及情志不舒。便秘的产生主要由于大肠传导糟粕机能失常,卒中后大多数患者肝郁气滞,情志失调,尤其以年龄偏小的患者最为常见。气机郁滞不能下行,水谷精微不能下输于大肠,堆积在体内则生便秘。正如《医林改错》王清任所云:“半身不遂之后……乃无气力催大恭下行……日久不行,自干燥也”。故在治疗上主要以行气、破气、补虚、通下为主。本研究取用俞募配穴,俞募二穴均为特定穴,是脏腑之气汇聚于背腰部及胸腹部的处所。早在《难经》就曾提出背俞穴可治疗五脏病,腹募穴可治疗六腑病的观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提出过“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的阐述,其指出腹部募穴与背部俞穴阴阳两两相对,脏病多与背俞穴相关,腑病则多与募穴联系。《奇病论》:“口苦者……治之以胆募、俞。”说明早在战国时代,古人就已经懂得运用俞募配穴法医治脏腑疾病。天枢穴属足阳明胃经,为大肠募穴及大肠经气聚集之处。《素问·六微旨大论》:“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故取双侧天枢穴上升精微,下降秽浊,破气导滞。关元属任脉,为小肠募穴,任脉与足三阴经之会穴,为先天之气海,具有固本培元的作用。中脘为胃之募穴,与关元穴均为主气之穴,针刺则有助于刺激肠腑经络,气畅则大肠传导有力,有助于胃肠道蠕动及大便的排出。小肠俞、大肠俞、胃俞均出自足太阳膀胱经,古人称背脊为俞,主治对应脏腑及器官病症。小肠俞外散小肠腑之热;大肠俞外散大肠腑之热,具有理气降逆、调和胃肠的功效。胃俞外散胃腑之热,具有健脾、和胃、降逆的作用。
目前西医治疗本病主要采取综合整体治疗,纠正患者饮食结构及生活习惯,多摄取膳食纤维与粗纤维食物;适当对腹部进行按摩以增强胃肠蠕动;必要时采取药物治疗,但口服泻药的长期疗效、安全性以及潜在不良反应仍值得考察。有研究表明[13-15]患者长时间大剂量滥用刺激性泻剂,尤其是蒽醌类泻药,会增加结肠黑变病的发生几率。便秘的中医治疗方法较多,主要有单纯中药治疗、单纯针灸治疗、针药并用以及穴位埋线、穴位注射等疗法。席作武[16]采用消痔灵注射配合针刺,对照单纯使用药物注射治疗便秘,研究显示针药并用疗效明显优于单药治疗,其有效率高达93.75%。王成伟等[17]运用电针干预预防卒中急性期后便秘的临床疗效显著,并且在12周的随访期内电针组疗效依然高于常规治疗组。吕建琴等[18]运用深刺结合电针的方法治疗功能性便秘,治疗第3~8周以及随访期间,深刺结合电针使每周排便频率大于3次的患者人数显著增加;治疗第4~5周时,电针深刺患者的粪便性状评分明显增加;治疗第4周开始,治疗组患者排便困难程度较对照组得到显著改善。王玉中[19]用穴位埋线治疗慢传输性便秘28例。治疗后观察临床疗效及结肠传输功能。第1次治疗后,有效率92.8%;第2次治疗后,有效率100%。以上研究均说明针刺及其衍生方法在治疗便秘的广泛运用,并且日渐成为治疗便秘的主流手段。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20],背部俞穴与相对应脊神经节段的分布基本一致,五脏六腑疾病通常反馈在体表的相应穴位,通过针刺体表反馈区域的背俞穴,刺激神经末梢,通过反射作用于相应的自主神经中枢,直接影响各脏腑机能,其目的在于恢复身体各脏器功能的平衡。近年的胃肠神经病学研究发现,功能性便秘的产生与脑-肠轴的关系密切。脑肠系统通过分泌神经递质传递信息而实现,而这种神经递质称之为“脑肠肽”,它在功能性胃肠病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21]。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俞募配穴针刺法治疗卒中后功能性便秘具有显著疗效,操作简便,耐受情况良好,是值得临床推行使用的针刺治疗方案。
[1] Halder SL, Locke GR 3rd, Schleck CD,. Natural history of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a 12-year longitudinal population-based study[J]., 2007,133(3):799-807.
[2] 邸英莲,严斌泓,赵滨,等.耳穴埋豆联合KEGEL运动治疗缺血性中风患者急性期虚秘40例[J].河南中医, 2017,37(10):1848-1850.
[3] 何静.小承气汤加减治疗脑卒中后便秘48例观察[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07,21(1):67.
[4] 黄小波.芪蓉润肠口服液治疗中风后便秘的临床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2,22(8):622-623.
[5] 中华医学会全国第四届中华医学会全国第四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各类脑脑血管病诊断要点[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12):379-380.
[6] Douglas A, Drossman R. The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and the Rome Ⅲ process[J]., 2006,130(5):1377-1390.
[7]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试行)[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9 (1):55-56.
[8]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18.
[9] Lewis SJ, Heaton KW. Stool form scale as a useful guide to intestinal transit time[J]., 1997, 32(9):920-924.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S].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131-133.
[11] Bonita R, Mendis S, Truelsen T,. The global stroke initiative[J]., 2004,3(3):391-393.
[12] Su Y, Zhang X, Zeng J,. New-onset constipation at acute stage after first stroke incidence, risk factors, and impact on the stroke outcome[J]., 2009,40(4): 1304-1309.
[13] 骆元斌,顾立萍,黄小玲,等.蒽醌类中药致结肠黑变病发病机制探讨[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2014,22 (2):78-79.
[14] 姜明明,徐杨.便秘病例结肠镜检查及追踪的回顾性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2,10(24):13-14.
[15] 李洪玉.87例结肠黑变病的相关因素分析[J].医学信息,2014,27(12):63-64.
[16] 席作武.针药并用治疗便秘160例临床研究[J].中国针灸,2003,23(11):649-650.
[17] 王成伟,刘梦阅.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电针干预防治便秘临床观察[J].中国针灸,2015,35(5):430-434.
[18] 吕建琴,王成伟,刘梦阅,等.电针深刺对功能性便秘患者排便次数及大便性状的影响[J].针刺研究,2017,42 (3):254-258.
[19] 王玉中.穴位埋线治疗慢传输性便秘28例临床疗效及结肠传输功能观察[J].时珍国医国药,2006,17(8): 1545-1546.
[20] 汪克明,周美启,王月兰,等.电针“脾俞”对胃窦部溃疡大鼠胃肠平滑肌电活动的干预作用及其机制探讨[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3,22(6):29-31.
[21] 黄更珍,张耀丹,贺国斌.脑-肠轴在功能性胃肠病中的作用及其研究进展[J].医学综述,2013,19(24):4473- 4475.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cupuncture at Gastrointestinal Back-Shu and Front-Mu Points for Post-stroke Constipation
-1,1,1,-1,-1,-2.
1.,150040,; 2.,150040,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cupuncture at gastrointestinal Back-Shu and Front-Mu points for post-stroke functional constipation.Sixty-six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were randomized to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s, 33 cases each.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acupuncture at gastrointestinal Back-Shu and Front-Mu points: Weishu (BL21), Dachangshu (BL25), Xiaochangshu (BL27), Zhongwan (CV12), Tianshu (ST25) and Guanyuan (CV4). The control group took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Liumo Decoction prescribed originally.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CCS score was recorded and fe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scored in the patients at baseline, during treatment and at follow-up.The total efficacy rate was 90.9%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42.4%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CS score and the fecal characteristic score were lower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before (<0.05)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was more marked in the treatment group (<0.05). The CCS score and the fecal characteristic score increased in the two groups at follow-up, but the increments we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0.05).Shu-Mu point combination acupuncture can significantly relieve the symptoms of post-stroke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and change fec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superior to Chinese herbal treatment alone.
Point, Back-Shu; Point, Front-Mu; Acupuncture therapy; Poststroke syndrome; Constipation
1005-0957(2019)02-0178-05
R246.6
A
10.13460/j.issn.1005-0957.2019.02.0178
2018-05-20
国家教育部“春晖计划”(Z2009-1-15015)
冷孟桐(1992—),女,2016级硕士生
孙晓伟(1979—),女,主任医师,博士后,Email:44792451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