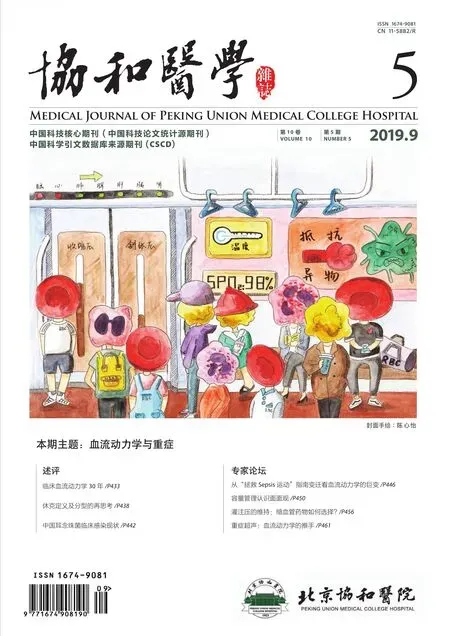中国耳念珠菌临床感染现状
徐英春,黄晶晶,肖 盟,陈新飞,宁雅婷,范 欣, 杨 洋,冯佳佳,林丽开
1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北京 1007302侵袭性真菌病机制研究与精准诊断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7303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武汉 430071
2019年4月9日,《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名为“超级真菌被美国列为‘紧急威胁’,中国已有18例确认感染”的文章(下文简称“文章”)在互联网广泛传播。
什么是“超级真菌”?“超级真菌”真的很可怕吗?为避免对该文内容进行过度解读,导致不必要的恐慌,我们特对“文章”中涉及的概念及我国耳念珠菌的流行及耐药现状予以报道。
1 所谓“超级真菌”的概念
首先,中文译名“超级真菌”是由“超级病原(英文:superbug)”的词义引申而来;准确地说, 国外研究报道中几乎未使用过“超级真菌(英文:super fungi等)”一词。“超级病原”指对绝大部分抗菌药物泛耐药或全耐药的病原微生物,该词过去主要应用于细菌,包括目前被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Staphylococcusaureus,MRSA)、泛耐药的结核分枝杆菌(extensively 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XDR-TB)等。因此,“超级病原”并非新的概念。早在2011年,为应对抗菌药物耐药,特别是“超级病原”带来的全球性威胁,世界卫生组织即提出了“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的行动口号[1],并获得了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积极响应与行动支持[2]。
但在真菌领域罕有提及“超级病原”这一概念。目前侵袭性真菌疾病治疗的药物主要包括以下4类:(1) 唑类药物:如氟康唑、伏立康唑、伊曲康唑、泊沙康唑;(2) 棘白菌素类药物:如卡泊芬净、米卡芬净、阿尼芬净;(3) 多烯类药物:如两性霉素B;(4) 嘧啶类药物:如5-氟胞嘧啶。目前真正对抗真菌药物泛耐药或全耐药的病原真菌全球罕见。
耳念珠菌(Candidaauris)是念珠菌属(Candida)中2009年新发现的菌种[3],其之所以在国际上被冠以“超级病原”的称号,主要归因于以美国为主的地区所受到的威胁[4- 5]。首先,美国首例耳念珠菌感染于2013年报道;随后,巴基斯坦、印度、南非、委内瑞拉等国家相继有散发病例报道[6],但自2016年以来,监测发现耳念珠菌感染在纽约、新泽西、芝加哥等地的发病率快速升高,并出现大量院内感染的暴发案例[4- 5]。其次,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报道,美国发现的耳念珠菌具有较高的耐药性,虽然当前该菌种无临床折点,但若以氟康唑最小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32 μg/ml、伏立康唑MIC≥2 μg/ml、两性霉素B MIC≥2 μg/ml作为判读标准[6],美国发现的耳念珠菌除对经典抗真菌药物氟康唑高度耐药外,半数以上的菌株对伏立康唑耐药,约1/3菌株对两性霉素B耐药。特别是对两性霉素B耐药在临床十分少见,使得耳念珠菌更受重视。此后,在包括英国、印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发现了高度耐药的耳念珠菌以及耳念珠菌引起院内感染暴发的案例[5,7- 8],故该病原获得了全球关注。
2 我国耳念珠菌的流行及耐药情况
现有的耳念珠菌病例报道及其流行病学监测数据显示,中国耳念珠菌在临床的发生发展情况与美国不同,但仍需重视以耳念珠菌为代表的临床真菌感染带来的医学挑战。
2.1 耳念珠菌感染在中国仍属个案
目前中国大陆共报道耳念珠菌感染18例,中国台湾地区仅有1例病例报道[9]。中国大陆的病例源自3篇研究性文章[10- 12],并无集中暴发的证据,同时在医疗机构环境中均未筛查到耳念珠菌[10- 11]。北京协和医院自2009年牵头我国首个多中心侵袭性真菌病流行病学与耐药性监测CHIF-NET项目,覆盖29个省级行政区的96家医院, 省级监测子网覆盖9个省133家机构;所有菌株均按规范收集至北京协和医院,使用分子测序或质谱方法进行准确鉴定[13]。在至今收集的逾2万例真菌样本中,仅在2016年发现1例耳念珠菌,发生率极低。
当然,目前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关注的院内真菌感染问题,的确需要引起临床重视。CHIF-NET 2009至2014年监测数据显示,作为非-白念珠菌代表的近平滑念珠菌(Candidaparapsilosis)在我国临床平均分离率约17%,发生率已排名第二(仅次于白念珠菌)[14],但部分医院该菌种的分离率(47.9%)显著高于平均水平[15]。通过菌株同源性研究,我们有证据怀疑,这种真菌可能已在医疗机构中传播[15]。通过制定管理政策,提高人员意识,医院感染控制部门、医务人员及检验科通力合作的综合措施,病原的院内传播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
2.2 中国大陆分离的耳念珠菌耐药情况并不严重
如上文所述,“超级病原”主要指对临床可选抗菌药物泛耐药或全耐药的病原微生物。此次耳念珠菌在美国受到重视,原因之一是美国分离的菌株体外药敏试验呈多重耐药,特别是对两性霉素B耐药[4],这在念珠菌中颇为罕见,可能影响临床的经验性治疗效果。
截至目前,我国的报道显示,全国首例耳念珠菌分离株对所有抗真菌药物敏感,包括4种唑类药物、3种棘白菌素类药物、两性霉素B和5-氟胞嘧啶[12]。另一篇研究报道的两例耳念珠菌仅对氟康唑耐药,对其他药物敏感[10]。第3篇研究中的15例耳念珠菌菌株同样仅对氟康唑耐药,未发现对包括两性霉素B在内的其他抗菌药物耐药[11]。因此,称中国的耳念珠菌为“超级病原”甚至“超级真菌”并不适宜。
需要警惕的是,高度泛耐药病原真菌在我国确实存在。2009年,日本报道全球第1例耳念珠菌感染病例时,即提出耳念珠菌与另外一种致病真菌——希木龙念珠菌(Candidahaemulonii)亲缘关系很近[3]。CHIF-NET 2009至2014年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共发现31例希木龙念珠菌,发生率约0.3%;其中65%的希木龙念珠菌对4种唑类药物全耐药,超过50%与25%的菌株分别对两性霉素B和5-氟胞嘧啶耐药[16],耐药性远超耳念珠菌。此外,我国一些常见真菌的耐药性趋势变化已非常严峻。例如热带念珠菌(Candidatropical)在全国监测中的分离率与近平滑念珠菌相近(17%),但目前该菌种对氟康唑的耐药率以及不同唑类药物的交叉耐药率已从2010年的6%剧增至超过21%,唑类不敏感率已超过40%[14],同时全国各地区耐药率均显著上升。
真菌感染的流行病学与耐药性分布存在国家与地域差异,必须持续加强我国监测网络建设,以便精准、有效地发现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2.3 耳念珠菌的致病性并无显著上升
“文章”中提到,“美国CDC已将耳念珠菌列入‘紧急威胁’名单。据其官网最新通报,全美感染病例已上升至587宗,近50%的感染者在90 d内身亡”。准确地说,美国CDC在该篇报道中所引用的原始文献[17]指出,在耳念珠菌引起的真菌血症中,30 d死亡率达39%(12/31),90 d死亡率达58%(18/31)。事实上,这一死亡率在真菌引起的侵袭性感染中并无异常,侵袭性真菌病死率高、预后差已是临床共识。2013年意大利发布的AURORA研究显示,ICU中发生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死亡率为40.2%(37/92),其中由热带念珠菌感染的死亡率甚至高达77.8%(7/9)[18]。欧洲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70例侵袭性感染/定植患者无一例因耳念珠菌感染死亡[8]。侵袭性真菌感染多发生在危重症及免疫功能缺陷患者,死亡并非单纯由于真菌感染导致,而是多因素的临床结局。截至目前,我国尚无耳念珠菌感染导致患者死亡的病例报道[11- 12]。
3 小结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我国耳念珠菌感染仍为临床偶发案例,且耐药性低,尚未发现异常致病性,因此无须受美国等主要流行地区影响而过度解读目前形势。当然,临床微生物实验室若怀疑检出耳念珠菌,应务必准确鉴定,并进行体外抗真菌药物敏感性检测。从国家健康发展战略层面看,应通过合理的顶层设计,持续推进病原真菌的流行病学与耐药性监测工作,加强临床真菌实验室能力建设,加大对国内真正面临的真菌感染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支持,以便提供数据支撑、提升技术储备、完善管理策略,从防、诊、治全方位应对真菌感染对患者乃至全社会带来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