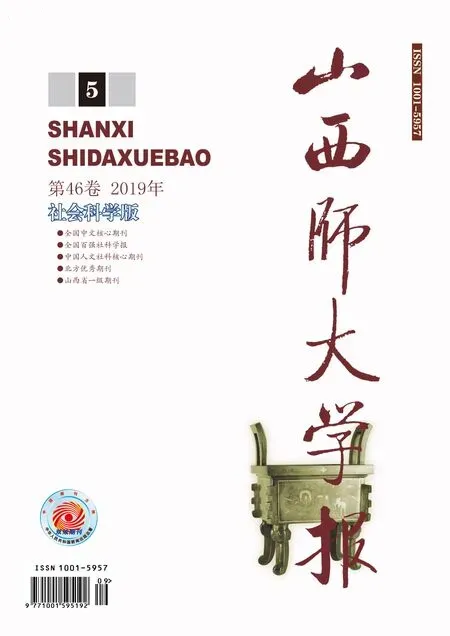早期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的政策取向与破解之道
秦金亮,陈 晨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杭州 311231)
我国自“单独二孩”“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新增人口并未达预期,彰显了新时代育龄家庭生育意愿选择的大逆转。是什么原因导致育龄夫妇“不敢生,不愿生”呢?除人口学家分析发现的儿童养育成本外,不少专家学者将原因指向我国尚未完善的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服务体系下,双职工家庭的工作与育儿矛盾所致的压力。有调查表明,我国上海99%的0—3岁幼儿依赖家庭照料,仅有0.2%的家庭有过送托的经历,而幼儿2岁时,有入托意愿的家庭达到四成。[1]同时,也有调查显示我国的幼儿入托率仅为4.1%。[2]社会力量申办儿童养育与照顾服务机构困难重重。[3]上述现状表明,我国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供给单一,社会化育儿成本高,专业水平低,家长信任度低,导致家庭育儿独脚跳,压力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幼有所育”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而如何做到“幼有所育”将是我国目前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解决我国“全面两孩”政策遇冷难题,要从完善我国的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敢生”“愿生”的儿童养育与照料生活服务支持入手。
家庭在儿童养育与照料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父母在儿童养育与照料过程中肩负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但是,自工业化革命以来,社会分工趋于专门化。儿童养育与照料也由家庭的全部责任过渡到家庭为主、社会与国家为辅的现状。也就是说,儿童养育与照顾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是指儿童养育与照顾由家庭逐步转移到专业机构或相关联的社会组织的过程。[4]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能够有效地提升儿童养育与照料的效率,提高儿童养育与照料质量,从而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不同服务需求。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是一种完善我国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体系的重要模式,这一改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许能够解决我国“全面两孩”政策的遇冷现状。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台湾地区同属儒家文化圈,教养理念和方式存在一定的相似,他们在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体系建立与完善过程中的社会化举措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因此,本文主要审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体系建立与完善过程中的供给服务社会化问题,探讨他们在这一进程中的举措,为我国的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社会化的过程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一、 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的社会背景
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主要由家庭承担。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国民经济收入不稳定、育儿经济压力大、“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转变、性别不平等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制度因素导致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不断下跌,并逐步进入少子化时代,少子化现象的日益突出,对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面对少子老龄化趋势,日本政府开始调整社会福利发展方针,朝着福利多元化目标重构国家福利,开始考虑让社会力量加入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的实施主体,推行以地方政府(都道府县)、地方公共团体、企业、民间团体等多元化供给的福利模式,以期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的供给日趋多元化,做到全社会共建支援儿童、支援育儿的社会环境,力图改变传统的只是由家庭和父母承担的育儿机制,从而构筑全社会共同援助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机制。[5][6]
同样,面对少子老龄化趋势,韩国政府开始转变人口政策,逐步改变儿童养育与照料的传统观念,增加儿童养育与照料的供给体,强调政府及社会力量在儿童养育与照料中的作用,进一步分担家庭育儿的压力,促进生育行为的产生。也就是说,逐步将家庭和父母在儿童养育与照料的首要地位分解出来,让国家和社会参与进来。例如,韩国政府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儿童养育与照料体系,并灵活调整儿童养育与照料形式与时间。此外,随着经济发展的停滞,生存压力与生育压力不断加大,台湾的少子化现象日趋严重。台湾当局为提升民众对生育的信心,从儿童养育与照料的法律法规、机构设置、经济补贴等方面不断完善儿童养育照料的服务体系。
二、 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的政策推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政府为缓解少子化状况,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育儿援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进程,完善了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体系,做到了“家庭育儿”到“社会育儿”的转化,构建儿童养育与照料的家庭—市场—国家—非盈利部门/社区的四边形模式。
(一)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的政策项目
1994年12月,日本政府(文部、厚生、劳动、建设省四部门协商)规划了未来10年的工作重心和重点对策,制定并出台了《关于今后支援育儿政策的基本方向》(简称《天使计划》)。《天使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为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确保《天使计划》的有效实施,日本政府还协商制定了《紧急保育对策五年计划》。1999年12月,日本政府出台《关于重点推进少子化对策具体实施计划》(也称为《新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是对《天使计划》的扩充与延续。2005年4月,日本政府开始实施新的少子化对策“支援儿童、支援育儿计划”,这是“根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重点措施的具体实施计划”,目标是全社会共建支援儿童、支援育儿的社会环境。要求根据前面两期“支援育儿的综合计划”的实施情况,以保育事业为中心有计划地开展工作。[7]2015年4月,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儿童及育儿援助新制度,就是根据2012年制定的《儿童及育儿援助法》等3个相关法律,推进幼儿期的教育和保育工作,扩充和提高地区育儿援助的“数量”和“质量”。[8]
韩国在1996年也开始转向新人口政策,强调生殖保健服务。2003年开始准备制定鼓励生育政策和项目,2006年开始实施第一次基本规划,项目为期5年,旨在培育有利于生育的环境,从而在低生育社会中获取经济增长的能量。此外,这一项目已进行3次,分别为第二次(2011—2015)基本计划和第三次(2016—2020)基本计划。每次基本计划中都强调政府及社会力量在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中的作用,从而很好地分担家庭育儿的压力,促进生育行为的产生。例如,第一次(2006—2010)基本规划中强调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责任,扩大多样性、高质量的育儿基础设施:(1)扩大公共和工厂托儿设施:扩大公共育儿设施,建立和支持一体化托儿设施,扩大工厂育儿设施;(2)改善私人育儿机构服务质量:支持私人育儿设施改进服务,实施育儿设施评价证书,延长育儿服务;(3)扩大育儿主体,赋予满足多种需求:增加全天制托儿所数量,支持兼职育儿机构,成立并支持托儿机构,为了母婴健康成立专业机构,为新生儿成立系统健康管理机构,提供可靠的分娩和育儿信息及咨询服务。[9]
(二)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的法令保障
1997年,日本政府大幅度修改《儿童福利法》,并强调儿童的养育与照料不仅是家庭的责任,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也应负有关责任,为应对少子化现况进行福利制度改革。[10]1997年修订的《儿童福利法》中有三点改革内容:第一,基于“使用者本位”的基本观点,从以往由行政处置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方式转变为通过建立服务供给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契约提供方式。第二,以区域为中心进行综合性支持,实施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第三,在服务供给上引入多元民间力量,扩大供给量,提高服务质量。日本社会福利基础改革促进了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进程。1998年,《儿童福利法》修正案正式实施,课后照料服务以“课后儿童健全育成事业”的名称法制化,自此获得了法律保障,确立了作为社会福利事业的地位。2008年,日本政府再次修订《儿童福利法》,首次对育儿支援事业进行了法律定位,实现了“保育妈妈”制度的法制化。[11]为今后进一步推进社会育儿支援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2003年,日本国会决议通过《少子化社会基本法》,该项法律指出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企事业单位有义务协助实施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要减轻儿童养育与照料的不安和负担,创建对儿童养育与照料实行支援的社区。[12]同年,日本国会决议通过《支援培育下一代对策推进法》,该法律中明确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企事业单位、国民在儿童养育和照料中的责任,进一步分化了家庭在儿童养育与照料过程中的作用,促进了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进程。[13]
韩国在2005 年制定《关于低出生率、老龄化问题的社会基本法》,强调政府与社会力量在儿童养育与照料中的作用,进一步从法律的角度去分化家庭在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中的压力,以及增加政府、社会等的作用与力量。例如,该法律提出要给予有新生儿的家庭适当的经济补贴,对多子女家庭实行减税政策,减免日托和学前教育的费用等。此外,台湾地区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法律保障。例如,台湾地区颁布《幼儿养育及照料法》,强调儿童养育与照料的内容、形式等,以及政府与社会的职责。强调儿童养育与照料供给体的多元化,从而保障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的高质量供给。同时,台湾地区对多子女家庭实行生育补贴,鼓励儿童养育与照料从家庭内部转移到家庭外部。
(三)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的政策组合
为应对少子化现况,日本的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进程日益加速。2003年,日本政府出台的《地方自治法部分修正案》中指出各自治体开始在公共设施的管理运营上导入制定管理者制度。根据类型的不同,日本政府购买的制度构建进行了分化和细化。[14]在社区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方面,以社区儿童设施为中心提供儿童服务,实施“指定管理者制度”推行政府购买,构建NPO(no-profit organization)、社区团体、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服务的供给体系。同时,日本颁布《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平成十年法律7号),设立NPO法人认证制度,税务减免等方式,为市民互助组织作为独立法人活动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15]此外,日本还成立儿童养育协会,负责企事业主导型的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的相关事宜。[16]
1994年,韩国政府成立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为新人口政策和实施指明方向。同时,2003年,韩国政府成立老龄化和未来社会发展委员会,准确制定鼓励生育和项目,应对未来老龄化社会。这一委员会在2006年升级为总统老龄化社会与人口政策委员会。台湾在制度结构方面也有一定的举措。日本政府不仅从儿童养育与照料的项目、法律法规、制度结构等方面为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进程保驾护航,还从育儿观念、财政投入等方面推波助澜。2010年,日本发布“孩子·育儿理想”倡导日本社会“家庭育儿”向“社会育儿”的转变,以期构筑全社会共同支援育儿的机制。[17]2012年6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以提高消费税税率为主的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相关法案,主要内容是提高消费税税率,消费税收入全部用于支付养老金、医疗费、儿童养育与照料支援等社会保障费用,其中5%用于充实儿童及育儿经费,并将儿童及育儿追加为社会保障对象。
三、 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的政策实施
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方式是家庭养育与照料者在家庭内进行的无偿劳动转变为家庭外人员提供的社会劳动等养育与照料场所上的转变(简称场所变换方式);另一种方式为通过提供现金支付、带薪休假等措施来肯定家庭养育与照料者的无偿劳动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简称替代价值方式)。[18]而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的评价标准则主要包括是否形成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的供给系统、是否形成多元化的儿童养育与照料供给主体、家庭外公共资源是否成为家庭儿童养育与照料的后盾等。[19]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的进程中,主要采取以下举措:
(一)场所变换方式的举措
日本政府通过场所变换的方式促进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采取的举措主要包括由国家、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或企事业单位独立或混合提供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的儿童养育中心或儿童照料机构等。例如,社区育儿支援中心主要是促进社区共同支援儿童养育与照料。儿童咨询所为儿童养育与照料过程出现的问题或困难进行咨询和指导。幼儿园和保育所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提供养育与照料服务,同时保育所还能够根据不同需求,灵活调整保育时间。除了对婴幼儿的养育与照料支援外,日本政府在儿童课后照料服务方面,也都有一系列的服务标准与准则,全方位促进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在场所变换上的社会化。在实施场所变换方式举措中,日本政府相关部门制定了相关服务的标准、服务内容、服务时间、从业人员资质、国家经济补贴等一系列保障场所变化举措实施的法律法规。
同样,韩国在“场所变换方式”上也有所举措。例如,在第一次(2006—2010)基本计划中,韩国政府强调扩大多样性、高质量的育儿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扩大公共和工厂托儿设施,建立和支持一体化托儿设施,扩大工厂育儿设施。同时,改善私人育儿机构服务质量,支持私人育儿设施改进服务、实施育儿设施评价证书、延长育儿服务。此外,为满足多种需求,增加全天制托儿所数量、支持兼职育儿机构、成立并支持托儿机构等。第二次(2011—2015)基本计划也强调要扩大儿童养育基础设施的支持,推介公共和私立育儿中心、延长育儿机构的开放时间、建立保姆市场、建立课后照料机制等举措。[8]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韩国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体系,并有效地促进了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进程。
(二)替代价值方式的举措
首先是经济上的补贴。日本在儿童养育与照料过程中给予一定的育儿补贴、医疗保险,并随时间的推移扩大育儿补贴的范围、提高育儿补贴额度,且不断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法律制度上保障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过程中的经济补贴作用。育儿家庭还可享受国家的减税、幼稚园入学奖励、地方政府减免保育费用、生产费用补助、企业的家庭补贴等。韩国通过对多子女家庭实行减税、降低多子女家庭参加医疗保险费用以及减免试管婴儿费用等举措对育儿家庭进行经济上的补贴。台湾则通过 “托育费用补助”,根据收入不同发放不同级别的托育费用。
其次是儿童养育与照料的时间保证举措。日本通过制定与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调整产假与育儿假,确保家庭内部儿童养育与照料劳动社会价值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支援儿童养育与照料,从而将儿童养育与照料压力从家庭内部逐渐转移出来,构建全社会的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机制。同样,韩国则推行育儿假,并且允许在育儿期间缩短工作时长。台湾则实施“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制度,办理育婴留职停薪者,即可享有申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的权益。
四、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体系,推动了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进程,相对缓解了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养育与照料难题。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的经验对我国构建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体系的启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更新理念,遵循养育与照料私人与公共的双重属性,通过政策建立合理分担机制。我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养育与照料儿童是家庭内部的事务。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儿童不再仅仅属于家庭,也属于国家和社会,国家与社会应在儿童的养育与照料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我国构建完善的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体系,要做到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就要转变观念,更新在儿童养育与照料方面的理念。我国的福利体系正在由“补缺型”到“普适性”的过渡,但在这一过渡过程中,我们要将福利多元主义的思想渗透其中,不断扩充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的供给主体,构建多元化的供给网络,从而提升服务的效率,提高服务的质量,并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
在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进程中,经济补贴或形式变换的经济支持是相对重要的一环。我国的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进程中也可通过免租金、免水电、减免税收等多形式对新生儿或多子女家庭进行经济上的支持。同时,也可通过政府购买专业人员服务,分担运营成本,免费提供专业人员培训等形式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进程中来,灵活多样地提供儿童养育与照料的家庭外部服务。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尊重区域及社会发展水平,形成家庭与社会的双轮驱动。完善的法律是一切行为举措的坚强基石。在构建我国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体系的过程中,首先要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从源头上保障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的运行与管理。在促进我国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的过程中,要从法律法规上明确多方面参与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保障地方分权,进而细化服务类型,促进各参与主体的参与最大化,做到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同时,要从法律方面去规定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过程中的财政投入,从经济上保障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体系的构建。此外,法律还应保障儿童养育与照料服务的细化,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我国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社会化进程需要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可以根据儿童年龄与养育难度和负担的配比,政府与社会、家庭分步分担;同时,根据育儿难度,增加形式灵活的育儿假期。例如,儿童在0—3岁期间鼓励居家照料。一线城市加强托育社区服务在专业机构与家庭间建立临时托管中心;欠发达地区、连片贫困地区支持母亲家庭养育,发放养育补贴,增加育儿假期。儿童在4—6岁期间鼓励家庭与外部机构(幼儿园)共同照料,家庭为主,外部机构为辅,拆分育儿责任,减小育儿的家庭压力。儿童在7—12岁期间鼓励家庭与外部机构(学校)共同承担养育,做到家庭与学校的双轮驱动。
第三,加强前瞻性研究,超前专业人才培养,形成立体化养育与照料社会服务体系。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不仅要有完美的法律法规,也需要有更加专业、科学的儿童养育与照料的理念与方式。我国要构建0—3岁、4—6岁和7—12岁儿童养育与照料的不同梯队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从年龄发展特点出发,用更专业的理念与方式去完善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服务体系。然而,0—3岁服务体系的建立是儿童养育与照料社会化进程的重要一环。服务于0—3岁儿童群体的专业化人才培养也是重中之重。0—3岁是人生最开始的三年,良好的养育与照料方式对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已覆盖4—6岁、7—12岁育儿人才,但0—3岁的育儿人才培养模式仍需进一步探讨。我们必须将0—3岁作为一个独立的时间节点去培养专业的人才。例如,对于服务于0—3岁群体的专业人才,可以从母婴健康指导、母婴交流互动指导、婴儿游戏、育儿与照料指导、母婴营养指导等多方面入手,努力培养一支专业化的队伍,给予家长更多科学的育儿指导,缓解育儿焦虑。
——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