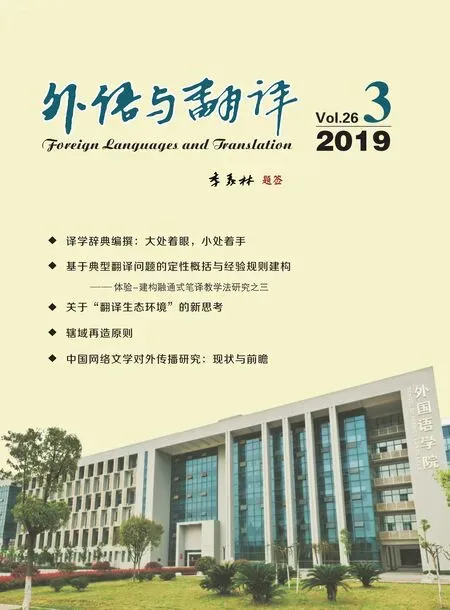关于“翻译生态环境”的新思考
蒋骁华 澳门理工学院
【提 要】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1869年提出生态学概念,认为它是研究动物与植物之间、动植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门学科。在人文学科中“生态”是一个隐喻,表示一种“美好的、健康的、和谐的”理想状态。在“生态翻译学”中,“生态”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也是一个隐喻,也是“美好的、健康的、和谐的”意思。因此,“翻译生态环境”是指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等所处的理想环境。本文从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出发,进一步探讨了“翻译生态环境”的性质、特点和内涵,并从生态伦理的角度讨论了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位置。
1. 胡庚申关于“翻译生态环境”的主要观点
“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胡庚申在多篇论文和专著中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了论述。按时间顺序,胡的主要观点如下:
1)“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Hu 2003:288)。
2)“翻译生态环境”构成的要素包含了原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胡庚申2004:40-41)。
3)由于生物体(动物和植物)都要适应自然生态环境,要接受“自然选择”;而译者和译品也都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也都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因此,就这一点来看,两者的确有相通的和类似的情形。这也表明,运用适用于生物界的法则来解释包括翻译行为在内的人类行为是可行的(胡庚申 2004:70)。
4)“翻译生态环境”,即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由于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要件很多(如原语文本、交际意图、译语文化等),每个要件本身又有不同维度和程度(如语言“维”的不同层面、文化“维”的不同系统等)的问题,因此,如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同样要由译者来判断和选择(胡庚申2004:105-106)。
5)由于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而包括社会、文化、诸“者”等在内的翻译生态环境又是在不断地、动态地变化之中,为了适应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在归化和异化、或者在直译和意译之间作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也就很自然了(胡庚申2004:125)。
6)“翻译生态环境”,是指由所涉文本、文化语境与“翻译群落”,以及由精神和物质所构成集合体(Hu 2006;胡庚申 2008)。
7)由于生态翻译学的早期研究将翻译描述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即译者的适应与译者的选择,因此,这里的“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即“翻译群落”)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这里的“世界”、“整体”、“集合”就是翻译的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有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之分;翻译生态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又包括精神环境等。可以这么说,对于翻译而言,译者以外的一切都可以看作是翻译的生态环境;同时,每个译者又都是他人翻译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胡庚申 2013:89-90)。
2.“生态”表示一种“健康、和谐、美好”的状态
从以上可以看出,胡庚申对“翻译生态环境”的论述在不断深入。2004年之前主要强调“翻译生态环境”的物质因素;2006年到2008年既强调“翻译生态环境”的物质因素,也强调其精神因素;2010年以来,在前些年探讨的基础上,探索更加深入:“翻译生态环境”分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翻译生态环境,而且相互依存,等等。胡庚申对“翻译生态环境”的论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进展。与此紧密相关,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位置也随之有所变化:从“译者中心”到最近的“译者责任”(胡庚申2014)。
生态翻译学近些年发展迅速,除了胡庚申及其团队的积极探索有力地推动了它的发展(见胡庚申 2013;胡庚申 2014;《中国翻译》2019年第4期“生态翻译学专栏”,等),Michael Cronin 的近著Eco-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Ecology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Cronin 2017)不仅充实了“生态翻译”的内涵,也拓展了“生态翻译”的研究范围。该书探讨了“一系列的问题:从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到动物交流(animal communication),再到全球单一文化(global monocluture)”等(Cronin 2017:i)。鉴于生态翻译学的新发展,本文不揣简陋,在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基础上,试从“生态”在人文学科中的基本涵义出发,对“翻译生态环境”做进一步的探讨。
“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家”(house)或“我们的环境”。简单的说,生态就是一定范围内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平衡关系。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69年提出“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认为它是研究动物与植物之间、动植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一门学科。近些年来,“生态”一词被运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在人文学科中,“生态”是“和谐、平衡、美好”的意思;“生态”强调“和谐性、整体性、全面性”。简言之,“生态”表示一种“健康的、和谐的、美好的”理想状态。近年来中国出现了“生态城市”、“生态乡村”、“生态食品”、“生态旅游”、“生态公园”等提法;也出现了“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文化学”、“生态翻译学”等新兴人文学科。总之,在人文学科中,“生态”基本上是一个隐喻,取其“健康的、和谐的、美好的”喻意。以此类推,“翻译生态环境”是指译者、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所处的“健康、和谐、美好”的环境。在这个理想环境中,译者与跟翻译相关的各种因素和谐相处。跟翻译相关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有:政治因素(如意识形态、权力干预等)、文化因素(如译文所处的文化环境、译者的诗学观等)和经济因素(如译文所处的市场、译者的经济状况,译者的赞助人等)。简单地说,“和谐的、健康的、美好的”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是构成“翻译生态环境”的关键。
3.“翻译环境”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区别
如果一个环境的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等不是“和谐的、健康的、美好的”,那么,这个环境可以是“翻译环境”,但不是“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环境的要求很低,只要翻译能进行,翻译环境就真实存在。试以季羡林翻译《罗摩衍那》的环境为例。季羡林说:
“我当时(文革中——笔者注)的任务是看门,当门房。我哪里敢公然把原书拿到我的门房里去呢?我当时还是“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我头上还戴着“帽子”——也不知是些什么“帽子”,反正沉甸甸的,我能感觉得到。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想出来了一个“妥善”的办法。《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我坚持要把它译成诗,不是古体诗,但也不完全是白话诗。我一向认为诗必须有韵,我也要押韵。但也不是旧韵,而是今天口语的韵。归纳起来,我的译诗可以称之为“押韵的顺口溜。”就是“顺口溜”吧,有时候想找一个恰当的韵脚,也是不容易的。我于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楼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中,把散文改成诗,改成押韵而每句字数基本相同的诗。我往往把散文译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闲坐无事,就拿了出来,推敲,琢磨。我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我在干什么。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了。偶一抬头向门外张望一眼,门两旁的海棠花正在怒放,其他的花也在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大好春光”(季羡林1998:199-120)。
季羡林翻译《罗摩衍那》时的政治因素、文化因素非常不“和谐、健康、美好”,甚至有点恶劣,但翻译环境(季羡林自己创造的小环境)依然存在1。
朱生豪在译完《暴风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又陆续译完了《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等九部喜剧。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朱生豪逃出寓所,随身只带有牛津版莎氏全集和部分译稿。世界书局被占为军营,朱生豪已交付的全部译稿被焚。8月26日他从上海避难至嘉兴,后辗转至新滕、新市等地避难,稍得安宁,即补译失稿。1938年夏,他又重返在上海租界中恢复开业的世界书局工作。1939年冬,朱生豪应邀成为中美日报社编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冲入报社,朱生豪虽混在排字工人中逃得一命,但全部译稿再遭厄运,多年心血又不幸毁于一旦。1942年6月至年底朱生豪又将译稿丢失的莎氏喜剧全部补译完毕。1943年1月,朱生豪回嘉兴定居。这段时间里,他仅借助两本词典完成了莎士比亚的几部重要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等的翻译工作。接着,他又译出莎氏悲剧、杂剧,以及英国史剧4 部,连同喜剧在内,共3l 部。1944年初朱生豪带病译出《约翰王》《理查二世》等4 部莎士比亚历史剧,4月完成《译者自序》的写作并编写《莎翁年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朱生豪一直忍受着病痛,在译出《亨利五世》第一,二幕后被确诊为肺结核。此时,他不得不放下已经开始译写的《亨利五世》译稿。1944年12月初朱生豪的病情日益严重,12月26日,一代翻译大师撒手人寰,年仅32 岁(贺爱军 2008:18)。
这是一个较特殊的例子。译者身处战争时期。战争与自然灾害一样,属于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战争可以扭曲翻译环境中的所有因素,包括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而且,译者还长期身患重病。在这种双重恶劣的状态下,朱生豪的翻译环境依然存在。
可以从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等是否有利于翻译来区分“翻译环境”和“翻译生态环境”,但很难制定客观或统一的标准来区分它们,因为二者之间是一个连续体,中间没有截然的界限;而且,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即“翻译生态环境”中的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如果不断恶化,“翻译生态环境”就会变成“翻译环境”。反过来,如果“翻译环境”中的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等不断改善,那么,“翻译环境”就会逐渐变成“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有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之分”(胡庚申2013:90)。以此类推,翻译环境也有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之分。就“翻译环境”而言,一般有三种状态:1)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都不好;2)大环境不好,但中环境、小环境还好;3)大环境、中环境都不好,而小环境还好。就“翻译生态环境”而言,一般只有一种状态: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都是“和谐的、健康的、美好的”,即“生态的”。
经济因素经常受到政治因素或(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我们以中国的翻译环境为例:美国著名文化学者Ruth Benedict 1946年出版的名著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在中国大陆最早的中译本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菊花与刀》(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1987)。这个译本比较准确,读起来流畅、自然,首印2 万多册,此后该社再没有重印,销量大致如此。与此形成对比,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的《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1990),读起来比孙志民等的译文明显生涩2,而且错译也相对较多。然而,因为有了“商务印书馆”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些“品牌”文化因素的介入,销路非常好。译者在“增订版前言”中说:“《菊与刀》中译本 1991年(应为“1990年”。笔者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至今已重印14 次,印数超过10 万册”(本尼迪克特2012:1)。同样是翻译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孙志民等人所处的,算是翻译环境,而吕万和等人所处的,可以算是翻译生态环境。自2012年9月日本非法“购买”钓鱼岛并引发中日关系骤然紧张以来,《菊与刀》各种译本的销量狂增。据笔者统计,到2013年7月底,至少有32 个《菊与刀》的不同译本在这段时间出版发行。这一空前销量的背后主要是国际政治的影响。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环境中政治因素对经济因素的影响。
笔者以外国的翻译环境为例:在欧美国家,20世纪20、30、40年代出版的女性主义经典文本在20 世纪70、80年代大量重印并热销,因为当时出现了非常有利于女性主义的文化氛围3(André Lefevere 1992:1-2)。有时候,其它因素会对经济因素产生一些特殊的影响,如著名翻译家萧萧(原名伊藤克,1915年出生于东京)在1949年前出于自己的精神需要和奉献社会的愿望,“一直无偿进行中国革命小说的翻译工作(中译日)”(吴丹2014)。后来,萧萧一般只进行有偿翻译(同上)。
4. 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位置
胡庚申(2004:11-12;83-100;174-175;2013:18)在早期认为,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处于“中心地位”。2011年有人明确提出不同看法(见《上海翻译》2011年第3 期》)。胡庚申在 2012年重庆“第三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主题发言,谈及此事此文,并说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论述。这些论述后来发表在《中国翻译》上,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胡庚申2014)。胡庚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思考和探索。笔者认为,无论“译者中心”还是“译者责任”都是有一定的道理(详见下文)。但既然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而且还言之凿凿,那么,我们不妨参与进来,对此问题作一点尝试性的新探索,企盼方家指教。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一般而言,这主要是看基于怎样的生态伦理观来思考这个问题。在不同的生态伦理中,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位置是不同的。下面笔者按西方不同生态伦理出现的时间顺序一一讨论:
1)西方18 世纪生态伦理之一:“帝国”传统或“帝国”论(empire tradition)。“帝国”论的生态伦理观是:希望通过理性的实践和健康的劳动建立人对自然的统治。其核心观点是自然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人服务的,人类有权力享受自然中的一切东西。其代表人物是瑞典学者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代表作是《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帝国”论的生态伦理观与中国的“人定胜天”生态伦理观有些相似,即强调人是自然的中心或主宰。中国“人定胜天”的思想早在《荀子》中就有基本雏形(秦榆2006:第二章),“人定胜天”的思想在毛泽东时代被广泛宣传,可谓深入人心。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汉语成语词典对“人定胜天”的解释基本是“人的智慧和力量可以战胜自然。人定:人谋,指人的主观努力”,如李一华等编的中型《汉语成语词典》对“人定胜天”的解释就是如此。“人定胜天”的最早出处笔者没有查到,但查到了以下参考资料:“兵强胜人,人强胜天”(《逸周书·卷三·文传》);“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史记·吴子胥传》);“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宋朝刘过《龙洲集·襄央歌》);“却又犯着恶相的,却因心地端正,肯积阴功,反祸为福。此是人定胜天,非相法之不灵也”(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九》);“彼虽不来,宁禁我不往,登门就之,或人定胜天不可知?”(蒲松龄《聊斋志异·萧七》);“小生每念物极必反,人定胜天,怯大敌者非丈夫,造时势者为俊杰,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梁启超《新罗马》)。这些资料显示“人定胜天”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不管如何解释,环境中人的因素被特别强调,这一点是相通的。以此生态伦理为基础来思考“翻译生态环境”,笔者认为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处于“主导”或“中心地位”;与其“中心地位”相连,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负有责任。因此,胡庚申的“译者中心”和“译者责任”的论断是站得住脚的。
2)西方18 世纪生态伦理之二:阿卡狄亚式的生态伦理 (the Arcadian eco-ethics,or arcadianism)。阿卡狄亚式的生态伦理强调人和自然环境中诸因素的和谐、平等、一致。其代表人物是Gilbert White(1720-1793),他的代表作是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rne。阿卡狄亚式的生态伦理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4生态伦理比较接近;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的生态伦理也比较接近,即都强调人与自然环境诸因素的和谐、一致。但二者也有所不同,在老子的“人→地→天→道→自然5”的生态伦理中,自然高于一切,人与自然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成为自然的主导。以此生态伦理为基础,译者只是翻译生态环境诸因素中的一个普通因素,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不会处于“主导”或“中心地位”,也不用承担“译者责任”。
3)西方19 世纪生态伦理:超验主义生态伦理(transcendentalist eco-ethics)。超验主义(或超越论)兴起于19 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后发展为美国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代表人物是R. W. Emerson (1803-1882) 和 H. D. Thoreau(1817-1862);代表作有 Emerson 的The Method of Nature、Spiritual Laws和 H. D. Thoreau 的Walden,or Life in the Woods。超验主义可视为神秘主义的一个分支,但与传统的神秘主义有所不同,不需要依赖神职人员或法器,普通人依赖自己的直接经验和主观能动性可直接从“超灵”(上帝)那里获得启示,也可以与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建立精神联系。它强调人与“超灵”(上帝)的直接沟通和人性中的神性。超验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简单地说,就是人高于自然,上帝高于人。在天地之间,人联通上下。超验主义的生态伦理观里既有“天人合一”的元素(事实上,超验主义者,如Thoreau 等,明确表示他们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中获得了灵感),又有浪漫主义的元素(即将自然视为有灵性的朋友),还有一些神秘主义的元素。超验主义生态伦理观强调“自然→人→上帝”三者既灵性相通又上下有序。超验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虽然认为人的灵性高于自然,但人必须谦虚而老实地向自然学习,从自然中体悟规律和法则。人虽灵性通“天”,但其律法、文字、乃至生活模式等都是对自然的笨拙模仿。人类不可猖狂,在人的意志之上存在着统领万事万物的更高法则6。在自然环境中,人既是高贵者,也必须是谦卑者。以此生态伦理观为参照,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没有“主导”或“中心地位”,但应该有协调翻译生态环境诸因素并与之和谐相处的“责任”。
4)西方20 世纪生态伦理:大地伦理(earth ethics)。大地伦理的首创者是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其代表作是《沙郡年记》(Sand Country Almanac)。大地伦理强调:(1)大地上的山川河流、虫鱼鸟兽和花草树木是一个有机体,人是这个有机体的一个普通组成部分;(2)生态整体主义方法论,即人类不应该只根据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进行活动,而应该将那些在大地社会中没有商业价值的各种因素视为大地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善加保护;(3)人类有道德义务和责任保护大地生态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见利奥波德2014)。以此生态伦理观为参照,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不处于“中心地位”,但处于“主导”地位,并负有不可推卸的协调翻译生态环境诸因素并与之和谐相处的“责任”。
5)西方21 世纪生态伦理: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是Philosophy Gone Wild(《哲学走向荒原》)。Holmes Rolston 继承了Aldo Leopold 的大地伦理思想,把它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Rolston 被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因环境伦理是从大地伦理发展而来,故二者有诸多类似,但环境伦理更强调:(1)生态整体主义,即人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构成一个有机整体;(2)尊重自然。Rolston 强调,在绝对的意义上遵循自然;在人为的意义上遵循自然;在相对的意义上遵循自然;在自动平衡的意义上遵循自然;在道德效仿的意义上遵循自然;在价值论的意义上遵循自然;在接受自然指导的意义上遵循自然(见罗尔斯顿2000)。以此生态伦理观为参照,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不处于“中心地位”,但处于“主导”地位,并在道德、伦理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协调翻译生态环境诸因素并与之和谐相处的“责任”。
5. 结语
“生态”在人文学科中的基本涵义是“健康的、和谐的、美好的”。本文根据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从“生态”的基本涵义出发,探讨并区分了“翻译环境”和“翻译生态环境”,这一探讨和区分的意义在于:(1)可以更清晰地诠释“翻译生态环境”的内涵;(2)有助于引发我们从人文“生态”角度进一步思考“翻译生态环境”,乃至生态翻译学。另外,本文根据不同生态伦理的内涵,探讨了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不同位置和作用。这有利于加深我们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内涵和“生态翻译伦理”的认识。当然,以上探讨还非常粗浅。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尚待方家指教。
注释:
1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从1958年开始,许渊冲陆续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法文。然而费力不讨好,译文没出版,过了几年,在文革中,红卫兵说他的翻译篡改了毛泽东思想。结果,笔杆犯“错”,屁股受过,被抽了一百鞭子,很长时间连落座都不能,但他仍坚持不懈(张经浩、陈可培 2005:196)。
2例如,通过对比《菊与刀》的第一段译文,我们就能看到吕万和等的译文与孙志民等的译文的区别:
原文:The Japanese were the most alien enemy the United States had ever fought in an all-out struggle. In no other war with a major foe had it been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such exceedingly different habits of acting and thinking. Like Czarist Russia before us in 1905, we were fighting a nation fully armed and trained which did not belong to the Western cultural tradition. Conventions of war which Western nations had come to accept as facts of human nature obviously did not exist for the Japanese. It made the war in the Pacific more than a series of landing on island beaches, more than an unsurpassed problem of logistics. It made it a major problem in the nature of the enemy. We had to understand their behaviour in order to cope with it(Benedict, 2005:1).
译文1: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主要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正如前此1905年的沙俄一样,我们作战的对手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而又充分武装和经过训练的民族。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则显然不存在。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是一系列岛屿登陆作战和困难卓绝的后勤工作问题,从而使了解“敌人的性格”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为了与之对抗,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熊达云、王智新 1990:1)。
译文2:日本人是美国曾竭尽全力与之战斗过的最异特的外敌。我们在其他任何一次与强敌的战争中都未曾需要顾及如此截然不同的行动与思想习性。同在我们之前的沙俄于1905年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与之作战的是一个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民族,他们不属于西方文化的传统。已被西方人视作人类自然习性的那些战争规范对日本人来说显然是不存在的。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面临的不仅仅是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的滩头登陆战,也不仅仅是棘手的后勤供应问题。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了解敌人的习性。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行为举止,以便同他们打交道(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1987:1)。
对比粗体部分,我们很容易发现:(1)吕译“正如前此1905年的沙俄一样”没有孙译“同在我们之前的沙俄于1905年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么准确、清晰。(2)吕译“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是一系列岛屿登陆作战和困难卓绝的后勤工作问题,从而使了解‘敌人的性格’成为一个主要问题。为了与之对抗,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存在至少两个问题:一是“不仅是……从而”句式不通,二是将in order to cope with it 译为“为了与之对抗”,是错译。因为此书的Foreword 中说得很清楚,应美国政府之邀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给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战后重建”提供帮助(Benedict 2005:x),因此,了解日本人不是为了“对抗”,而是为了日后“打交道”。孙志民等的译文是正确的。
3Similarly, many “foreign”feminist classic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twenties, thirties, and forties of our century have been republished in the late seventies and eighties.The actual content of the novels was, presumably, no less feminist then than it is now, since we are dealing with exactly the same texts. The reason why the republished feminist classics are not forgotten all over again lies not in the intrinsic value of the texts themselves, or even the (possible) lack of thereof, but in the fact that they are now being publish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n impressive array of feminist criticism, which advertises, incorporates, and supports them(André Lefevere, 1992: 1-2).
4“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命题之一。不同的学者对“天人合一”有不同的理解和阐述。季羡林的解释是: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天人合一”,或称“天人合德”、“天人相应”,儒、道、释三家均有阐述。其基本思想是:人类的生理、伦理、政治等社会现象是自然的直接反映。它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汉朝董仲舒引申为天人感应之说,程朱理学引申为天理之说。中医《黄帝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黄帝内经》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谓“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
5有学者认为,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的“自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此”。“道法自然”就是道以自然而然为法则。“法自然”就是顺其自然(陈其荣2004:36)。即使按此理解,老子此言与本节论及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并不矛盾。
6R. W. Emerson 在其 Self-reliance, Spiritual Laws, The Method of Nature, The Poet, The Over-soul 等名篇中既阐述了人类灵性的高贵,也反复强调人类必须向自然学习。如,Emerson 在 The Method of Nature 中说:In the absence of man, we turn to nature, which stands next. In the divine order, intellect is primary; nature, secondary; it is the memory of the mind. That which once existed in intellect as pure law, has now taken body as Nature. It existed already in the mind in solution; now, it has been precipitated, and the bright sediment is the world. We can never be quite strangers or inferiors in nature. It is flesh of our flesh, and bone of our bone. But we no longer hold it by the hand; we have lost our miraculous power; our arm is no more as strong as the frost; nor our will equivalent to gravity and the elective attractions. Yet we can use nature as a convenient standard, and the meter of our rise and fall.It has this advantage as a witness, it cannot be debauched.When man curses, nature still testifies to truth and love.We may, therefore, safely study the mind in nature, because we cannot steadily gaze on it in mind; as we explore the face of the sun in a pool, when our eyes cannot brook his direct splendours(Emerson 1841)。这里明确告诉我们:人高于自然;人与自然是天然的朋友。Emerson 在Spiritual Laws中说:If we look wider, things are all alike; laws,and letters, and creeds, and modes of living, seem a travesty of truth. … Let us draw a lesson from nature, which always works by short ways. … A little consideration of what takes place around us every day would show us, that a higher law than that of our will regulates events(Emerson 1841)。这里明确告诉我们:有更高的法则在人的意志之上,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人必须谦卑地向自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