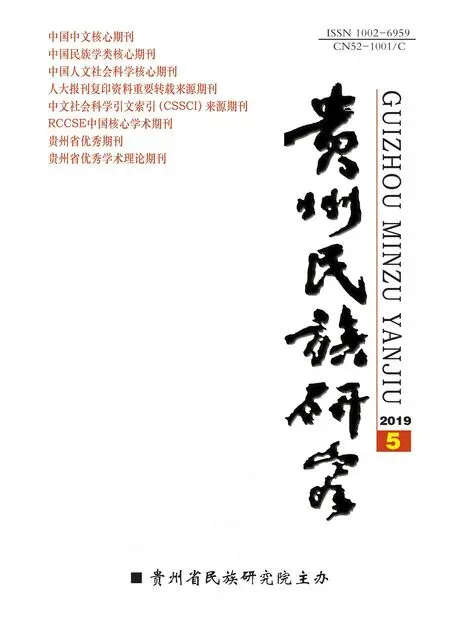民族语言教育权的提出与保护
李德嘉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2)
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协同发展的统一国家,古代的王朝往往通过“书同文”的文化政策语言文字的通行,进而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近代以来,伴随民族国家概念的兴起,“中华民族”逐渐成为我国各民族的共识,在“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之下,近代学人提出了边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的平衡问题,进而指出必须在推行“国语”的同时,保留边疆固有民族语言文字的特色和习惯,使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行语言“互相沟通、互相光辉”[1]。新中国成立以来,保护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已经成为政策制定的基本共识。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原则,提倡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语言,是我国长期关于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基本认识。“中华民族”本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产物,“多元一体”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民族发展特点所作的总结,也基本反映了中国民族语言传承发展的基本趋势。“多元一体”也基本反映了中国民族语言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即中华民族的语言谱系是由中国各民族语言长期交流,共同发展所形成的,在坚持规范使用国家通行语言的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保护发展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语言政策[2]。
然而,在现代化过程中,世界各国出现了弱势语言在不同程度上的退化和濒危现象,在此基础上,各国都提出了相应的语言保护政策。有学者指出,语言保护必须处理好民族语言与通行语言、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等关系[3]。在依法治国的宏观战略下,以法律手段尊重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权利成为语言保护的重中之重。我国《宪法》第四条规定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发展和使用自由和风俗习惯自由,是语言权利的宪法规范基础。语言的学习和教育,尤其是在民族自治地区推行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教育是民族语言文字保护的重要基础,因此,保护民族语言文字受教育的权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所提出的民族语言教育权是指民族自治地区公民所享有的接受民族语言教育机会的权利,属于民族语言文字权的派生性权利。民族语言教育权的提出,不仅具有法律和政策依据,而且具有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意义。本文旨在通过提出民族语言教育权的概念,突出民族语文教育权利的重要价值,并尝试探讨民族语言教育权的基本内容和规范原则。
一、提出民族语言教育权的必要性
一般而言,民族语言文字权利属于人权范畴,是族群或个人选择一种或多种语言作为私人或公共领域交流工具的权利,这项权利不因语言使用范围的广狭、族群人数的多寡而有所区别[4]。一般认为,语言权利的权能可以概括为:学习权、使用权、传播权和接受权。语言权利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语言群体,如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有使用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其具体落实的权利主体往往体现为诉讼关系中的个人[5]。而就某一民族的语言文字权利而言,其主体则往往是某一语言群体。语言权利其实不限于少数民族,多数语言群体和少数语言群体均享有语言权利,但多数语言因为语言使用群体广泛,存在使用习惯上的强大优势,需要提出保护的往往是少数语言群体的语言权利,多数表现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语言文字权。一般而言,民族语言文字权的义务主体往往是国家、政府机关或社会团体。也就是说,民族语言文字权的实现往往需要国家或政府机关从政策层面予以支持,并以国家的力量予以保障。换言之,民族语言文字权利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国家通过政府教育部门和公共教育组织积极履行组织民族语言文字教育、传播的义务,除国家的积极义务之外,社会、组织和个人也负有尊重民族语言权利的义务。
民族语言文字权利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面向。第一重面向是消极意义上的语言权利,是指少数人所具有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国家不得否认或歧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27条中规定了少数族裔有保留自己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的权利。该公约因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而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该公约对于语言权利的定义主要是一种消极权利,即要求国家和政府不得歧视、不得干预,但并未赋予国家和政府推动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积极义务。《公约》中的非歧视规定对于少数群体的语言权利明显不足,因此,必须具有积极意义上的民族语言文字权利。第二重面向的权利则要求赋予国家积极推动权利保护的义务。1992年联合国《在民族或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第一条中就明确赋予缔约国保护少数民族的存在发展及其语言、文化、宗教方面的民族特征的积极义务,并且以赋予缔约国积极义务的方式在第四条第三款中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确保少数人有充分机会学习母语或在教学中使用母语。
民族语言文字权利所具有的积极面向主要依靠国家促进语言文字的教育来实现,也是民族语言文字权利得到有力保障的重要条件,因此,需要将此积极意义上的语言文字权利抽象为民族语言教育权,以突出国家对民族语言的教育、传播所承担的义务。
二、民族语言教育权的基本内涵与法律保障
(一)基本内涵
民族语言教育权是指民族自治地区公民所享有的接受民族语言教育机会的权利。民族语言教育权可以分解为两个维度的内容:一是接受民族语言的语文教育,二是接受以民族语言为媒介的公共教育。国家公共教育中的民族语言教育和使用民族语言的教育是民族语言权利保护的重要方式,只有将本民族语言成为教育媒介,公民可以使用民族语言接受各类文化、科学、艺术教育,才能保证民族语言不至于濒危或成为使用程度极低的“文化遗产”。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民族语言教育权的权利主体是个体而非集体。过去有观点认为,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民族语言文字权利是一种集体权利,即将民族作为权利主体加以整体保护。事实上,民族是一抽象概念,既非法律上的实体,也非拟制的权利义务主体,难以作为权利主体存在。故而,长期以来《宪法》中的民族语言文字权多是一种原则性规定,在实际的立法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出现民族自治地区“一刀切”现象,政策往往在强化通行语言和弱化通行语言之间摇摆,将民族语言的发展、使用摆在了国家通行语言的对立面。事实上,只有将民族语言教育权定义为个体权利,法律所保障的是个人接受民族语言教育的机会,法律要求国家为民族自治地区的公民提供选择接受优良民族语言教育的机会。既然是权利,而非义务,也就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公民选择语言教育的自由。
其次,民族语言教育权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国家需在公共教育体系中设置民族语言的语文教育和以民族语言为教育媒介的知识教育,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公民提供接受民族语言教育的机会。除国家所承担的积极义务外,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也负有不得干涉、歧视民族语言教育的义务,不得干涉他人自愿接受民族语言教育的权利。
最后,民族语言教育权的内容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公民享有自主选择语言教育的权利,也具有要求国家提供良好语言教育机会的权利。作为国家应该提供良好的民族语言教育机会,通过民族语言教育促进语言文化发展,实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但作为权利主体而言,个人则有选择接受何种语言教育的自由。当然,语言权利不仅具有消极自由的内容,更具有积极自由的意义,个人也具有向国家主张要求接受良好民族语言教育的权利。
(二)法律保障
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民族语言教育权的法律保障措施:第一,赋予自治机关在教育使用语言上的自治权。自治机关可以根据国家的教育法律、方针政策,根据本民族自治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在公共教育中的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内使用民族语言。《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6条规定了民族自治机关在教育用语上的决定权。第二,保障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和少数民族语言授课。《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7条第3款和第4款规定了民族学校中间使用民族语言授课和采纳少数民族课本,同时赋予各级政府扶持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编译出版的义务。第37条同时明确要求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实际上是在落实民族语言教育权和推行普通话之间寻找平衡的位置。第三,坚持“民汉兼通”的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实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行语言的双语教学,秉持“民族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交融进行”的民族语文教学观念。
三、民族语言教育权的规范原则
(一)平衡国家通行语言教育与民族语言教育
语言不仅具有交流工具的功能,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通行的语言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形成共同的文明记忆的文化沟通作用,是国家统一、民族共融的文化基础。因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往往会推广使用国家通行语言,以期实现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我国制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一方面以法律形式规范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使用;另一方面,保证了在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传播和发展。就民族语言教育权的规范而言,首先应该平衡国家通行语言教育和民族语言教育,既不能厚此薄彼,忽视国家通行语言教育,也不能忽视民族语言教育,导致民族语言的传承失序。
平衡国家通行语言教育和民族语言教育关系,需要国家对语言政策采取最小干预的立场,既不能为保护民族语言而在民族自治地方强推民族语言教育,也不能为促进民族交流着力于国家通行语言教育而自然忽视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教育。国家以中立姿态,在民族自治地方同时提供国家通行语言教育和民族语言教育,为公民提供选择良好民族语言教育的机会。国家通行语言的地位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在经济交往、文化发展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民族语言只要有良好的教育传承,有宽松的发展环境,也自然在民族自治地方处于重要的文化交流地位。国家的民族语言保护义务主要是为少数语言族群提供语言选择机会,保护濒危语言的传承,不宜矫枉过正,忽视国家通行语言的重要价值。
(二)突出双语教学在民族语言教育中的意义
在教学中运用民、汉双语模式是保障民族语言自由使用和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民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措施。生活是语言发展的源动力,如果一门语言难以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则势必成为“活化石”。因此,民族语言教育中的重要环节是双语教学,使学生能够运用民族语言学习各科科学文化知识。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权利的真正落实,需要双语教学实现民族语言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真正运用,有助于实现社会整合[6]。同时,双语教学的培养目标是“民汉兼通”,在促进民族语言传承保护的同时,兼顾国家通行语言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目前,双语教学的开展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其中原因有三:一是当地人对双语教学存在认知错误,要么认为民族语言无用,要么不愿意学习通行语言,认为会被“同化”;二是双语教学缺乏优良的师资和教材,师资和教材建设无法适应社会需求;三是双语发展不平衡,双语教学实施过程中,有重汉语轻民族语的普遍倾向,导致学生双语发展不平衡[7]。
破解当下双语教学中的问题,需要在民族语言教育法规政策中倾向扶持双语教学建设发展。一是鼓励培养双语教学的优秀师资,选拔兼通民族语言和汉语的人才担任双语教学的师资;二是鼓励编写、出版优秀的双语教材,组织力量翻译、编撰优秀的民族语言教材。
(三)促进民族融合,维护国家统一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维护民族繁荣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语言的融合交流在促进民族融合、国家统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统一虽然离不开通行语言的支持,但也并不意味着国家统一必然采取语言同化政策。语言生活的多样性有助于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交流。因此,语言的多样性对于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而言同样重要。但从另一角度而言,语言权利的发展和传播不得有破坏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不正当目的,保护民族语言的教育、发展和传播也并非意在阻碍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前述联合国《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第8条第4款明确规定宣言中所提出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违背联合国宗旨与原则的活动,特别是国家主权的平等、领土完整。宣言在序言中表明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旨在促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四、结语
当下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与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在新时代民族团结发展的语境中提出民族语言教育权不仅具有法律依据而且有现实的意义。明确民族语言教育权的基本内涵和规范原则对于解决民族语言发展中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民族语言教育权的提出也呼唤在法律层面明确民族语言教育权的内涵与规范。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的发展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点。民族语言权利保护也需要坚持“多元一体”思路,民族语言教育权实质是要求国家在推行通行语言的同时,在民族自治地区提供优质的民族语言教育机会。综上所述,在学理和法律上提出民族语言教育权有助于推动新时代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语言是民族融合交流的媒介,多样化的语言生活环境有助于实现民族间的交流交融,做到语言文化方面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实现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