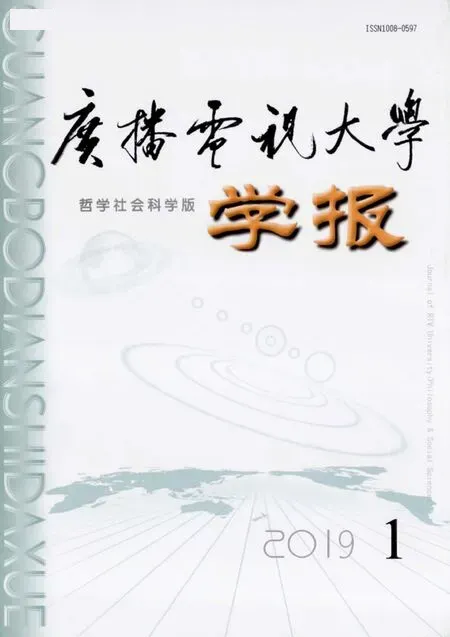清末民初戏界性别结构变迁
杜 溯
(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贵州 贵阳550023)
传统戏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剧本的创作、唱腔的发展、戏班的设立、剧目的演出都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明清以降,传统戏剧演出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最喜闻乐见的娱乐休闲活动,某种程度上还成为下层民众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成为影响社会风尚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学界已开始重视将戏剧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加以考察,借以全面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①。本文尝试以清末民初戏界的性别变化为切入点,通过探讨这些变化出现的背景、过程以及特点,来分析其与社会风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进一步考察当时社会风尚变迁的内在特征。
涉及戏剧的性别讨论都必须区分角色性别和生理性别。②本文所谓的“戏界性别结构的变化”主要指:清末民初戏界演员群体生理性别结构由单一的男性转变为女演员开始登上戏剧舞台,并由坤班发展到男女合演的现象;角色性别方面,角色阵容由以生角为主转变为以旦角为主,出现了旦角主戏的现象。此外,女观众群体的形成也可以看作是戏界性别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因为女观众群体的形成又是促成女子演戏、旦角主戏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本文将其作为女子演戏、旦角主戏的一部分加以讨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清末民初戏界性别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区域集中于开埠城市,主要是上海、天津。北京(平)剧坛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但在时间上要稍晚于上海、天津。依据当时戏界“北平学戏,天津唱红,上海赚钱”的现象,天津似乎更具有典型意义。但当时京、津、沪三地的演员流动极为频繁,并不局限于一地演出,很难依地域界定演员。③所以本文在进行个案分析时主要选择天津,但在论述戏界的性别变化时并不局限于天津一地,而是将变化的过程尽量系统地加以呈现。此外,由于当时戏界“京剧、梆子两下锅”的现象十分普遍,④本文在论述时对此也不刻意加以区分,而是注重从整体上加以考察。对于二十世纪初年出现于戏剧改良运动中的“文明戏”,由于主要受政治思潮影响,革命意义超过了娱乐消遣功能,在反映社会风尚方面与传统戏剧相比不具备典型意义,故本文对此不做讨论。
一、意象化特征下角色性别与演员性别的分野
中国传统戏剧与西方戏剧相比有着明显的意象化特征。所谓“以意取象”,通过程式化的表演形式、音乐唱腔、服饰化妆、剧本创作追求对现实生活的神似,演员准确掌握角色行当的表演程式是戏剧人物塑造及戏剧环境交代的关键所在。正是这种意象化的表现方式使得戏剧表演中的角色性别成为一个可以被塑造的符号学意义上的概念。
中国传统戏剧的这种意象化特征的具体表现有很多。《清稗类钞》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京剧以声歌代语言,以姿势表动作,故精神上之能事极缜密,而物质上之布置转多忽略不备。扬鞭则为骑,累桌则为山。出宅入户,但举足作踰限之势;开门掩扉,但凭手为挽环之状。纱帽里,门旗则为人头,饰以为须,则为马首。委衣于地,是为尸身,俯首翻入,是为坠井。乃至数丈之地,举足则为宅。内外绕行一周,即是若干里。凡此皆神到意会,无须责其形似者。”[1]P30
这段描述是从情节和布景上来说明戏剧的意象化特征的。对于这一特征,论者大多认为这正是中国戏曲艺术性之所在。张次溪即认为旧戏“于假之中更见其技艺之精超乎真相之外,而独用形容使观者想象得之。一人有一人之特点,一技有一技之妙境,故能百观而不厌。”[2]P4署名为梦觉生的《江天小阁谭戏》一文也认为“京剧皮簧亦属写意之艺术,重精神而不重物质。京戏之精神从唱工、做工表出之”[3]P1苏少卿也认为“虚拟法者,凭依精神之灵而模拟物态以暗示于人者也……此真中国剧之特色也。”[4]P2这些观点肯定了戏曲作为艺术形式在表现方式上的张力。但也有论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意象化的演出方式“是使它逐渐远离俗众的原因之一。”[5]P599无论这些说法哪种更为合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承认中国传统戏剧是以意象化为主要特征的。
传统戏剧在对角色性别的表现上也有着明显的意象化色彩。首先,服饰的差异是体现性别的重要手段。⑤由于日常生活中男女服饰有着极大的差异,所以服装、饰物成为区分性别的重要依据,是最直观的性别符号。而某些饰物还起着区分角色行当的作用。比如京剧小生依据服装饰物又有翎子生和扇子生的区分;文丑又有官衣丑、方巾丑和茶衣丑的区分。这种作用本身也说明了服饰在反映人物性格方面的符号作用。其次,化妆和道具是戏剧表演规范化的重要方面,也能直观地反映角色性别。比如旦角用以改变和美化自然脸型的“贴片子”以及武旦、刀马旦和花旦使用跷鞋表示缠足妇女等等。此外,戏剧意象化特征的巩固是以业已取得广泛认同的表演程式为基础的。这种表演程式包括一系列的表演动作,比如开门、关门、上马、下马、上楼、下楼、起霸、趟马、走边等等。同一表演动作旦角和生角的做法是不同的,有时甚至同为生角,文官和武将的做法也是不同的。这种程式动作或者说做工、身段的区分无疑也是极为重要的性别符号。甚至可以说,这是我国传统戏剧高度艺术化的性别符号,最能反映不同性别角色的本质不同。
传统戏剧的这种意象化特征决定了角色性别可以用服装、道具、化妆、身段和做工等舞台表演来表现,而不一定必须与演员的生理性别相吻合。这在实质上为角色性别与演员性别的分野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乾旦、坤生乃至禁止女子演戏提供了可能。
二、戏界参与群体性别结构的变化
中国戏剧的表现方式虽然是意象化的,但其在编演内容上多涉及政治情事、道德伦理,其中既有合乎统治者利益的内容,也有与其政治哲学、礼法制度相抵触的地方。因此,戏剧演出这一传统社会重要的集体娱乐活动往往受到诸多禁令的约束。虽然有学者认为这种禁令“不过是虚张声势,强化精神威慑而已。”[6]P129但禁令本身就可以说明戏剧活动不可能独立的存在于道德礼法和政治哲学之外,特别是在传统礼法制度之下,为戏剧活动设立“性别规范”的往往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律令、谕旨,甚至还包括社会舆论色彩浓厚的乡规民约、梨园规约等等。这些“性别规范”主要是针对女性而设立的,甚至包括禁止妇女入庙、入场看戏,禁止女戏游唱等等。其共同借口就是“男女混杂,有伤风化”,其共同目的就是通过性别樊篱来规范社会性别关系,确保性别界限。
清代中后期,有妇女不得进戏园看戏的禁令。对于这一禁令开始实施的具体时间,有着不同的说法。近代戏曲家齐如山认为:“乾隆以前,京中妇女听戏,不在禁例。经郎苏门学士奏请,才奉旨禁止,所以二百年以来,妇女不得进戏园听戏。”[7]P13徐珂则认为“道光时,京师戏园演剧,妇女皆可往观。惟须在楼上耳。某御史巡视中城,谓有伤风化,疏请严禁。旋奉严旨禁止。而世族豪门仍不敛迹。”[1]P72这两种说法有不同之处,但也共同证明了晚清以来妇女被排斥在戏园之外的现象。
女子演戏在明时并未禁止,《清稗类钞》记述了“女伶远祖,近三百年当推陈圆圆为第一。”[1]P10然而到了清朝,政府颁令禁止女戏游唱,“光绪十六(1890) 年,朝廷以女班有伤风化为由,禁止女伶演出”[8]这样,清代中后期,戏剧演出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群体——演员和观众——都没有女性的参与,使得戏剧界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成为纯粹的男性世界。
对女性参与戏界的禁止是在传统礼法制度下依靠国家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力而实现的。随着晚清社会的动荡和国家社会控制力的下降,戏界的性别樊篱也相继被突破,使得其参与群体的性别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般认为清末民初女子演戏最早出现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垂云阁主的《女伶旧话》即认为“现在流行的戏剧用女子化妆登台演唱好像是始于光绪初年上海的愚园,那时候叫作髦儿戏,后又叫做猫儿戏。”[9]P6关于髦儿戏名称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张次溪曾有如下的记述:“平津之坤戏,上海则谓之髦儿戏,有时髦之意。海上初有坤伶时,人多乐观之。彼辈亦乘机而起以投时好。故群以髦儿称之。亦有称猫儿者,相传谓苏州某女子擅长此艺,教女徒率髫年稚齿登台献技。此女子小名猫儿,故称。或称帽儿,则以戏脚中有纱帽方巾,各色女子装演男子故名。”[2]P8
根据张氏的记述,坤伶演戏至少有髦儿戏、猫儿戏、帽儿戏三种称呼,而且各种名称的由来也不相同。⑥此外,曾有人认为髦儿戏是因第一个京剧女科班的主办人李毛儿的名字而得名,这种说法已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但李毛儿确实推动了上海女子演戏的发展。上海的女子演戏也由女戏班出演堂会戏发展到女班戏院的建立。但此时(光绪中叶)“毛儿戏尤未风行,演员角色不多,习艺未臻美善。”[10]P2上海的女子演戏活动多出现在租界地区。天津自开埠以后,租界地区也出现了女子演戏的情况。哈老熨在其《黄华琐谈》中就曾记述“吾于津埠日界某公司常聆男女合演之剧焉。”[11]P2垂云阁主也曾记述 “光绪末年,天津租界有翔云戏园专演坤戏。天津的女伶就从那时候方才开始”[9]P6与津沪两地相比,北京女子演戏现象则出现比较晚。《清稗类钞》认为“京师旧无女伶,光宣年间始有之。故不若天津、奉天、武昌、上海之久著也。”[1]P10“自鲜灵芝有津入都,而京师始有女伶。”[1]P72就具体时间而言,一般都认为是“民元赵智庵长内务,为维持市面计,特许女伶演剧。”[12]P1醒石在其《坤伶开始至平之略历》中说,“民国初年平市始有坤伶之发现……辛亥事起,北平风鹤频惊,市面萧条,达于极点。时赵智庵长内务,开放小班牌禁,借以维系人心,老俞(毛包)之子俞五(振庭),绰号土行孙者,见有机可乘,遂尔招致坤伶,借以标新立异。当时递呈警厅请解除坤伶入京之禁。批准后进在香厂建一戏棚,仿外埠男女合演之例,要金月梅、金秀英、金玉兰、孙一清加入,平人耳目一新,趋之若慕羶之蚁。”[13]P1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至于坤角进北京人人都说是民国初年俞振亭创出来的。其实不然,光绪末年有尤金花、尤玉花姊妹两到了北京。那时候的功令不准女子上台演戏。尤氏姊妹在东交民巷使馆界内搭了一个芦席棚子借重外人的庇荫唱了几天戏”[9]P11然而,后一种情况毕竟只是持续了几天的一个特例。而自俞振庭之后,北京的女子演戏虽经历了由男女合演到男女分班的挫折。⑦但一直未再中断。这样,自同治末年、光绪初年起直到民国建立,上海、天津、北京相继突破了禁止女子演戏的限制。戏界性别结构由纯粹的男性转变为女演员开始登上戏曲舞台。
三、女子演戏的社会认同与戏界男性群体的分化
清末民初,戏界参与群体性别结构的变化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具体而言,女子演戏的实现不但受到政治局势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且迎合了新形成的女观众群体的审美需求,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反礼法倾向和价值取向上的重商逐利之风。其中戏园经营者的实利化取向促成了女子演戏的实现,进而导致男性群体的分化。
女子演戏的逐渐实现正处于新旧嬗蜕期的清末民初,当时政治局势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前提。首先,闭关锁国局面的结束为西方新思潮的传入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其次,租界的设立为女子演戏摆脱封建禁令提供了庇荫之所。据黄楙材的《沪游脞记》记载:“夷场(即租界)由大小戏园30余所,或男串,或女串,或男女合串。”⑧此外,清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和辛亥革命等反清起义的发展使其制定的各项禁令相继被打破。这在京城妇女获得进戏园看戏权利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据《清稗类钞》记载:“光绪庚子,两宫西巡后,京师南城各处,歌舞太平如故也。辛丑和议成,巨室眷属悉乘未回銮前相率观剧。粉白黛绿,座为之满,迨薄暮车归,辄为洋兵所嬲……然自光绪季年以至宣统,妇女入园观剧已相习成风矣。”[1]P72这段描述反映了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社会控制力下降,与妇女进园看戏的禁令被打破之间的关系。
女观众群体形成对女子演戏的实现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时是与当时因“庚子赔款”而上演的义务戏紧密联系着的。著名琴师徐兰沅在其《徐兰沅操琴生活》中就有这样的表述,“由于义务戏的兴起,妇女才能走进剧场。最初义务戏的性质,是为了‘庚子赔款’,当时人民还有所谓‘国民捐’,都是清室王朝附加在人民头上的负担。由于是这样一个性质,义务戏就必须满座,因此就不得不让妇女走进了剧场。”[14]P103据云巢居士《春明会串琐话》的解释,义务戏一般有赈灾、筹款,显贵堂会以及救助同行等几种形式。[15]P1因其性质的要求,对观众而言准许女观众进园;对演员而言多安排名角登台。因其叫座能力较强,而当时坤伶的发展十分迅速。时人多感叹“自坤伶突起后,刘喜奎、鲜灵芝、金玉兰、张小仙等先后称雄,一时男伶大班之营业遂有不振之势。”[16]这说明坤伶演戏已取得了一定的社会认同。
从女子演戏的实现过程来看,上海的李毛儿为谋利而开设女班。⑨天津戏园“老板喜其(平常坤角)包银稍廉,而广收女伶”[17]P2北平亦有“中和园主薛翰臣默察北平人士惑于坤伶者綦众,念于此时成立坤班定能获利蓰倍”[13]P2这无不反映了重商逐利之风对于女子演戏的推动作用,同时又可以看出女伶自身乃至女性群体在女子演戏实现过程中的集体失语。方言的《伶史》就记述了清末天津“坤角极具兴盛一时,可是不能独立,须有男伶帮佐才能成班”的现象。[18]P6这在客观上也体现了当时女性群体主体意识和主体性的缺失。然而正是这种重商逐利之风推动了女子演戏的实现,并努力使之适合社会大众的审美取向,赢得社会认同。这也在客观上挤压了男伶的生存空间,促使男伶群体分化。对女子演戏特别是男女同台,社会大众经历了由不认同到认同的过程。以清末重臣荣庆为例,他在民国成立后以平民身份迁居天津。荣庆在日记中记录了其他在天津的生活状况,其中第一次提到他在天津看戏是在民国元年阴历六月二十七日(1912年8月9日),他留下的记录是:“并至天仙观剧,中杂女伶,规矩尚整。”[19]P213这表明他对女伶演戏首先关注的是礼法问题。对女子演戏持有条件的赞同态度。但未多时他的态度就有了极大的变化。民国三年阴历三月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这三天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多次观看金月梅、刘喜奎等女伶演戏的情况。如果不是真正喜欢女伶的话,不会如此频繁地去看金、刘的演戏,而且郑重其事的作为一天主要活动记录在日记里。⑩当时,与荣庆相仿者极多,社会大众逐渐认同了女子演戏。以至于有“津门自近年以来坤伶之风大盛,一时声势之高几欲驾男伶而上之。”[20]P1的说法。同时,也有人认为此时的坤伶只是以色娱人,在演唱艺术上并无可取之处。如徐慕云即认为“往昔坤旦之本身对于艺术上只以点到应景为能事,绝无深刻动人之功夫。”[21]P202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时并不在少数,汪从明即不无讽刺地说:“一晚雪艳红演唱《葬花》,看客在这晚到的因为女性吸引的魔力十二分地拥挤”[22]P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观众群体在对女子演戏认同上的分化,但这种分化随着后来女伶艺术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弱直至消失。
男性群体的分化主要表现在戏界内部,一部分戏园经营者为谋求实利而推动女子演戏,随着坤伶的进一步发展而挤压了部分男伶和男班班主的生存空间后。他们便以“有伤风化”为名呈请禁止男女合演,但这并不是从审美情感上否定女子演戏,而是在女伶获取普遍社会认同的情况下出于自身利益要求而产生的巨大恐惧。这种恐惧与另外一部分班主因开办女班获利而极力推动女子演戏形成一种形式上的分野。然而,如果从他们的目的上看,这种分野无疑又是不存在的。最终随着名角挑班制的确立和男女合演的实现,戏界男性群体的分化逐渐消失。
四、花衫出现与踩跷废止:旦角在审美和技术上的内在突破
清末民初,随着戏界参与群体性别结构的变化,角色性别结构也开始发生改变。旦角主戏现象逐步取代了汉调进京以来奠定的角色阵容以生为主的局面。正如吴幻荪所说“二十年来戏界由趋重生角转而趋重旦角”[23]P4
旦角主戏现象的出现首先应归功于女观众群体。对此梅兰芳有深切理解。他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指出: “民国以后大批的女看客涌进了戏馆,就引起了整个戏剧界急遽的变化。过去是老生武生占着优势,因为男看客听戏的经验,已有他的悠久的历史,对于老生武生的艺术,很普遍地能够加以批判和欣赏。女看客是刚刚开始看戏,自然比较外行,无非是来看个热闹,那就一定先要拣漂亮的看。像谭鑫培这样一个干瘪老头,要不是懂得欣赏他的艺术,看了是不会对它发生兴趣的。所以旦的一行,就成了他们爱看的对象,不到几年工夫,青衣拥有了大量的观众,一跃而居戏曲行当里最重要的地位,后来参加的这一批新观众也有了一点促成的力量的。”[24]P11-113他的这段分析是客观的,从观众审美趣味和审美层次的差异性方面,指出了旦角主戏局面形成的原因。
旦角主戏现象不仅仅是适应了女性群体观众的审美需求,而且注重自身的内在突破。新旦角行当花衫的出现就体现了社会大众对女性理想形象的新期待,从而适应了社会风尚的变迁,迎合了社会大众的审美情感。
传统的旦角行当包括青衣、花旦、武旦、刀马旦、老旦和彩旦。其中花旦又可细分为闺门旦、泼辣旦、刺杀旦和顽笑旦。在传统礼法社会中,青衣以其稳重、端庄、正派的性格特征成为理想的女性形象,塑造的人物主要是贤妻良母和贞节烈女,也被称为正旦。在二十世纪初,王瑶卿、梅兰芳在青衣的基础上吸收了花旦的做和刀马旦的某些武打动作,创造了一种新的旦角行当——花衫。由于“花衫所表现的女性在身体上更加健康,在心理上更加坚强。”[25]P111与传统青衣性格中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特征有很大不同,塑造了大批有胆有识、智勇双全的人物,使得这一行当迅速取代青衣成为京剧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也推动了旦角主戏局面的确立。何一雁的《说旦》就指出了这一点:
“仅以旦言,今日之旦虽已如火如荼不可一世,而其本身旦之性质亦复少有变迁,非复旧观矣。盖旧日之旦,统言之为小旦,分言之有旦与贴,亦即平班之青衣与花旦,然今日最红之旦非青衣也,亦绝非花旦也,其专工青衣与专工花旦者皆仍不能红,其红而有名者惟新式之花衫耳。何谓花衫,冶青衣花旦与一炉。从花旦一名上摘一‘花’字之冠,复于青衣俗称青衫子一名之下截一‘衫’字之足,凑合而得一新名曰‘花衫’,已表示其新奇与雅博也,故此项花衫必须具之条件,一在能有青衣优美甜润之唱工,一在兼具花旦妖冶轻盈之做派,而其最大之连锁则又为艳丽之颜色,绚烂之服装。”[26]P4
这段描述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当时旦角确实居于角色阵容的主要地位;二是旦角中花衫已取代青衣、花旦成为最红的行当;三是花衫这一行当融合了青衣和花旦的优点和长处。注意到旦角内部行当变化的还有沈菊痴,他认为“现代戏剧界可算是青衣的世界了,其实真正的青衣简直可说没有,不过是些朦人的花衫罢了。至于向为台柱的须生,却是一天一天的潦倒下去了。”[27]P1这些都证明了旦角主戏现象的存在以及花衫这一旦角新行当的兴起。
花衫兴起的同时,踩跷的废止也是旦角新行当在表演技术上的一项重要突破。这一突破的实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旦角的表演技术而言,废跷使得诸多无跷工的演员不再受到技术上的约束,刀马旦、花旦和武旦等一些过去必须踩跷的行当不再受是否有跷工的影响,客观上扩大了旦角演员的表演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当间的技术限制。废跷还有助于改变女性角色弱不禁风的传统形象,有助于塑造女性新的性格特征,促进了旦角主戏现象的确立。冯小隐就曾针对早年票友习花旦极少而废跷之后习花旦的票友不可胜数的现象说:“习旦角而无跷工之苦,可谓生逢其时,稍具姿首便足以为旦,又何怪旦角之日增月盛耶。”[28]P5此外,坤旦学习程氏唱法也是旦角在技术上的重要突破。由于坤旦的嗓音以往多被讥讽为鬼音,限制了坤旦在唱工上获得社会认同。而“利用砚秋唱法此等补救之良药,不啻坤旦之还阳草。一时风从,遂有无旦不程腔之盛况。此举对坤旦嗓音唱法大有裨益”。[21]P203
由上可知,旦角主戏现象出现的原因绝非仅仅是“旦角俱有美色,唱作皆能感人”,[29]P6而是在观众审美倾向与旦角自身努力在审美和技术上寻求突破的共同作用下而达到的,其中花衫的兴起和踩跷的废止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重新塑造了新的女性理想形象,既反映了社会风尚,又推动了社会风尚的进一步变迁。
五、尝试性突破与普遍性认同:社会风尚变迁的内在特征
据英涵廬《追记北京票选名剧》的记述,“民国五六年春,北京《顺天时报》举行希望剧之票选。各界人士投票,结果被选男伶五十一人共八十五剧……女伶四十三人共一百十五剧……”[30]P1这再次证明了清末民初戏界性别结构的主要变化:女伶登上戏剧舞台并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反映情感家庭生活的旦角戏受欢迎程度超过了反映政治伦理、忠孝节义的生角戏,旦角开始在角色阵容中居于主要地位。这种戏界的新变化能够反映社会风尚的变迁。
女子演戏的实现,一方面体现了女性开始突破封建禁令和传统礼教设置的性别樊篱,反映了社会风尚中反礼法倾向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其实现过程中戏班经营者的谋利动机又有着浓厚的商业色彩,反映了社会风尚中实利化的倾向。同时也表现了女伶只能依靠男伶及班主帮助才能实现突破的状况,反映了传统礼法制度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这种反礼法倾向的存在与礼法制度的支配地位相纠缠的现象也正是清末民初社会新旧嬗娧的普遍表现。
旦角主戏现象与女子演戏相比更能反映社会风尚中的反礼法倾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旦角为主的剧目多反映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家庭关系、情感生活等内容,虽也有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成分,但与以生角为主的剧目相比,生角剧的内容多是政治斗争、朝代更替、战场厮杀,既不能贴近群众日常生活,又充斥着忠孝节义的封建礼法说教。戏界旦角主戏现象的出现可以说反映了社会大众希望摆脱礼法说教的要求,表达了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特点,体现了一定的实用主义倾向。其次,旦角新行当花衫的兴起既是旦角主戏的重要推动因素,也反映了社会大众对花衫所塑造人物形象的认同。这种认同本身不仅仅是对戏剧中人物的赞扬,也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社会作用的再思考和新定位,表现了对聪明而善良、美丽而坚强的新女性的向往。实际上表明社会大众已开始抛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和单纯的贤妻良母、贞节烈女式的传统礼法标准。
社会风尚既然是在一定时期内在社会上流行的风气和习惯。那么,在讨论戏界的“突破”以外,还必须专门对观众群体进行分析,观众对这些“突破”的认同过程和程度是反映社会风尚变化的重要标本。
戏剧演出的观众群体在严格意义上讲是由多个不同的“亚群体”组成的。因为观众所处的社会阶层,从事的职业、受教育程度乃至生活地域有很大差异,导致社会成员对社会风尚的认同存在差异。就本文探讨的对象而言,教育背景和文化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成员的群体归属。如果依照文化程度为标准进行群体分层的话,观众群体可分为精英层和通俗层。精英层因具体教育背景或接受新思潮的不同导致在社会风尚的认同程度上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而通俗层对社会风尚的认同主要是在社会思潮影响下做出的主观选择。由于社会风尚的主要传播方式是模仿、从众和暗示,这样就造成了在社会思潮这一上层的社会意识方面精英层引导通俗层,而在社会风尚这一底层的社会意识方面通俗层影响精英层的现象。所以,在社会风尚的认同上,通俗层的主观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我国观众在传统戏剧演出活动的审美上长期以来已形成心理定势。根据学者归纳,这种心理定势主要表现在“既不‘泥真’,又不‘认假’的艺术真实观;既要看戏,又要看艺的双重鉴赏观;心灵默契,约定俗成的程式体认;善善恶恶,爱憎分明的情感基调”[31]P155等四个方面。女子演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不认假”的艺术真实观,有观众“尤喜观坤角剧,诚以男子化装就不能免矫揉造作之弊”。[32]P1而旦角主戏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其双重鉴赏观和程式体认。“伶界大王”谭鑫培曾发出了“男唱不过梅兰芳,女唱不过刘喜奎”的感叹,这也说明了当时旦角的受欢迎程度。有论者就指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现代观众的心理趋于爱美的途径,而他(指梅兰芳)的扮相、装束、做派等项都是恰合于美底原则的。”[33]P1这些都在客观上反映了社会大众审美心态的“求真”色彩和注重观感的倾向。其注重观感而不理性的批判和鉴赏演员艺术水平的审美心态也最易于以模仿、从众的形式广泛传播,从而在社会大众中迅速得到广泛认同。
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女子演戏是当时戏界经营者为谋利而进行的尝试;旦角主戏虽然更多地体现着观众的审美心态,但促使其确立的花衫兴起和踩跷废止都是某些演员为扩大表演范围而进行的打破行当界限、降低技术难度的尝试。二者在本质上虽说都是戏界性别结构的一种尝试性突破,但其迅速地获得了社会认同,而且这种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普遍性的。这种尝试的初期,精英层的一部分传统士人(如本文所提到的荣庆)基于传统礼法观念曾提出过质疑或持有保留的认同态度,也曾导致戏界男性群体一度分化,但这些因传统道学思维或利益冲突而引起的质疑或分化并未持续多久即在从众、模仿乃至暗示的作用力下逐渐减弱直至消失。这种尝试性的突破和普遍性的认同体现了这一时期戏界性别结构与社会风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共同构成了社会风尚变迁的内在特征。
六、结语
中国传统戏剧的意象化特征为角色性别和演员性别的分野提供了理论基础,乾旦、坤生及其从事的反串演出就是这种分野的现实表现。随着中国传统礼法制度的确立,严格的性别樊篱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使得禁止女性群体参与戏剧活动的封建禁令相继出台,这种最初极具娱乐色彩的反串活动也因此由自发演变成不得不为。清末民初,随着清政府社会控制力的减弱,改良革命等社会政治思潮的传播,一些戏园经营者因女伶包银低廉而叫座能力强,有利于其盈利而尝试性的突破这些封建禁令,由此开启并推动了女子演戏现象的出现。在女伶登上演出舞台的同时,女观众也大量涌入戏园并形成了女观众群体,这一戏界新群体的审美心态促进了旦角主戏现象的出现。此外,旦行内部在审美和技术上的内在突破——花衫兴起和踩跷废止——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旦角表演艺术水平的提高,也使旦角主戏现象进一步得以确立。
这种戏界性别结构的变化反映了当时社会风尚的反礼法倾向和重商逐利之风。同时这一变化在实现过程中也体现着明显的尝试性色彩,但这种尝试性的社会认同却十分普遍。现象与回应之间在形式上的这种不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风尚变迁的内在特征。这种特征也是与清末民初社会嬗变的大背景相吻合的。
[注 释]
①以性别为切入点进行戏剧史研究的成果较多,与本文论旨相近的著作主要有:黄育馥著《京剧:跷和中国的性别关系:1902—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李祥林著《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路应昆著《中国戏曲与社会诸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田根胜著《近代戏剧的传承与开拓》(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论文主要有:叶长海,《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黄育馥,《跷在京剧中的功能:性别研究的视点》(《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周慧玲《女演员、写实主义、“新女性”论述:晚清至五四中国现代剧场中的性别表演》(《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4-26页);陈永祥、罗素敏,《女演员的兴起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观念的变化》(《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第65-70页)。对于戏剧史研究成果溢出本文论旨的部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②角色性别是戏剧演出时剧中人物的性别属性。生理性别则包含所有与戏剧相关的群体——剧作家、演员、观众、乐师、戏班主、舞台服务人员——的生理属性。本文谈到生理性别时一般指演员的生理性别。
③对于“京剧、梆子两下锅”的现象及其具体的形式可参看马少波、章力挥等主编的《中国京剧史》(上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242页。关于这种现象的持续时间,此书认为“始于19世纪80年代盛于20世纪前30年,而余风所被,绵延到20世纪80年代。”(第242页)。
④文明戏,又被时人称为“新戏”,因其在演出形式上多念白而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端。在戏剧领域讨论以服装改变性别的问题应注意其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戏剧的表现方法上,演员饰演与自己生理性别相反的角色时,以服饰来隐藏生理性别,传达角色性别的信息。一是戏剧的表演内容上,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是发生在剧中人身上,“换装”是构成故事情节的重要部分。本文是指前一种形式。后一种形式在廖炜春《服饰造型别:英国文艺复兴与中国明清戏剧中的换装与性别》(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中有着详细的介绍。
⑤据马少波、章力挥等主编的《中国京剧史》的考证,“猫儿戏”之称见于王韬《瀛濡杂志》。“髦儿戏”之称见于姚公鹤《上海闲话》(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对“帽儿戏”由来的解释,是书则认为是张次溪《梨窝琐记》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根据张次溪的记述,以上三种说法均非他自己的观点,而只是客观地记述见闻而已。而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中有“另据葛元煦《沪游杂记》云:‘髦儿实为帽儿,因戏中角色有纱帽、方巾等名色。且系女人装演男子,故有此称。’”的说法,实际上认为“帽儿”的提法出于葛元煦《沪游杂记》。这种观点似比马少波、章力挥等主编的《中国京剧史》的观点可靠。
⑥据醒石《坤伶开始至平之略历》一文记载,“自坤伶势力扩张后,男伶几无立足地,同时趣闻百出,报纸 上书不胜书,男班认为有机可乘,虽于正乐育化会提一个借以男女合演有伤风化为词呈请警厅禁止。警厅有鉴于报载遂如所请,取缔男女合演,勒限八月一日,男女分班。”这段记载说明了女伶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男伶的生存空间,反映了在女伶突破性别樊篱的初期,男伶与女伶、男班与女班的利益冲突。但也间接说明了社会大众对女伶的广泛认同。虽在演出形式上禁止了合演,但毕竟认可了女子演戏。
⑦黄楙材,《沪游脞记》,转引自马少波、章力挥等主编,《中国京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但是《中国京剧史》关于此段引文出处的解释似乎有误。该书认为引文来源于王懋材的《沪游纪胜》,但笔者翻阅《中国丛书综录》《贩书偶记》均未发现有《沪游纪胜》一书。在上海通社编辑的《上海研究资料》(《民国丛书》第四编第80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91—193页有“沪游脞记提要”一节,为胡道静所著。其中写道:“沪游脞记一卷,清黄楙材著。材一作裁。楙材字豪伯,别号千顷波渔者,江西上高人。所著尚有《西輏日记》《印度剳记》《游历芻言》《西檄水道》各一卷,彙刻为《得一斋杂著》。……。这本书(《沪游脞记》)到了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才由湖北沔阳李世勋氏把它刻在铁香室丛刻续集里。”(第191页)由此可见,王懋材似应为黄楙材,《沪游纪胜》似应为《沪游脞记》。
⑧可参看海上漱石生《梨园旧事鳞爪录》[《戏剧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28年11月)]中“李毛儿首创女班”一节的记述。
⑨荣庆的日记与其他人有很大不同,每天仅以二三句话记录主要活动,字数较多的记录主要是包含了他与人相互唱和的诗歌、对联。所以说,他的日记可以很清晰的反应其日常生活习惯。
⑩关于废跷的背景、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黄育馥的《京剧·跷和中国的性别关系:1902—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书已有较为详尽的论述,本文不再专门讨论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