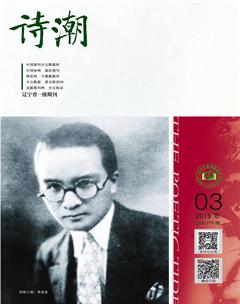为海子起另外三个笔名的人
姜红伟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黄金时代。在那个百年难遇的诗歌年代里,发生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一个叫李青松,一个叫海子。
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位于北京海淀区学院路41号的中国政法大学校园。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分团委宣传部长、诗社社长、《星尘》诗刊主编、《法官的摇篮》主编、《法学士》主编的大学生李青松,在主编的刊物上首发了当年在诗坛默默无闻的诗歌爱好者海子创作的《阿尔的太阳》等31篇早期诗歌、散文、评论作品(其中18篇诗文被《海子诗全集》漏收,成为海子的“轶诗轶文”),而且为海子重新命名了三个大家闻所未闻的笔名,还邀请海子举办了一场关于现代诗的诗歌讲座,从而使海子在这场诗歌讲座期间结识了初恋女友,开始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
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开始于1983年9月。
结识海子
1983年9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对于来自内蒙古赤峰市第三中学的学生李青松来说,经过寒窗苦读,勤奋拼搏,终于以优异的高考成绩收获了一张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对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79 级毕业生查海生(海子)(以下名字均以海子简称)来说,他的收获则是一份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校刊编辑部担任编辑的工作。
尤其令他们两个人意想不到的是,除了各自的收获之外,原本十分陌生的他们,从此之后,在法大校园还相互收获了相识的缘分,收获了坦诚的信任,收获了快乐的交往,收获了彼此的欣赏,收获了真挚的友情,收获了一生中最难忘、最美好的一段佳话,收获了一生中令人温暖、令人感动的一段往事。
1980年代初期,诗歌热潮已经开始一浪高过一浪地席卷全国各地。无论是社会上,还是高校内,抑或是中学里,爱好诗歌、写作诗歌的青年学生数以百万计。尤其是在各地的中学校园,涌现出如火如荼的校园诗潮热,喜爱诗歌的中学生遍布了每一所中学,每一个班级。
那时候,李青松正在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第一中学读高中,写作成为贯穿他整个中学时代的校园主流生活。当一名诗人,当一名作家,成为文学少年李青松的理想。当时,他的语文老师叫刘智,是当地的一位作家。看见李青松写的作文,刘老师意识到这是一棵有潜力、有希望,值得培养的文学新苗,于是经常鼓励他多看书、多学习,并亲自指导他写作。当时,刘老师在学校创办了一份油印文学小报《新长征》,凡是李青松写的好作品,他便给予刊登,从而激励李青松不断地写出更好的诗歌、散文和散文诗并发表在《阿伦河文艺》《呼伦贝尔报》等报刊。
1981年,李青松更是凭借散文《菱角泡》荣获了北京《中学生》杂志社举办的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三等奖,并入选了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获奖作品集《可爱的家乡》一书,成为内蒙古中学生中有名气、有影响的学生作家、诗人之一。
可惜的是,由于爱好文学和诗歌,李青松严重偏科,数学、英语成为高考路上的两块绊脚石,把他绊倒在1982年。
1983年,李青松来到赤峰市姐姐家,开始了在赤峰市三中的复读生活,并最终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而出身于诗歌氛围十分浓厚的北京大学的海子,对诗歌更是痴迷,更是热爱。这位79级法律系学生,在大三那年开始学习写作诗歌,不但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创办的油印刊物《启明星》上发表了第一首诗作,而且在毕业前夕还自费编印出版了一本汇集25首习作的油印诗集《小站》,作为献给自己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的“见面礼”。
由于对诗歌的共同热爱,共同追求,李青松和海子的相识便成为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而他俩的初次相识,则缘于为《中国政法大学校刊》投送诗歌稿件。
入学后不久,李青松获悉学校创办了一份校刊,并开设了一个叫“芳草地”的文艺副刊,专门刊登本校师生创作的文艺作品,主要是诗歌、散文和散文诗。负责编辑副刊的一位叫吴霖的老师,是一位青年诗人。于是,有一天下午,他拿着自己上大学后新写的几首诗去校刊办公室投稿。
在校刊办公室,李青松的詩稿得到了吴霖老师的认可,并被留用。而通过吴霖老师的介绍,李青松和吴霖的对桌同事、同样爱写诗的海子结识了。
那一年,李青松26岁,海子19岁。
李青松和海子两个人,论称呼,李青松直呼海子叫“小查”,海子则管他叫“青松”;论年龄,李青松出生于1963年,比海子大一岁;论个头,李青松1米83,比海子高一头;论写诗的经历,李青松于1981年开始写诗,比海子早一年;然而,论身份,李青松只是学生,海子却是教工。因此,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师生关系又不是同学关系,更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类似那种诗歌伙伴的关系。
从此之后,这对诗歌伙伴开始携手同行在1980年代。
选登海子小说评论文章
进入法大之后,李青松的文学创作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并陆续在《法大校刊》和《法大团刊》上发表散文诗作品,并因为投稿,结识了主编团刊的毛磊。
毛磊是80级法学专业学生,是李青松非常尊敬的一位师兄。身兼多职的他,既是学校记者团团长,还是《法大短波》主编,又是《法大团刊》主编。由于李青松经常投稿,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交流、沟通,毛磊时于他在文学特长这方面认识比较清楚,情况也比较了解,对李青松的能力也非常认可。
大约是1084年4月,为了让李青松的才华得到更全面的展现,才干得到更全面的锻炼,毛磊便把编辑副刊这项工作交给了李青松,请他担任副刊栏目《诗叶》的责任编辑。
担任团刊副刊编辑,是李青松进入法大后承担的第一个社会职务。为了不辜负毛磊师兄的信任,李青松十分认真地履行自己的编辑责任,忙着约稿,忙着编稿,忙着写稿,把只有五个页码左右的《诗页》副刊办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为了办好这个文学副刊,李青松四处奔走,征集诗歌、散文、散文诗等各类稿件。有一天,在学校门口,李青松遇见了海子,便和他说起了编辑团刊副刊的事,希望他给予大力支持。当时,海子刚读完张承志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对这部小说十分推崇,并写了一篇精短的小说评论,于是,便将这篇稿子给了李青松。两个月之后,在6月份出版的第6期团刊上,经过李青松的编辑,海子的这篇题为《我们的水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男子汉——张承志<北方的河>印象》的小说评论发表了。
海子的这篇小说评论是李青松担任编辑编发的第一篇海子作品(事后经过考证,发现此文是被《海子诗全集》漏收的“轶文”)。此后,因为编稿和投稿的缘故,李青松与海子之间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聘请海子担任诗社顾问
20世纪80年代是大学生诗歌社团群雄并起的时代,全国各地高校诗社风起云涌。尤其是到了1984年,全国各地高校掀起的大学生诗歌社团热潮渐渐达到了高潮。作为会集了众多诗歌爱好者的中国政法大学,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这股大学生诗歌社团潮流。
1984年4月,一个成立中国政法大学诗社的新计划在校刊编辑、青年诗人吴霖的脑海中酝酿着。而此时的李青松,由于在同学中间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善于团结同学,善于策划活动,并且发表过一定数量的作品,在同学们中间既有威信又有名声。因此,在吴霖的心目中,李青松是发起成立法大诗社并担任社长的最佳人选。于是,有一天,在遇到李青松的时候,吴霖将这个想法和他进行了沟通,鼓励他发起成立中国政法大学诗社。
李青松接受这项“重任”后,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诗社的筹备工作中。9月13日,以李青松为首,以王彦、李燕丽、张国森等为骨干力量的诗社筹备组成立,并在校园内贴出了醒目的
海报,开始面向全校“招兵买马”。
“当年贴海报,大体有这样三处,那都是要贴的地方。一处是教学楼一楼,那里有一个地方,招收诗社成员和录取诗社成员以及公布成立诗社消息各贴了一次海报。第二个地方,是食堂门口,人来人往,比较集中,大家容易看到。第三个地方,从宿舍楼到食堂中间要经过一段路,路旁边有一个广告栏,贴着各式各样的《人民日报》等。每次海报共计三份,贴在三个地方。进行招生的时候,在通往食堂的一个广告栏前,拉了一张桌子,我安排几个骨干,拟定的诗社成员,在这儿值班,对报名进行登记,然后把报名登记的情况报给我,由我定,哪些人够条件。报名的时候,要有过去发表的诗,有的是写在作文纸上、稿纸上,大部分没有发表过,都是习作。我大体上翻了翻,看了看,圈定了一些诗社成员。然后由我班同学,毛笔字写得好的朱红霞,根据我拟定的人员名字写了一张海报,内容是哪些人被正式录取为诗社成员。”
回忆当年筹备诗社的往事,李青松记忆犹新。
为了办好中国政法大学诗社,有一天,李青松专门到校刊办公室找到了海子,请他担任诗社顾问,参与诗社建设,指导学生写作。海子受到盛情相邀,颇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有点喜出望外。面对这位诗歌伙伴的信任,海子愉快地接受了邀请,高兴地答应李青松做了诗社顾问。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在学校党委书记陈卓等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1984年10月27日,由李青松担任诗社社长、吴霖担任名誉社长的中国政法大学诗社正式成立了,并聘请邹荻帆、徐刚、刘湛秋等著名诗人以及政法大学语文教研室主任、著名修辞学专家高潮担任顾问。诗社主要成员包括:副社长:王彦、李燕丽;秘书长:张国森;社员:王志敏、韩鸥、宋纯杰、韩勤耿、武彦彬、荀红艳、钱国新、郁红祥、王曙光、朱红霞、曹洪波、李成林、刘志忠、姜继宝、孙红、付宏伟、李艳辉、刘奇、葛庆学、孙志彤、杨宏峰、杨记明、王旗。
“诗社成立没有搞仪式,也没有开大会。我印象中,好像是贴了一张海报,内容是哪些人被正式录取为诗社成员。那一天的时间大概是10月27日,大体上就把海报贴出的时间作为诗社成立的时间。成立好像是在晚上307大教室,所有成员见了一个面,因为晚上是自習,怕耽误功课,很仓促地就成立了。”
诗社顾问,是海子诗歌生涯中担任的第一个社会职务。作为诗社顾问,海子可不是那种对诗社工作不管不顾、不闻不问的人,而是十分热心地支持李青松的工作。诗社成立之后,他不但积极地支持参与诗社的建设,献言献策,而且还积极参加诗社举办的活动,尽心尽力。
尽管中国政法大学诗社仅仅是一个学生社团,但是,对于当时在诗坛上默默无闻、从未公开发表诗作的海子来说,却是一个唯一让他如鱼得水,感觉自信、感觉快乐、感觉轻松、感觉温暖的“诗歌之家”。因为,在这里,有李青松这样可以和他经常交流诗歌、探讨诗歌艺术的诗歌伙伴,还有众多喜欢写诗的学生诗友,大家在一起朗诵诗歌、讨论诗作、交流思想,不但有助于开阔视野,激发灵感,更有助于创作佳篇,写出好诗,像这样温馨温情的创作氛围,像这样自由自在的诗歌岁月,对于海子来说,是极为难得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在海子短暂的一生中,参加中国政法大学诗社的活动,应该是他一生中最陕乐、最美好的—段时光。
1985年1月,新疆石河子《绿风》诗刊社在全国组建了国内群众性青年诗歌社团联络中心,鉴于中国政法大学诗社举办了一系列在校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诗歌活动,成为中国高校诗坛上具有一流创作实力、取得一流创作实绩的高校诗社,于是将该苴吸收为会员,会员号为098,并在1985年第4瑚《绿风》诗刊上登载了诗社名录和社长李青松的名字,从而使中国政法大学诗社成为全国高校诗坛最有实力、最有影响的代表性诗社之一。
编发海子大量诗作诗论
诗社成立,当务之急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创办社刊。作为社长和主编,李青松肩上的担子可不“轻松”。那段时间里,他忙着征稿、组稿、改稿、审稿、编稿,并亲自撰写了约稿启事,策划了栏目名称,忙得焦头烂额、昏天暗地,终于将创刊号的诗歌稿件编好。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什么是这本诗刊的“东风”呢?这本诗刊的“东风”就是一个响亮的刊物名称和一篇精彩的刊首寄语。
对于刊名的命名,李青松找到了吴霖老师,很陕便得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刊名—_星尘。为什么叫星尘呢?
“当时商量刊名,为什么叫《星尘》,这个名字是吴霖提出来的。我当时还提出了星尘的尘字应该是那个辰字,这个尘是尘埃的尘,尘土的尘,别让外界以为咱们搞错了。后来吴霖说,这个尘是指小,是宇宙中的小星星。后来,海子的刊首寄语也有了这个意思,都是未来的小星星,一个个的个体,小星星汇聚起来,就是一条星河,就会发出光芒万丈,就能照亮世界。后来我一听,吴霖这么讲,挺有道理的,便同意了这个意见。”

刊名确定之后,迫在眉睫的事就是由谁来执笔撰写刊首寄语。
想来想去,李青松想到了最佳人选———诗社顾问海子。拿定主意后,李青松来到了校刊办公室找到了海子,请他为创刊号写刊首寄语。海子十分热情,也十分爽快,一口应承了下来,并认真地阅读了诗刊的稿件,仅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完成了李青松交给的这项光荣的任务。
“《星尘》诗刊创刊号的刊首寄语是海子写的,是我请海子写的。我当时找到他说,你是诗社顾问,要做点贡献,尽点义务,给我们写一篇刊首寄语吧!海子没有推辞,很爽快地答应了,叫我把稿子拿给他好好看看。于是我把已经编辑好的第一期稿件送到他手上。他从里面摘录了曹红波、郁红祥等人很多的句子,也把为什么叫《星尘》诗刊大体上解释清楚了。”
那么,海子的这篇刊首寄语是怎样写的呢?
海子的这篇题为《“太阳和你的心出自同样的物质”——写给拿起笔来的小星星们》的刊首寄语是这样写的:
1
你们拿起笔来了。
你们自信而默默的燃烧着,用你们纯净的灵魂。你们对着阳光大声宣告:“我是春的生命” (郁红祥)。
2
生活不是一种肤浅的堆积,也不是一场时间的游戏。总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在前边照亮我们大家。
要不,为什么要活着?
他“没有什么目的
只是去看看海”L王彦);她在秋天,“走进林中金黄的土地”(吴漠);他说“天空属于你的爱
大地属于我的自由”,他更说“即使我失去了一切
海啊永远存在”(宋纯杰)。
我想,这大海,秋天的土地,还有天空,都是我们生存的依托,是我们的根基。我们不认为个体的生命是暂时的现实。我们集合成不朽。我们的存在价值由土地天空大海等巨大的物质实体来证明。
我,作为人来到世界上,世界就只能是谓语。原野,记得刮过的风和栖落的鸟,而把繁衍的人群永久的挂在心上。
3
我要特别提出的是韩鸥的两首诗,这两首有灵性的小诗,自自然然的渗透了诗神微微的鼻息。真不容易。
他觉得音乐在他“寂寞的床头堆满了厚厚的云”。他说“查找你的名字但我不敢读出声来只能在这冰凉的桌面上用我柔弱的手去划”真是一个可怜而纯洁的男孩子!那么,那美丽的名字,属于谁呢?它的主人难道就永远这样——悄悄而幸福的居住在少年诗人正在苏醒的感觉中吗?
心怦怦跳着。
“绿色的窗关着”“红色的门开着”
“一群群跳跃的花朵闪过”——韩鸥啊,你是怎样想出来的?
4
你们的心灵划出不同的弧线。
有的朴素:从“丢手帕”(刘志忠)到“挂满童年的失望”的一棵树(李成林);有的新鲜:“星星是海中的鱼”(宋纯洁)“高粱是一堆高高的火”(钱国新),“黑色的岩岸上落满白色的海鸥”(张国森);有的则厚实:“乌黑的牛亡牛踏響河床”“风舔尽了天下的叶子”(吴漠)。你们在这些审美对象倾注了你们全部的情感和希望。你们甚至直接喊出我的“心海中有盐”的句子(曹洪波)。
你们是河岸上一股新鲜的气流,逼近了。
当然,与时代和历史相较,你们还缺少一种沉重的气质。你们刚刚开始燃烧。你们还须在一种更广阔的意义和背景上去领悟诗歌。诗,不能是个人的囊内物。走向群体,也就是走向自己。
5
你们“一大群一大群像葵花子聚在一起”(陈默)。
你们就要出发了。
幸福啊,光荣——你们——你们,这些中国的孩子——不,地球的孩子,不,星体的孩子——男孩子,女孩子——小星星们。
我已找不到恰当的背景来勾勒你们,那就赠一句法国现代诗人皮埃尔·勒韦迪的诗给你们吧:
有时一些几乎是裸赤的孩子从那儿走过
水是清澈的
一根红色的铜丝把灯引到那里
太阳和你的心都出自同样的物质
写完之后,小查将刊首寄语通过他们之间的“特殊通道”——什么是“特殊通道”呢?李青松回忆道:“我当时的宿舍跟校刊编辑部只有一墙之隔(准确地说,是一板之隔——同一座楼,楼道用纤维板隔开;一边是教工办公区,一边是学生宿舍区)。海子为了投稿方便,就把纤维板隔离墙抠开一一个洞。我们约定暗号——他在洞那边嘭嘭嘭敲三下,我在这边把稿子接过来。”
捧读着海子这篇文采飞扬的刊首寄语,李青松那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轻松”了。尤其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海子不但完成了这篇精彩的刊首寄语,而且还将自己的两首最新力作《面对河流》《苹果的歌》交给李青松发表(事后经过考证,发现这三篇诗文是被《海子诗全集》漏收的“轶诗轶文”),从而使他“满载而归”。
面对河流
在大河边,城市像一颗灰眼珠
瞅着原野
发愣
钥匙在孩子们的脖子上
开着一串串带齿的花儿
在大河边
最受人崇拜的是笨重的水管
孩子们说:水
水,给我水
金属的灰眼珠
被水沾住
一枝无花果
像人影一样
轻轻叩着
河流的门
开门的会是谁呢?
下雨了
条条墨绿色的影子
坐在中心广场上
早些时候
在美国
有一个戴草帽的大胡子
叫惠特曼
经常在雨中穿过广场
来到大河边
他是一株活着的橡树,结实,响亮
对着月亮和自己的血管
深深的呼吸
我是一株什么树呢
河上刮来的风
弄得我脸上到处都是灯火
手持兰花的屈原
和我站在一起
他跌进河里
我活了下来
生和死同样不容易
一想起对岸
我就变得沉默
苹果的歌
在立交桥上
一个男人
拎着苹果
遇见另一个拎着苹果的男人
他们寒暄了一会儿
他们并没有听见
两兜苹果
见面后
正在合唱一支歌
那些种籽和种树人在她们身体里常唱
的忧伤的歌
他们分手了
苹果的歌还没有唱完
11月1日,《星尘》诗刊创刊号出版后,李青松拿着两本散发着浓重油墨香的刊物送给了海子。尽管这是一本大学生办的油印刊物,但是,看着这本刊物登载了自己的诗作和文章,海子的脸上顿时写满了开心和喜悦,本来就像一个孩子的他高兴的样子就更像一个孩子了。
1984年,海子的诗歌创作迎来了一个“小高潮”。在这一年间,他写作了大量短诗作品,包括后来很有影响的《亚洲铜》《阿尔的太阳》等名篇佳作。但是,由于没有名气,尽管海子到处投稿,遭遇的却是到处退稿,从而使海子的心情比较沮丧,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受了不小的打击。
因此,面对这本发表自己诗文的《星尘》诗刊,海子内心深处的阴霾顿时一扫而光。因为,他看到了自己作品可以发表的希望,他看到了自己才华得到展现的曙光。同时,他也坚信自己一定能成为灿烂的星尘,在诗歌的天空闪烁出与众不同、耀眼辉煌的光芒!
《星尘》诗刊创刊号共计印刷了二百册,出版后,由于作品质量较高,优秀力作较多,不但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内深受好评,更是在首都高校之间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一本影响较大的大学生诗歌刊物,并得到了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好评。“当年,我和同学去了东城区赵堂子胡同十五号,拜访了臧克家,把我们的刊物《星尘》送给藏老,他认真翻看着,说了一些鼓励的话。”
作为诗刊主编,李青松为了力好刊物,可谓费心费力。回忆起当年办刊的情景,李青松向我讲述了几件趣事:
“那时候,刊物在打印社打出来以后,有时候装订活多,一放就放几天。我就号召诗社成员义务劳动,把没有课上自习的同学召集到打印社后面的一棵大树下、草坪上,把打印好的纸张,让大家按照页码装订好,以便早日让刊物出版。
每期刊物大体印200本左右,因为诗社成员每人一本,剩下的每个系要送,另外,各个高校需要交流,这也需要一定的数量。当时学校团委和学生会将诗社活动经费列支,实报实销,团委学生会到年底统一到打印社结算。”
为海子起了另外三个笔名
在担任诗社社长兼《星尘》诗刊主编前,李青松由于各方面能力比较突出,被法律系团总支任命为宣传部长。当时,团总支创办了一个刊物叫《共青团员》。为了推动学生文学创作,编辑部决定出版一期文学专号。而主编这期文学专号的重任便自然落在了李青松的身上。李青松找到了海子,向他约稿,请他给予大力支持,共同办好这期文学专号。海子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并在自己的作品中精挑细选了一篇散文和七首诗歌交到了李青松的手上。
尽管海子这八篇作品写得都比较好,李青松也很喜欢,但是,作为主编,他却犯难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一本刊物里是不可能发表一个人的八首作品的,那样的话,容易引发其他同学或作者的意见。但是呢,李青松对海子的这八首作品爱不释手,一首也不想删去。怎么办呢?李青松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给海子的作品多署几个名字,这样既保证了海子的作品一篇也不能少,又不会让其他作者产生异议。
结果,李青松“擅自做主”,除了海子以及原名查海生之外,他又绞尽脑汁给海子重新命名了三个新的笔名,一个叫小楂,一个叫阿米子,一个叫海生。这样,在这本《蓝天与宝剑》上,海子以本名“海子”发表了题为《我是太阳的儿子》的散文,以“小楂”署名发表了题为《阿尔的太阳》的诗歌,以原名“查海生”署名发表了题为《渡神》的诗歌,以“海生”署名发表了题为《新娘》《流浪诗人》的诗歌,以“阿米子”署名发表了题为《雕塑》《你根本就没有见过大红马》《沙漠上》的诗歌:
雕塑
孩子……孩子
一群孩子爬上粗糙的石头
等待中的姐妹
躯干
连同湖泊上双生的白马
风
甚至忧伤
都弯弯曲曲的占领地面
靠眼睛铺平道路
靠腿站立
或者顺着伸出的手臂
和天空一起
体会突然的断裂
淡淡笑一笑……
说着
说着
除了他们,没有人坐得那么久
把土地坐热
你根本就没有见过大红马
太陽打在脸上
山峦像一片薄薄的金属
闪亮,那么短暂
岁月默默地射下几颗星
你根本就没有见过大红马
野萝卜花开了
一粒青色的小虫在自然界边缘消失
燕子挑选洁净的尘土
挑选新娘
你根本就没有见过大红马
礁石后许多黝黑的海兽生息
夜晚,小甲鱼把四条腿支起
在沙地上
忧伤地瞭望
你根本就没见过大红马
沙漠上
原野上有一排牛皮鼓
听着
用牙齿听着
死去的父亲用沾沙的牙齿听着
饮水的声音
走过所有的额头和喉咙
对着月亮
骆驼流泪了
人,笔直地倒下去
还有影子
原野上有一排牛皮鼓
用牙齿咬住土地
咬住土地
你就是一棵树,一棵树
不会烂在这里
1984年11月1日,在李青松精心而巧妙的编排下,海子的这八篇作品全部刊登在文学专号《蓝天与宝剑》上。(事后经过考证,除了《阿尔的太阳》和《新娘》被收入《海子诗全集》之外,其余六篇诗文均从未公开发表,并且是被《海子诗全集》漏收的“轶诗轶文”)。
在一本刊物上一次性发表八篇诗文,在海子的个人作品发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喜事。因此,海子收到这本发表他八篇诗文的刊物,兴奋异常,连声向李青松说,谢谢你,谢谢你,青松!
对于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李青松向我讲述了具体的细节:
在我担任法律系团委宣传部长期间,团委刊物《共青团员》要出一期文学专刊,由诗社组稿(实际上就是由我来组稿主编)。我说,既然是文学专刊,那就起个专刊刊名吧———于是,就起了《蓝天与宝剑》。我当时好像正读一本苏联方面的小说,受捷尔任斯基说过的一句话影响很深———那句话大意是“法律就是蓝天下出鞘的宝剑”。校党委副书记宋振国说:“这名字好!———既有正义感,又有艺术性。”
我当时激情澎湃,撸起袖子撰写了刊首寄语。吴霖写了一组诗《在远方》,海子写了《我是太阳的儿子》等一篇散文和七首诗。还有郁红祥、张国森、葛庆学、王旗等同学的作品。由于海子这七首诗各自都是独立的主题,不能按组诗编发,只能每首单独发——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海子的名字就要在同一期刊物上出现七次。这样似乎不妥。我跟海子商量,能不能用不同的笔名,把这七首诗一次发出来。海子说,行啊!能发出来就行。
打字室那边催大样了,刊物出版流程不能再耽搁了。我便自行决定,除了查海生和海子之外,又给他起了另外三个笔名——“海生”“阿米子”“小楂”。
“海生”——这个简单,查海生三个字去掉一个字。“阿米子”——因为海子喜欢梵高,在诗中常称其瘦哥哥,我随手就给他起了这个外国名字。“小楂”———也没什么特别的寓意,只是当时我由查字联想到山楂树,就在查字前面加了木字旁。事后,海子对这几个笔名也都很认可。
在那期《蓝天与宝剑》文学专号上———海子的《我是太阳的儿子》,阿米子的《雕塑》(外二首),查海生的《渡神》,小楂的《阿尔的太阳》,海生的《新娘》《流浪诗人》等,其实都是海子一个人的作品。至于“阿米子”“小楂”“海生”等笔名,海子在别处用没用过,我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海子写的《阿尔的太阳》这首诗,我印象中那时候他正在读《梵高传》,有了些感悟,便写了这首诗,副标题是——给我的瘦哥哥梵高。”

邀请海子举办诗歌讲座
在李青松和副社长王彦、李燕丽以及秘书长张国森的精心组织下,中国政法大学诗社办得热火朝天、风生水起。除了编辑出版诗歌刊物《星尘》,举办“法大之春”诗歌朗诵会,组织法大诗歌朗诵会以及创作奖、朗诵奖评选之外,诗社组织最多的活动便是邀请著名作家、诗人开办文学讲座和诗歌讲座。诗社成立之后的1984年底至1985年初,著名诗人、作家刘湛秋、徐刚、顾城、梁晓声等先后来到法大校园举办讲座。
诗社开力、文学诗歌讲座,不但使诗社成员受益匪浅,而且更使海子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1984年11月27日,按照计划,诗社将邀请一位著名作家来诗社举办讲座。谁知道,那个作家却因故未来。李青松当机立断,跑到校刊力公室去找吴霖老师,请他救场。岂料,事不凑巧,吴霖也偏巧不在,只有海子在力公室。结果,经过李青松“花言巧语”的劝说,面对李青松的热情相邀,海子毅然应承了下来,跟随李青松来到了讲座现场。
由于准备仓促,海子的那场诗歌讲座并不是一场成功的诗歌讲座,但是,他在这场诗歌讲座上却收获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初恋。李青松在《怎样握住一颗眼泪》里写道:
“有一次,我们请某诗人来校讲座,结果,那个诗人因故没来,我就跑到校刊编辑部找吴霖救场,偏巧吴霖不在,就跟海子说:“小查,你来救场吧,你讲。”海子说:“讲什么啊?”我说:“你就讲朦胧诗吧,对付一个多小时就行。”
海子说:“不行,临时抱佛脚,我哪有那本事啊!”我说:“今天听讲座的可全是漂亮女生,你不去讲会后悔的。”海子的眼里放出欢喜的光芒。海子是鱼,女生是鱼钩。漂亮女生,是钓海子这条鱼的鱼钩。于是,海子就跟我来到那间教室。
不过,确实有点难为海子了。那次讲座由我主持,海子都讲了什么,我一句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额头和鼻尖上浸满了汗珠,讲话的逻辑有些凌乱。然而,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在那次讲座的现场,他的目光与坐在头排认真听讲的一位女生的目光,倏地碰撞在一起——海子的初戀开始了。”
这是李青松没有想到的,更是海子没有想到的,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这场初恋,不但使海子品尝到了幸福的爱情,更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灵感。在那段时间里,海子写作了大量抒情诗作,并挑选出《主人》《你的手》《夏天的太阳》《窗户》《渔人》《行路人》《日落》《归来》《南方》《一壶水》《暮色中的房屋》《埋头咏》《离合》《三位姑娘》《苞谷地》《母亲的姻缘》《思念今生》《手》《鱼》等19 首诗作拿给李青松发表在1985 年3 月出版的第2期《星尘》、1985 年5 月出版的第3 期《星尘》和1985 年12 月出版的第4 期《星尘》上。(事后经过考证,发现其中有8 首诗作是被《海子诗全集》漏收的“轶诗”)
据统计,海子生前,共计在公开发行和内部出版的书报刊上发表诗歌和评论183篇,而李青松主编(包括王彦、张国森参与编辑)的刊物发表海子的早期诗文作品竟然多达31篇,约占海子作品发表量的六分之一,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在时隔多年后,谈到编发海子诗文这件事,李青松说:
“在这个时候,我们创办诗社,创办诗刊《星尘》,编发大量海子的诗,其实是对他的一个认可、一个肯定、一个鼓励。即便这些学生刊物在校园里内部发行,也是一个载体,其实对他起了一个激励和鼓舞作用,我觉得应该乐观地看,它有这个作用。因为他有这样一帮朋友每周都要在一起讨论诗,使他的心情很愉悦,当年非常阳光,诗歌让他快乐,找到了那种他表达情绪的方式。”
怀念海子
中国政法大学诗社最红火的时期是1984年11 月至1985 年12 月。这段时期的诗歌时光,被李青松记录在一篇题为《诗社的回顾》文章中: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好像是一支歌中有这句话。
我们留下脚印了吗?不知道。但我们实实在在留下了一个诗社,一个稚嫩的,孩子气十足的,甚至有些童话色彩的诗社。
真说不清楚,当初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搞一个诗社,为什么要出几期刊物,为什么要搞几次活动,为什么要请诗人走进法大,走进这块从来都是被法学家占领的严肃的土地,很不严肃地谈起诗来。
我们只知道生活是多彩的,生活里应该有诗。
我们只知道青春是宝贵的,青春应该辐射诗的华美。
于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诗社成立了。
不几天,《星尘》第一期印出来了,我们几个人将其从打字社搬到一个教室里,召集社员自己装订,大家干得很起劲。尽管第一期很粗糙,但我们很兴奋。李燕丽、武彦彬等几个女同学一边干着还一边哼起歌子来。
静悄悄的,法大有了一本诗刊,静悄悄的,人们开始知道,在正常生活里,还有一群不正常地写起诗来的人。
《星尘》发往各地,社会也在关注她了。
戴鸭舌帽的刘湛秋匆匆从诗刊社赶来,指点一番,又匆匆离去了。
既有名又无名的海子在一个朦朦胧胧的晚上,朦朦胧胧地讲起朦胧诗来。
诗的原野,向远方展开。湛蓝湛蓝的天空下,新鲜的花朵睁大眼睛。
八四年寒假,我把全部诗稿带回家,在大兴安岭脚下:一间破旧的小木屋里编定了《星尘》第二期,接着国森、王彦又编定了第三期,由于经费紧张,周折了一番,好不容易。
今年夏季,社员的作品不断地见诸于报刊杂志上。王彦的《每天,她匆匆走着》(《诗刊》85·7),苟红艳的《三月》,吴兴科的《大海与老人》(《福建文学》85·7)。此外,志忠、成林、郁红祥、国森等人的作品也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目前,全国各地五十余家诗社杂志同《星尘》保持密切的联系。
诗社的工作得到校党委、校团委的大力支持。
诗社的工作得到《诗刊》《绿风》《诗魂》《晨刊》的大力帮助。
诗社培养了一批人,不仅在写诗上,更多的是在诗外。
今后一段对间,诗社将由成林、志忠、春瑞、王旗等同学继续搞下去,他们的思维活跃且敏锐,相信他们会搞得更好的。
诗社,迎着初生的太阳,走向壮美。”
在那段美好的岁月里,李青松成为海子最信任的诗歌伙伴之一。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诗艺、畅谈诗歌、交换诗作,互相点评、互相探讨、互相鼓励。那时候,海子经常到打印社打印出版自己的油印诗集,不但将自己的新作交给李青松发表,而且还将自己的油印诗集赠送给他,请他批评指正。
然而,由于李青松面临着毕业实习、写毕业论文、毕业分配工作等各种压力,使这种美好的诗歌生活在1986年到来的时候戛然而止。
1986年6月,李青松离开了母校,奔赴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太平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实习。在为期四个月的实习期内,李青松凭借自己的勤奋苦干和聪明才智以及农村孩子的朴实能干,在实习期间独立办理了三个案件,因办案质量较高,他被法院评为“优秀实习生”,并受到了奖励。
当年9月,回到母校之后,李青松便开始撰写毕业论文。
1987年3月,由于即将毕业,李青松提前卸任了中国政法大学诗社社长和《星尘》诗刊主编的职务,将诗社的重任交给了师弟师妹们。
鉴于创社社长李青松为诗社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后来的诗社将他作为排名第一的荣誉社员保留在诗社组织机构里。
从此之后,忙于撰写毕业论文的李青松参加的诗社活动少了,他和海子的联系也少了,但是却始终关注着海子的诗歌创作,并为他发表在《滇池》《草原》《这一代》《诗选刊》《诗林》《诗歌报》《山西文学》等刊物上的作品而高兴。
大学毕业后,李青松成为一家报纸的副刊编辑。
而海子对这位诗歌伙伴也同样惦记在心里。有一天,来自母校法大诗社的师弟刘春瑞来报社看望师兄李青松,从书包里拿出一本海子自费印刷的油印诗集《传说》送给了他,并告诉他,这是海子让他转交给李青松的,请他批评指正。捧着海子转赠的油印诗集,李青松的内心深深地感受到了海子这位诗歌伙伴帶给自己的温暖。
在当了一段时间的副刊编辑之后,李青松又被调任到新闻部当记者。这段时间,他到全国各地采访,和海子的见面越来越少了。
而他和海子见的最后一面,已经是1988年秋天了。“当时,我回学校去昌平校区看望一位老师。我记得,是在去昌平校区的班车上见到了海子。他当时很疲惫,眼神迷离,好像刚从西藏回来。我们坐在最后—排座位。他告诉我,他已不在校刊编辑部当编辑,而到哲学教研室教自然辩证法课了。”
1989年3月26日,对于李青松来说,是一个悲伤痛苦的日子。在这一天,他的诗歌伙伴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了。大约三天后,在母校工作的—个同学告诉了他这个噩耗。李青松闻讯,顿时目瞪口呆,不敢相信海子自杀是真的,却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不幸的消息。
回想起与海子在一起交流诗歌的美好情景,回忆起与海子在一起参加诗歌活动的快乐往事,背诵着海子的音容笑貌,默想着海子的言谈举止,翻看着海子生前赠送给他的两本油印诗集,阅读着海子生前投稿给他的作品手稿,想到从此以后将永远再也见不到这个诗歌伙伴了,李青松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情绪,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流下来……
在那个时刻,李青松深深地意识到:那个昔日的诗歌伙伴和自己永别了,永别了的,还有那个美好的诗歌年代。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一晃儿,30 年过去了。30 年的磨砺,使昔日这對关系特殊的诗歌伙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海子来说,他已经不再是当年李青松眼里的那个“小查”,而已经神话般地成为万众敬仰的天才诗人。而对于李青松来说,他也不再是海子眼里的大学诗社社长和《星尘》诗刊主编了,而是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与奋斗,成了著名作家,成为中国生态文学领军人物,并发表出版了《一种精神》《茶油时代》《粒粒饱满》《万物笔记》《开国林垦部长》《遥远的虎啸》《大地伦理》《薇甘菊》等12部优秀生态文学作品。
而说到从事生态文学的创作经历,李青松谈到了海子当年对他的影响:
“海子对我还是有影响的,海子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他读了大量西方的书,西方的一些思想家、诗人的诗,这一点是我当年看到的。他的案头,包括诗社的活动中,他谈的一些话,看得出来是受到一些诗人、思想家的影响较大。因此,对我起到了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
那么生态文学这块呢,你可以看出我中学、大学时代发表的作品,其实都是写生态的,写乡村,写自然,写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海子本身就来自乡下,我也是来自内蒙古农村,都是从土地,从泥泞中走出来的,这一点我们是共同的。
那年我记得,惠特曼的《草叶集》,海子从西四书店买回来的时候,在床头放了很长时间,我就很注意。因为我看到了,我买了惠特曼的书《草叶集》是受海子的影响。因为惠特曼对自然的理解,独特的感受,这个应该是来自海子对惠特曼的兴趣,后来对我从事生态文学创作是有用的。”
尽管30年间,海子和李青松的身上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是,对于李青松来说,有一种情感却始终依旧,从未改变,那就是对海子这位诗歌伙伴的深深怀念。
经过日积月累,经过朝夕发酵,这种真情实感演化为一篇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发人深省的散文,发表在2018年第10期《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开设的“怀念海子小辑”专栏上。
在这篇题为《怎样握住一颗眼泪》的散文中,李青松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和海子交往四年的点点滴滴,真挚地表达了自己对海子卧轨自杀的伤感痛惜,深刻地反思了海子的死因,理性地阐述了海子的人生,可谓众多有关海子文章中一篇极其优秀的散文作品。
在这篇散文的开头,李青松是这样写的:“我跟海子接触有四年时间,因之诗社与诗。”
而在文章最后,李青松引用了海子的两句诗,令人读后,先是怦然心动,然后,怦然心碎: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2018年10月22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