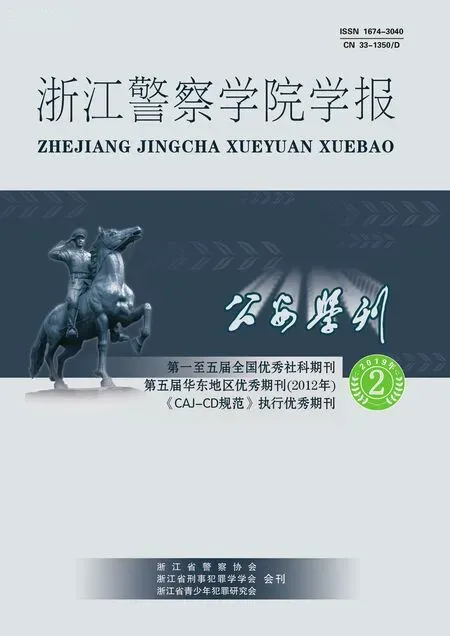循证矫正理念下亲犯罪态度的价值探索
张丽欣
(河北经贸大学,石家庄050061)
新形势下,监狱管理部门提出深化监狱体制改革,要求监管工作从“底线安全观”向“治本安全观”转变,在将服刑人员改造成守法公民上加大监管机制改革的工作力度,提高服刑人员的改造质量。[1]2012年,我国监狱矫正和社区矫正系统正式引入了循证矫正这一新型的矫正方法和理念,这一矫正方法以降低重新犯罪率和减少犯罪为主要目的。[2]根据一般人格和认知社会学习模型,亲犯罪同伴(pro-criminalcompanions)、亲犯罪态度(pro-criminalattitudes)、反社会人格模式(如自我控制能力弱、过早过多的犯罪行为、麻木不仁、敌意情绪和精力过剩等)及犯罪行为史是影响反社会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Andrews和Bonta提出亲犯罪态度是服刑人员矫正过程中风险—需要—对应性模型中“四大”犯因性需要因素①之一。[3]为了降低服刑人员的重新犯罪率,在设计矫正方案的过程中应设置以改变亲犯罪态度为目标的矫正项目②。这一矫正项目的开发需要明确亲犯罪态度的内涵、具体量化方式,并确保矫正项目使用有效,即接受该矫正项目的服刑人员与没有接受该矫正项目的服刑人员相比,前者刑释后重新犯罪率显著低于后者。因此,本文将从亲犯罪态度的概念界定、量化方式和循证路径等基本问题入手进行探讨。
一、亲犯罪态度的界定
(一)亲犯罪态度的内涵
态度(Attitude)是个体对特定社会客体以一定方式做出反应时所持有的稳定的、评价性的内部心理倾向。[4]研究发现,态度在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5]元分析结果表明,在犯罪态度和犯罪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6]许多犯罪理论强调犯罪态度的核心作用,现代控制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大卫·马茨阿在《青少年犯罪与漂移》中提出,青少年做出犯罪行为不是抛弃了正统的伦理价值,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和(neutralize)”了它们,使他们能够实施犯罪行为还可以认为自己是无辜的。[7]根据萨瑟兰的差异交往理论,犯罪行为是与同伴交往习得的,可能是学习犯罪的技巧,也可能是习得特殊的犯罪动机或使犯罪合理化的理由、对待犯罪的态度等。[8]
Andrews和Bonta最初在一般人格和认知社会学习模型中提出,犯罪态度是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四大风险性因素之一,在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心理时刻”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主流的犯罪行为研究中,因为缺乏统一的术语导致对犯罪态度的研究比较混乱,但是犯罪态度一词应广泛包括指向犯罪的态度、价值观、信念和合理化方法等。在后来的研究中,Andrews和Bonta将影响犯罪行为的四大动态风险因素中的犯罪态度具体界定为亲犯罪态度(pro-criminalattitude)并做出了明确的界定,提出亲犯罪态度是一种反社会态度,是对违反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呈赞许性的态度,是通过找理由、找借口甚至强调特殊情况将犯罪行为合理化、正当化的一种心理历程。[9]在心理学理论中,根据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更容易理解亲犯罪态度在犯罪行为中的作用:当个体做出的犯罪行为与个体关于社会规范的认知和信守发生矛盾的时候,通过增加对犯罪行为的认同感可以消除认知失调带来的不良体验。[10]
(二)亲犯罪态度的量化
亲犯罪态度的测量工具有多种,大多数的支持理念可归结为三个类别,即中和技术,个体对犯罪同伴的认同,个体对社会法规的抗拒。从理论角度看,这三个类别在概念层面上是不同的,表明了亲犯罪态度三个不同的心理功能。中和技术是个体做出与社会、道义和法律规范相反的行为时对行为进行正当化、合理化,这样可能会减轻在应该怎么做和实际做出的行为发生不一致时的冲突感,是个体做出犯罪行为的支持性因素。个体对犯罪同伴的认同会强化其对犯罪模式的赞同感和模仿感,会优化个体在犯罪亚文化群体中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个体对社会法规的抗拒包括对法律系统及相关人员如警察、法庭等的反对态度,这种抗拒除了贬低主流的社会价值外,还表现在将与社会对抗的、非传统的、叛逆的、刺激的甚至是“英雄式”的犯罪行为视为荣耀,而这种荣耀感或对消极行为的认同感能够满足个体高自尊的需求,如对自己积极的认同和个体独特性的心理需要。[6]
在当前的亲犯罪态度的测量工具中只有极个别得到了充分的实证性的验证。犯罪情感量表(修订版)(CriminalSentimentsScale-Modified,CSS-M)[11]和犯罪思维调查量表(PsychologicalInventoryofCriminalThinkingStyles,PICTS)是最为常用的测量亲犯罪态度的工具。这两个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较高,前者侧重对态度内容的测量,后者侧重对态度过程的测量。[12]犯罪情感量表(修订版)(CSS-M)是自我评定量表,共41个条目,包括五个分量表:对法律的态度、对法院相关内容的态度、对警察的态度、对犯罪行为的容忍程度、对犯罪同伴的认同度。前三个分量表联合起来组成法律—法庭—警察分量表(LCP),主要测量行为人对法律和刑事司法系统的态度。对犯罪行为的容忍度分量表(TLV)是以合理化概念为基础,反映对犯罪行为的一种特殊的正当化过程。对犯罪同伴的认同分量表(ICO)主要测量个体对于违法犯罪人的个人评价③。犯罪情感量表(修订版)(CSS-M)已在不同的研究对象中试用,包括假释者、监禁犯、青少年犯等,并对量表的效度进行检验,Wormith等发现运用犯罪情感量表能够对首犯为财产犯的年轻犯罪人的重新犯罪行为做出预测,[13]而Simound等发现犯罪情感量表(修订版)(CSS-M)可以预测年龄较大的犯罪人和暴力犯再犯的可能性。[14]犯罪思维风格心理调查量表(PsychologicalInventoryofCriminalThinkingStyles,PICTS)理论基础是生活风格理论,[15]其中有32个条目,主要对八种思维风格进行调查,包括对犯罪行为的合理化、对犯罪行为的放纵、对犯罪行为想当然、崇尚权利、赎罪心理、过分自大、考虑问题简单及自控能力差。[16]犯罪思维风格心理调查量表(PICTS)的信度和效度在多个研究中得到了检验,Walters运用该量表中的八个子量表对遵守监狱纪律与重新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八个分量表对遵守监狱纪律和重新犯罪预测的平均效应值(r)在0.10和0.15之间。[17]Walters还发现,与其他已知的风险因素如年龄、前科、早期事件等相比,犯罪思维风格心理调查量表(PICTS)的总分对重新犯罪的预测力更强。[18]事实证明,犯罪情感量表(修订版)(CSS-M)的适用性更强,其分量表可以反映不同的理论成分。这个量表测量的是态度的内容而不是过程,所测的态度内容更丰富,目前在矫正理论和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二、亲犯罪态度与重新犯罪之间的关系——循证过程与实践
循证矫正,顾名思义就是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矫正,或者说是遵循证据的矫正。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循证医学,并在医学各学科领域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模式。20世纪90年代,美国、加拿大等国为解决重新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现状,切实有效提高矫正效果,开始引入循证的理念和方法,由此形成了全新的循证矫正实践。2012年9月,我国正式提出在监狱、社区矫正机构、戒毒所等开展循证矫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试点工作。循证矫正涉及矫正研究者、矫正工作者、矫正对象和矫正管理者四方主体。其中,矫正研究者提供与矫正相关的最佳理论研究证据,矫正工作者根据最佳理论研究证据进行实践。在整个循证矫正的过程中,核心就是矫正所遵循的证据,即以现有的最佳证据来为矫正实践提供依据。这里所说的证据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它包括经验、理论研究成果、有效的矫正方法等。所谓最佳证据,就是经过精准评估,已经被研究者证明能够明显降低矫正对象的重新犯罪率,与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最为契合的经验、思路和方法等。遵循最佳证据的目的是要揭示问题的症结并提出相应的矫正方案。[19]
当前,诸多理论均在论证亲犯罪态度和犯罪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在矫正实践中,针对矫正对象设置以改变亲犯罪态度为目标的矫正项目前须进行充分、精确的评估,确保所选择的证据是最佳的,即有充分的研究能够表明亲犯罪态度的转变能够显著降低刑释人员的危险性。因此,需要从研究设计和实践操作等方面检验亲犯罪态度能否作为矫正的最佳证据。
(一)亲犯罪态度作为最佳证据的评价路径
仅仅根据理论观点简单地提出亲犯罪态度的转变会自动减少重新犯罪的逻辑似乎不够严谨。根据循证矫正的理念,需要对亲犯罪态度的改变所引起的效果进行实证性评估。这一过程往往涉及三个问题:亲犯罪态度与重新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多强?什么样的干预措施可以有效改变亲犯罪态度?以亲犯罪态度为目标的干预方案在减少重新犯罪上的效果如何?

亲犯罪态度与重新犯罪之间逻辑关系图示
为了回答上述三个问题,需要明确亲犯罪态度、干预与犯罪行为及重新犯罪之间的逻辑关系(见图示)。如果仅能证明犯罪行为和亲犯罪态度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则仍不能区分是亲犯罪态度引起了犯罪行为(路径A),还是犯罪行为导致了亲犯罪态度的形成(路径B)。尽管二者并不相互排斥,亲犯罪态度和犯罪行为也能相互加强和保持,但通过亲犯罪态度的转变是否能够预测未来的犯罪行为才是最为重要的。为了能够证明亲犯罪态度干预方案的有效性,必须明确两个方面:一是干预方案的确改变了亲犯罪态度(如路径D);二是不实施干预方案,这种改变就不会发生(如路径C)。第二个方面至关重要,因为亲犯罪态度也可能通过定罪或拘留而发生变化,或在监禁过程中由于思想逐步成熟而改变。想要证明干预方案的确有效果,必须采取控制相关变量的设计来测试路径D和路径C的排斥性。很多干预项目包含对多个因素的干预,针对犯罪人不同的犯因性需要进行干预。如果仅证明该干预方案改变了亲犯罪态度(与无干预相比),则仍不能充分说明这一用于改变亲犯罪态度的干预项目是有效的。为了能够证明含有特定因素的干预项目能够改变亲犯罪态度,有必要从包含或不包含专门针对亲犯罪态度而设计的模块运行出发,将路径D和路径E进行对比。最后,只有当亲犯罪态度的转变能够减少重新犯罪行为的时候(路径G),亲犯罪态度干预项目才是真正有效的。另外,有的服刑人员可能会假装亲犯罪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期望在干预项目中有好的表现,或者期望获得与监禁有关的好处,如更多的奖励、提前释放或更宽松的监禁环境。重新犯罪行为的减少也有可能归因于其他犯因性需要的改变,而与亲犯罪态度无关(路径E)。要想获得关于亲犯罪态度干预项目是否有效的确凿的实证性证据,必须通过与控制条件(路径C)的比较来证实干预方案的确改变了亲犯罪态度(路径D),并且明确是通过亲犯罪态度转变,而不是其他的犯因性需要的转变(路径E),导致重新犯罪行为的减少。总之,最佳证据的选择存在不同的路径,通过随机对照组实验设计和元分析得到的证据最好、可信度最高,通过质化研究得来的证据次之,凭借个人经验提出的证据可信度最差。
(二)循证实践中的发现
根据上述逻辑关系,笔者对当前发表的以亲犯罪态度为主题的文章进行检索、筛选、剔除,发现目前国内尚没有发表专门针对亲犯罪态度的文献资料,域外的文献资料其研究水平也参差不齐。从域外的研究设计来看,个别研究没有对照组,有的研究使用的控制组缺乏充分的实证证据用以说明干预组和对照组是可以对比的,只有少部分研究采取严格的研究设计。有的研究以一般的亲犯罪态度(Generalpro-criminalattitudes)或与具体犯罪类型相关的亲犯罪态度(Pro-criminalattitudesrelatedtospecificoffencetypes)为干预目标对干预效果进行检验;有的研究以一般的亲犯罪态度或与具体犯罪类型有关的亲犯罪态度为干预目标,将重新犯罪状况作为干预效果的衡量标准;还有极少数研究同时使用亲犯罪态度和重新犯罪情况作为干预效果的衡量标准。大部分的研究其样本量较小,干预组大多是40到100名服刑人员,甚至有的研究在这个范围以下,只有两项研究其样本量大于3000。[20]
研究结果显示,以一般的亲犯罪态度为干预目标的16项研究中有12项研究的前后测验数据变化表明,干预项目的确可以改变亲犯罪态度。[21]以与具体犯罪类型有关的亲犯罪态度为干预目标的研究其结果比较丰富,如Bickley和Beech以对儿童实施性侵的犯罪人为研究对象进行干预研究,结果发现,犯罪目标明确的犯罪人其态度有明显变化,而对于没有明确目标的犯罪人,如那些对儿童实施了性侵但又缺乏明确动机的犯罪人在亲犯罪态度的改变上不明显。[22]以一般的亲犯罪态度或与具体犯罪类型有关的亲犯罪态度为干预目标,将重新犯罪状况作为干预效果的衡量标准的研究发现,亲犯罪态度和重新犯罪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直接的,是否存在相互作用或中介效果仍需进一步证明。亲犯罪态度的转变对重新犯罪产生的影响是我们最想看到的。Berman以372名瑞典籍男性服刑人员为研究对象实施认知矫治项目,项目实施后运用犯罪情感量表(修订版)(CSS-M)对被试的亲犯罪态度转变状况进行测查,发现三个分量表均发生了变化。项目完成者重新被定罪的比例显著低于中途退出者,与控制组相比呈现显著差异。回归分析显示,36个月之后项目完成者与控制组、中途退出者相比表现出更低的重新犯罪率。但是,这项研究没有报告犯罪情感量表(修订版)(CSS-M)的分数变化与重新犯罪之间的关系这一关键性的信息。[23]Beech等人采取实验组和控制组对照设计对413名性犯罪人进行干预研究,运用三个亲犯罪态度量表和三个社会情感量表对项目参与者进行测量,亲犯罪态度变化显著。虽然实验组(9%)的重新被定罪率低于控制组(15%),但这种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24]
综上所述,一般的犯罪态度和与具体犯罪类型有关的亲犯罪态度与重新犯罪呈微弱到中等程度的相关,[6]二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基本是可以确定的;基于认知行为治疗(CBT)的干预项目被认为是当前改变亲犯罪态度最有效的干预模式;[25]以一般的亲犯罪态度或与具体犯罪类型有关的亲犯罪态度为干预目标的认知行为疗法项目似乎可以减少再犯,但仍需充分的实证性数据,即亲犯罪态度的转变和减少重新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模型仍需要大量的深入研究以获得充分的实证材料予以佐证。
三、总结与展望
(一)完善亲犯罪态度作为最佳证据的评价过程
源于循证理念,以改变亲犯罪态度为目标的矫正项目仍需进一步验证该项目与重新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当前所得到的这方面的实证材料还存在许多局限性,如有的研究样本量太小或没有控制组,导致在亲犯罪态度转变和重新犯罪之间的关系程度缺乏足够的统计效力。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应根据亲犯罪态度的概念实质明确和优化亲犯罪态度的干预方案,严格按照上文图示中的设计模型设置控制组,排除可以引发亲犯罪态度改变的其他因素,如监禁本身、时间、心理成熟或需求效应,甚至是自我掩饰或印象管理的成分。一般来说,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验设计④是最为普遍的,但这种实验设计的方法也存在一定的伦理问题,可能剥夺了控制组被试必要的干预内容。因此,可以使用一个更加可行的、不存在道德问题的替代方案,无论是实验组还是控制组均参加一个综合性的评估,而控制组的被试不参加亲犯罪态度的干预模块。关于研究结果的报告应充分针对亲犯罪态度这一犯因性需要的干预效果,明确测定专门针对亲犯罪态度干预项目的影响效果(而不是对其他因素进行干预),以及亲犯罪态度的变化是否影响重新犯罪(而不是其他因素的干预效果)。关于亲犯罪态度与重新犯罪之间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挖掘,为明确二者的因果关系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此外,当前我们所掌握的有限的关于亲犯罪态度的研究成果均是基于国外的研究样本,仍需扩大样本容量和样本性质检验以改变亲犯罪态度为矫正目标的矫正项目的有效性,因为文化差异等客观原因,国外被评价为“最佳证据”的证据,在国内的矫正实践中未必是最佳的证据。
(二)开发以改变亲犯罪态度为目标的矫正项目
循证矫正的过程是由一个个被研究和实践证明了的有效的矫正项目的实施组成的,目前我国在循证矫正实践探索的道路上值得借鉴的、规范的、可操作的矫正项目较少,更没有以改变亲犯罪态度为目标的矫正项目,即一套经过实证研究和实践证明了的、以改变犯罪态度为目标的、有具体操作内容和程序的干预措施或课程体系。[26]经过证据优选程序确定的亲犯罪态度可以作为最佳的证据后,还要充分结合当前我国矫正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矫治对象的心理特点、受教育程度、职业经验及矫正环境等因素设计个性化的矫正项目,量体裁衣制定切合我国文化背景和监狱实情的本土化亲犯罪态度矫正方案。另外,开发循证矫正项目不是对现有的教育改造模式的否认,而是对现有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造模式进行总结、提炼和升华,并予以模块化和规范化,使其更加科学和有效,更适宜大范围的推广和效果评价。
(三)循证矫正专业人员的培养
循证矫正作为一种新的矫正模式,必然给监狱心理矫治人员带来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上的冲击和变革,要求新的能力构成。面对科学属性和专业属性十分明显的循证矫正实践,在诸多现代矫正技术和矫正项目建构中,暴露出当前我国心理矫治领域人才短缺和技能匮乏的现象。当前,监狱系统对于循证矫正有了一定的认知,但认知度和理解度还远不够。同时,来自一线监区的心理矫治民警接受培训的机会较少,加之循证矫正理论与实践自身系统的完整性和严密性。对此,建议司法系统充分联合科研院所、高校专家开发一套专门的适合我国监狱系统矫正人员和基层民警的线上循证培训课程。为确保以改变亲犯罪态度为目标的矫正项目的顺利实施,需要注重几点。首先,应提高心理矫治专业人员对当前亲犯罪态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加强与之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如认知理论和人格理论的学习。其次,掌握以亲犯罪态度转变为目标的循证矫正对象的筛选、矫正技术、矫正效果评价等步骤。可靠且准确地评估矫正对象是科学有效矫正的关键环节,因此,需要开发一个能够准确反映服刑人员亲犯罪态度的有效工具。最后,在以亲犯罪态度转变为目标的矫正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实证的反复检验和理论的深入挖掘,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实现服刑人员亲犯罪态度的转变,进而提升服刑人员的改造质量,降低其再犯的可能性。
注释:
①犯因性需要因素(criminogenicneeds)是指那些和犯罪行为密切相关的,且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干预可以降低重新犯罪可能性的动态风险因素,包括个人的认知、每天交往的同伴、冲动性、自我管理和控制、对犯罪行为的赞许态度、物质滥用的类型或程度。参见张丽欣:《重新犯罪研究未来之路径选择》,《铁道警察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②矫正项目是具有矫正内容、矫正量与矫正程序的矫正模块,是具有结构性的矫正方法。参见翟中东:《矫正的变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第276页。
③LCP:AttitudetowardLaw-Court-Police.TLV:ToleranceforLawViolations.ICO:IdentificationwithCriminalOthers.
④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验设计是指研究者在实验前采用随机分配的方法将被试分为两组,并随机选择一组为实验组,另一组为控制组。实验组接受实验处理,而控制组则不给予实验处理。在实验开始前对两组被试进行前测验O1,O3,得到被试初始状态,在实验处理结束后再次对两组被试进行后测验O2,O4,最后对所得的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