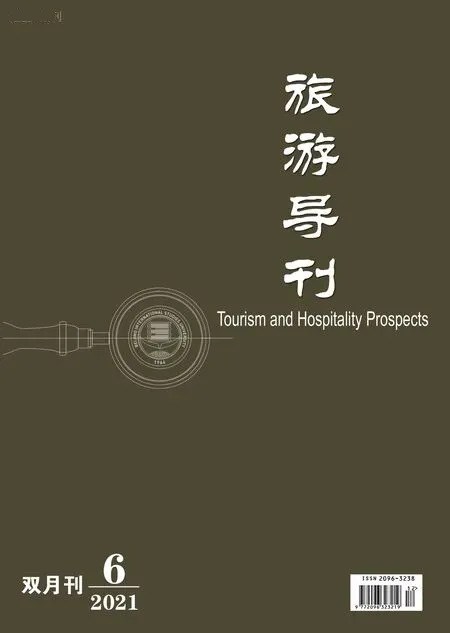从零相关的结果中发现机遇:对工作—家庭冲突来源归因机制的探索
张 勉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 北京 100084)
本文是笔者根据在《旅游导刊》组织的第二届“旅游理论建构”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和修改而成,既保留了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增加了研究背后的经验和感悟。
一、机遇的来源
当研究者对数据进行分析的时候,特别希望预期的变量关系在统计上表现出显著性,以便支持提出的研究假设。如果感兴趣的变量之间是零相关的关系,研究者一般会比较失望,因为零相关的结果似乎等于什么都没有发现,很难支持文章发表。近几年来,笔者与合作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以工作—家庭冲突为主题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围绕着同一个主线,即探索来源归因机制在我国文化情景下的适用性,尤其是哪些个体层面的变量在该机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这一切都是从笔者对零相关结果的思考开始的。
笔者曾经研究员工离职现象多年,但一直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为了寻求新的突破,笔者从2007年开始关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交互的变量,尤其是工作—家庭冲突,即来自工作的需求和来自家庭的需求互不兼容的情况(Greenhaus & Beutell,1985)。在开始阶段,笔者主要是用国外已有的成熟量表测量工作家庭冲突,并研究这种冲突如何影响一些工作领域的变量,如工作满意感、组织承诺、离职意向等。
以往的研究文献指出,工作—家庭冲突有方向性,既包括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如由于工作原因而错过了家庭活动),也包括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如由于家庭原因而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Netemeyer,Boles & McMurrian,1996)。通过阅读文献,笔者发现工作—家庭冲突对结果变量有两种影响机制:一种是Frone、Russell 和Cooper(1992)首先提出的资源耗竭机制(resource depletion),主要用来解释跨领域的影响。例如,对“为什么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会造成家庭领域表现的降低?”这一问题,该机制的核心观点是:由于人们的资源(如时间和精力)有限,因此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会造成人们用于家庭领域的资源不足,进而导致在家庭领域表现不佳。另一种是解释同领域的影响的机制,例如,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会不会造成个体对工作的不满?对同领域影响的研究比较零散(Grandey,Cordeiro & Crouter,2005),没有被正式命名成某种机制。
笔者在2007年下半年,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的管理培训班上收集了一批问卷调查数据,参与问卷的被调查者主要是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在分析数据时,笔者发现,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和个体工作满意感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即零相关。该发现既和以往以美国样本为主的元分析结论不一致,也和当时国内的很多研究发现不一致。已有研究发现,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和工作满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工作对家庭的冲突越强,人们对自己的工作越不满意。零相关结果的发现,激发了笔者的好奇心,促使笔者开始仔细思考其中的原因。
当笔者向参与问卷调查的管理者反馈这个“意外”结果的时候,同时给他们展示了工作对家庭冲突的具体测量项目,例如,“由于工作需要,我不得不改变家庭活动计划”等。有一位管理者当场回应说,这些事情能算冲突吗?现场不少人同意其观点。在这些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看来,为了工作上的事情,错过和家人的一些团聚时间,是很正常的事情,而收入、晋升等因素对工作满意感的影响,比工作—家庭冲突因素的影响大得多。这启发笔者思考:如果这些中高层管理者们并不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测量项目里面提到的行为描述对他们有什么显著影响,那么,虽然这些行为在术语上被称为“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但其实不会导致管理者们对工作有什么负面看法。笔者其时正在MBA 教学中教授《企业文化》课程,对文化的因素很感兴趣,于是在思考及参阅文献(Aryee,Fields & Luk,1999;Yang,Chen & Choi,et al.,2000)的基础上,在文化上不断聚焦,最终对“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这个文化现象有了一些体会。
“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的主要特征为:第一,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庭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个体工作的目的是服务于家庭的整体福利。由于工作可以获得金钱、职位和声誉等资源,有利于家庭的整体福利,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即工作优先行为是外显的,是增加家庭整体福利的一种手段,但并不代表工作比家庭的重要性高。第二,“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需要考虑性别的因素。我国传统儒家文化鼓励“男主外,女主内”,这种观念一直到现在还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和女性相比,男性更有可能表现出“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
二、对来源归因机制的理论发展
为了解释遇到的零相关结果,笔者把“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的思考应用到来源归因机制中,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在同行评议中取得了审稿人的认可。总结起来,笔者团队走过的研究历程可以分为如下3 个阶段。
1.探索期
笔者团队于2012年在解释为什么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会对一些工作领域的结果变量产生影响的时候,对来源归因机制作了总结说明(Zhang,Griffeth & Fried,2012)。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引用了Shockley 和Singla(2011)的观点,即当工作对家庭产生冲突时,由于工作是造成冲突的来源,因此人们会对工作产生不满。笔者在写论文之前就已经想到了这个解释,并写在论文初稿中,但在修改过程中,被评阅人要求引用文献支持此解释,于是找到并引用了Shockley 和Singla(2011)在其文章中使用的“来源归因机制”(source attribution)视角,并一直沿用。
但笔者认为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来源评价机制”(source appraisal)。因为当工作对家庭产生冲突时,尽管工作是造成冲突的来源,测量题项也把这个来源表述得很清楚,但处在冲突中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责备(blame)这个来源,并对这个来源产生不满,是个评价问题,而不是仅把冲突来源归因为是工作领域还是家庭领域的问题。
在来源归因机制的基础上,笔者应用了“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的第一个特征。具体来说,由于工作优先行为是增加家庭整体福利的一种手段,所以我国的管理者们并不认为,当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发生后,需要责备工作领域,因此,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不会降低管理者的组织承诺,也不会增加离职意向。当然,仅仅指出存在零相关的变量关系是不够的。作为和零相关的对比,笔者在文章中基于资源耗竭机制的观点,提出了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对于工作领域变量存在显著影响的假设,并强调资源耗竭机制和来源归因机制不一样,前者和文化背景没有关系,即无论美国管理者还是中国管理者,当家庭对工作形成冲突时,他们用于工作的资源都会减少,进而影响其工作中的表现。
2013年,笔者团队撰写了一篇概念化的理论文章,把关于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想法进行了较完整的阐述(Zhang,Li & Foley,2014)。在文章中,笔者提出一个观点:越是持有“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观念的人,其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与工作领域结果变量之间越有可能是零相关关系。在完成此文章后,笔者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人们对“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接受程度是不同的,我国的中高层管理者倾向于接受“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的观念,但其他群体则不一定。那么,如何具体地测量“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并在个体层面上把各群体区别开呢?直接测量“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难度较大,可行的方法是找到一些所谓的代理(proxy)变量,例如工作和家庭界面是融合还是分割的偏好、家庭责任感、性别角色态度、家庭集体主义导向等。
2.发展期
在这一阶段,笔者尝试引入更具体的调节变量,并选择先从性别因素切入研究。笔者曾认为男性比女性更认可“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的观念,但是,通过反复尝试,笔者并没有发现作为男女两分变量的性别起到稳定的调节作用。同期,笔者接触到性别角色态度(gender role attitudes)概念(Korabik,McElwain & Chappell,2008)。这个概念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男性和女性在性别角色观上,不仅有性别间的差异,性别内的差异也可能很大。例如,有的女性可能符合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形象,但有的女性是不让须眉的“女汉子”。简而言之,即使同样都是男性,或者同样都是女性,对“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性别观念的接受度的差异也可能很大。
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笔者尝试从性别内差异的角度切入,发表了以中高层管理者为样本,检验基于资源耗竭机制和来源归因机制预期的变量关系的文章(Zhao,Zhang & Foley,2019)。在检验基于来源归因机制的变量关系时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我们预期,持有非传统性别导向的男性相对于持有传统性别导向的男性,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与自我感知的工作成就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后来我们发现,不但预期的这项假设得到了支持,而且对于持有传统性别导向的男性来说,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和工作成就感之间有边际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越是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男性,当工作对家庭产生被术语所命名的“冲突”时,他们甚至有更多的工作成就感。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冲突”行为是他们工作投入程度高的一种表现。
笔者团队接着探索了新的调节变量在来源归因机制中的作用,聚焦在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策略,以及性别间和性别内的差异上(Zhao,Zhang & Kraimer,et al.,2019)。我们预期,采用把工作和家庭分割策略的管理者,由于他们原本的意图是尽量不让工作侵入家庭,但当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仍然发生的时候,根据来源归因机制,他们将对工作产生显著的不满。相比之下,采用把工作和家庭融合策略的管理者,他们原本就并不在意工作侵入家庭,因此当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发生的时候,他们对工作不会产生显著的不满。性别间和性别内的差异因素起到了三重甚至四重交互作用,虽然加入性别因素后的交互作用看起来复杂,但核心仍然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
笔者原本在文章中只使用了横截面的数据,但为回答文章评阅人提出的因果关系的问题,以及指出来源归因机制的中介过程不清楚及缺乏具体证据的问题,笔者想到了情景实验的方法。我们设计了工作—家庭冲突的高、低两种情景,并选择对家庭身份的威胁性(threat to family identity)作为反映来源归因机制的具体中介变量。我们成功地把随机分开的两组被试进行了处于高、低两种情景的操控,同时发现,对家庭身份的威胁性的确在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和工作满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尽管这个实验是把被试放在一个假想的情景当中,但和过去只是使用横截面数据的研究相比,有了显著的进步。
3.提升期
前面两个阶段的成功,激发笔者进一步研究更复杂的模型,探索来源归因机制的中介和调节过程。Karen Korabik 教授指导其博士生于2008年提出了工作—家庭内疚(work-family guilt)概念,并细分成由于工作冲突家庭导致的内疚和由于家庭冲突工作导致的内疚(McElwain,2008)。笔者认为这个概念能够反映来源归因机制强调的中介过程,具体来说,当工作对家庭产生冲突时,人们感到对家人有内疚,因此对工作会产生不满,即内疚在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和工作满意感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Zhang,Zhao & Korabik,2019)。同时,沿着从“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研究中形成的思路,笔者提出了两个调节变量,即工作—家庭管理策略的偏好和家庭集体主义导向,其中工作—家庭管理策略的偏好调节整个模型前半段的关系,家庭集体主义导向调节后半段的关系。笔者发现,对于那些希望把工作和家庭分开的人,当工作对家庭的冲突真的发生时,他们会有更多的内疚感;相反,希望把两者融合的人,当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发生时,他们的内疚感会相对少一些。家庭集体主义导向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把家庭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笔者研究发现,越是有家庭集体主义导向的人,内疚感和工作满意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烈。
针对横截面数据存在因果关系不能检验的问题,在这项研究中,笔者团队再一次采用了情景实验方法。针对内疚感的中介效应做的两次情景实验中(由于实验内容相同,所以发表的文章中只报告了一次),实验结果均一致表明了工作对家庭冲突和内疚感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且内疚感在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和工作满意感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三、研究心得
回顾研究历程,笔者总结出4 点经验,希望对读者们有所启发。
第一,不要放弃意外的结果,意外可能孕育着机遇。笔者就是在对零相关这个意外结果进行刨根问底的探索过程中,走出了一条新路。笔者在工作—家庭研究方面的产出投入比是笔者曾有的众多研究方向中最高的,写作和修改文章都很顺利。原因可能在于支撑文章的核心观点是笔者自己琢磨出来的,而且确实存在新意,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当然,遇到意外结果也不容易。笔者之后在研究中也遇到过一些“意外”的结果,但因为统计方法或样本数据的问题,结果均很不稳健。本文所提到的“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这种观念不是人人都有,但笔者在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样本中,反复地发现这个观念起到作用。由于对这种稳健的“意外”有了信心,所以笔者愿意花时间去琢磨为什么是零相关关系,以及思考各种在零相关关系中可能起作用的调节变量。
第二,新想法要和已有的理论结合,做到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关于这一点,笔者结合自己对本土化理论的看法,谈谈自己的观点。在本文讲到的例子中,新的想法是“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相关文章在编辑的建议下,还加上了“一个中国本土观点”的副标题(Zhang,Li & Foley,2014)。但是,光有这个想法还不够。由于中西方哲学取向从根本上存在不同,直接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来论证本土化理论,存在较大难度。如“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这个观点,直接地、完整地测量其内容就存在极大难度,缺乏较好的办法。因此,笔者在写文章时,并没有从开始就用“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这样的本土化观点作为理论基础,而是采用了中西方都认可的最基础的理论,即来源归因机制,并将研究重点放在“这个机制起作用是有条件的、有边界的”上面。由于有些人具有“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所以这些人不会对冲突的来源有强烈的负面评价。如果笔者没有选取来源归因机制作为文章的理论基础,只强调我国某种文化的特殊性,即“为了家庭的工作优先行为”,作为提出研究假设需要的逻辑基础是不够的。笔者认为,特殊性无法单独存在,特殊性需要普遍性来作为基底;对本土化理论和研究感兴趣的同行们,如果把“性相近,习相远”作为深层指导原则,也许有更多的机会把有趣的发现发表到国际期刊上。
第三,数据质量很重要。获取数据不难,获取高质量的数据很难。如果研究者对数据没有充足的信心,遇到和理论不一致的发现,就会怀疑是否需要重新收集数据。能让笔者锲而不舍地思考零相关结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获得数据的质量有充足的信心。由于被调查者在填写问卷前,和笔者有充分的交流,而且议题不那么敏感,所以他们愿意提供真实的想法。虽然是横截面数据,但因为质量高,又能不断重复自己的发现,所以笔者对报告出来的结果心里很踏实。然后,在保证数据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用更严谨的方法,如笔者用情景实验方法弥补横截面数据的短板,就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信性。
第四,重视与实践者的交流和反馈。笔者的教学对象大部分是中高层管理人员,实践经验丰富,不盲从教师的观点。笔者经常能从与他们的交流中获益,如果没有这些管理人员对研究结果的反馈,也许笔者就错过了对零相关结果的深入思考。笔者认为,作为大学教师的第一身份是教学向导,引导和帮助学生发现知识的美好,第二身份才是研究者,研究是为教学服务的,教师应该关心研究的成果帮助学生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或者在思想上有什么重要的启发或升华。尤其是在组织和管理领域,研究更不能脱离实践。
结语
笔者团队已经做过的实证研究中,样本来自各行各业,对于情景化的因素还不够聚焦。如果能在旅游服务行业结合具体的情景,把握住关键的因素,笔者预期能做出更多有趣的研究,甚至发展出新的理论。例如,旅游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由于整天和人打交道,是不是更容易把在工作中获得的技能和行为,迁移到家庭生活中?尤其是旅游服务行业的女性管理者,她们的性别角色导向会比其他行业的女性管理者更传统吗?她们如何管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的类似问题还有很多。笔者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激发出更多、更好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