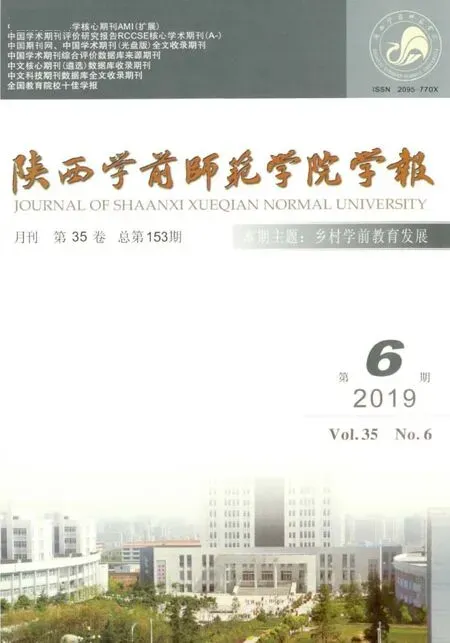概念隐喻视角下英汉情感隐喻比较研究
陈抒婷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福建福州 350007)
概念隐喻最先由认知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提出,并在其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The Metaphors We Live By)中进行详细描述。他们认为,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其本质上是“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的方式”[1]。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不仅存在语言中,在思想和行动中也存在,即“通常有关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本质上是隐喻性质的”[2]。英国修辞学家Richards也指出,语言和思想实际上是隐喻性的[3],概念隐喻是隐藏在日常语言中的隐喻系统,并构成我们日常的概念系统,包括最抽象的概念。
一、概念隐喻内涵
“隐喻的核心是思想,而不是语言,隐喻是传统的概念化世界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的日常行为反映了我们对隐喻理解的经验”[4]。许多重要的概念要么是抽象的,要么在我们的经验中没有明确的描述,比如情感、想法、时间等。通过隐喻,可以用更清晰的表达来描述抽象化的概念。例如:
You are wasting my time.你正在浪费我的时间。
How do you spend your time?你怎样度过业余时间?
The flat tire cost me an hour.这个瘪了的轮胎花了我一个小时。
Is that worth your while?它值得你花时间吗?
以上关于时间的隐喻正是基于“Time is money”(时间是金钱)的概念。如果说,概念隐喻是“太阳”,包含在不同隐喻中的词汇则是从“太阳”辐射出来的“射线”。很明显,许多用于描述“金钱”的词汇被用来描述“时间”,如waste (浪费)、spend(花费)、cost(成本)、worth(价值)等。正如Lakoff所提及,所有涉及时间的概念都是由“Time is money”这一隐喻来支配的。显然,在语言的表象下,存在着指引着人类隐喻地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而隐喻影响着人类概念系统的形成和对世界的认知。
此外,在概念隐喻理论中,源域和目标域是两个主要的概念域。这两个域的元素之间有一组系统的对应关系,即映射。换言之,概念隐喻构成一个复杂的系统,并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跨域映射。概念隐喻本身的系统性是由隐喻蕴涵构成的,并系统地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层次结构。以Lakoff提出的Life is a journey.(生命是一场旅行)为例见表1。

表1 从journey到life的映射
层次一:Life is a journey.
层次二:Love is a journey; A career is a journey.
在此例中,层次二是更高层次的映射,是层次一更具体的体现,包含了两个隐喻,即Love is a journey.(爱是一段旅程);A career is a journey.(事业是一段旅程)。
爱是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 Love is a journey.(爱是一场旅行)隐喻中,包含Life is a journey.(人生是一场旅行)这一结构。正如表1所示,journey到life的跨越映射体现为,情侣(lovers)就像旅行者(travelers),而爱情关系(relationship)是交通工具(vehicles),而其余的映射则是Life is a journey.这一隐喻的结果。同理,事业(career)也是人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因此,A career is a journey.也包含Life is a journey.这一隐喻结构。总之,人生(life)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目的地(destination),并且,人在旅途,难免会遇到十字路口、障碍(obstacles)等。
可见,在概念隐喻的层次结构中,“较低”层次映射了“更高”的层次。概念隐喻通常以更抽象、更模糊的概念为目标,以更具体的概念为源头;其次,映射是单向的,从源域到目标域。但隐喻映射是局部的,源域的每一个元素并非都可以映射到目标域的每个元素上。第三,隐喻映射不是随意的,而是基于身体、生活体验以及语言。
二、英汉语情感概念隐喻的异同点
情感在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由于认知和情感的互相影响,对情感的研究构成了探究人类认知的关键部分。根据认知语义学,描述情感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可以作为探索情感概念的重要工具。情感在本质上是抽象的、模糊的,为了生动、清晰地进行描述,人类通过以身体体验为基础的隐喻来概念化表达。由于隐喻思维具有普遍性,本文将在跨语言和跨文化的基础上,对英汉语中“喜、怒、哀、惧”情感隐喻进行对比研究。
(一)“喜悦”的概念隐喻
认知语言学家Kovecses认为,关于喜悦的隐喻大多与up(向上)的方向有关[5]。因为“up”一词通常对情绪和身体状态都有积极的评价,所以“Happiness is up”(喜悦是向上的)这一概念在英汉语中都是适用的。例如:
I’m in high spirits./My spirits rose./ I’m feeling up.我情绪高涨。
Cheer up!加油!
汉语中则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自己的计划”“他正在兴头上”。
众所周知,当个体感到高兴时,面容和眼神会变得更明亮,这源于其愉悦的内在能量。在英汉语中,常用光或亮度来描述“喜悦”。例如:
Her eyes gleamed with relief and joy.她双目露出喜悦的光芒。
The two women chatted,both aglow with happiness.两个女人兴高采烈地聊着。
汉语中则有“满面红光”“容光焕发”。
可见,概念隐喻“Happiness is light”(喜悦是明亮的)是以上表达的基础。
此外,英汉语在“Happiness is a fluid in a container”(心中充满喜悦)这一隐喻中也有相似之处,它将幸福、快乐的情感映射到“fluid in a container”(容器中的液体)。例如:
His heart is overflowing with happiness.喜悦之情流入他的心里。
He couldn’t contain her joy and excitement.他内心有股按捺不住的喜悦和激动。
We are filled with joy.我们充满了喜悦。
尽管英汉语在表达“喜悦”的概念中有共同的隐喻,但也有各自独特的表达。例如,在英语中,可以用概念隐喻“Being happy is being off the ground”(离开地面)来表达“喜悦”,例如:
We were in the clouds.
I’m flying high.
I was just soaring with happiness.
而汉语中,“being off the ground”(离开地面)意味着骄傲和自满,中国人把谦虚视为美德,才有了诸如“高高在上”“飘飘然”“脚踏实地”等说法。显然,用“Being happy is being off the ground”(离开地面)来表示“喜悦”在汉语里是不适用的。
(二)“悲伤”的概念隐喻
“悲伤”是与“喜悦”相反的情绪,但二者有着相同的源域,即“方向”。也就是说,“悲伤”是“向下”的(“Sadness is down”)。因为直立向上的姿势带有积极的情绪,反之,垂直向下的姿态通常用于描述负面情绪。例如:
Don’t let your spirits droop.不要让你的情绪低落。
Thinking of him makes me down.想到他就让我失望。
I have been in very low spirits.我一直情绪低落。
汉语中则有“垂头丧气”“心情沉重”等。
此外,在英汉语中“悲伤”的概念隐喻大多是“Sadness is dark”(悲伤是暗淡的),这与“Happiness is light”(喜悦是明亮的)恰恰相反。例如:
The future looks dismal.前途黯淡。
She is in a dark mood.她情绪不好。
She was engulfed in a deep depression.她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
汉语中则有“心情灰暗”、“黯然神伤”等。
英汉语都将悲伤的情绪映射到“fluid in a container”(容器中的液体)中,即“Sadness is a fluid in a container”(心中充满悲伤),例如:
His heart is full of sorrow.他的心中充满悲伤。
She is immersed in deep sorrow.她沉浸在悲伤中。
汉语则有“沉浸在悲痛中”、“悲伤涌上心头”“他心中充满着痛苦和悲伤”等。
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两种语言关于“悲伤”的隐喻也存在“各有千秋”的差异。英语常用“blue”表示伤感。例如:
She has been in the blues these days.
Tom is in a blue mood.
Don’t look so blue,smile.
然而,这种概念隐喻在汉语中并不存在,这也许是因为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心理。正如Kovecses所提出,每一种语言中都存在着隐喻表达系统,它涉及心理、生理或行为反应对情绪的影响。汉语中,情绪可以反映在身体上,许多表达悲伤的隐喻与面部表情、眼睛、眉毛,以及内脏器官的反应有关,例如“伤心”“愁眉苦脸”“愁眉紧锁”“肝肠寸断”等。
(三)“愤怒”的概念隐喻
根据认知心理学,“愤怒”是由于欲望无法满足或实现欲望的行为被阻止而产生的情感体验。英汉语常使用相应的生理反应来表达愤怒的情绪,从而产生了大量相似的概念隐喻,例如:
His face was red with anger.
He gets red-hot with anger.
He turned scarlet with rage.
汉语则有:“气得脸红耳赤”“气得两肺直炸”“气得头昏眼花”。
在英语中,Lakoff和Kovecses也曾提出生理效应的“文化模式”,其中强调“Anger is heat”(愤怒是热量)的部分,为更广泛的“愤怒”隐喻表达提供了基础。“heat”(热量)的概念可以分别映射到液体和固体上。当它被映射到固体时,形成了这样的隐喻:“Anger is fire”(愤怒是火),它与汉语的“火”是完全一样的。例如:
Our apology just added fuel to the fire.火上浇油。
A flame of anger lighted in her heart.怒火中烧”。
汉语则有:“火冒三丈”、“大动肝火”、“满腔怒火”等。
当“heat”被映射到液体时,英汉语的隐喻诠释是不同的。英语强调“Anger is the hot fluid in the container”(愤怒是容器中的热液体),例如:
It still makes my blood boil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it.每当我想到它,就让我怒发冲冠。
I had reached the boiling point.我已经火冒三丈了。
在英语语言文化中,普遍认为“水”是万物之源,于是,把“愤怒”的概念映射到“容器里的热液体”。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物质来源,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则意味着生命能量。因此汉语中相应的概念是Anger is Qi/Gas.(愤怒是气)此外,“气”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术语。基于以上因素,中国人除了用“火”之外,常用“气”来表达愤怒,如“耍脾气”“生闷气”“肝气郁结”“气势汹汹”等。
(四)“恐惧”的概念隐喻
“恐惧”是个体试图摆脱和逃离某些危险情境时产生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是由于处理可怕情况的无能而造成的[6]348。恐惧来源于危险的出现,人类将其视为敌人并试图躲避。因而,英汉语对于“恐惧”都带有敌对的情绪,例如:
Only when people overcome their fears do they live confidently.只有战胜了恐惧后,才会获得生活的自信!
Fear slowly crept upon him.恐惧慢慢向他袭来。
汉语中则有“他被无名的恐惧死死揪住”“战胜内心的恐惧”。
此外,英汉语均认为“Fear is disease,fear is insanity”(恐惧是病,恐惧是疯狂),例如:
He was tormented by fear.他被恐惧折磨着。
He was insane with fear.他因恐惧而精神失常。
汉语则有“他被吓出了病”、“他受了惊吓,变得神志不清”。
英汉语中,“恐惧”的概念隐喻因传统文化、地理环境、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也存在一些差别。例如,汉语里常用与“丧失灵魂”或“胆量”有关的隐喻来表达“恐惧”,如“吓得魂飞魄散”、“敌人吓得亡魂丧胆”“他被吓破了胆”等。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相信灵魂的存在,认为死后会变成鬼魂,当一个人处于极度恐怖时,灵魂将从身体出窍。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从而产生了大量与灵魂有关的隐喻以表达恐惧[7]162,177。此外,根据中医理论,勇敢和胆怯与胆量有关[8]。这就是在上述例子中,用“胆量”来概念化恐惧和勇气的原因。而对于英语国家的人而言,他们大多是希望在死后上天堂的基督徒,地狱被视为一个可怕的地方,在那里将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因此,英语中用地狱来表达恐惧的感觉。例如:
Kid with a mask scares the hell out of a cop.带面具的孩子把警察吓坏了。
It emits a hellish shriek.它发出地狱般的尖叫声。
综上,在英汉情感概念隐喻对比研究中,表达“喜”、“怒”、“哀”三种情感时,通常将人体看成容器,而情感则是容器里的承载物。因而产生了“An emotion is a substance in a container.”的隐喻,即用容器中的某种物质来概念化情感表达。此外,多数情感都会引起一连串身体行为和心理变化,所以英汉语都擅长用相应的身体行为和心理变化来表达抽象的概念,遵循的隐喻原则是:“The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an emotion stand for the emotion”(用情感的生理反应代表情感)。然而,情感的表达并非总是基于身体体验,更多的是基于不同的传统文化、哲学理念和地理位置等方面,从而呈现出情感隐喻的文化差异性和独特性。
三、跨文化交际中的隐喻理解——英汉情感隐喻的相似性原因
从“喜、怒、哀、惧”四种基本情感的隐喻生成机制中,不难发现,英汉语情感概念隐喻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相似性。当两种不同的语言被不同的种族的人使用时,之所以能有显著的相似之处,可以归因于人类的某些普遍特性。
(一)共同的身体体验
人类的概念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它将更抽象的领域映射到更具体的领域。而隐喻的映射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植于人类的基本体验。人类有共同的身体和生活体验,所以存在认知和语言共性。由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诸多因素是相同的,在许多情况下,产生了相似的生理和行为反应。例如,生气的时候,体温就会上升,因此,热量(heat)的隐喻在英汉语中都存在。当感到恐惧或突然看到可怕的事物时,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尖叫,如“She came near screaming with fear”(她惊恐地尖叫着),汉语中则有“她吓得尖叫起来”等。因此,属于不同语系的两种语言之所以有很多相似的概念隐喻,是因为与世界互动的共同身体体验决定了理解事物的共同方式。
(二)相似的心理和认知基础
人类通过经验,通过与环境以及彼此之间的不断互动来理解世界。Lakoff 和Johnson认为,没有经验基础,就无法理解或描述隐喻。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有着同样的生理结构,当接触到同样的自然环境时,会产生同样的身体体验,这基于相同的心理和认知基础。在晴朗的天气里,心情愉快,感觉舒适;在恶劣的天气里,感觉不适或沮丧。因此,人们常说“She has a sunny smile on the face.”(她脸上有灿烂的笑容) “His face clouded over when he heard the news.”(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的脸变得阴沉。)太阳象征光明和温暖,给人们带来好心情;相反,云,尤其是乌云,遮蔽太阳,阻挡阳光,常常预示着风雨来临,因此难免带来沮丧、低落的情绪。这些自然现象对人类情绪的影响是共通的。
可见,在自然世界中,英汉情感隐喻中存在的共性主要源自相似的生理体验和共同的心理认知系统。
四、跨文化交际中的隐喻理解——英汉情感隐喻的差异性原因
情感概念隐喻不仅与人类共有的身体体验相关联,同时也受到特定社会中形成的文化体验的影响。由于身体体验仅仅是体验世界的一个起点,因此,探索社会和文化背景对于弄清情感隐喻表达的确切含义是必不可少的。在NoamiQuinn看来,文化模式在人类理解世界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并限制了隐喻的选择。不同文化根源导致概念隐喻的迥异[9]。
(一)不同的地理位置
虽然人类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地球有着丰富多样的地理特征。不同的民族可能处于在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Kovecse曾声称:“自然和物理环境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塑造了一种语言,主要是词汇;因此,它也将塑造隐喻。”在他看来,生活在特定自然环境中的人会熟悉该环境的现象和特征。同时,也会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特有的隐喻概念。因此,生活环境的差异,尤其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英汉语中情感隐喻表达的差异性。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南沿海,主要由大片的陆地组成,而英国位于欧洲的西北部,实际上是由一些小岛组成,被几个内海分开。所以,在英语中有许多与海洋或水有关的隐喻。例如:spend money like water(花钱如流水)、in deep water(遇到麻烦或困难)。此外,由于渔业高度发达,也衍生出与鱼类有关的隐喻。例如,big fish指的是非常重要和有影响力的人;cold fish指不友好、缺乏感情的人。同时,作为鱼类重要的呼吸器官,gill(鳃)在很多情感隐喻中都有出现,例如“white in (or about)the gills”表示极大的恐惧;“blue about the gills”表示沮丧和悲伤;“turnred in the gills”的意思是愤怒。这样的情感隐喻表达只存在于英语中。
(二)不同的文化价值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智慧和经验的沉淀。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影响着各个层次的语言发展。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在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语言又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塑造。语言和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隐喻是人类语言中无处不在的现象,也深受民族文化背景的影响。
汉语中,常用“心花怒放”表示高兴,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在中国,盛开的花朵,尤其是大红花,被认为是幸福和繁荣的象征。与此同时,中国人相对沉默内向,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感情,对愉悦情绪的反应往往深埋在心底,从而产生“心花怒放”这一隐喻。相反,西方人更直率、更外向,所以他们倾向于外在上表现出快乐的情绪,正如概念隐喻Happiness is being off the ground.中呈现的一样。对他们来说,“being off the ground”意味着可以像鸟儿一样拥有自由。大多数西方人崇尚自由和独立,“拥有自由”意味着拥有幸福和快乐。但这一隐喻在汉语中显然并不适用。对中国人来说,“being off the ground”意味着傲慢和自满。在中国文化中,谦虚是美德,年轻人经常被告诫,要“脚踏实地”、“得意不能忘形”。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影响人们表达情感和情绪的方式。
(三)不同的哲学观和医学观
概念隐喻不仅是语言文化的一部分,同时还反映出语言的文化特征。西方人相信宇宙是由四种基本元素组成:火、空气、土壤和水,并形成了“四体液学说”即人体内有四种主要的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不同体液混合比例决定了不同的气质类型。所以英语喜欢用液体(fluid)隐喻表达感情。在英语中,“愤怒”被描述成容器中的热液体(hot fluid)。然而,在Anger is heat.(愤怒是热)的核心概念隐喻中,汉语倾向用“气”隐喻。此外,汉语通常用内脏器官来表达在特定情绪状态下,生理反应发生的确切位置,如用“胆”中来概念化“恐惧”。这两种隐喻现象可以用中国哲学和医学的相关理论来解释。
首先,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阴阳两种力量结合而成的,从而产生了阴阳理论。实际上,“阴”和“阳”是用来描述自然界中明显对立或相反的力量是如何相互补充、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以及当它们相互关联时是如何产生相互作用的。许多有形的二元对立,如明与暗、火与水、男与女,都被认为是阴阳对立的物理表现。根据阴阳理论,火和气(gas)属于“阳”的范畴,水和其他液体属于“阴”的范畴。前者与热量(heat)相关,后者与冷(cold)密切相关。由于这种差异,在概念隐喻Anger is heat.中,汉语选择火(fire)和气(gas),而非英语中的火(fire)和液体(fluid)。
其次,气(gas)也是中医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中医认为,所谓气,是“能动的、看不见的、有营养的物质,是内脏器官运动的动力”,气的培养和运用是身体健康的基础。如果气在体内保持良好的循环,人体将处于健康状态;如果气在某处受阻或被阻塞,则会影响血液循环,而发生局部疼痛,甚至在相关部位也会发生疾病。气循环障碍的原因可能不同,但负面情绪,尤其是愤怒,是最主要的因素。这恰好解释了“气”是“愤怒”的概念隐喻之一的原因。
此外,汉语之所以喜欢用内脏器官来表达情感,是因为内脏器官的选择与特定的情感相关。根据中医五行学说,宇宙由五种基本元素组成——金、木、水、火、土,它们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实现了宇宙的平衡。“五行”理论在中医学中定义了自然和人体,以及它们之间的潜在关系。金、木、水、火、土五元素分别对应的脏器是:肺、肝、肾、心、脾。这五个脏器也分别支配五种情绪,即:肺主悲伤,肝主愤怒,肾主恐惧,心主欢乐,脾主焦虑。因此有“大动肝火”“吓得屁滚尿流”“撕心裂肺”等说法。显然,五行理论对汉语情感隐喻的用法有很大的影响。
总之,情感体验在认知上是普遍的,在文化上是特定的,所以在相同的生物和认知基础上有许多共同的情感隐喻。但生活环境、文化价值观、哲学观和医学观的差异也导致了不同的认知情感隐喻的体现。
五、提升跨文化隐喻理解的途径
(一)培养跨文化差异的意识
Hanvey R .把跨文化意识分为四个层次[10],即对表面文化特质的意识;对重要和微妙的文化特质差异的意识(认知上不可信的,如文化冲突);对重要和微妙的文化特质差异的意识(认知上可信的,如智力分析);以局内人的角度的感受另一种文化,即同理心。文化意识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文化信息的持续输入:地理信息、社会学数据、历史人物和事件、社会习俗、世界观、生活方式等。跨文化信息需要不断地重复输入,使之内化成为英语学习者知识的一部分。
(二)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文化差异不仅指的是外在的差异,如语言、服饰、食物等,还包含文化深层结构中存在的无形差异,如价值、理念和交际原则等。如果学习者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就会更容易捕捉到深层结构的文化差异性和目标文化的特点。通过情感隐喻的研究,可以了解隐喻概念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内涵,从而理解该文化的内在认知机制,掌握目标文化和自身文化的特点和差异。
综上,由于人类情感和身体体验的共性,以及文化差异性,导致了英汉情感隐喻的诸多异同点,这也正是跨文化交际的基础。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意识和敏感性,是促进两种语言相互理解,提高学习者跨文化意识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