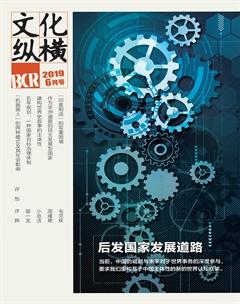新媒介,新政治?
左灿



[关键词]英国脱欧 新媒介 数据隐私
自2016年6月23日的脱欧公投之后,或者说自2015年卡梅伦(David Cameron)政府决定脱欧公投之后,英国似乎就陷入了脱欧的泥沼之中。如今,英国的脱欧大戏继续上演,特瑞莎·梅(Theresa May)政府的脱欧协议被否决,二次公投被否决,无协议脱欧也被否决。原定于2019年3月29日的脱欧未能达成,2019年10月31日成为新的脱欧期限。但未来怎么脱欧,何去何从,仍是一团乱麻。
在如何应对脱欧的困局中,何以脱欧反倒似乎越来越不辩自明。极端右翼势力的崛起,民粹主义的流行,都成为理解脱欧的核心词汇。尤其是各类数据的支持,更让脱欧的选择表现为某种群氓式的无知:公投数据显示,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高的人群更倾向留欧,反之则倾向脱欧;[1]谷歌搜索显示,脱欧公投结果出来之后,以“什么是欧盟”为关键词的搜索激增。那么,在整个公投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场公投所暴露的是新的政治危机,还是已有政治症结的延续?公众的情绪如何被激发为政治行动?这些问题都值得细究。本文将从脱欧公投中双方阵营的政治策略入手,分析脱欧政治所联结的英国的历史与当下,并试图探讨新媒介的力量如何介入政治,以及新的政治能否由此诞生。
新危机还是旧症结?
公投结束后,留欧团队的主管克雷格·奥利弗(Craig Oliver)回顾整个历程,对留欧阵营的失败做出了反思。[2]一方面,脱欧阵营“拿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的口号、对土耳其移民涌入和欧盟费用的大肆渲染,尤其是那句“著名”的宣传语:“脱欧后,每周就会有额外的3.5亿英镑投入到国民医疗系统(NHS)中”,煽动了大量公众。而另一方面,对于脱欧阵营提出的移民问题,奥利弗承认留欧团队一直没有做出有效的回应。卡梅伦政府收紧移民福利的政策没有得到预想的支持,反倒因没有对移民进一步收紧被视为对欧盟的让步。留欧团队将拉票重点放在理性的经济分析,以为可以抵消移民问题,只是没想到,自90年代就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拉票宣言“经济是关键,蠢货”这一次失效了。
更出乎奥利弗意料的是,很多自1980年代就没有参加过任何投票的人竟然大规模参加了投票。参加2016年公投的人口比例达72.2%,比2015年的大选多了6个百分点,约280万人,而这些新增选民压倒性地投向了脱欧。这些人把多年来担心、焦虑、愤怒的所有问题:移民的冲击、对政策的失望、生活止步不前的无望、被忽略被背叛的情绪,都投注到公投的一张选票上。[3]《衛报》的采访也指向了这些不满的情绪。选择脱欧的被访者们控诉,银行家们为所欲为,而工人阶级早已遭到背叛,贫穷成为一种罪恶,政府毫不理解也不关心普通人的诉求。他们被忽略了太久,他们希望政客们担起责任,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4]
对移民的排斥也好,被背叛的情绪也好,它们是新的危机吗?事实上,如果将历史推回到1970年代,这些问题其实早已上演过一轮。参照如斯图亚尔·霍尔(Stuart Hall)等人的研究,[5]二战后由工党建立的福利国家体系本就是个折衷的方式。福利体系的基础是私有资本的增长,实行伊始,私有资本和社会集体利益就相互拉扯。经济稳定时,双方尚能一切太平,而一旦经济下滑,共识就有破裂之势。英国战后的经济繁荣与整个西方世界的战后复苏有关,但英国工业基础老化,技术革新缓慢,又有长期的帝国主义遗产,经济形势并不有利。1960年代,英国经济就开始下滑,至1970年代全球经济动荡,加上油价危机,英国经济更是大幅下滑,工业和经济的结构性弱点浮现,衰退难以阻挡。1970年代初,保守党希思(Edward Heath)政府实行经济紧缩,削减社会福利,遭到工人阶级的强烈不满和联合抵抗。1974年,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带领的工党政府上台,被寄予厚望。但工党奉行的是费边改良主义,其社会政策具有浓烈的小资产阶级特点,经济上受制于私有资本,政治上受制于议会民主,决定了其变革始终局限在资本主义的传统框架中。一方面,工党需要联合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另一方面,工党又要在旧有体系下解决经济危机,赢得资本支持。[6] 事实上,威尔逊政府延续了希思政府的策略,削减工人利益,降低工人工资,将经济危机的代价转移到工人阶级身上,背叛了他自己的支持者。如霍尔所说的:1970年代的英国,既没有可行的资本主义方式解决危机,也没有改行社会主义战略的政治基础。[7]
移民问题也非横空出世。1960年代,就有极端右翼组织“英国国民阵线”(The National Front),也有法拉奇似的政治人物因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 以保持英国性为旗号,煽动民众,抵制移民,尤其是当时的黑人移民。鲍威尔赢得了大量公众支持。究其原因,一方面,战后的短暂繁荣带来了新的消费观念,享乐主义、极端物质主义、放任主义滋生,引发了一向以节俭自律为道德准则的中产阶级,尤其是低下层中产阶级的不安,以及他们对道德沦丧的担忧。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北爱尔兰的独立运动等社会问题更加剧了他们对社会秩序的焦虑。但政治讨论过于抽象,而移民问题具体可感,因此中产阶级的这些担忧以及对当局的失望情绪很容易就被转移到移民身上。另一方面,战后社会变迁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也影响到了工人阶级的文化,工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工人阶级自身的组织性削弱。随着经济下滑,工人阶级承受了经济危机的巨大代价,工党和保守党都没能够实现对工人的承诺,反倒通过国家干预 ,以政治正确的姿态对移民施予了很多援助。这带来了工人阶级内部以种族为界的分化,白人工人阶级和黑人工人阶级出现分裂。这些情绪累积起来,再加上经济危机后大量的黑人失业和黑人犯罪问题,发生1970年代对黑人移民的社会恐慌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事实上,移民的存在,或者说作为失业人口的移民的存在,本来就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积累的必需品。正是由于失业人口的存在,才能保障资本扩大生产进行资本积累所需的劳动力储备,并加强资本与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在福利国家体系下,国内就业的实现是政治需求,失业人口势必要从别的渠道产生,移民显然是重要来源;[8]而当资本发展出现危机时,因资本积累需要的移民又成了替罪羊。
在种种社会情绪不断发酵的局势下,撒切尔主义抓住了机会。自1970年代中期,右翼势力就开始采用一系列手段重塑意识形态:用爱国主义口号绑架工会运动,以歪曲危机来源;阴谋化青年亚文化、黑人移民等社会问题,从而间接导向对权威、法律的诉求;将经济话语道德化,强调英国人应该独立自主,对自己负责,不应在社会福利中“娇生惯养”; 将自由等同于自由市场;等等。而工党完全无视各种矛盾冲突,局限于僵化的政治话语,认定阶级身份自动决定了阶级立场。终于,工党成了陷于官僚体系的国家机器,而撒切尔主义,以自由为旗号,宣称和人民站在一起。如霍尔分析的,人民选择她,不是因为人民愚蠢,相信了她的承诺,而是她成功地捕捉到了人们的恐慌、焦虑和失去的身份认同,建立了和人民日常经验的对话,诉诸情感,在混杂的各种矛盾对立中建构了共识。[9]
而如今,一场脱欧,将撒切尔主义曾经掩盖的、制造的、遗留的一系列矛盾一股脑暴露了出来。失望的钢铁工人,沮丧的中年女性,不满的外来移民,控诉的不过是历史的旧债,是从未被解决的资本主义危机。
新媒介是新的操控者吗?
相较于留欧阵营的反思,脱欧阵营将其胜利归功于社交媒体和大数据。官方脱欧组织“为脱欧投票”(Vote Leave)[10]的CEO马修·艾略特(Matthew Elliott)强调,“我们的成功之处在于,我们更精确、更高效地在脸书网站上对目标人群进行锁定,发现那些潜在的‘脱欧支持者,并将我们的信息传送给他们。新媒体时代,一个成功的政治运动领导人一定能在最好的数据专家的帮助下,发现正确的目标人群、发送正确的信息”。[11]该组织的策划主管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则盛赞其聘用的加拿大数据分析公司联合智囊(Aggregate IQ, 简称AIQ):“没有联合智囊,我们不可能赢”。
联合智囊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数据服务,得到卡明斯和艾略特的如此赞誉?最近,基于现实事件和核心人物采访改编的电视电影《脱欧:无理之战》(Brexit: the Uncivil War),复原了脱欧阵营和联合智囊公司的合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在影片中,联合智囊的首席执行官扎克·马辛厄姆(Zackary Massingham)向卡明斯解释,社交平台的设计可以帮人们更高效地找到兴趣相投的人,而借助社交平台,“我们的系统能够定位并锁定那些从未成为拉票活动的目标对象的人,那些从来不投票的人”。 他进一步解释,“互联网算法会研究我们的行为,甚至是我们的心理、我们的情感状态。依据用户的点赞、点击和分享率,我们的软件可以测试出不同广告对不同人群的效果如何, 并对其实时进行改进提升。数据可以帮助政党接触每个选民,向他们发送通过算法为其量身定制的宣传信息”。由此,脱欧公投前,联合智囊在脸书(Facebook)投放了一条与欧锦赛有关的广告:“赢得五千万英镑奖金,预测2018年欧洲锦标赛结果”,以吸引用户填写一份约有20个问题的问卷。一个看上去与政治无关的问卷,既收集了这些用户的联系方式信息,又可以通过回答更了解用户。而通过联合智囊的软件,这些用户个人的脸书账户信息与选民手册、投票预测以及拉票情况结合,所有信息都在一个能够实时更新、实时反馈的数据库中,从而可以投放有针对性的脱欧广告。 正是借此,卡明斯得到了近300万从未被关注过的选民数据,并在公投前向他们投放了10亿条脱欧广告,这是传统数据库所没有做到的。
影片讲解了联合智囊的数据技术,但该公司在现实中的故事远比影片复杂。首先,根据有关人员爆料,“为脱欧投票”组织曾以向另一个脱欧组织“离开”(BeLeave)组织捐赠的名义,向联合智囊公司支付了62.5万英镑的费用。依照选举法,如果两个竞选组织是独立的,捐赠是允许的。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以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为主的脱欧组织,“离开”的每一步都是受“为脱欧投票”指导的,包括组织章程和银行账户的设立。如此一来,就很难说这是两个独立的组织,而“投脱”组织的总费用就违反了法律对竞选组织花费额度上限的规定。[12]
其次,如此高额的数据究竟从何而来?这里涉及另一家与脱欧公投有关的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2018年3月,根据剑桥分析重要人物克瑞斯特弗·瓦力(Christopher Wylie)的爆料,《卫报》 发表系列调查报道,指出剑桥分析收集并利用了脸书上近5000万用户的信息,[13]而这些数据的使用是未经用户允许的。报道称,数据的收集主要是通过付费性格测试,用户在填写测试问卷时,其脸书信息,以及用户朋友的脸书信息都可以被收集,平均每个“种子”用户会连带出160个其他用户的信息。基于这些数据,剑桥分析可以建立算法,并描绘更多人的心理。这些数据如何被收集,以及将如何被使用,用户都是不知情的。脸书是知情的,却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14]在脱欧公投前,亿万富翁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将剑橋分析公司介绍给另一个脱欧组织: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离开欧盟”(Leave. EU)组织,该公司同样通过利用脸书数据,将脱欧广告定向投放给选民。默瑟是剑桥分析的投资人,也是特朗普总统竞选的最大捐助人,该公司也为特朗普竞选提供了数据服务。[15]
更有意思的是,在剑桥分析—这家英国公司的网站上,其加拿大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正是联合智囊首席执行官扎克的。按照瓦力的爆料,剑桥分析的母公司SCL为拓展业务,在加拿大成立了联合智囊。因此,联合智囊就像是剑桥分析在加拿大的一个部门,二者共享知识产权和服务协议。剑桥分析的技术基础Ripon平台,正是联合智囊开发的。[16]而这些信息得以被验证,在于联合智囊的大量代码数据库没有加密,很容易就可以直接下载。网络安全公司UpGuard将其下载,发现了剑桥分析和联合智囊的紧密联系,并发现数据库中的大量用户信息可以被随意使用。[17]此外,除了卡明斯的“为脱欧投票”,联合智囊还为其他多家脱欧组织提供了网站建设等数据服务,包括爱尔兰民主统一党(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改变英国”(Change Britain)、“老英国”(Veterans for Britain)等。[18]由此,我们终于能够看清这样一幅图景:各式各样的脱欧组织事实上由密切相连的两家私有数据公司所连接起来。脱欧的数据控制背后,是强大的资本力量。
资本的介入不止于此。虽然《卫报》一系列的报道中提及了这些数据与脱欧公投的关系、数据公司对民意的操控,及其与背后财团的关系,但更多的媒体并不报道这些。脱欧公投的结果已成事实,联合智囊、剑桥分析或是其母公司SCL与脱欧的关系,不在英国政治的讨论范围。[19]即使曝光后的剑桥分析公司破产了,同样的数据库和人员可以换个公司名字照常运转,没有什么变化。令爆料人瓦力更为耿耿于怀的是,他在接受的各项质询中多次提到,剑桥分析和联合智囊不过都是冰山一角,其母公司SCL 长年从事有关政治选举和国防信息的服务,在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操纵民意,干预政治,但那些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事情没有新闻价值,也没有人过问。[20]2019年2月,历经18个月的调查后,英国数字、文化、媒介和体育委员会(The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s Committee)发布最终报告,报告中罗列了SCL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干预过的选举和公投,长串的名单涵盖了28个国家,包括加拿大、巴西、捷克、法国、冈比亚、德国、加纳、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等。[21]但是,英国的议会质询还是主要集中在了脸书的数据泄露问题。在“数字、文化、媒介和体育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中,称脸书及其主管为“数字黑帮”,认为其行为没有有效处理数据泄露问题,侵犯了用户隐私,且多次有意阻碍调查,是对民意的操纵、对民主的威胁,建议加强政府管制。[22]脸书的数据泄露当然是个严重的问题,网络公司对用户隐私的侵犯需要管理,但显然,集中在脸书的火力遮蔽了更多、更深的问题。
新政治来了吗?
脱欧公投中,新媒介和大数据显示了强大的政治操控能力,近300万新选民的挖掘和定向广告的投放都突破了传统的媒介动员能力。那么,新媒介会带来新政治吗?
互联网新媒介在1990年代就被寄予厚望。很多学者如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在对互联网的畅想中,提到互联网可以实现组织的扁平化、社会的全球化、控制的去中心化,以及人类的和谐化。[23]网民在网络平台的内容生产,使得“观点的自由市场”这个概念萌发了新的活力;丰富的网络信息,以及网民在网络中的积极互动参与,更是拓展了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引发了关于公民社会的新讨论;依托新媒介,社会运动也有了新的组织方式,“阿拉伯之春”、“华尔街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社交媒体在其中都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个平等、自由、去中心化的社会建设图景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事实上,新媒介能够为谁所用,依旧是一个博弈的过程。2008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成功竞选彰显了脸书等社交媒体的强大作用。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奥巴马团队充分利用博客、邮件、短信、视频和社交媒体等多种方式,进行政治宣传,吸引了广大选民。其团队积极参与到网络平台中,与选民互动,回答选民问题,从而了解选民的想法和诉求,并根据选民填写的信息有针对性地投放选民关注的议题。同时,团队鼓励选民利用社交平台,向其朋友推广奥巴马的政治观点,使选民自身成为传播渠道,积极参与到竞选中。[24]通过这些策略,奥巴马赢得了大量支持者,成为利用社交媒体赢得大选的典范。奥巴马时期对新媒介的利用还集中在其平台作用,而如今在特朗普的竞选和脱欧公投中,新媒介则既是平台,更是数据来源,而数据分析的背后则是资本的运作。新媒介创造的可能性背后,政治和资本的拉扯没有改变。
另一方面,依托新媒介进行数据收集和定向投放的媒介内容,究竟对个体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个体在面对媒介内容时又能发挥多少主体性,其实一直都存在争议。剑桥分析的瓦力曾介紹了相关数据分析的原理,如对网民个性的分析,主要是通过网民在脸书上的点赞数据,寻找相关性,从而将人的个性定量化。他举了其中一些有趣的发现,比如点赞了“我恨以色列”的人通常倾向于喜欢耐克鞋子和KitKats巧克力。[25]“这种‘我恨以色列和‘喜欢KitKats两者之间的关联,其实只是说明这些年政治已经娱乐化了,这些消费者在点赞‘我恨以色列的时候,就是个身份标签,并不确定自己在说什么。只能证明身份政治的有效性,而真正的政治教育和政治意识完全崩溃了”。[26]
回到脱欧公投,新媒介真正发挥的作用,其实还是在于释放出那些一直存在而未被解开的政治症结。那些长期积压于日常生活中的情绪需要表达,那些被忽视、被遗忘的人需要发声的渠道,依托新媒介的数据分析只是精确地捕捉到了这些人,并加以利用。但如果没有这些长期累积的问题,公众情绪的煽动并不会那么容易。奥巴马竞选时的口号“Change”(改变),脱欧公投中的口号“Take Back Control”(拿回控制权),无不集中了社会危机中人的心理诉求。在这个技术革新的时代,新媒介、大数据和政治的结合不一定是坏事,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用、被谁用——是用来解决暴露出来的政治症结,还是用来煽动群体情绪、制造更多的问题?是商业利益驱动的数据公司在利用,还是以公共利益为重的机构在使用?按照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说法,政治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领域,而是生产性的,是一个结局开放的过程;在其中,经济、社会和文化中的各种力量和关系相互互动、影响,从而生成某种权力形式和领导方式。[27]新媒介提供的只是新的平台和形式,而新的政治则是在各种力量的复杂互动与博弈中产生的。它需要历史的回顾、自身的省思;需要培育新的政治主体,进行积极的政治讨论,将各种被冷落的意见表达出来;需要打破陈旧的、僵化的政治话语,寻找新的共识。
(作者单位: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注释:
[1] “EU referendum: full results and analysis”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ng-interactive/2016/jun/23/eu-referendum-live-results-and-analysis.
[2] Crag Oliver, Unleashing Demons: The inside story of Brexit, Qurecus, 2016.
[3] Crag Oliver, Unleashing Demons: The inside story of Brexit, Qurecus, 2016, p. 318.
[4] Carmen Fishwick, “Meet 10 Britons who voted to leave the EU”, The Guardian, June 25th, 2016.
[5] Stuart Hall, et al.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 ord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6] 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crisis of the left, Verso, 1988.
[7] [9] 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crisis of the left, Verso, 1988, p. 23; p. 167.
[8] Stuart Hall, et al.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 order, pp. 372~373.
[10] 英國选举委员会任命的脱欧阵营的官方拉票组织。
[11] 嘉月:《英国脱欧阵营为何能胜?—专访“为脱欧投票”组织原CEO 马修·艾略特》,载《南方周末》2017年3月30日。
[12] Carol Cadwalladr, Emma Graham-Harrison and Mark Townsend, “Revealed: Brexit insider claims Vote Leave team may have breached spending limits”,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8/mar/24/brexit-whistleblower-cambridge-analytica-beleave-vote-leave-shahmir-sanni.
[13] 之后脸书承认不是5000万用户的信息,而是8700万用户信息。
[14] [25] Carole Cadwalladr, “‘I made Steve Bannons psychological warfare tool: meet the data war whistleblow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r/17/data-war-whistleblower-christopher-wylie-faceook-nix-bannon-trump.
[15] Carole Cadwalladr, “Revealed: how US billionaire helped to back Brexit”,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7/feb/26/us-billionaire-mercer-helped-back-brexit.
[16] Carole Cadwalladr, “AggregateIQ: the obscure Canadian tech firm and the Brexit data riddle”,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8/mar/31/aggregateiq-canadian-tech-brexit-data-riddle-cambridge-analytica.
[17] UpGuard, “The Aggregate IQ Files, Part One: How a Political Engineering Firm Exposed Their Code Base”,https://www.upguard.com/breaches/aggregate-iq-part-one
[18] UpGuard, “The AggregateIQ Files, Part Two: The Brexit Connection”,https://www.upguard.com/breaches/aggregate-iq-part-two-brexit
[19] [20] Carole Cadwalladr , “Cambridge Analytica a year on: ‘a lesson in institutional failure”,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9/mar/17/cambridge-analytica-year-on-lesson-in-institutional-failure-christopher-wylie.
[21] House of Commons,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s Committee, Disinformation and ‘Fake News: Final report(eighth report of session 2017-2019), 14 Feb. 2019, p78.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1719/cmselect/cmcumeds/1791/1791.pdf.
[22] “Disinformation and “fake news”: final report published”, https://www.parliament.uk/business/committees/committees-a-z/commons-select/digital-culture-media-and-sport-committee/news/fake-news-report-published-17-19/.
[23] Nicholas Negroponte, Being Digital. Knopf, 1995.
[24] Rahaf Harfoush, Yes We Did: An inside look at how social media built the Obama brand, New Riders, 2009.
[26]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吴靖教授访谈,2018年3月18日。
[27] Antonio Gramsci,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