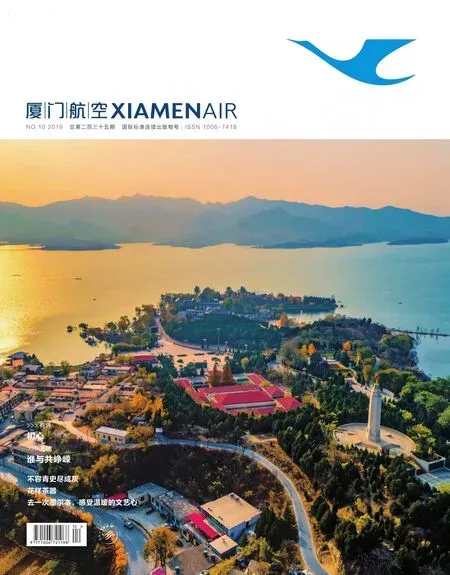良贾何负鸿儒:中国商人的百年家国情怀
撰文_毛剑杰
1937年,随着“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各个阶层,此前忙于打内战的军阀,埋头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以及逐时以牟利的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号召,迅速行动了起来。
抗战前一年,中国刚经历了民国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十年”,相应的,民间资本实力也在1936年达到了一个巅峰。但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商人们自晚清民国以来的实业报国理想、家国情怀,被迫以另一种方式去践行,然而这却成了他们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一
1938年夏,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华中战场激战正酣,武汉即将沦陷,大量从东部沦陷区撤退的人员物资,经武汉到达长江枢纽港宜昌,等待从水路入川。晚清民国时,长江水路几乎是入川唯一的畅通大道。宜昌以上峡江航道滩多浪急,1500 吨以上吞吐量轮船不能溯江而上,从中下游来的大船也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才能继续溯江入川。但是,再过40 天左右,这入川唯一的峡江航道,就要迎来漫长的枯水期,届时,装载大型设备的轮船将根本无法行驶。这也就是说,所有滞留宜昌的人员、物资,都必须在40 天内运完。据当时报刊报道,这年夏天的宜昌,“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汉口陷落后,还有三万以上待运的人员,这三万多人中,有许多教师、医生、工程师、工商界人士,荟萃了当时的各界精英。比难民更亟须进川的,是各种各样的抢运物资,它们是全中国航空、军工、轻重工业的精华。入川物资人员之外,还有需要出川的几十万川军人员、装备,亟待通过长江水道转运到抗日前线。于是,原本只有10 万余人的宜昌城,一下子被挤爆了。有幸挤上船的作家老舍当时如此形容:“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
物资人员积压,运力却严重不足,而日军正在逼近,头顶还有飞机轰炸,各企业、各机关都在争先恐后要求尽快撤到后方去,宜昌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物资转运进程仍旧缓慢,正当众人陷入绝望时,事情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转机。这个扭转局势的人正是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作孚。
二
卢作孚,合川人,1893年生于贫寒之家,读完小学就开始做活。1925年,卢作孚在合川创建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一艘运力仅有70 余吨、从重庆至合川的小客轮起家,十余年时间发展壮大成为川江航运的主力军。1938年能够穿行三峡的船只,民生公司有22 艘轮船,中国招商局有两艘轮船可以通行,这几乎是所有可以调动的运输力量。因此,宜昌大撤退中,卢作孚和民生公司被寄予厚望。
国难当前,素以实业报国为志向的卢作孚,除了民生公司总经理,还有另一个身份上任刚半年的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作为实业家,卢本人十分淡泊名利,但这个危急时刻,卢作孚果断地接受了使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交通方式,将中国仅存的工业基础设施转运到大后方去。
1938年10月23日,当他抵达宜昌码头时,民生公司宜昌分部的办公楼外,挤满了急等购票入川、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办公通道已被购票者围起了好几圈。卢作孚次子卢国纪回忆说:“混乱局面下,父亲表现得十分镇定,他对那些争吵不休的人有礼貌但很坚决地说,请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见!”或许受其诚意感召,躁动的人们突然停止了喧嚣。
当晚卢作孚立刻召集宜昌的民生公司员工,召开了一次通宵达旦的紧急会议,以完成这个看似不能完成的任务——40 天时间内,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10月24日一大早,卢作孚从办公楼中走出。此时,门外已经站满了要求运货的客户和西行的旅客。让人欣喜的是,秩序比之前井然了许多。他很快宣布了刚刚出炉的“三段航行法”。为躲避敌机轰炸,卢作孚又在中途设多个转运站,甚至临时增加了许多新码头。为了分担运输物资,民生公司又从民间临时征用了上千艘木船。
危亡年代的中国,这些船只成了一艘艘承载希望的“诺亚方舟”。黄昏前,两岸江边数百盏煤气灯迅速点亮,江水中的灯影摇摇晃晃。不到一天时间,第一艘满载人员、货物的轮船驶出宜昌港。登上“诺亚方舟”的第一批乘客是“保卫中国同盟”收留的数百名孤儿。经历现场的乘客记述说:“汽笛声中,这些孩子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动容。”从10月24日这天开始,民生公司的22 艘轮船和850 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来回穿梭,“宜昌大撤退”就此拉开序幕。
三
宜昌至重庆的航程近1000 公里,光是险滩暗流就有数百处之多。除了暗流险滩,空中轰炸是另一个威胁。抢运开始后,民生公司船队每天都有船只被炸毁的消息传来,每天都有民生公司职员、码头工人、航道上的纤夫在日机轰炸中牺牲或受重伤致残。40 天的大撤退结束后,民生公司有16 艘轮船被炸毁,116 名员工牺牲。
转眼到了12月,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城突然完全宁静下来。“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2/3。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卢作孚《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事后统计,枯水季到来之前,卢作孚共指挥宜昌港输送了3 万多滞留人员和2/3 的滞留物资,这几乎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一年的运量。同时,当时中国的教育、商业、文化艺术等种种事业的精髓也转移到重庆。他深知,这些看似破碎的元素,将会在那里重新被组合,陪都的经济、教育、军事版图将被一一拼凑完成……
多年后,常常有人将卢作孚导演的宜昌大撤退视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宜昌大撤退的持续时间更长,运输长度和难度更大——重庆至宜昌航道超过600 公里,远大于英吉利海峡的航程,而三峡水道的自然条件也更为险恶。
敦刻尔克大撤退靠的是一个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
四
卢作孚竭尽全力指挥宜昌大撤退的同时,另一位商界领袖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新加坡筹赈会”,宣布“今日大会目的专在筹款,而筹款要在多量及持久”。
这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代表一些人盲目乐观心态的“中国抗战速胜论”破产,与此同时,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主张中日和谈的“低调俱乐部”开始高调。公开提出“和平乃救亡图存之上策”。三天后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身份,发来电报提案:“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这份提案无疑在主和论、亡国论雾霾下的重庆引爆惊天巨响。20 多位国民参政员联名签署,议长汪精卫只得向大会朗读根据陈嘉庚提案提炼修改的11 个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这时,广州也已失守,中国失去了所有海港,抗战物资囤积香港,需要紧急从西南滇缅通道运往前线。1939年2月7日,陈嘉庚领导下的南侨总会发出第六号通告《征募汽车机修、司机人员回国服务》,他亲自接见第一批回国服务的80 名机工:“青年有志具以牺牲精神,足为马来亚之模范。”滇缅公路崎岖难行,翻越3000 多米的横断山脉,途经怒江、澜沧江、漾濞江,这是一片荒凉的烟瘴之地。3200 多名华侨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克服种种困难,日夜驰骋,运送军需物资450 万吨。艰险的滇缅公路成为西南边陲抗战救国的生命线,而在这条生命线上,1000 多名南侨机工长眠于此。
从1937年至1941年,南洋华侨累计义捐5 亿国币,认购的2 亿5000 万救国公债全部捐献祖国。当时,厦门大学交给国家公办了,集美学校经费依然紧张,为了抗日筹赈,陈嘉庚“常月捐,至战事终止,每月国币贰仟元”。而他平日所带,不过5 元钱,一个月的花费,不过2 元钱。
在这抗日烽火中,厦门大学内迁长汀,萨本栋成为国立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领导厦大师生,自强不息。在这一时期,厦大培养了16 位院士;日本投降后,500 多名厦大学生奉命赴台,参加接管台湾,助力台湾经济起飞。长汀时期的厦大,也因此被人誉为福建的“西南联大”。
1940年,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组织回国慰劳团。下榻重庆时,听说国民政府拨款8 万元负责接待事宜,陈嘉庚深感不安,他在重庆各报纸刊登了启事:“慰劳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须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愿实践新生活节约条件,且在此抗战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慰劳期间,时年67 岁的陈嘉庚历时9月慰劳15 个省份,不顾日军轰炸的危险,亲赴前线慰劳将士。1942年2月1日,日军进攻新加坡,陈嘉庚连夜离开新加坡,集美学校、厦大校友舍命护送。此后,日军追杀三年,陈嘉庚安然无恙。
1945年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陈嘉庚结束了匿居生活。在陈嘉庚率领下,1941 至1945年4年半期间,南洋华侨共计捐款约15亿元,几乎相当于当时国民政府一年的军费。由于陈嘉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毛泽东主席以“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誉之。
整个抗战期间,从松花江到长江再到珠江,中国民族企业家们一直站在对敌战斗的最前线。在上海等地区,企业家们都坚决不与日寇合作。当时著名的“火柴大王”刘鸿生,日寇要他当上海商会会长,他严词拒绝。“中国唯一的财团”荣氏兄长荣宗敬身患重病还整日为国忧虑,他叮嘱后人:“开办工厂不易,你们千万不要把它们留给日本人……”
范旭东创办的天津永利碱厂,亚洲一流,日寇觊觎已久。1937年秋,日寇派其代表刀根几次“拜访”,范旭东回答:“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日寇终于失去耐心。日军逼近南京前夕,有意将工厂完整保存下来为其所用,范旭东断然拒绝:“宁举丧,不受奠仪!”
有着“一品百姓”之称的虞洽卿,更是倾其所有。1945年4月26日他因急性淋巴腺炎去世,弥留之际还捐献黄金千两用于抗战,国民政府赠予他“输财报国”的匾额。
五
晚清民国之际,在帝制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同时,响应孙中山实业报国的号召,同时也是对传统中国商人“良贾何负鸿儒”观念的继承,以江苏南通籍晚清状元张謇投身实业为参照,许多商人也坚信“仕商异术而同志”,然后“货殖以起家,散财以治乡”。
比如无锡,荣氏家族世居无锡荣巷,以长途贩运的小本生意起家,渐渐兴盛。但在1860年太平军攻入无锡的战乱中,荣氏全族男丁尽数死难,唯一幸存者是在上海做学徒的11 岁男孩荣熙泰。然而,正是这位孤苦的幸存孩子,成年后利用他在上海大码头积累的见识和少量资本,于1896年以1500元银洋与人合资,在上海开办了广生钱庄,成为近现代荣家走向中国工商巨子的起点。
荣熙泰感于人世求存之不易,发迹后常思回报桑梓。其子荣德生、荣宗敬兄弟,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一生在无锡故乡造桥数百座,又捐资办学、投身各种公益事业……直到当代,荣氏公益传统仍在延续。
1994年,当老宝界桥逐渐不能满足交通需要时,已成香港商界达人的荣德生之孙、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又捐资3000万港币,在老桥旁边又续建一座新宝界桥,两座设计风格、外观造型几乎完全一致的宝界桥,在湖中倒映,交融,正是百年中国悠长的商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