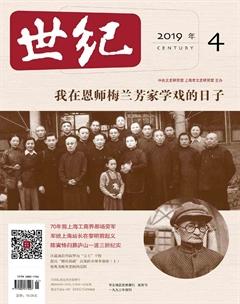冯骥才:我的事业只有生命能给它画上句号
孙小琪
冯骥才在他新近出版的非虚构作品《漩涡里》开篇中说:“在现实中我没有实现的,我要在书中呈现。这也是写作的意义。”这段话,使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见冯先生的情景。
第一次到天津采访冯骥才,临别他送我一本《秋天的音乐》
1994年10月,我在参加一次全国妇女报刊的会议之后,专程去天津,计划是要采访蒋子龙和冯骥才,他们两位当时在全国已是名声大噪的作家。那时的套路,或是请作家写与婚姻家庭有关的文章,或是由记者自己采写,请作家谈。作家因其独特的思想和出色的文笔,写出的文章大多出彩,很受读者欢迎。那次不巧蒋子龙没在天津,我只见到了冯骥才先生。我记得他家整洁而富有书卷气,冯先生很健谈,也可能是我并没有十分强调我的要求,整个访谈过程,冯先生几乎都在说保护历史建筑历史文化的重要,如天津的什么什么如何如何了不起。冯先生说,艺术就是要把美留住,这在现实中不可能,就在作品中留住,永远留住,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这么多年过去,冯先生的这番解说常常在我心头萦绕,现在他在《漩涡里》再度重申,使我明白,永远地不遗余力地追求理想世界的美,是他从未放弃的信仰。冯先生高大魁梧,站起来好像把门框撑满了。临别,他從一包拆封了的书里取出一本,签了字送我,还有一张他的绘画精选卡片。
那是我第一次去天津,晚上大街上黑咕隆咚。离开上海时还是夏末的炎热,我只穿了单薄的衣裙,没想到北方秋风一吹,腰背疼得直不起来,躺在旅店床上,看冯先生送我的《秋天的音乐》。那是李辉主编的金蔷薇随笔文丛中的一种,收录了冯骥才自选的几十篇散文随笔,有些是他给自己的书写的前言后语,每一篇大约两千字上下。大多为小人物,小故事,他给自己写的自序,题目是《真实高于一切》。那些文字,短小精致,不仅具有语言意境的美,每每都有独特的内涵和寓意,我很喜欢,有的还看了几遍。当时觉得,《秋天的音乐》好像不是其中最出色的,为何要置头条并用作书名呢?文末关于艺术是欺骗人生还是安慰人生的对话,曲折地传递着什么。那张卡片是他的绘画《树后边是太阳》,大雪覆盖的斜坡,萧瑟稀疏的树木,被太阳光投射在雪原上的拉长了的树影。但画面上没有太阳。我想,这画表达的,应该是一种压抑和忧郁以及散落其间的呼吸和希望。冯骥才笔下的画,还有他的文章,都是细微精致的。
回到上海,为了疼痛的腰椎我开始往返医院,状况却是越来越糟,几乎不能行走,直到半年后手术了事。那半年,看书会多一些,《秋天的音乐》中一些短篇也在其中,诸如《珍珠鸟》《挑山工》那些名篇,文字不管长短,都有思想在,给人以美好积极的情感熏陶。
写作者的担当
2018年9月,我去甘肃张掖,参加了由河西学院中国非虚构写作研究中心和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等单位主办的“冯骥才非虚构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张掖宾馆报到那天,晚饭时冯先生来了,在几个陪同者中,他高大的身影很突出,走路缓缓的。这是我第二次见他,虽然从没有机会当面交谈,却一点不感觉陌生隔阂。在这二十多年里,冯先生的文章、书画、言论、行动,常常不断地从各种媒体渠道传播出来,我除了精神上认同,还十分敬佩,敬佩他年逾古稀仍葆有的家国情怀、赤子之心。第二天在去会场的面包车上,我拿出带去的24年前那本《秋天的音乐》,冯先生在晃动的车厢里,再次题词,那字真漂亮。
读冯骥才的非虚构作品,感觉他描述过去半个世纪中国人的生活的笔,是被强烈的精神和情感驱使的,在世事洞察和关于普通人命运的描述里,有对暴戾和黑暗的揭发憎恨,有对生命被蹂躏、承受无尽苦难的悲悯,有对人的尊严和生命意义的追问和捍卫,有对爱和未来的坚定信仰。他的五本书:《一百个人的十年》《无路可逃 1966-1976 自我口述史》《凌汛 朝内大街166号 1977-1979》《激流中 1979-1988 我与新时期文学》《炼狱·天堂·韩美林口述史》,70多万字,还有相当数量的能够还原彼时彼刻的照片和素描、绘画,忠实于历史事实和人物心灵真实的非虚构描述,冯先生力图把那个正在远去却还没被充分看清、真正读透的时代写下来、留下来。这些作品中,超过半数的内容是描述“文革”生态,那些讲述令人揪心、惊惧,有时几乎有痛不欲生的感觉。
冯骥才是有大成就的作家、画家、文化学者,“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凭借自身的刻苦勤奋和天赋,已经做出令国内外同行广泛赞誉的成绩。出于记录历史的神圣使命感,不愿也不敢让那些不堪,在新的时代来临后悄无声息地溜走,便以辛勤的劳动,在非虚构创作领域,为这中国历史上不可忽略的半个世纪,开垦园地,留存历史真相。冯骥才的非虚构作品,那些煞费苦心的回忆、采访、整理、记录,包括《凌汛》和《激流中》,对“文革”结束后,文学在社会生活的巨大转折中所呈现的众生相,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种种冲突和较量,以亲历,以辨识,点点滴滴记录在案。不是创作,而是纪实,需要更多的奔波和案头劳作,体力脑力兼备。对于事实的认定甄别,往往还会牵涉很多现实状况的干扰,如若没有坚定的思想力量支撑,是不能坚持也不可能完成的。
在现实中拿出有写作价值的东西
甘肃省的河西学院地处河西走廊中段,校园朗阔而美丽。研讨会期间,作为河西学院贾植芳讲堂的第17讲,冯骥才先生以非虚构写作为题,作了精彩演讲。那天晚上,近1000个座位的大礼堂座无虚席,当冯先生出现在舞台一角时,礼堂里爆发的掌声,如海浪涌动般有力而持续。冯骥才在很多人眼里,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在祖国的大西北,台下的莘莘学子,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在课本里读过冯先生的文章,现在能亲眼见到近距离交流,那兴奋可想而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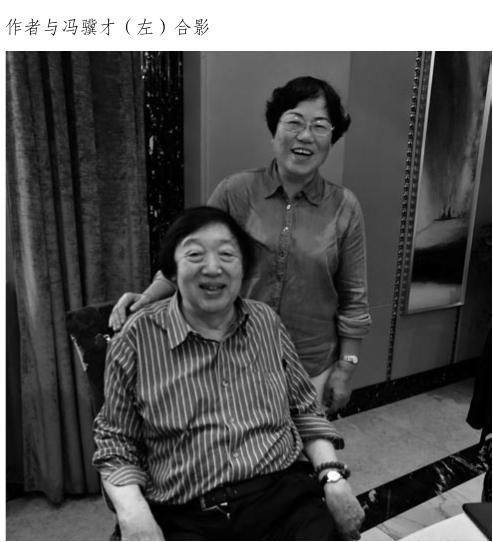
冯先生用纯正的普通话侃侃而谈,不疾不徐。从“非虚构”的内涵、外延,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和体验,还有随处拈来古今中外各种写作事例,亲切而自然。他认为非虚构文学是在现实中拿出有写作价值的东西来呈现,非虚构凭借的是事实,非虚构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现实,现实有着不可辩驳的力量。他说到自己决定写《一百个人的十年》时,每天要端着脸盆去接满满一盆信箱里装满的来信,那些从全国各地遥远的边疆农村写来的信,很多都曾被眼泪浸湿过,纸就粘连起来,打开的时候,会有轻微的沙沙声,“那声音打雷一样感动了我的心”。素昧平生,却又是无限信赖,这就是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读者是你精神的朋友”,冯骥才说。
我坐在礼堂中间的位置,聆听中想到了什么叫“出口成章”,也感受着前后左右的全神贯注。最后互动环节,他很有耐心地回答学生提问,还不忘开玩笑。
回到后台休息室,看得出他还是累了。隔天到张掖时,冯先生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上台前,他曾跟主持人李辉说,我大概说40分钟,可一旦他坐下开讲,一口气讲了1小时20分钟。我想起2017年曾读到他在一个会议上的讲话:我今年75岁了,我还有理想。而他前行的路,每一步都是全力以赴的。
(作者为《现代家庭》原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