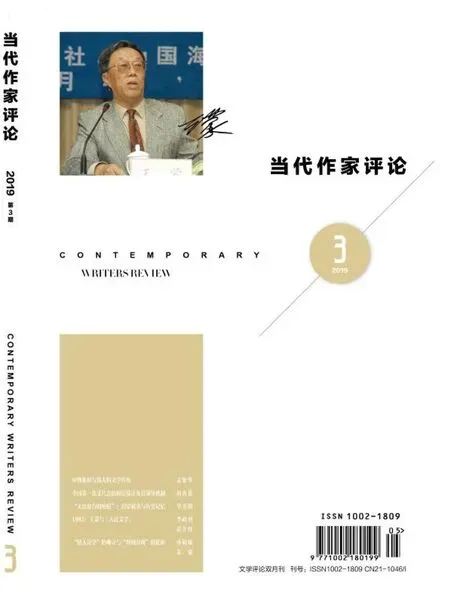谁的“白鹿原”?
——话语的争夺与改编的政治
李定通
陈忠实(1942—2016),不仅是当代文坛的代表性作家,更是现象级作家。所谓现象级作家,即除了写出经典作品以外,还应该具有时代性与特殊性,引领一时风潮,并形成持续广泛的影响。不同于莫言,陈忠实并不高产,甚至可以说是凭借一本《白鹿原》超越当代作家,成为当代文坛的领军人物。小说《白鹿原》作为陈忠实呕心沥血的“垫棺作枕”之作,不仅是一本书写时代史诗的经典小说,更是寄托了一代知识分子文化夙愿和社会反思的诚意之作。小说《白鹿原》既接续了80年代改革转型新时期新启蒙浪潮下的“反思文学”的创作精神,同时也旗帜鲜明地昭示了后80年代在激情消退、物质主义庸俗之风骤起的文化生活中一种人文精神的选择和立场。
《白鹿原》研究历时20余载,涉及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叙事分析等各个方向,卓有成效。究其根本,研究者关注的核心主要限于儒家道统的瓦解与现代性的焦虑,以及乡土与地域文化的当代定位。2012年,电影《白鹿原》上映以来,出现了数量有限的研究电影《白鹿原》的文章,但主要纠结于电影的好坏得失,还有的研究者只是把电影《白鹿原》视作小说的副本。事实上,由于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双重构造,“白鹿原”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地方、一本小说或一部电影,更是一个象征,一个被争夺的话语符号。为解码“白鹿原”这一文化符号的文本张力与历史内涵,一方面要在追溯《白鹿原》的创作历史与文化批评的过程中重塑“白鹿原”的文化历史意义;另一方面要尊重电影《白鹿原》的文本特性,通过电影语言分析以及小说与电影的异质性比照,勾勒出“白鹿原”符号变迁的整个历史图景。
一、小说《白鹿原》的创作冲动及其效用
谈及《白鹿原》,论者总是不免要重复“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一命题。其实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中,小说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更是一个民族的“明史”——也就是说除了文学审美的功能以外,小说还担当了补足正史无暇顾及的历史细节,以及纠正部分由于正统性导致正史书写谬误的重任。新时期以来,在“新启蒙运动”的浪潮下,一种“反政治的政治”意识形态盛行起来,文学尤其是小说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世俗化、娱乐化趋势成为一种世界潮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可以视作节点与宣言。这种新启蒙精英的视角一方面就显得有失公允、过分担心了;但另一方面却又陈述了一定的历史事实,至少是吐露了知识阶层对世俗化偏向批评的文化心态。
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在这样一种暧昧不明,甚至可以说精神颓废的文化氛围中发生的。这种颓废正如《废都》,同为文学陕军代表人物的贾平凹塑造了庄之蝶这一人物形象,一个放弃了为人民写作的颓废作家,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消解责任之后的“动物化”特征——丧失了作为人的精神层面的信仰和文化追求,回到肉体的存在和本能冲动的动物状态。陈忠实是要借《白鹿原》来寻求一种新变,一种对于时代变革与文化传统的关切。用作家自己的话讲,“是一个重大的命题由开始产生到日趋深入,就是关于我们民族命运的思考。”这一思考是“在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中所触发起来的”。象征道统乡土的蓝袍加在主人公“慎行”的身上,而他的生活和命运却不可避免地卷入新时代爱情和现代思想观念的旋涡之中,《蓝袍先生》落脚在“慎独”的“归去来”,“这种‘辩证法’的惊人‘历险’昭示着,一切的现代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折腾’,只有类似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超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才是永恒的现实。”这里的重点,恰好是陈忠实所不断强调的要发掘民族的“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具体而言,陈忠实在实地考察了白鹿原的历史以及以《乡约》为载体的关学传统后,结合自身的阅读史——重点提到了《创业史》的地域色彩和《静静的顿河》《百年孤独》的细节描写,通过打造白嘉轩这个中国“最后一个地主”,以实现文化突围。
当然,陈忠实的创作欲望远不止于此,在曲笔隐晦的文学历史构建中,作者更意图突破意识形态控制和物欲横流的浮躁空气,亦即超越政治局限,以历史视野来观察、描写生活,突破“地主——农民”的农村描写二元模式,发掘中国农民的深层文化心理内涵。这种超越的架构聚焦的是乡土道德与文化秩序的重构,其目的无疑是倾向于塑造“绝对中国”的典型,重建前现代的以乡约民规为基础的儒家道德理想社会。农民身份和张载式的“为往圣继绝学”的旧乡绅学养,构成了陈忠实创作的主要冲动和前意识动机,这在朱先生近乎神话的刻画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朱先生的刻画是《白鹿原》最大的亮点,一个多智而近妖的关中儒学代表,以其超越世俗苟且的神性赋予了陈忠实文化道德的力量,同时也使得小说拥有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想象力。通过小说书写,以历史再解读的方式契合了当时社会精神文化缺失与重建的渴望。
然而,朱先生显然也是最大的败笔,三言化兵戈、中条山赴死、身死知后世……这无一不是忠勇神武的民间神话模式,所演绎的无疑是某种无济于事的后见之明,神化的朱先生对于现实社会并无多少真实意义。需要借助神话的力量,从另一个侧面看恰恰显示剥离了世俗影响力的道统的虚弱。人们一开始就把这些事迹当作神话看,那么就不会真正相信,尔后身体力行了,所以于现实的文化重构也就没有几分价值。就如陈忠实在文中所昭示的那样,以黑娃、孝文为代表的黑白两极要么走向背离要么走向堕落,小说人物的荒诞命运带来的是发人深省的隐喻。作者通过白嘉轩追求仁义之德和对仁义精神不自觉的伤害——作为掌握“乡约”解释权的白鹿村族长,白氏既有维护纲纪、保护族群、公正仁义的儒家信徒的一面,也有投机巧取、豪狠残忍、虚伪狡诈的老式农民的一面;以及突出朱先生最终的“好人难活”的哀叹,分别暗示了儒家仁义道德体系的自我消解与不合时宜。白鹿原所昭示的正是道统秩序最后的挣扎与无奈,“仁义白鹿村”注定只是世纪末中国式田园牧歌最后的回望。
除了塑造典型,陈忠实还有那代人共同的书写史诗的欲望。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小说的叙事分析审视陈忠实的创作冲动及其效用是如何在文本中实现的。中国小说习惯以叙事结构呼应“天人之道”,“叙事文学作品的开头,往往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形式,属于叙事外的叙事层次。”因此,小说《白鹿原》的开头绝不是孤立的开头,而是一个宏大结构原点,既涵盖了全书的历史哲学和“民族秘密”,又隐藏着全书的结构逻辑和叙事策略。故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传奇叙述中展开,喻示了白鹿原的历史命运,沟通了天理与人欲,融合了历史与生活,是一个丰富多彩,张弛有度,立体的复合结构。
白鹿原上的各方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场。这种“复调”设计促成了人与情欲、信仰与现实、历史与命运的多重对话。此外,叙事时间上的不平衡分配、空间和人物安排上的来回穿插、文本的疏密度变化,形成了小说强烈的叙事节奏感。不仅仅是人物的多重对话与气氛营造,小说还通过把白鹿原这一历史平台作为载体,以戏楼、祠堂为舞台,将各色人物笼络起来。祠堂属于精神世界,白鹿村的村民在这里祭祀先主、祈福禳灾,白鹿村长在这里执行族权、立权威维护纲纪。戏楼则属于现实世界,人们在这里看戏寻乐,上演暴力与阴谋,压迫与反抗,仇杀与报复的好戏一场接一场。在通过戏楼和祠堂联系的白鹿原公共空间里,世俗的、政治的、文化的场相互作用推动历史的进程。以复杂的形态组合多种叙事部分和单元,成了小说最大的隐义所在和亮点所在。
二、中国式欲望:政治、情色与商业投机
将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从电影诞生伊始便开始建立的传统。电影《白鹿原》的改编上映,拓宽了“白鹿原”这一文化符码的历史内涵,并且映射了商业市场的诉求和主流意识形态视域下的当代文化生产。同时,小说和电影又是两种不同的看见方式:小说以语言为实体,电影则借助现实的影像;小说的看见依靠的是无限的联想,而电影的看见则付诸于鲜活的直观。从小说到电影的过程又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电影改编自原著,进行了改动增删,这里面混入了编导的基因,主流话语的意志,市场的期待。于是,作为小说的电影与作为小说的小说并不是相同的一回事,或者说是不同的两回事。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白鹿原》同小说《白鹿原》、同作家陈忠实并无直接的关联。然而,从电影《白鹿原》开拍以来大家最关注的,编导最强调的却是“还原”,还原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再现三秦大地渭河平原上的历史。
《白鹿原》开篇就宣告了要写作民族的秘史,因此还原的首要表现就是要拍摄一部“史诗性大片”。为了构建“史诗性”的格局,影片在156分钟的文本容量里全景式地涉足了白鹿原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风俗等各个方面。讲述社会变革、家族恩怨、乡愿党争、市井生活各种场合,呈现了包括仇杀与报复、情色与阴谋、欢实与放纵等多样场景,覆盖了城市、原上、战场等不同空间,刻画了地主、乡绅、士人、流寇以及革命者等不同人物,表现了神魔、善恶、忠孝以及放纵与叛逆等人性的多个侧面。然而有限的电影文本容量毕竟无法涵盖广阔的历史内容,电影编导却不顾电影文本容量,对原著的还原到了事无巨细,一段不漏的地步,贪大求全就难免情节拖沓和叙事苍白。
小说的“复调”设计有效地勾连了白鹿原上的风云际会的人物对话,“恰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连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它让读者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观察生活,它展示生活的不同侧面,又给人统一的完整的印象。电影则全盘围绕田小娥展开,然而单一的田氏视角显然不利于对话的展开,田氏所具有的结构功能和隐喻意义也相当有限,所以整体呈现出内容丰富而内涵贫瘠的状态。
虽然宣称打造史诗大片,但电影明显染上了娱乐时代商业媚俗的时代病。情色和政治向来是商业电影的利器。王全安打出“田小娥是中国式的欲望”的标语,将第一关注点放到田身上,寻求新意和突破。但是,“田氏的形象的多义性本身构成了自我消解”,田小娥既要承担起连接黑娃、白孝文两极的结构任务又要作为性的象征,“田氏所具有的性和繁衍的力量激发了白孝文反抗父权的冲动……再也不想做大家族的孝子贤孙……不得不说,在这里面制作者超越了对性爱的一般性展示,赋予了田氏性爱新的美学意义。但正是因为田小娥形象的多义性,意义从一个能指飘浮到另一个能指,人物结构抛弃了中心,使得人物的隐喻功能被消解。”哪怕单独把田小娥拎出来,小说写作之时至少还具有继承和突破80年代性探索的开创意义,但对于拍摄于21世纪头十年的电影来说这还不够。还需要回到作家的初衷,“既然我想揭示这道原的‘秘史’,既然我已经意识到支撑这道原和原上人的心理结构中性这根重要构件的分量,如果回避,将会留下‘秘史’里的大缺空。”揭露仁义道德背后的隐秘,撕开传统陋习中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发出“《贞妇烈女卷》里无以计数的女人不敢出口的心声”,还有“留在我幼年记忆里的那位逃婚者被刺刷抽击时的尖叫”。美人和肉欲,导演在高高举起之后,选择了一个最容易获得商业青睐的切入,很难说这是导演的虚弱还是投机。
陈忠实在接受相关《白鹿原》的电影改编的采访时说:“不光是她,中国式的欲望是一群白鹿原上人的欲望。里面还有白嘉轩、鹿子霖,他们都有各自的生存欲望。”亦即是说,田小娥的欲望要在其他各色人的欲望的映照中才能显现为有批判性的欲望,田小娥的性只有在“绝对中国”这一环境中,在男权礼教的压抑中,她的性才是武器、才有价值。
为实现这种诉求,田小娥与朱先生的神魔对立,与白嘉轩的礼教冲突就不可或缺。陈忠实就是在塑造一个“绝对中国的”典型人物,白嘉轩。而在电影中朱先生被全部拿掉了,而白嘉轩则是薄弱的并且是残缺的,其“绝对中国”的人物地位被消解了,只剩下田小娥。选取田小娥为线索人物和切入的视角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一个被取消价值内核后的“婊子”的视角终究支撑不起史诗性格局。电影忽视了绝对中国的塑造,弱化了礼教与情欲的矛盾,而仅仅把田小娥的欲望放到舞台中央,其实际意义最终只剩下色情媚俗。从此白鹿原上的繁衍生息和时代奔流,隐没在田氏的“奸情”里。于是历史和民族退缩到情欲背后,中国式历史或者命运,变成了“中国式欲望”。
不深入文化心理结构的内里,挖掘细节之处最激烈的冲突,而仅仅靠商业媚俗和所谓的大制作,终究不能长久。“电影和人生一样,都要靠余味定输赢”,真正的经典必然要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电影不过是冰山一角,水面以下有整个影视生产价值在支持,禁忌过多,主题复杂,价值观混乱的弊端在《白鹿原》的电影改编中展露无遗。《白鹿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难产。
“瘦身”后的公映版,造成的重大影响主要集中在结尾部分。小说里,《白鹿原》的故事一直讲到建国以后,而电影公映版的内容则在1938年被强行终止了。结尾整整删掉了20分钟,显得非常仓促,故事没有讲完就草草收尾。黑娃莫名冒出来又消失了,白孝文当兵走了不知下落。“根据电影局的审查意见,影片中删减的地方是跟白孝文有关系的,比如后来白孝文当了县长,到鹿子霖疯了回来后日本人的轰炸,电影在那就结束了,白嘉轩很困惑地站在烟雾里,这是一部分。再一个就是跟农会有关系的,比如砸祠堂,主要改的是这两个地方。还有些表现激情戏的地方短了些,大概就是这么三个部分。”于是,“中国式欲望”不仅镶嵌在作品中,更是弥散在商业生产与审查制度中。
三、审查制度: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
福柯的话语理论向人们揭示了在话语实践中隐藏的权力运作,“话语即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即权力。同样,权力即话语,权力的拥有意味着对话语的实现。”权力话语的意志体现往往是直接而且高效的,不合宜的直接删减,考虑故事的发展和结构是多余的,删去往往是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于是,电影《白鹿原》的删减也就是合乎法理的,然而抗战到解放的情况被整体删除使得结构上的前后呼应、地点重复和人物命运的衬托失去了价值,电影的结构性价值被消解了。“结构之所以能够携带着作者灵性的内容进行活性处理,全然在于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可容量和隐喻功能的构成,任何一个深刻的叙述者都不会轻易放过结构或忽视结构这种容量和功能的。”一个作品就是一个结果,它有一个完整的结构,结构的删改对作品造成的遗憾和困惑是不言而喻的。
小说《白鹿原》的故事在建国后结束,谋杀黑娃的白孝文因为策反有功摇身一变成为新政府的县长,而一开始干革命,发起过“风搅雪”运动,后来也做了土匪,最后“学为好人”的黑娃却被白孝文“正法”。共产党员白灵则在革命队伍内部斗争中牺牲,而加入革命党的军人没有在抗战而是在“围剿红军”中死去。而电影则是开头出现三个小孩:白孝文、鹿兆鹏和黑娃;末了,三个人的命运都没有交代,不知所终。前后失联,《白鹿原》的架构已经被完全破坏,父子反目是铺垫到位了,但上下两代人的传承关系只交代了一半,白鹿的传说估计也成了封建迷信。留下许多理不清的头绪,给人突兀的视觉观感,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线索被生硬掐断呈现出“头重脚轻、无疾而终”的硬伤,这硬伤不仅是编导对于全局把握的欠缺,更是审查删减造成的断裂性后果。电影以日本人飞机炸了祠堂草草结尾。走马观花式地呈现了白鹿原的半个世纪,而传说、乡约和藤条维持的威严全部土崩瓦解,挟裹一切人物命运的历史洪流,也成了田小娥的陪衬。
除了政治,《白鹿原》的删减当然绕不开情色。性是白鹿原的一个重点,一个连接故事的枢纽,一个反抗礼教的武器。陈忠实谈到在创作《白鹿原》时,曾给自己写过一个小纸条,上面有十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陈忠实解释,他刚开始写作小说的几年不由自主地以男性为主要对象,因为很长时期里,不同于西方小说写爱情里具体的性都是禁忌。但到了《白鹿原》的写作,以田小娥为重点,决定不再回避对性爱的描写,“不仅不回避,而且是撕开写”,要撕开“我们传统封建文化中最腐朽的黑幕”。然而面对大幅度的删减,作为硕果仅存的田小娥的性道具也不能幸免。从结构上来讲,“黑娃和白孝文,这黑白两个男人跟田小娥之间的戏剧扭结,是全片最有戏剧意味、最有人物情感冲突魅力的桥段。”从内容上讲田小娥的性承载了电影表达“中国式欲望”的寄托。所以,田小娥太重要了,重要到一旦被删减,整个电影的格局就大打折扣。
在当代电影史上,真正还原或者完全背离小说底本的改编电影都不多,电影制作者大多熟练地打起擦边球,在文学与政策以及市场对“黄”、“暴”的猎奇之间寻求平衡。导演王全安试图通过拍摄一部耗资巨大的史诗片来奠定自身地位,引领新一代导演的商业大潮。如果《白鹿原》完整版得以上映,其规模架势和残酷结局,绝对不逊色于他迎娶张雨绮的“鸽子蛋”。只是,正如刚开拍时外界的顾虑,《白鹿原》书中有诸多与性有关的描写,那肯定是审查忌讳,一旦去掉这些,拍摄《白鹿原》又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电影,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产品,其生产的过程自然从头至尾都将打上主流意志的烙印。电影是现实的镜像,主流意识形态和影视市场各种驱力的纠合会映射在电影中。于是,不管是史诗性的宏大叙事,还是苦难书写抑或是对于还原经典的耿耿于怀,背后除了影视制作者水平的千差万别和商业投机以外,还有强大的社会文化力量在推波助澜。按理说电影有着不同于文学的特性,电影改编是一个重构文本或者说创作新文本的过程。电影改编的首要要义在于遵循电影创作自身的规律。前面已经谈到过改编电影是独立于文学文本的新文本,和原创电影没有区别也是独立的艺术创作,电影是否忠实于原著本是个无伤大雅的问题。
《白鹿原》的电影改编暴露了中国影视生态的一个重要问题,经典作品一方面为电影制作提供了优良的素材资源和话语空间,但另一方面也为电影创作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原著小说的历史跨度这么大,电影呈现也已经是非常长的,在中国电影史上已是不多见了。要很细致很到位地把他们的人物关系和情节一步一步发展的逻辑关系都梳理得很好是很难的。”然而,“王全安对《白鹿原》的改编偏于保守,从中也可一窥中国电影屡遭诟病的缘由。在名著改编问题上,中国导演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不敢擅自大动干戈。一方面是中国人的中庸与理智作祟,另一方面则归罪于好莱坞模式的过度入侵。”既要以忠实原著为宗旨向前辈高人致敬,又要考虑电影文本容量的有限性,同时还要面临来自严肃作家的某些成见,“电影是非常糟糕的东西,电影给我们造成了最浅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最平庸的故事。”这无疑在一开始就为中国影视制造了强大的道德压力,当矛盾不可调和电影改编陷入两难境地的时候,电影编导也就只能敷衍了事了。不重视电影艺术创作的独立性,不尊重电影语言表达的特殊性,平庸在所难免。
比起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受众面更广,传播和接受也更为直观与迅速,更是一种群众艺术、大众文化,影响力是更大的。小说《白鹿原》在鲁迅文学奖评奖时就兴起了整改风波,作为电影的《白鹿原》也就更难,更敏感,受到的关注和审查也更严。可以说,公映的电影《白鹿原》是审查机构、电影市场和文学圈多方对话的结果。小说经典的电影改编就像是一面镜子,在从小说到电影的文化互动中,照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以及文化场域中的多元话语的竞争性对话。
四、结语
从1990到2010,“白鹿原”这一符号经过了不断的重塑,而文化生产的机制与作用方式就内嵌在文本的生成中。《白鹿原》的文学创作和电影改编就像是一个缩影,一方面昭示了时代精神与文学写作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则暴露了中国影视文化生态的几个的关键问题。一、无法实现的还原。影视文学作品很多改编自小说,因此保留原著的情节、意旨成了影视创作的一个焦点。然而受制于文本容量、电影语言表达规律、传播媒介、编导水平和市场需求等因素,还原成了难以摆脱的心结。二、流于形式的创新与政治、情色的商业投机。全力打造的人物形象只是吸人眼球的噱头,而叙事新方法则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意象塑造失去个性和实质,蜕化为可模仿的、雷同的流行歌词和礼品卡语言。三、主流话语的有效管控。半世纪以来文化管制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然而主流话语依旧保持着绝对权威。影视文化正逐步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主流。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研究对象从莎士比亚转向麦当娜,由诗歌小说进入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与市场诉求对于影视制作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在此视域下我们会看到来自主流意识、文学场和商业文化等不同话语竞相在影视生产过程中发挥效用,在一场——“谁是大赢家?”——的游戏中,冲突、对话以及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