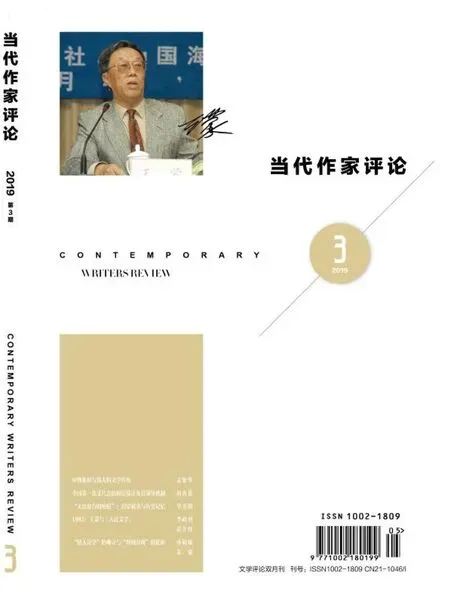有根的文学与“精神之岛”的塑造
——张炜文学版图中的儿童文学创作
杜未未 白 杨
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张炜忽然开始密集地创作儿童文学,先后出版了《少年与海》(2014)、《寻找鱼王》(2015)、《兔子作家》(2016)等作品,还将此前创作中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篇目修改结集,贡献出“我们小时候”系列中的《描花的日子》(2014)、“张炜少年书系”《林子深处》(2015),以及“张炜文学名篇少年读本”系列等作品。他内心中沉睡的那个顽童,在2011年创作《半岛哈里哈气》的时候被唤醒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同流俗保持一种紧张关系的张炜,在60岁之后表露出童趣而洒脱的一面,他说:“童心和诗心才是文学的核心。离开这两个方向,也就离开了纯文学的方向。”也许,读者不应把他的创作进行切分式阅读,因为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儿童文学正犹如恢宏交响乐中切入的一支轻快优美的旋律,相辅相成地展现了他文学世界的丰富与独特。
一、野物观与野地儿童形象:植根于齐地文化的文学表达
读张炜的儿童文学作品常会有种错觉,仿佛在听一位坐在村口大树下的老人讲故事,故事里有山野的精灵、与人逗趣的野物,有荒原里一代代人过熟了的日子,以及海风吹来的鱼腥气……他对于野物的认知态度有别于我们熟悉的写作经验,这些野物虽也有《聊斋志异》里花精狐妖神通广大的异能,但与《聊斋志异》重在语“怪、力、乱、神”的价值取向相比,张炜笔下的野物更多了一分随性或通透。这些野物也不同于以往童话里“与人为善”的拟人化动物符号,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思维,并不依附于人类而存在。如果说张炜在用野物讲述多样化的人类故事,显然是把张炜硬拽入了俗套,他并没有刻意把野物打造成人的意图,他只是在描述一个生灵和谐共存的世界,想要解读出大地孕育的其他生灵们有怎样的情感或自洽的逻辑。对他而言,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这个世界、对自然的尊重和信服”。而这种态度正来自作者从小耳濡目染,长大后更深入探究的齐文化。
齐地这片古时活跃着游学墨客、神秘方士、形色商贾的山水之界,直到民国以前仍旧“林木葱茏”,“再早的时候更是野气悍然,真有点古书上所写的‘人民不胜鸟兽虫蛇’的味道。”对张炜而言,齐地遗风对后代的滋养既外显为奇异瑰丽的传奇,也内化于安静却恣意的心境,他有着高度的“文化敏感”与“文化自觉”,“对给自己提供了丰厚滋养的文化传统有着无限的热情”,于是张炜以“深刻的激情”和“足够的耐心”,去发现生活中隐而不彰的要素,并由此建构起自成体系的文学世界。有了这种文化系统做支撑,他在不同作品中提及的野物故事,看似松散,实则具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关联,如同一棵巨树上各向舒展的枝丫,共同呈现了文化系统的丰富面貌。这一方面是作者在想象空间中复苏齐文化的有益尝试,因为“文化或文学传统是一个不断变化、流动的脉流,是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另一方面更使得张炜的创作成为一种有根的儿童文学,不仅扎根于孕育生灵的物质大地,也扎根于坚强恣意的文化齐地,我们或许可以更深一步将之视为文学地理学视角的考察。不过,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上,张炜似乎更注重给孩子们一个感受的机会,不刻意进行说教,而是从这贮藏惊人的素材、精神库存中取出最诱人的部分,让小读者们放心地沉浸在带有神秘色彩和童真童趣的故事里,在这片齐地文化隐了身、浓缩后具象成“像一只犄角伸入了海中”、“细细的尖尖的”的半岛上感受现实的另一种可能。鉴于此,张炜的“野物”书写不仅仅是写作手法的技巧性渲染,更是源于内心对复杂存在的好奇,这并非是对拉美“魔幻现实”的挪移,而是原生于此乡此地的现实主义书写,舍弃了民间传说在时代变革中被附加的“人”与“物”的不对等关系,复原出齐地文化里视为常识的“野物观”。他以一种“老实本分、口齿不清甚至颇有几分拙讷的讲述”方式,将齐地文化空间中的野物故事传神地表达出来。
有了从齐地文化中提取的野物观,“野地儿童”形象就有了跃然纸上的环境肌理,张炜笔下的野物身上最闪耀的“野”的特性也被赋予到孩童身上。学界常用“顽童”形象来概括张炜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少年,“作品表现出了努力挣脱成人社会,特别是正统教育的规约,在大自然和游戏中获得了身心的自由和解放的少年世界。”的确,“顽”是他们最显在的特质之一,是“野”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天然的灵动、恣意不羁的姿态、大地孕育的敦厚阳刚,以及时代磨砺下对苦难的有意钝感交织在一起凝练成“野地儿童”的复杂人格。这种“野地儿童”在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形象中自成一派。张炜塑造的“野地儿童”以原生性的大地故事为底色,一扫“乡土儿童”形象中固化的沉默与被动,又赋予他们“都市儿童”身上的活力和对生活的掌控力。这些长在乡土的少年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勇气,敢于对生活提出质疑,更不放弃探寻真相的时机,在荒野上咂摸出最为质朴的浪漫。
在“野地儿童”形象的塑造中,潜藏的反抗本能与朴素的善良本真交替主导着人物的成长进阶,《半岛哈里哈气》系列中的最后一个故事《抽烟与捉鱼》,正是“野地儿童”成长轨迹的缩影。在《美少年》《海边歌手》《长跑神童》等故事中与同龄人互动频繁,在嬉闹与坎坷中享受童年的“果孩儿”“老憨”长成了村庄里一伙孩童的孩子王,他们曾对大人世界观望不解,又暗中琢磨出自己的逻辑,然而这一次,他们真正介入了一段成人恩怨。孩子们得知神秘的“狐狸老婆”曾经夺走了“老玉石眼”的爱人,为了给看鱼铺的“老玉石眼”报仇,少年们设计打劫了“狐狸老婆”的小院,却发现相比于两位老人间的情仇纠葛,夹杂其中更多的是误会与无奈,于是少年们拿不定主意,“见了玉石眼以后,是否把报仇的经过讲出来?都有些犹豫。因为这事儿不但没有让我们产生多少自豪感,反而还有些心虚。”从善良出发的行为却得到非正义的结果,一点点的孩童式小聪明竟可能揭起他人封藏的苦痛,成人世界的苦恼、残忍、悔过无门好像突然间砸到了野地儿童面前。曾以为抽过了烟叶就算是长大的少年们陷入了从未有过的两难,打劫来的美食不再诱人,瓜干换来的美酒又让“老玉石眼”一醉解千愁,害得存在了40多年的老鱼铺失火。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少年们因为反思自我耽搁了回家的时间,在火灾中及时救出了“老玉石眼”,进而促成了两位老人言和的契机。可以说,他们救出的也是自己的童年,是踏入成人世界之前最完好无损的心灵起点,张炜在儿童文学中的仁慈正在于此。
二、讲述历史的方式:成人童话与儿童的接受边界
如果说张炜构建“野物观”与“野地儿童”形象,还停留在现实层面上对儿童文学进行思考,那么讲述历史的方式无疑牵扯着对真实层面的深究。客观地看,张炜在儿童文学中渗透的成年人思维与新历史主义史观,使得其笔下的儿童故事带有一种“成人讲童话”或“成人式童话”的特质。
虽然《半岛哈里哈气》和《你在高原》的基调、主题截然不同,但由于都是建立在个人经历之上的书写,两者之间又难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主角宁伽与果孩儿有着共同的家庭原型,即“老仆人留下的丛林小屋”+“犯错缺席的父亲”+“慈爱隐忍的女性亲属”的叙事背景。在《你在高原》系列中,作者选取近似于成长题材的小说要素,以成年人的理性深沉讲述了一个家族与一代人的时代际遇,如果说“成长叙事的精彩之处,在于作品表达出成长主人公丰富的心理变化与精神升华过程,充分展现出生命应有的潜质与可能性。”那么宁伽作为家族纵向叙事和同代人横向叙事的交点,则侧重于窥探着命运的悲欢沉浮与人性的激情和冷漠。其中男仆清滆开辟的林中小屋到了《半岛哈里哈气》里,更为接近自然,接近野物,少了人际间的倾轧,多了稀释苦难的恬淡,成为主人公温暖回忆的主要源头。
《你在高原》中宁伽在心理上对身世和父辈的事迹处于一种妄图逃避但又避无可避的困局,但在《半岛哈里哈气》和《少年与海》中则是对少年时期单纯欢乐的回忆碎片进行拼接加工,呈现出一段段纯净透彻的童年叙事。如对“打鱼”情节的描绘中,《你在高原》系列的首部作品《家族》中宁伽回忆幼年时为了追逐小兔而“向着大海跑去”,在孩子的欢呼声中“我一抬头看到了从网绠那儿射过来一道目光……父亲正盯着我”,他看到的是“瘦弱而干硬的父亲被人赶到了大海边上。那是一种单调的苦役在等着他。焦烤的白沙之上、火毒的太阳之下,夹着一群浑身赤裸的男人,他们都伏在一条粗长的网绠上。海上老大手持一根棍子,有时击打绠绳,有时直接把拉大网的人打倒。惊天动地的号子声压平了海浪,在骇人的号子声中,那些人像蠕动的蚂蚁。”宁伽的感受是“憎恶又好奇,还有一丝奇怪的关切”。父子间的隔阂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渐渐消磨,而在年幼的儿子心中仍是一种负担,看打渔这种消遣也不是纯粹的消遣,更像被派去盯着一直对父亲虎视眈眈的厄运,即便无力制止,也只能以此让家人略微心安。
剔除父亲带来的心理压力,张炜用回忆绘声绘色地营造了一个当代孩子们已经陌生的有趣场景,将童年记忆中的美好进行提纯。除了情感基调上的简化与美化,看撒网、听拉网号子、排队喝鱼汤……这些多次出现的同质内容与《你在高原》系列相比较,写法上也更加纯朴。我们很难界定哪种写法更精准,对于回忆这种个人史的言说,心理真实远远大于事实的还原。张炜在《半岛哈里哈气》中突出语气词,模仿儿童的组句方式、认知顺序,使文字通俗、浅显、强调动作性。由此,即便《你在高原》与《半岛哈里哈气》的诸多情节发生在同一个现实空间中,但由于有了儿童视角的转变,《半岛哈里哈气》等作品中的情节变得富有童趣,追求纯粹。在近20年的创作中,张炜愈发执著于用生命进行书写,又顽固地书写自我生命,他逃不开童年时期的阴影与暖色,索性就不逃了,一心一意地将儿时记忆与成长际遇中的真实,混杂着隐喻和想象,建构出属于他的山海人间。
张炜终究是一个肩负着道德高度和人性关怀的知识者,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文字风格的轻松恬淡并不能抹杀他深植血肉的对生命本质的探寻。在《半岛哈里哈气》中,主人公老果儿孩的“父亲”虽未缺席,与“母亲”“外祖母”共同成为“我”童年生活中不可抹杀的亲情因素,但也依旧被塑造成“犯过错”而谨言慎行的知识分子。由于父亲身份的时代特殊性,老果儿孩比一般的儿童对人情冷暖有了更深切的体察。于是,越来越俊美的老果儿孩,得到的只是父亲的规劝:“我们家俊不起啊!你生在这个家里,就得往壮里长!”父亲体察了时代的喜恶,连带孩子也不可以“招眼儿”。张炜是善良的,但也有坦诚的残忍,作为他笔下的主角,少年也需识得愁滋味,与其说张炜用儿童的视角窥探了一段历史的缩影,不如说他用亲身的体悟再现了时代的一个侧面。张炜谈到写作状态时曾说:“有时一个写作者的全部行为,好像只为了取悦‘另一个我’。”那么书写儿童文学时,坐在高处俯视着他的“另一个我”,想必有着他年少时的烂漫心性和顽皮,又有着历经世事后的通达透彻。同时,“转型、变化、复杂、不确定,对作家的认识和呈现都是一种重大的挑战,而张炜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作家”,儿童文学中的历史言说,也是他更新自我书写经验的一次出击,他要用少年的口吻识破大人们的伪善与困惑,讲出涤清后的真实。
除了个人历史的言说,讲述时代史、民族史的方式所挑战的不仅是成人童话的接受体验,更是儿童读者的理解深度。生活在哈里哈气半岛和林子深处的少年们身上都映着张炜和同代人记忆的影子,成为那个不可说的时代最无偏见的见证人,海边抓特务、听老人讲打土匪、开忆苦会时硬逼着自己哭……他们不是又红又专到形象固化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也不是受苦挨饿苦大仇深的可怜娃;他们有着所有时代孩童共有的顽劣、善良与烂漫,又要在坎坷面前保持一颗坚韧宽容的心;他们无意去界定苦难,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包容了挫折与不公,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儿童式的幽默,态度严肃、观点清奇,看似一派天真却又隐隐撩拨真相。
张炜多次强调“文学”是作家唯一的信仰,划分“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只是“研究者和出版者的事情”,这种创作观也决定着张炜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既注重寻找符合儿童阅读习惯的艺术形式,也在选材和深度上不避讳深刻主题,不有意进行低龄化叙事,相信并尊重儿童的审美能力。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张炜一方面很放肆,任由这个回忆美化出的半虚构空间随性而为;另一方面他又前所未有地克制,他一贯用浪漫、张扬、恣意做着修葺的活,修葺被物质过度侵吞的现代文明,修葺被掩于千年风尘下的齐地文化,修葺被商业主义腐蚀诱惑的人心。而这次,他要用乐观夹带沉思,用幽默包裹苦难,直面精神上嗷嗷待哺的儿童与少年,这次不是修葺,而是从零到一的建构,如果可以,他还想带着不同年龄、不同理解深度的读者走得更远。
于是张炜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有着引导儿童探求自身接受界限的能力,看不到历史深处的孩童可以在故事里感受温暖,获得勇气;对历史有了模糊感观的少年可以获得以史为镜的不同视角;对有更深理解需求的读者,一样可以在故事的导向中发现历史与现实的交界。张炜很少选择当下儿童作品中极为热门的单条主线叙事,他的故事讲着讲着,主目标之外还会闪现无数不甚明朗的分支,小读者可以搁置这些支脉,也可以在积累了更为丰厚的阅读经验后回头思索,而这正是生活最本真的面目。总的来说,这是一些可以陪伴并引导儿童读者自我进化的故事,这种文学与史观交叠的艺术,从当下儿童文学出版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冒险的,但是在代际进化越来越提速的今天,儿童文学的目标受众对于文学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不同时代的同龄人接受能力并不相同,我们不能只相信顽童,也需要正视智童的存在,儿童的接受能力、接受底线可能正远远高于我们的预期。
三、精神之“岛”:空间意象的多重指涉
地质学专业背景和长期的地质考察经历使得张炜对地理空间有着远超常人的敏感,无论是原乡化的芦清河畔,还是《九月寓言》中互为他者的平原与山地,再到《你在高原》系列中精神与地理的双重高原,山、海、平原、高原、丛林……作品中多次出现的一系列地理意象都日渐成为学界解读张炜作品的着力点,然而在这些意象之外,“岛”意象似乎因为文本体量上的不突出,很少受到关注。但实际上,在张炜2011年后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此前的儿童视角叙事中,“岛”恰恰是极为关键的精神航标。
空间上的“岛”本与大陆具有同样的陆地属性,是人类及其他生灵的安居之所,但又与大陆有所隔离,成为神秘海洋中更为神秘的所在。所以,“隔离”与“神秘”即是张炜作品中岛的初始设定,无论是张炜新出版的旧作《狮子崖》中有着可怖山洞的狮子崖、主角被海豚带到的无名小岛,还是《兔子作家》中眼镜兔海上探险发现的由金龟子做岛主的荒岛,儿童文学中的岛均被张炜作为少年好奇心的寄托。但是在让文学形象登上岛屿之后,作家又有意对岛上生活的“神秘”进行日常化的化解,这里的岛并不是“他乡”,而是“此地”奇异的一部分。
而在张炜自身的创作轨迹上,儿童文学作品也如同张炜文学版图中的“岛”,在此前以儿童视角进行叙事的《鹿眼》中,作者刻画了两个“岛”的符号,一是传说中的岛,有着小海神的庇佑,野物长生不老宛如仙境。另一个是现实中的岛,由大公司投资建起了休闲别墅和娱乐设施,但光鲜背后却是罔顾伦理迫害少年的罪恶之地,“那个海岛留给唐小岷的是一生难忘的恐吓和屈辱。这与她的向往之地相距太远了:岛上不光没有一个天使,还遍布着魔鬼。”这两个“岛”意象,一个从正面描摹作者以自由、恣意、宁静为主体的精神追寻,正如同张炜在儿童文学作品中进行的积极展现;另一个是从对现实的深度剖析入手,剖解异化的人心,鞭笞暗中滋长的罪行,而这又是《鹿眼》等结合了儿童视角叙事的成人文学的主题。因此,张炜的儿童文学之于此前的成人文学创作,无所谓回归或转向,本身就是文学版图中具有同一性的一部分,它在艺术手段上的些许隔阂,在主题基调上的刻意乐观,都容纳着作家精神领域提纯后的美好愿景,而这种对于“曾经拥有而又失却的美好”的回顾、反思与追求,就是张炜秉持多年的文学母题,也正是解答张炜为何创作儿童文学的核心要素。
从“曾经拥有而又失却的美好”这一精神对象出发,张炜半个世纪以来的写作脉络可以视为是返回人类的童年期的实践。他回望农业文明时期大地的原始生机,与人类曾经赖以为生的野地精神气质,对现代文明加以反思,这也是包括《你在高原》在内的众多文本的共有母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张炜“回头看”的姿态太明显,对商业、物欲、城市的拷问太猛烈,于是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读,那就是张炜似乎对现代化、对技术发展有着暧昧的拒绝。张炜反对的并非现代主义本身,更不是反对技术的进化,而是警惕着物欲过重的商业文明带来的伦理缺失与道德退位,如同他在《棋形不好》中讲的那样,棋技精湛的老者“赢了棋且棋形好看,才是最高兴的事情;输了棋但棋形尚好,也还不错;最糟糕的莫过于出现一个丑陋的棋形了,这时无论赢输都让他败兴”。所以对张炜而言,他批判的绝非输赢,而是好坏,气质、道德、风度这些抽象精神层面的好坏。别有深意的,是老者棋艺日渐精进,后来只要摆出好的棋形,自然就会赢棋。应该说,张炜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与现代性的探讨是一致的,都是“好”和“赢”的共赢,只是在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上,他认为“好”比“赢”更加重要。
张炜对儿童文学的书写正是这一脉络的延续,从人类的童年具化为人的童年,更细化为最熟悉的个体的童年,用儿童文学来辨认少年时的小聪明和成年后的大愚蠢。在张炜看来,成人臣服于成人的逻辑,即耽溺于商业主义、物质主义,追求低成本、高产出,牺牲质量更不顾精神风度的道德悬置。而只有儿童才葆有无污染的灵性,才能在自然的逻辑中反抗绝对化的利益至上。当然这并不代表张炜笔下的儿童文学传递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漂浮的纯真,作品中的小主角们也有着自己的“世故”,但他们内心的小算盘绝不包括过于奢侈的报酬或欲望,他们是还没有被成人逻辑收买的一群。张炜并不把“世故”作为一种负面人格,世故反而成了魅力的锦上添花,作者赋予野地儿童的,正是这种不浓不淡、不失善意的世故与另类的通透。
在精神追求的选择上,《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寻找鱼王》等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山野纪事,一扫张炜以往作品中混杂着悲悯的残酷,但张扬着一以贯之的恣意浪漫。无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灵动野物,还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乡村平民,每一个生灵都鲜活地跃动在记忆中的山林海滨,抚慰着这颗见过沧桑的游子心。就像历经狂风骤浪的颠簸洗礼,也会留恋靠岸的时光,这些深埋心底的温暖故事,成了张炜笔墨耕耘中最静谧的不冻港,他可以修补起残损的记忆,给自己一点心灵的慰藉,一点温暖的念头。对于张炜此前同根同源的成人文学创作而言,这些以宽恕抚平伤痕的文字并非解构,而是补偿。
四、“了不起的大事业”
“茅奖”作家写儿童文学,作品一经问世就注定被置于聚光灯下。书评人和出版人丝毫不肯浪费张炜的名气,《寻找鱼王》封面上赫然印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张炜最新儿童文学作品”,“书评”“获奖消息”频频见报;教育界也不甘落后,《描花的日子》等作品中的篇目多次变成了各地各级考试的语文阅读题。然而,社会各界对张炜儿童文学创作的热闹应和,很容易将他对儿童文学写作的认真思考淹没在商业化宣传的声浪中。对张炜而言,“比起数字时代浑浊的文风,坚守着儿童文学、自己的童心与诗心,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业”。其作品中凝聚的野物观、野地儿童形象,大胆挑战儿童接受边界的讲述方式,以及由创作轨迹自然生发的精神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对当下少年图书出版状况与少年阅读教育现状的一种“抗拒”。
张炜正视“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的差异,不介意用儿童视角进行更广阔的写作尝试,他坚持把“儿童文学”视为“文学”的一分子,用纯粹的文学态度进行创作,并不因为受众对象的低龄化而在文学素养上有所轻视,更坚持“如果只是成人眼里的肤浅读物,那就一定不是‘儿童文学’,而且可能什么文学都不是”。
在文学发展史上,成年作家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事例并不少见,国外有奥斯卡·王尔德、马克·吐温、塞尔玛·拉格勒夫等作家同步进行儿童文学创作与成人文学的革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有周作人、茅盾、冰心等人,在新文学理念下书写了诸多具有开创之举的儿童文学名篇;然而到了当代文坛,儿童文学却一度面临着失语的困境。这种失语不仅体现在创作中,更体现在儿童主体缺少发声的途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儿童从被忽视到被发现,如今却险些在约定俗成的偏颇观念中再次被遮蔽。在文化的进程中,凡不可自主发声的必将被代言,而后在代言中被误解,同质内容竞相模仿,职业写手远远多于专业作家。与此同时,就整体创作态势而言,强调儿童文学作品“内容的广度、艺术的高度和思想的深度”,也正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超越传统范式和商业局限的重要契机。”
整体观之,张炜的儿童文学提供的是与世界沟通的媒介,而非对世界的最终呈现,在这片山海人间中,显性的是自然、顽童、苦难与幽默,藏起来的又有根植于齐文化的精神气质、言说历史的方式、介入当下的姿态。张炜用对个人历史的一次提纯,给生活得刻板局限的当代少年一个窥探过往的机会,看到一片野地上,野物和孩童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也用对人类历史的回顾给本土儿童文学的深度书写提供了一次经验的积累,给自己追求恣意、享受安宁的齐地精神版图添上了纯净的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