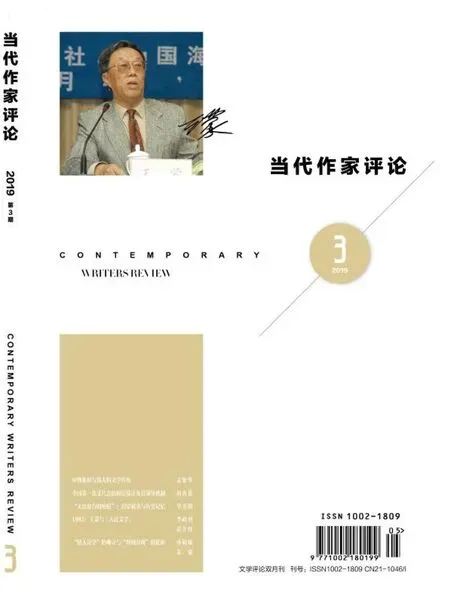“情人诗学”的确立与“地域景观”的延展
——评雁西诗集《致大海》
孙晓娅 朱 瑜
雁西是一位拥有纯粹的诗心、高洁的灵魂和对世界充满爱的诗人。他游弋于主流诗坛之外,以使徒的朝圣之姿坚执于一个古老的话题——探寻爱的终极意义。他的新诗集《致大海》,是丰盈的生命独白,诗人以“爱神”之名对后现代语境中拟像化、碎片化生存空间进行了个性化的整合,温和流动的诗情如大海的波澜起伏荡漾,回荡并召唤着纯净神秘的人间情愫。《致大海》延续了诗人细腻婉转的创作风格和饱满的人文魅力,亦彰显出诗人努力拓展诗写空间的艺术实验和探索精神——诗人有意或无意间构建了极度私密化和缠绕着神秘情感的“情人诗学”和地理景观。
一、爱从大海的镜面升起
《致大海》曾是俄国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反抗暴政独裁,讴歌自由和光明的政治抒情诗,以同题为诗集命名,可见雁西对普希金的喜爱。不过与普希金将大海作为自由精神的象征和知音、借大海自由奔放的壮美形象表达渴求自由的愿望不同,雁西在其诗集《致大海》中构建了一个以情人为轴心的抒情主体,主体我与世界万事万物是热烈平等而相互爱恋的情人关系。诗人毫无作意和遮掩地向这个世界诉说自己的爱情经验乃至爱情想象。诗中的“爱人”,代表情人的不同面向和想象,可以是美丽柔婉、体贴知性的女子,也可以是生活中所有触及其情思的景物人事,那些没有生命和身份归属的客观对应物,被诗人赋予了情人的性格与美好的形象,她们纷呈而迥异的个性色调。笔者将这种诗歌观和创作经验称之为“情人诗学”,它虽然不绝然独属于雁西,不过确实是雁西将这一诗学特质发挥到得心应手的境界。多年的诗歌创作中,雁西有意忽略事物本身所存在的自然属性或物理属性,以丰沛的想象给予其一定的社会属性、人类情感能事,大海、雪花、树木花草山石……不一而足,它们以情人的身份介入诗人的情感世界,诗人自如出入其中,尽情表达他对女性的尊重,对日常事物和自然景观抱持的“爱”的感受力,不断升华他对这个尘世平等浓烈、细腻缠绵的爱。“情人诗学”的确立看似和郭沫若的“泛神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在诗性思维方式上存有一定差异。在郭沫若看来:“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人到一有我见的时候,只看见宇宙万汇和自我之外相,变灭无常而生生死存亡的悲感。”两者创作思维的同一性在于都追求“泛化”,郭沫若基于“泛神论”思想的诗歌创作,是以一种“万物皆神”的姿态面对世界,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郭沫若打破旧式思想与审美的束缚,创作出《女神》等灵逸飞动,洋溢着破坏力的“开一代诗风之作”。雁西绝非模仿郭沫若要将世界“泛神化”,而是将一切“泛情人化”,构建一种“万物皆情人”的诗学空间。
从诗歌内容来看,《致大海》以表现爱、亲情、爱情观、人的尊严和价值、个体神秘的生命直觉和体验为主题,呈现出美丽又浪漫,崇高又忧伤的审美风范。费瑟斯通在《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文化》一书中曾提及,“西方国家审美化的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艺术亚文化的兴起,二是追求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三是日常生活符号和影像的弥漫。”在第一点中,费瑟斯通强调“艺术亚文化的兴起认为艺术无处不在,一切事物都可以进入艺术的范畴,成为艺术或审美的客观存在,并且追求突破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线”。以此审视雁西的“情人诗学”,他打破“日常生活符号”正是遵从心灵的呼唤去“追求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行为,他将对“爱”的多样想象嵌入诗歌创作体系绝非一种抒情传统的简单延续,而是富有突破意味的心灵构建。在《日月潭,什么时候我们再见呢》《孔雀从红酒中飞来》《是你?》《小雪》《立冬的柿子树》《牡丹花都开了呀》《等着你》《珠穆朗玛峰上的一对鹦鹉螺化石》《致一块女神石》《桂花香》《致大海》系列诗篇中,他突破通常意味的爱情所指,“情人”无所不含,诗人与这个世界建立起亲密一如的“爱情”关联,被诗性化了的“情人”不再具体指某一人或物,诗人把“她们”纳入自己的审美范畴和情感想象世界之中。
在诗中,诗人以情人之间的絮语方式倾吐出“我”对“你”永恒的眷恋、信任和理解,“你”时而是最美的女神,周身闪耀着金光又神秘变幻;时而如女王激情奔涌舞蹈于海上;时而如多思的少女温情忧伤;时而是胸怀世间万物的大爱者,眷顾着每一寸山河每一个生灵。诗人以情人的口吻创设了一种浓烈的爱的语境,这里的“你”指涉大海,大海兼具了诗人所爱慕的情人的多重化身,大海既呈现出其本身的自然属性又烙印着诗人赋予它的女性情感、性格,被抒情主人公人像化为不同女性的形象。
对待女性,雁西始终秉具理解尊重和温暖关爱的情怀,雁西的诗学体系中不存在两性权力的分野对峙或从属被动与主动的关系,他以平等欣赏之情主动理解和赞美女性,有时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不乏其性格的侧影,诗人善于自我营构两性的对话场景:“可是/我要问/为什么叫小雪/这么美的名字/看着你成片地飞落/我端着酒杯/打开门/让你落入杯中/与我同醉/不冷了吧/可是你化了/我害了你”(《小雪》)。新诗中较早把雪花拟化为女性、恋人的是徐志摩写于1924年的《一朵雪花的快乐》,但不同于徐志摩笔下热烈清新的雪花,雁西细腻轻柔地刻绘出化身为单纯静美女子的雪花降临到这个世界后短暂的遭遇——这也是诗人生活中一个细琐的片段。小雪与诗人在雪天邂逅,彼此温暖慰藉,点燃寂寞的心灵,却也带来了生存形式的毁灭。将客观物拟化为女子——诗人的情人,既尊重其本来的属性特征又赋予恋人的美好形象,同时抒发“我”对“她”的爱恋或情感交流,三者兼顾是雁西“情人诗学”的核心框架,再如“我吻过之后你也吻/或是脸贴着/咔嚓照一张相/开心的/嘴唇有些粉/像蜜蜂叮过的蜜/挺好的/继续等着/你这只科尔沁草原的蝴蝶/你也在等吗”(《等着你》);“但你坐在这里/等谁/就是为了你我的这一刻相遇/我想说:别悄悄地流泪/我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片海/哭吧/为你我的再次重逢/这片海/足以盛下你全部的泪”(《致一块女神石》)……不论是小雪、蝴蝶还是女神石,诗人都着力赋予小雪、蝴蝶、女神石以女性身份、女性的情思与形象。完成了身份的置换,诗人一起笔就以情人的口吻对“她们”倾吐内心的爱慕、相思或怜爱,对万事万物葆有情人的诗意和温度,仿若恋人间在诉说缠绵的情怀,实则诗人在传达他对世界的热爱。仅就这一点来看,雁西的情人诗学非单纯情爱的抒情,是充盈情感与心灵的表达策略,明显有别于聂鲁达的爱情诗。雁西笔下的“你”非指代具体人物,从创作心路来看,与其说雁西尊重、依恋美好的女性,不如说他热爱和倾心感怀于不同形态的美好生命。
诗歌是表达人世间最真实的情愫与最朴素的真理,别林斯基说:“诗歌通过外部事物来表现概念的意义,把内心世界组织在完全明确的、柔韧优美的形象中。”雁西以大海为核心意象进行主体情感的观照,大海如恋人般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最幽微的情感和无有边界的爱。雁西与大海相互倾吐,他们之间单纯净澈又奥妙深邃,两个维度的爱天衣无缝地连缀在一起。大海和抒情主人公是如影随形、同频互涉的恋人,大海一方面给予诗人灵感、慰藉和胸怀,另一方面被诗人赋予了恋人身份和不同的生命属性,还时而闪现出诗人的感悟情思,作为读者,我们也常常分不清它或她或他,但这有什么影响吗?
雁西在《致大海》的序言中写道“海是一首无穷无尽的长诗”,“从别人眼中的海,体会自己心中的海,海是充满人性的,与人类和生命息息相关,在‘海的故事’,我对于海的浪漫、海的情感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海像我的老师,也像是我的知己。海引领我们走向广阔、博大和自由,使我们更爱这个世界,诗人不仅有小我,更应该像海一样有大我,努力构造一个诗意的大境”,“大海,人海,心海,只有爱海、懂海的人才会真正像海一样辽阔和无限”,诗人绝非停留在以我观物的界面,他通过大海反思和观照人的生命意义、人生的格局和境界,通过模拟或亲近大海的情绪感受外部世界,海岸的绵延也是诗人崇高的爱情追求和真挚的情感的衍生——“我又听到了舒婷的《致大海》,感受到人与环境的不同,心情的不同,海也不同,诗也不同”。大海浪漫,令人心驰神往;大海深邃,变化莫测,它是理想与现实、怀疑与信任的综合体,它用自身的包容和仁慈接纳了作者无数的爱恨离合悲欢之绪,正是大海的特质,让诗人成为其坚定的追随者。
日本当代文论家浜田正秀如是定义现代抒情诗:“现在(包括过去和未来的现在化)的自己(个人独特的主观)的内在体验(感情、感觉、情绪、热情、愿望、冥想)的直接的(或象征的)语言表现。”大海是雁西内心体验的外在映照:“海”本体意象的博大浩瀚承载了诗人个体复杂丰富的主观情绪,契合了诗人感性的心理特质,跳跃着诗人的情感律动,诗人把自己对爱情的感受,通过大海这一意象,化为诗情流淌出来,偶尔,波涛汹涌的大海扰乱了诗人的思绪,诗人在骚动的大海面前如此渺小又苍凉,悲观怀疑暗滋增长,诗人思索着自己在爱情中的位置,往事的迷茫、现实的失落痛苦交织在大海的面前,深深的“被弃感”油然而生,于是诗人把自己的爱情、理想、痛苦诉诸大海,把爱人毅然离去的无奈、爱情转瞬即逝的痛苦、自己人生的追求、遭遇和忧患毫无保留地告知大海(《致大海》之三、《致大海》之四);大海成为诗人精神空间的独立部分,成为作者放逐自我情绪和表现爱情困顿的重要组成部分(《漂》《岸》)……雁西诗中的大海,不仅是真实的海,还是心灵的大海,情感的汪洋与独立的诗学品格互为熔铸,从某种程度上说,“大海”这一意象成就了雁西梦幻般的真实,洒脱灵动的诗歌品质,两者摩擦相生出灵魂的声音,亦如上个世纪30年代陈梦家所言:“抒情诗好比灵魂的底奥里一颗古怪的火星,和一宗不会遗失的声音,一和我们交感以后,像云和云相擦而生的闪电,变成我们自己的灵魂的声音,这真是自然的奇迹!”
二、丰沛浪漫、深情绵密的美学风格
诗人华兹华斯坦言“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无论是在画作还是诗作中,雁西都饱蘸深情,任浪漫绵密的情思自然流泻,他的诗不乏小小的感伤与忧叹,不过整部诗集被热烈光明的情愫以及宇宙生命间神秘低语的对话或倾诉所萦绕。雁西的好友袁贤民曾在文章中说道:“雁西说,不错,诗言志,但更应该言情、言爱,一个真正的诗人,首先是人民的诗人,只有对这个世界充满暖暖的爱意,你的灵魂才能得到升华,赢得诗神的青睐,你的诗篇才能浪漫、纯净、唯美、刻骨。”雁西也曾在访谈中说道:“我一直认为诗言志,更言情和爱,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对这个世界充满深情的爱,有爱才有诗,有爱便有一切。我认为世界上最美的诗歌一定是情诗,尤其是爱情诗。”雁西是立志对这个世界写情诗的人,《致大海》中,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至纯至善的“诗神之子”,一个与“爱海”共享秘密的纯情诗人,一个以“爱”之姿态进入生活的独语者,一个对爱人、父母、对海南、对老街道甚至对一草一木、自然界的生物都充满悲悯之心的生命歌者,一个边走边留下鲜花与柔情蜜意的爱之匠人。他独抚竖琴行吟海上,为我们留下大海一般透明、璀璨、热烈的诗句。
整本诗集共有九辑,均展示出缠绵细腻的诗美品格,第一辑到第六辑的代表诗作《我是谁》《我的灵魂呢》《我往哪里去》《我活在你的影子中》《早恋》《印象森林》《月亮,时间的钟盘》《到此为止》《宇宙树》《在世界的每一天都爱你》中,雁西以审视者和叙事者的身份,与所见所想交换情思,浪漫的情感和婉转的语言绝妙地跳脱在读者面前,浪漫的“爱情”成为诗人写作的美感基调与创作源泉。
第七辑中雁西进一步延展了写作空间,亲情和乡思在凝神静听处迸发,《母亲》《父亲》《安魂曲(组诗)》《一滴水》《乡愁》《江南》《池孜坑》《故乡,在任何时候都最亲》等诗中,诗人在时间的长河中体会父母以及故乡因时间流逝而带来的诸多变化,饱含诗人对亲情的依恋、对故乡的眷念。对父母和家乡的深厚感情,流溢着广博的爱和炙热的亲情,诗人以平静的心态超越现实的苦难,在理想的境界中寻求精神的寄托。
在第八辑和第九辑中诗人从个体生活经验和情感诉求中跳脱出来,在《致李清照》《致黄公望》《致王羲之》《苏东坡:我的海南日记》《像雪霜一样,这冷白的头发呀》等诗中,历代伟大的诗人或书法家成为文化符号,承载着诗人的阅读经验、人生感悟、精神寄寓,以及对命运、历史的反思。雁西对文化葆有情人般的拥抱姿态和热情,他以情人热恋般的眼神穿越于历代诗人所留下的诗歌精神,并重新构建起深邃的阐释空间,诗人以对话的姿态重新挖掘黄公望、李清照、苏轼等伟大诗人和艺术家的精神世界,从当下的视角反思他们在历史中的文化意义和人格高度。这一部分的诗歌语言保持了诗人一贯的浪漫深情,又不失庄重的历史感,两者和谐统一,形成阅读的张力,给人以心灵触动。
雁西善用繁复的独白体,深情絮语中蕴含了生命智慧,浸透着思想的深度,有些诗歌还展示了从自身生活和危机中所发掘的困惑、迷茫。深情绵密诗思中交错着冷静理性的反省,带我们穿透表象叩寻人生的真切处境。
“在诗的历史中,我们目前正面临一种不寻常的、唯一的现象,这就是不论哪一位诗人,都在自己所处的一隅,用自己的笛子,吹奏自己所喜爱的乐曲。”从乐音的独特属性上看《致大海》这部诗集是由钢琴和小提琴合奏出来的交响乐和小夜曲——“这本诗集,我的一百多首诗歌作品,是在海南创作或写给海南的诗,是大海的抒情诗,唯美、浪漫、纯净,既像小提琴般的小夜曲,又像交响乐般大气浑雄,表达了我对海南深深的爱和故乡般的情怀。”同时被诗人用画笔调染出童话的色调,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幻想,拒绝丑恶与黑暗的正义散发出金色的光芒,人以童话世界的爱来理解和进入日常生活的碎片。在《你呢?你在哪?》一诗中,诗人用具体的“时间点”寓意着生命和爱犹如清早一般美好和升腾,随后置入“手机”这一“现代”媒介,隐喻着物欲时代诗人对爱的执著和坚定不移。雁西对世界的爱是如此的浪漫多情,他甘心停留在纯粹的童话世界中,以纯透的诗心经营爱的世界(《牡丹花都开了呀》《桂花香》)。作为爱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纯真信念无异于精神的守城,虽然《致大海》这部诗集不乏作者对已逝爱情的祭奠、对亲人去世的伤悲和对生命存在意义的哲学探察,但整部诗集统摄在深情浪漫的爱的氛围之中。
三、以“海南”为轴心的“地域景观”
追溯中国诗歌发展史,从先秦《诗经》《楚辞》到唐宋“山水诗”“羁旅思乡诗”“边塞诗”再到明清“边塞词”“记游诗”等,诗歌与地理结合,成就不少经典篇目。百年新诗发展史上,许多诗人的写作也是从自己最熟悉的地域起笔,几乎每一位诗人都有关乎故乡或熟悉的地景之作,不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还是工作了数年的“居住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在诗人的精神世界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由此成为诗人创作的灵感源泉,也成就了不少诗人的标识性作品。
在雁西的生平中,海南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其诗作重要的“地域景观”,雁西两次入海南的经历使他对这座城市滋生别样的情感:“我很感激命运之神对我的厚爱,这种城市的转变,使得我有着比别人有着更多不同寻常的经历,其中包括爱情。”海南是一个海岛,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人文环境也具有大海般宽容的品质。正是远离内地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中寂寞失落的人文环境,使雁西爱上了这里的自然之海和人文之海——“诗人在时间中向大海致敬”。接下来,笔者从“地域景观”的维度考量其笔下的海南的诗学蕴含。
“地域景观”是近年来诗歌研究的一个前沿话题,现实中的“地域景观”被诗人接受之后经过个人情感的溶解,内视化为诗人的心理景观,承载着诗人主观色彩的标志性物象,化为诗人创作的“风景”,反映了诗人的心理和情感的波动,形成带有诗人个性印记和其独特风格的“文学装置”。同时,这一手段和策略的运用,既表现了特定区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又为诗人们的写作提供了鲜活的题材。雁西的《致大海》是建构现代意义的诗歌地理的一次实践,在《我在骑楼老街等你》《我经过海棠湾的时候》《海南的灰尘都是干净的》《海口,我就这样把你当故乡》《时间的玫瑰》《海的故事》《东坡海南》(组诗)等诗中,海南的“地域景观”在诗中密集出现,诗人不断将“地域经验”纳入“情人诗学”的体系之中,构造出“情人诗学”视域下独特的“海南地景”。客居在海南的诗人沉湎于引发其心理归属感的景观之中,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客居身份而对海南的大小城市以及自然文化景观产生疏离感,恰恰相反,“椰树”“骑楼老街”“红树林中的鸟”“沙滩”“世纪大桥”等地理景观让诗人产生了无限的亲近感和身份认同,这些意象随之被镶嵌进诗行,如同精灵一般跳脱纸背,就连“海南的日光和月光”都被诗人想象成了“父亲和母亲的目光”。由是,诗人对海南交汇生发出诗意和崇高的爱与理解,他已然把海南当成了精神故园,灵魂归属的土地。
美国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过“恋地情结”,即“恋地情结并非人类最强烈的一种情感。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我们便能明确,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以此观照雁西对海南的审美书写,有利于进一步挖掘诗人情感的生发原点。雁西曾说“海南的美无处不在,用任何语言赞美都不为过,海南是一块净地,是充满诗意的海岛,可以称之为‘诗歌岛’,能在海南岛生活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诗人们应该到海南来”。雁西把海南作为一个文化意象符号融入到诗歌中,借助海南这一文化意象彰显其自身的美学判断、情感寄寓和个性心理,反之他也为这一文化意象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诗人用特有的语调,倾诉着这座城市带给他的回忆,不见浮夸的抒情,只是深情款款地述说,作为“第二故乡”的“海南”始终叠合着诗人丰沛而深情的生命感怀:“说实话/是我已经移情别恋/爱上这片海/蔚蓝/湛蓝/蓝得海天不分/不想回北方/北方雾霾/冷得风中抖缩/冷地心也巴凉巴凉的/来吧/就在海南/海南的温度/会温暖你/在这里一起看海/一起听海的故事”(《海的故事》),海南每一寸土地和景观已经诗意地潜入诗人内心,他对海南强烈的“文化认同”和“精神认同”深深嵌入其精神世界,化为诗人的“吾乡”。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大到城市建筑小至街道,从都市文化气质到市民人文素养……要而言之,一座城市的“面目”,是这座城市的个性。雁西善于选取富有海南个性特征的“地理景观”入诗,清晰准确地呈现出这座城市的独特性,也表现出诗人对这座城市真挚的依恋。诗人刻绘“雕像”“油画”“古董”“黄花梨”“沉香”“骑楼老街”“自在咖啡”“国新书苑”等物象来标记属于海南的独特的“诗歌地理”。此外,有些关乎海南的诗歌的叙述折射出诗人对事物的深切体悟与审视,诗人将人生的复杂经验运用到对日常事物的观照之中,人、情、景、物交融一体。
生命的活力蕴藏在海南的每一处景观中,在这方“情感原乡”中,“海棠湾”和“凤凰花”等极具“海南特征”和浪漫气息的地标和物标被诗人不厌其烦的书写,当诗人赞美“海棠花”和“凤凰花”的美魅以及“花”所代表的爱情,作者故意在想象中将“海棠花”和“凤凰花”造成混乱,以便形成诗歌的黏稠感和模糊感,诗人旨在表达他对这方土地上的每一处景观的迷醉之情。
海南是地处中国最南边的省份,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其在历史发展中积淀下独特的精神内涵和人文景观,加之特殊的地理气候,形成了清朗温暖的文化景观与热带风貌。苏轼因被贬谪到海南岛而与其结下了不可磨灭的渊源,诗人借对苏轼的追思挖掘海南的文化寄寓,创作出洋溢着唯美古典特质的系列组诗——《东坡海南》。这里海南纯净的风光重新整合了城市的破碎,远离陆地、清净偏远也是诗人钟情于此海岛的原因,亦如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小说家亨利·德·雷涅埃和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维尼他们择选辽远之地安家一样,他们其实是在选择一方心灵的净土。
结语
雁西的“情人诗学”以爱情抒写为主旋律,大海作为审视自我、世界的镜像,与诗人确立了平等亲密的情人关系,架构起抒情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联,表达了诗人对爱情以及亲情乃至社会的思考。在消费主义至上众生万象碎片化的AI时代,雁西拒绝冷漠与主体性的消解,他以丰沛深沉的浪漫情感谱写一首首动人心弦且细腻的诗歌,为我们描绘出童话城堡似的“故乡”。诚然,海南作为诗人的“第二故乡”,不仅在诗人的人生历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对于诗人的诗歌创作也有深刻的意义,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城市风貌都在雁西的笔下以诗的方式得以展现。作为画家的诗人雁西,他的每一首诗又构成了一幅幅画作,他的诗与画互为文本,彼此标识,印证着那颗情人的诗心,爱的星海。海南的空间景观是承载着雁西情感和诗性的会所,这是“情人”的精神栖居地,爱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