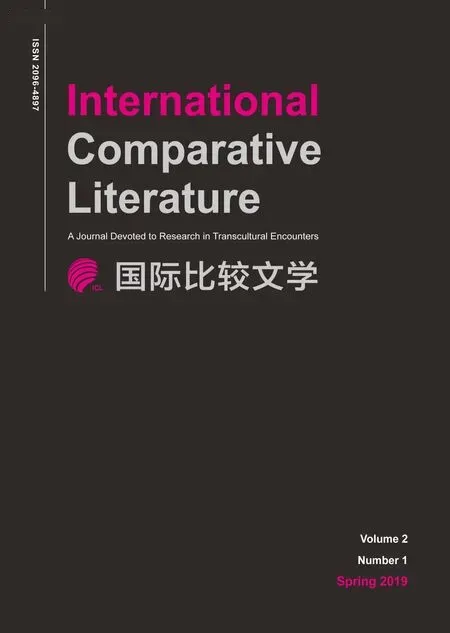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资源配置模式论* #
张慧佳 湘潭大学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即在1912—1949年的现代中国这一时空中得力于西方自由主义诗学和中国传统个性主义诗学资源的共同浇筑而萌芽、发展,并在与马克思主义诗学、保守主义诗学的话语斗争中逐渐走向边缘化的一种艺术至上主义的文学理论形态。作为中国现代诗学场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自由主义诗学既提倡借鉴西方自由主义诗学资源来建构中国文学新形态,从而突破传统诗学的条条框框对于文学发展的束缚;又潜在地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经验,从纵向上延续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本土个性。
一、横向整合
五四运动伊始,中国新文学即以革命者的形象出现,不惜彻底推翻以孔儒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来建立新文学。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中国社会,尊礼法重道德的儒家文化掌握了社会场域中的话语权,是封建文化的权力象征。因此,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科学”(Science),是西方近代文明精神的缩影,亦是五四新青年的时代信仰,那么,新青年若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为自己在文学场域内争取到一份话语权,必须要推翻既有权力关系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主体,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国粹和旧文学等封建文化载体自然成为了五四运动口诛笔伐的对象。由此,以实现启蒙民智与文化现代性转向为目标的五四青年便期待引入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来探寻民族救亡之路,而西方近代以来的诸种诗学资源亦成为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重要渊源。
具体而言,这些西方诗学资源涵括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先后出现并盛行于西方世界的浪漫主义诗学、唯美主义诗学、现代主义诗学等多种诗学资源。虽然这些资源在发生机制、审美追求、价值观念、外部表征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均主张摆脱理性和逻辑对于艺术的束缚,强调艺术主体对客观物象的主观感受,从而突显艺术之主体性。为了尽快完成解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之“大我”形象,继而建构“小我”形象的历史任务,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在建构其诗学形态时首先是以一种横向整合的态度来择取诗学资源的。
文学本质究竟为何,是诗学体系中最基本且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自诞生起就提出,文学本质在于表现自我情感、重塑自我形象。自文学革命发端起,宣泄自我情感的话语就大量涌现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体系之中。前期创造社作家甫一登上历史舞台,就亮出了诸如“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了,”“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之类的观点,而其重视自我情感这一诉求与西方浪漫主义诗学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借助于充沛的情感、大胆的想象来实现艺术家对于理想的追求。事实上,以前期创造社和新月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诗学家的确是在西方浪漫主义诗学的影响下,借鉴浪漫主义的诗学资源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的,激进直白如拜伦、歌德、雪莱,含蓄内敛如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均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师。
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何以如此积极地横向汲取西方浪漫主义诗学以建构一套新的诗学话语?更甚之,部分诗学主体更是片面而激烈地要求摒弃中国传统的文化经验?究其根本,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对西方浪漫主义诗学的接受提供了契机。
从社会关系角度来看,作为法国大革命催生的产物,西方浪漫主义诗学对于初生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有着借鉴的价值。浪漫主义诗学上承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人本主义思想,起初是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文化秩序的理论武器出现。与之相似,自晚清以来,面对着积重难返的封建政治体制,以及数千年以来在政治、道德、经济等场域控制下愈发失去自主声音的文学场域,中国自由主义诗学家便效法于西欧浪漫主义艺术家们以“情感”为核心反对“理性”,以恢复“自我”主体性为目标的方法,对传统的诗学范式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挑战,从而踏上了对于文学自主性诉求的征途。
西方社会关于浪漫的想象在19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诗学话语,且集中表现为两种形态,即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以德国的歌德、席勒,英国恶魔派诗人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热心于批判现实、改造世界,以一种“虽九死其尤未悔”的政治激情主义精神鼓舞着中华民族完成启蒙民智、破“旧”立“新”的历史任务。不同于此,以英国湖畔诗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则寄情于“令人生怀古之幽情”的衰颓之景或乌托邦化的美好意象的描述与想象,这种看似逃避现世的诗学态度也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理论建构及创作实践。
总的来说,两类浪漫主义诗学的共同倾向是“主情主义”,而这种倾向引起了中国文坛极大的共鸣,自由主义文人也以情为本,发起了对旧有文学传统的挑战,郭沫若指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以此将中国诗学从“文以载道”的轨道上带回文学艺术本身。而其“情绪的吕律,情绪的色彩便是诗”,郁达夫的“诗的实质,全在情感” ,梁实秋的“艺术品的中心是情感”,以及闻一多的“诗是被热烈的情感蒸发了的水气之凝结”等观念则更是直接地为“诗”重新定义,道出诗之内容即情绪、情感,从而将文学从政治、经济、道德等外在条件的约束之中解脱出来,以使诗歌获得独立的审美价值。除了在诗学理论方面的建树,“主情主义”的诗学理论更是进入了创作实践。怀疑、愤怒和抗争,是一代中国青年的普遍情绪,作为个人主体意识确立的标志,亦作为时代的需要,情感抒发的要求促使数千年来依附于政治、道德、经济等外在之物而生的文学场内部出现了反抗的因素,也就是说,在积极的浪漫主义诗学影响之下,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呈现出一种个人情绪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趋势。
除此之外,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在论及文学思维模式时亦明显受到了西方诗学理论的影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认为,文学思维是一种非理性的、以直觉和灵感为主导的主体意向性思维。正如弥洒社成员胡山源所说:“我们乃是艺文之神;/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何为而生;/……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灵感)。”换言之,他们将灵感思维置于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应的,诗人的主体理性思维则被抛诸脑后。而这种主体性思维模式的形成,正是受到了西方非理性思维传统的影响。自古希腊时期起,西方人已然意识到艺术创作有一套独立且异于他者的思维规律,继而将之视作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恰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最早使用“灵感”概念来这样解释诗人的创作过程:“没有心灵的火焰,就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在德谟克利特看来,灵感点燃了心灵的火焰,并引导诗人的思维走进非理性的疯狂状态,而艺术作品的产生就与这种“迷狂”的精神状态有着莫大的关联。德谟克利特关于灵感的这套言说启发了柏拉图的“迷狂”说。柏拉图肯定了德谟克利特等人论述“灵感”时谈及的“非理性”属性,认为诗人作诗须得在“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的状态下完成,此外,更是深化了“灵感”概念中的“神灵”之内涵。这种从精神层面观照艺术创作的倾向无疑推动了西方的主体性诗学的发展,亦直接影响了后世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诗学的形成。五四时期,伴随着主体性的浪漫主义诗学和现代主义诗学的传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亦受到了西方“灵感”说的影响,并提出,诗不等同于历史和科学文献,它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是“生底颤动”,“灵底喊叫”,所以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既然文学艺术是生命力的冲动爆发所致,它的思维模式必定不是受制于理性和意志的逻辑思维,而是在非理性的思维状态下生成的。情感来了,生命的冲动来了,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冲动也随之而来,因此,灵感思维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自然偶发的思维形式。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在试图颠覆本土的传统审美范式时,分别从文学本质、文学思维、文学形式、文学功能等方面借鉴了西方自由主义诗学资源来重建了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并由此产生了诸如“艺术品的中心是情感”、“生命是文学底本质”之类的以自我的情感和意志为文学本质,从而以“小我”代替“大我”的观点。
二、纵向传承
不能否认,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确实是在西方文化的催生下形成的,而且,其最初更是以反叛中国传统诗学的形象出现。这种一味地强调西方诗学之优越性而轻视中国诗学资源之主体性的话语更是一度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种主流的话语模式。然而,以场域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来观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不难发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场是一个动态的权力关系网络,多种诗学资源于其中相互抗衡、相互阐发、相互补充,主体性的中国传统诗学资源不仅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且作用不可小觑。
事实上,一种诗学形态能否顺利地融入新的语境,与新语境中的本土文化经验与审美范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便徐志摩等人曾提出诸如“我们中国人尽管具备各种德行和特性,但作为一个民族,却没有像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透过艺术来充分认识和表达自己,而艺术就是生命的自觉”的观念,全盘否定了以“中庸之道”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精神体系,而中国古典诗学思维的确有“中庸”的一面,其目的在于追求一种天人的平和、身心的平衡与精神的静穆。在诗学方面表现为《诗经》风格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汉大赋华美文辞尾端的温柔讽谏、唐诗宋词的清丽雅健,诸如此类。这正是徐志摩所谓的“理智的调和”。不可否认,相对于感情挚烈的西方文化而言,中庸思维影响下的中国古典文化的确显得持重、内敛、沉静,然而,任何民族的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绝非以单一形式演进。中国诗学不仅沿以“中庸静穆”为美这一条脉络发展,其内在的抒情性、个人情感的爆发性亦在文学发展的彷徨历程中得到了体现。可以说,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乃是一以贯之、不可小觑的。与《诗经》并称“风骚”的《楚辞》实际已开中国抒情诗之先河。屈子在湘水边任情地表达内心的惆怅,这绝非“诗经”所谓敦厚之旨可以框定;汉代抒情小赋直接承袭了《离骚》的哀婉之情状,并注入了更多个人的情感因素,以表达对大一统政权下黑暗现实的不遇之悲;抒情传统在魏晋六朝达到高峰,“竹林七贤”的情感放任与行为失礼,不仅表露出对封建礼教的蔑视,更突显了个人对自由地表达真挚情感的渴求。阮籍月夜抚琴,嵇康斗酒吟醉,其间透出了个性的膨胀与自由意识的勃发,显然,他们绝非徐志摩所谓的“行为的懦弱”、“生命的浅薄”之徒,反而是中国古典诗学苑囿里行为任情、个性诗意的典型形象。如果说阮籍、嵇康之辈用行为演示了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那么西晋陆机则首次在诗学理论上确立了中国诗学抒情之风尚。陆机《文赋》中“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一言宣告了诗学的“抒情”旨归得到了普遍认同。文学之本质,不再是儒家“言志”之类的为国、为民、为时而作,自此,文学可以为个人、为情感、为个体情性、甚至为靡靡之音。陆机的“诗缘情”主张,既延续了“诗言志”传统中对创作主体情志的关注,又进一步强化了情感的主体性,将表现对象由有关国家与现世功利的“大我”之“志”转向有关个人与审美愉悦的“小我”之“情”,使得“情感”彻底摆脱了国家意志和道德伦常的束缚,推动了文学自律的实现。
由此可见,关于“情感本质论”,中国古典诗学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话语阐述是相似的。以此来观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对于西方浪漫主义诗学资源的接受行为,即可发现,作为一种既有的文化经验和知识形态,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抒情传统已固定地存在于中华民族的知识结构之中。那么,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家在接受西方自由主义诗学资源时,就会按照一种“意义预期”来对之进行相应的择取,因此,与中国古典诗学中“主情主义”的文化经验相契合的,宣扬“情感本体论”的西方浪漫主义诗学自然进入了中国现代诗学家的视野。
与之相关,虽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明显受到了西方主体性思维的影响,但是,是否可以说该体系中关于“灵感”的诗学话语完全是照搬西方诗学资源而摒弃中国传统诗学资源的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英国美学家冈布里奇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没有一种艺术传统像中国古代的艺术传统那样着力坚持对灵感的自发性的需要。”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家设想建构一套新的诗学话语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审美心理经验,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接纳、选择并改造西方相关的诗学资源有着潜在的影响。
虽然“灵感”这一词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才出现在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之内的,然而,中华民族对于这种非理性的主体思维的追求却早已开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和作家往往结合自身创作经验和审美体验来谈文艺创作的主体性思维,只不过,在话语形态表述上可能与西方诗学家的表述不尽相同。应该说,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极为重视“心”在艺术中的独特作用的。自老庄思想一脉演化发展而成的中国诗学传统提倡从精神层面观照艺术创作,那么,作为诗人创作过程中非常特殊且重要的一种精神现象,“灵感”自然受到了历代文论家的关注。西晋的陆机在《文赋》中首次以“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这样的文辞论述灵感来临之际的感受:突如其来、不由自主,且极具创造力,这恰好与西方诗学关于“灵感”的描述极为相似。如果说陆机对于灵感思维的探讨只限于现象表述,而“未识平开塞之所由”的话,那么,齐梁间的刘勰则以“神思”之说发展并深化了前人对“灵感”思维的认识。“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神思不随主观意愿而来去,“枢机”和“关键”决定了神思的通塞;“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
Wenfu yizhu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 ofWen Fu),
Beijing:Beijing Press, 1984, 29.]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神思是虚静沉淀之后的一种思理之妙,一旦枢机通畅,大脑思维进入高度亢奋状态,创作的激情膨胀,想象力和创造力爆发,奇思妙想也随之喷薄而出。刘勰对于“神思”的探索又不止于此,他在表述了灵感思维的现象的基础上,更是写道:“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也就是说,他认为“神思”源于日常生活中知识、经验的积累,而且,主体之心境决定了“神思”的去留及效果,“虚静”之境,即“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之内心纯净,为神思之来去疏清了障碍,有利于文思的培育与表达。一旦灵感之思开启,作家能够达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神妙境地,乃至高傲宣称“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事实上,中国现代诗学选择、接受西方诗学资源的行为,是中华民族在异域寻找本民族的历史记忆的过程,传统文化经验往往在背后影响着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方向。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因此,中国传统诗论中对于“神思”、“妙悟”乃至相关诗学概念的讨论,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接受西方的“灵感”、“直觉”概念和思维模式提供了审美心理基础。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谈到,“清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是“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一观点既道出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基本面貌,亦为论证中国现代诗学与古典诗学之连续性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正如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所言一般,我们不应盲目地割裂中国现代诗学与古典诗学之间的联系,而片面地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全盘西化。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曾指出,“现代性”突出表现为现代主体的生成,而现代主体的典型特征之一,正是“‘个人'被赋予一个具有深度的‘自我'”,“给予感情 (sentiment) 一个中心、正面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对于西方浪漫主义诗学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提供的外在牵引力量而言,中国古典诗学更是内在且自发地为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支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的建构,正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型,而这个现代转型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中西诗学话语的融合过程。
三、创造性转化
无论是一味地横向汲取西方诗学资源以建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抑或是单纯地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内部的统一性和承继性,这对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乃至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而言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不难发现,随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逐渐走向成熟阶段,知识分子们开始以一种多维视野来观照诗学体系的理论建构。具体而言,即对相应的中西诗学资源进行创造性的整合与转化,从而实现西方诗学资源的本土化和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化转型,以期建构出一种理想的诗学形态。
首先,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主体的创造性整合与转化体现在知识分子面对不同诗学资源时的择取态度上。事实上,除了西方浪漫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抒情传统在审美倾向上的相似性使得前者得以顺利被中国诗学所接纳,差异的存在更是推动且左右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接纳行为。中国诗学虽历来有着“诗言志”、“诗缘情”的抒情传统,但封建礼教加之于其上的束缚亦是相当明显。在《尚书·尧典》中,舜帝命夔典乐时即在“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后附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一言,以示“谐”、“伦”、“和”于诗歌表现效果之重要性,而这亦展示了“礼”、“序”对“诗言志”的约束。《毛诗序》中,作者在阐述了诗的生成机制,即“志”借助“言”,生成“诗”之后,亦附有“发乎情,止乎礼义”一言,进一步把人的主观情绪纳入了封建政治伦理的规范领域之内。朱自清亦指出,这种主观情绪与“礼”有关,事关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有着强烈的道德与政治关怀。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的抒情主义诗学传统中,主体情感的抒发是以不违背封建伦理道德为前提的,“小我”的形象常常为历史所湮没。而吹响号角、高骑战马的西方浪漫主义英雄形象则不同,他们势如破竹的呐喊震醒了不知所措的中国人,适应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的时代需求,积极浪漫主义思潮就在一片水深火热的呻吟、呐喊中顺利地进入了中国现代诗学场域。因此,为适应当时中国社会兴起的政治激进主义热潮,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就更倾向于介绍并发展西方浪漫主义诗学资源中的积极浪漫主义诗学,而非消极浪漫主义诗学。其中的革命、反抗精神激发了中国青年重建“自我”的决心和勇气。相对而言,消极浪漫主义虽也受到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青睐,但其中的避世倾向也注定了这一类诗学资源在社会环境复杂、危机重重的现代中国受到冷遇的命运。
其次,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主体对中西诗学资源的创造性整合还体现其接纳方式上。中西双方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虽是在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诗学资源的直接启发下形成,然而,在接受西方诗学资源时,中国知识分子依然会依据本土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而对异域资源作出相应的改造,以期适应本土文化的心理图式。因此,经历了一番跨语际旅行后的诗学话语在本土文化经验的影响下亦产生了内涵上的变异。
以前文提到的“灵感”思维为例,数千年来,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的、以“实用理性”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这种“实用理性”精神的观照下,中国文化关注现实生活,由此,我们看到,中唐禅僧皎然以“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一句论及灵感来袭时“宛如神助”的同时,又以“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一言辩证地阐明灵感的出现是主体经验积累的产物。南宋诗论家严羽亦道:“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所谓之“妙悟”,与柏拉图所谓之“迷狂”状态一样,意指创作的冲动袭来而不受主观意志控制,然而,不同于柏拉图之“迷狂”说中所指的失去心理平衡、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的酒神般热烈的迷狂,“妙悟”更倾向于在一种平静的状态中,以主体的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而渐入悟境。正如严羽所谓“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妙悟”乃是主体修炼自身功夫,自然水到渠成之结果。因此,“妙悟”说与“迷狂”说虽讨论的均为文学创作中的“灵感”这一特殊且关键的思维,且对于该思维有着基本相同的认知、判断,然而,从双方的论述中亦可看出,“妙悟”说较之“迷狂”说,少了一份宗教狂热和神秘性,却多了一份理智性和经验性。那么,这种超验的、神秘的、非理性的“灵感”思维能否与中国文化语境完全融合呢?
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关于“灵感”的话语虽作为一种主体性理论被纳入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但中国知识分子却在传递过程中对于该话语形态的原有的神秘性、超验性内涵做了有意的遮蔽和误读。恰如郭沫若在谈及“灵感”时所说:“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灵魂附了体或是所谓‘神来'。”在郭沫若看来,“灵感”都是诗人大脑活动踊跃的一种表现,亦是创作过程中的一种体验。然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于“鬼神之说”等神秘观念的讨论虽一直不绝于耳,却从未真正进入中国文化的主流话语体系,因此,郭沫若一扫“灵感”一词在原语境中的宗教性、神秘性内涵,认为真正触发灵感出现的,并非缪斯神的亲吻、或灵的时空穿越,而是生活经验的累积,并在生活中为谨守真理和正义而生的真挚情感。那么,“灵感”思维在中国就失去了原有的超验内涵,转而成为了一种以现世经验为基础的创作思维形式。也就是说,中国现代诗学延续了实用理性的中国文化精神,并从现世生活立场出发解读“灵感”思维,认为给予作家暗示的不再是超自然的神灵,而是生活经验,而创造性、主体性的大脑思维则是真正能促使生活转变为艺术的关键因素,颠覆了西方诗学对于“灵感”的定义。
综上所述,西方诗学理论无疑给予了中国现代诗学诸多的启示,但是,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以及本土文化经验和思维惯式决定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在接纳西方诗学资源的过程中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照搬,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有其一套独立且系统的诗学话语。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结合本土文化语境而对异域话语资源进行改造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家建构其诗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事实上正是其根据本土文化经验提出自己的诗学理念,进而实现理论自省与自觉的过程。
可见,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在建构其诗学理论体系时,经历了从单方面地横向汲取西方诗学资源,到认识到中国文化传统内在的统一性,从而在本土文化经验的基础上吸纳并整合中西诗学资源的逐渐成熟的过程。在这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主体为实现其文学理想和历史任务而在资源择取和配置方面作出的努力,亦看到了中西方诗学资源在现代中国这个特殊的时代语境中相互对话、逐渐融合,而这无疑将推进西方诗学资源的本土化和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化转型。
Bibliography 参考文献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Bourdieu, Pierre.Yishu de faze:wenxuechang de shengcheng he jiegou
(Laws of Art:Generation and Structure of Literature Field).Translated by LIU Hui.Beijing: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
[Foucault, Michel.Zhishi kaoguxu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Translated by XIE Qiang and MA Yue.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黄药眠、童庆炳:《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HUANG Yaomian, TONG Qingbing.Zhongxi bijiao shixue tixi
(System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mparative Poetics).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1.]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LIN Yusheng.Zhongguo chuantong de chuangzaoxing zhuanhu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Marcuse, Herbert.Shenmei zhi wei
(The Aesthetic Dimension).Translated by LI Xiaobing.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捷克)普实克:《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李欧梵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Prusek, Jaroslav.Shuqing yu shishi:xiandai Zhongguo wenxue lunji
(Lyric and Epic:Collected Essay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Edited by LI Oufan.Shanghai: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0.]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REN Jiantao.Zhongguo xiandai sixiang mailuo zhong de ziyouzhuyi
(Liberalism in Vein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SUN Yushi.Zhongguo xiandaizhuyi shichao shi lun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ist Poetry Trend).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
[WANG Dewei.Shuqing chuantong yu Zhongguo xiandaixing:zai beida de ba tang ke
(Lyric Tradition and Chinese Modernity:Eight Lessons in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0.]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年。
[XIE Zhixi.Mei de pianzhi:Zhongguo xiandai weimei
—tuifeizhuyi wenxue sichao yanjiu
(Prejudice of Beauty:Study on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ism and Decadentist Thought).Shanghai: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7.]余英时:《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
[YU Yingshi.Zhongguo wenhua yu xiandai bianqian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Taipei:San Min Bookstore, 1995.]赵小琪:《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ZHAO Xiaoqi.Xifang huayu yu Zhongguo xinshi xiandaihua
(Western Discourse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New Poetry).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的其它文章
- 注释范例
- Tara Zahra.The Great Departure:Mass Migration from Eastern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Free World
- The Muted Lover and the Singing Poet:Ekphrasis and Gender in the Canzoniere*
- Where Does Poetry Take Place? On Tensions in the Concept of a National Art* #
- The Trauma of Another:The Female Body and National Victimhood*
- 宋丽娟:《 “中学西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1735—1911)
——以英语世界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