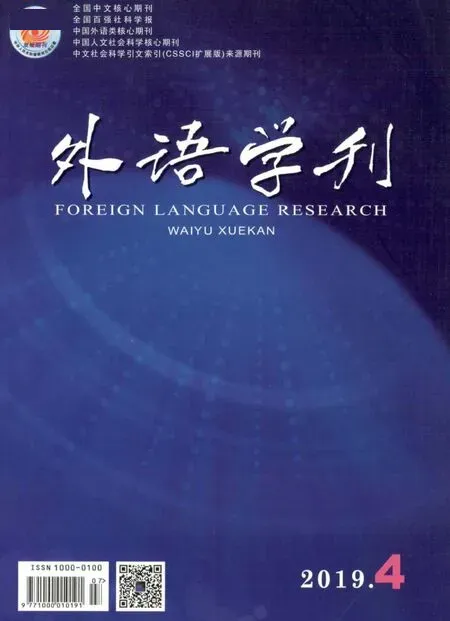“语义滞留”原则再认识∗
史维国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提 要:我们从“语义滞留”原则对以下4个问题进行解释。第一,时间副词“就/才”与“了”搭配的不对称性,源于助词“了”滞留有动词“了”的“终了、了结”义。第二,处置介词“把”滞留动词“把”的“把持”义,要求“把”字句中的动词必须含处置义,同时处置介词“把”的宾语不能是结果宾语,打破这一限制的条件是谓语动词进一步被有界化。第三,现代汉语程度副词“挺”修饰的中心语倾向于积极意义,源于滞留动词“挺”的“挺拔、笔直地伸展”义。第四,“一X就Y”表示“紧随性”构式义,源于“一X”表动量的用法,具体反映在该构式中的连词“一”是从数词“一”语法化而来。
1 副词“就/才”与“了”搭配的不对称性
现代汉语中,时间副词“就”和“才”在与时间词搭配时,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表示时间早,而“才”表示时间晚。我们结合“语义滞留”原则给出的解释是:时间副词“就”和“才”是由动词“就”和“才”语法化来的。动词“就”的词汇意义为“完成、结束”,词汇意义中蕴含“表时间早”;动词“才”词汇意义为“开始”,词汇意义中蕴含“表时间晚”。“就”和“才”语法化过程中,动词的词汇意义“完成,结束”和“开始”分别滞留在时间副词中,因此,对时间副词“就”和“才”的语义功能有如此的制约。看起来,这个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还没有完,我们发现,时间副词“就”和“才”在与时间词搭配时,还有新的限制,那就是时间副词“就”可与“了”搭配,而时间副词“才”不可以。比如:
① a.他10点就来了。
b.他10点才来。
∗c.他10点才来了。
②a.小明28岁就结婚了。
b.小明28岁才结婚。
∗c.小明28岁才结婚了。
我们的问题是为何可以说“时间词+就……了”,但不能说“时间词+才……了”。时间副词“就”和“才”在这点上的不对称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关于现代汉语“了1”和“了2”的来源问题,很多学者都有相关探讨,代表性的有王力(1989:91-94)、曹广顺(1995:16-97)、蒋绍愚(2017:162-184)等。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是:“了1”和“了2”是同一来源,都源于完成义动词“了”。曹广顺(1995:16-97)指出,在唐代,“了”可以构成表示完成状态的“动词+宾语+了(完成动词)”句式,充当谓语性成分,它的功能是对事件的状态作出评述。陈述简单的事件发展为动态助词“了1”,陈述完整的事件发展为事态助词“了2”。可见,本文涉及的与时间副词“就/才”搭配的“了”源于完成义动词“了”。
“语义滞留”是一个形式从词汇项语法化为语法项时,语法项的语义和语法功能受到词汇项词汇意义的制约和影响,即词汇项的词汇意义‘滞留’在语法项中。(史维国2016:94)根据“语义滞留”原则,“终了、了结”义的完成义动词“了”语法化为助词“了”时,对其语法分布上的制约和要求是应与滞留着“完成义”的语法成分搭配,不能与滞留着“开始义”的语法成分搭配。前文已提到,时间副词“就”和“才”是由含“完成、结束”义的动词“就”和含“开始”义的动词“才”语法化来的。因此,现代汉语中只能说“时间词+就……了”,而不能说“时间词+才……了”。
由此,我们对“语义滞留”有重新认识:“语义滞留”原则的两种表现形式并不一定是各自独立的,有时候,某一语法现象在形式和意义上的限制是“语义滞留”原则两种表现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时间副词“就/才”与“了”搭配的不对称性很能说明这一点。时间副词“就”表时间早,时间副词“才”表时间晚,这是“语义滞留”原则在语义功能上的表现,即词汇项的词汇意义对语法项语法意义有制约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就”和“才”语法化过程中,其动词的词汇意义“完成,结束”和“开始”分别滞留在时间副词当中,造成二者语义功能上的这种区别。能说“时间词+就……了”,不能说“时间词+才……了”,这是“语义滞留”原则在语法功能上的表现,即词汇项的词汇意义对语法项的语法分布或结构功能有制约作用。具体来说就是,现代汉语的语气词“了”源于“终了、了结”的动词“了”,对其语法分布上的制约和要求能与滞留着“完成义”的时间副词“就”搭配,不能与滞留着“开始义”的时间副词“才”搭配。
2 汉语“把”字句中宾语的出现条件
我们知道,动作发生以前不存在、动作发生以后才存在的事物不能成为处置介词“把”的宾语,即处置介词“把”的宾语不能是结果宾语。比如:
③ a.拆房子(受事宾语)→我把房子拆了。
b.盖房子(结果宾语)→∗我把房子盖了。
④ a.拆毛衣(受事宾语)→她把毛衣拆了。
b.织毛衣(结果宾语)→∗她把毛衣织了。
例③、④实际上是“语义滞留”原则在语法功能上的表现,即词汇项的词汇意义对语法项的语法分布或结构功能有制约作用。动词“把”有“把持”的意义,当它语法化为处置介词“把”后,其“把持”义仍然滞留在处置介词“把”中,对“把”字句语法功能的要求是动词必须体现“处置义”,即“把持义”。处置总得先有个处置的对象,动作发生以前就存在的事物才能进行处置。也就说,动作发生以前不存在、发生以后才存在的事物(结果宾语)不能激活动词的“处置义”,当然也就不能在“把”字句中出现。
问题是,有时候处置介词“把”的宾语似乎也可以是结果宾语。如:
⑤盖房子(结果宾语)
a.我把房子盖好了。
b.我把房子盖了一大片。
⑥织毛衣(结果宾语)
a.她把毛衣织好了。
b.她把毛衣织出了好看的图案。
在与动词“盖”“织”搭配时,“房子”“毛衣”是结果宾语,是动作发生以前不存在、动作发生以后才存在的事物,按照“语义滞留”原则的要求,不应该出现在“把”字句中作宾语,但为何例⑤和例⑥中的a、b两句都能说。我们认为,主要是两句中动词“盖”和“织”后都附带补充性成分,使谓语动词有界化。谓语动词有界化以后,与宾语搭配时,具有不同的“处置义”,再以“盖房子”为例进行说明。如:
⑦盖房子(结果宾语)
a.∗我把房子盖了。
b.我把房子盖好了。
我们认为“盖房子”和“盖好房子”是不同的,“盖房子”中的“房子”是结果宾语,“房子”这个事物在动作“盖”发生之后出现,所以不能说“我把房子盖了”。“盖好房子”则不同,“盖好”这个动补短语实际上包含动作“盖”和其结果“好”两个语义成分。动词“盖”被有界化为“盖好”,说明房子已处在盖完的阶段,也就经历过开始盖、正在盖的阶段,即在“盖好”之前已存在“房子”这个事物,只不过是一个未完成品,当然也就可以作处置介词“把”的宾语,变换成“我把房子盖好了”。
3 积极性特征对程度副词的语义制约
邹韶华(2001:208)提出,“现代汉语语义系统中,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分布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分布密的一方频率高,为积极意义;分布疏的一方频率低,为消极意义。这种特征必然要制约语言的结构和理解。”通过考察,我们发现,现代汉语程度副词所修饰的中心语有这种积极性特征倾向。对此,我们将从“语义滞留”原则角度给予解释。
太田辰夫(1987:252)认为,“挺”用作程度副词始见于清代,时代往后,程度副词‘挺’放在很多形容词前面,保留着用于积极的、意味较强的词的倾向,比如‘挺大’‘挺深’‘挺长’等,像‘挺小’‘挺软’等那样的用法时代还要晚些”。我们通过对“挺+形”用法的考察,进一步印证太田的看法。如:
⑧只见脑后有三根毫毛,十分挺硬。(《西游记》第七十五回)
⑨刘姥姥一下子却摸着了,但觉那老婆子的脸冰凉挺硬的,倒把刘姥姥唬了一跳。(《红楼梦》第四十一回)
⑩正闭着眼睛背到这里,只觉得一个冰凉挺硬的东西在嘴唇上哧溜了一下子,吓了一跳。(《儿女英雄传》第四回)
⑪ 挺长挺深的一个大口子,长血直流的。(《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一回)
⑫这个东西可不是顽儿的,一个不留神,把手指头拉个挺大的大口子生疼,要流血的。(《儿女英雄传》第八回)
⑬这天他正跟着我吃包,只见他才打了个挺大的包捂在嘴上吃着。(《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九回)
问题是,为何程度副词主要是修饰积极意义的形容词。太田先生对此的解释是:“挺”指直立或者笔直地伸展,较早的用例必定复合成“挺硬”,这大概是因为笔直的意义和“硬”的意义有相通之点的缘故。我们认为这是“语义滞留”原则语义功能上的表现。《说文》:“挺,拔也”。如《周礼·考工记·弓人》有“於挺臂中有焉”。郑玄注:“挺,直也。”孙诒让《正义》有“惟当把处挺直,故谓之梃。”可见,“挺”本为动词,义为“挺拔、笔直地伸展”。“挺”的词汇项(动词)语义中蕴含积极意义,当其语法化为语法项(程度副词)后,词汇项的词汇义“挺拔、笔直地伸展”仍然滞留在语法项中,并对其语义功能上有制约和影响,那就是作为程度副词的“挺”初期只能与语义上积极的、意味较强的形容词搭配。随着程度副词“挺”使用频率的提高,后来也逐渐可以用于修饰消极意义的形容词,如“挺冷”“挺坏”“挺难”“挺矮”等,并且积极义与消极义之间趋向于平衡。不过,方言中还是能看到“挺”在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分布上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黑龙江方言中有一个程度义后助词“挺”,读轻声[tʻiŋ],主要用于含消极意义的形容词后面,如“烦挺”“饿挺”“闹挺”“累挺”“辣挺”等。我们发现程度义后助词“挺”出现时代晚于程度副词“挺”,清代以前的文献没有“形+挺”的用法。方言中存在“形(消极意义)+挺”的语言现象,可能与“挺+形”的积极性特征有关。由于程度副词“挺”早期主要用于中心语之前,修饰积极意义的形容词,为了体现区别性的互补分布特征,消极意义的形容词就只好用在“挺”之前。用在形容词后的“挺”语音弱化,慢慢发展成程度义后助词“挺”。另一方面,由于全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基本语序具有较强的规约性,程度副词“挺”用在形容词前是基本语序,同样表程度义的后助词“挺”用在形容词后就显得不合规范,只保留在方言当中。
4 “一X就Y”构式的语义特征
“一X就Y”构式中的X和Y是两个谓词性成分,关联两个动作或者两个事件。其构式义为:X动作发生之后紧接着发生Y的动作或者情况,强调的是两个动作发生的“紧随性”或“瞬接性”。“一X就Y”构式在现代汉语中很普遍,以下是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的用例。
⑭湖南稻农说,多效唑技术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共产党的技术干部真行。
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人民一掌握了政权就立即着手实施义务教育。
⑯国王到了开化党的手里以后,下诏召事上党领袖。他们一进宫就被杀了。
Goldberg对构式所下的定义是“C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Fi,Si>,且 C 形式(Fi)或意义(S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C的构式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Goldberg 1995:4)。这说明构式意义是高度抽象的、规约化的,不是构式成分简单地叠加,整体义大于部分义。但就“一X就Y”构式来说,其构式义与其构成成分“一X”及“就”密切相关,是“语义滞留”原则语义功能上的表现。太田辰夫(2003:155)认为,“古代汉语中表示次数的方法在现代汉语中变得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只有‘一’转变成连词的用法而依然保留下来”。太田认为,第一,“一X就Y”构式中的“一”是个连词;第二,“一X”实际上是古代汉语表示次数的方法。我们知道,上古汉语的动量表示法是“数词+动词”。如:
⑰吾日三省吾身。 (《论语·学而》)
⑱季子文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
当数词为“一”时,动量表示法就可表示为“一+动词”,如:
⑲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唐·白居易《井底引银瓶》)
⑳一闻千悟,得大总持。一念不生,前後际断。(唐《禅源诠序》)
上述两例中的“一见”“一闻”是动量表示法,意义为“见一次”“听闻一遍”。当“一X”与“便/就Y”搭配时,慢慢就发展成“一 X便/就 Y”构式。据我们考察,“一X便Y”最早出现在六朝时期,“一 X就 Y”出现在明清时期。在构式中,“一”已语法化为连词,如:
㉑修以公所撰兵书示松,松宴饮之间一看便诵。修以此益异之。(六朝《六国志》)
㉒你与我包谎,只说十二分人才,或者该是我的姻缘,一说就成,不要面看,也不可知。(明《今古奇观》)
由此我们可以对现代汉语“一X就Y”构式表“紧随性”给出解释。构式成分“一X”原为上古汉语“数词+动词”的动量表示法。“一X”实际上等于“X一次”“X一遍”,“一X就Y”构式可以理解为“X一次”“X一遍”以后,出现“就Y”的结果。这一点通过变换分析可以看出来。如:
一学就会→学一次/遍就会
一听就明白→听一次/遍就明白
一看就懂→看一次/遍就懂
我们又知道,“一X就Y”构式中的连词“一”是从数词“一”语法化而来,数词“一”表数量小,“一X”表动量少的语义特征仍然滞留在连词“一”以及整个构式中,造成构式表示“紧随性”。试想,“学一遍就会”(一学就会)与“学十遍就会”(十学就会)相比,当然更能体现“一X”与“就Y”的前后相继。
另外,“一X就Y”构式中的副词“就”源于含“完成”义的动词“就”,“完成”意味着“时间早,速度快”,动词“就”的这一语义特征仍然滞留在“一X就Y”构式的副词“就”中,对该构式义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关于副词“就”的语义滞留问题,前文已论及,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