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该如何生活”作为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田书峰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一、“人该如何生活”作为伦理的基本视域

这个核心问题可以说是苏格拉底整个实践哲学的基础。虽然,对于善好生活的追问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哲学的内容,但是,任何一种哲学在某种程度上都会与这个问题相关。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像在解答一道几何题或数学题,求证可以提前被给出的未知数x,而是我们必须亲自去寻找不可以被提前给出的解答,并检验这些答案是否正确。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苏格拉底将“人应当如何生活”设定为自己的哲学关切的基本视域,他对于智慧的锲而不舍的追求,对于何谓德性与幸福本质的叩问,与对话者所进行的不计其数的提问与回答,抑或反驳与训斥,以及他在自己与传统权威之间所做的区分等都是围绕着“人该如何生活”来进行的,如若苏格拉底的上述行动与这个问题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关联,那么,他所进行的这些活动也便与那些政客、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活动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了。虽然,商人、政客或手工业者的生活也在某种意义上与“人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具有关联,他们所追求的善(财富,城邦的兴旺与技艺)也与“人如何过一种善好生活”中的善相关,但是,他们最终并不能在一种整全的意义上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提供给我们一种有关不同的善之间的关系图景。
二、“好的生活”与德性
一方面,“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的提出会在苏格拉底的对话者的灵魂里产生震撼,因为这个问题会使人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它打破了人们满足于日常的人云亦云、得过且过的不加思索的寂静状态,它促使人们返回内心,追问自己生活的价值与意义;而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又具有某种统一或整合的作用,正因为这个问题的提出,生活的各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部分,看似支离破碎的地方才被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个体灵魂中的欲望部分、激情部分和理性部分都能被统一到对好的生活的追求上去,而个体在自己的城邦生活中所从事的各项活动,所进行的各种事业也都是以“好的生活”为目的。
苏格拉底并没有随意地给出一个回答而让听众感到满意,相反,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苏格拉底与来自当时希腊城邦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进行对话,比如演说家、诗人、政客、智者、医生、商人等,他们分别代表着希腊社会中流行的对“人如何过一种善好生活”的问题的观点。面对这些不同的观点,苏格拉底总是能够以其睿智的眼光看出其矛盾的地方,并能指出不足,进而提出自己的反驳。尽管,这种对流行的哲学观点的批驳并不一帆风顺,相反,这是一场极具挑战性与危险性的交锋,甚至,苏格拉底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丝毫退让,他在《申辩篇》中将自己比作牛虻,刺激那些陷入昏昏沉沉中的马匹,使它们活跃起来。他有时也将自己的这种工作比喻为神的工作,是对神的命令的服从。他这样做是受神的委托。我们暂且不去追问苏格拉底本人是否经历了某种不可言说的神秘经验,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即不管是把自己自喻为牛虻,还是寻求于神明的相助,这都显示出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以及他所使用的诘问法和其他哲学方法具有某种威胁性,至少对于当时那些控告他的人分别所代表的人群具有威胁,这三位控告人应该集中地代表了当时的政治权利与主流文化阶层,比如代表政界的阿尼图斯,代表悲剧诗人(或诗艺)的梅勒托和代表修辞演说家的吕孔。从这三人对苏格拉底的控告来看,这表明苏格拉底与他们三人所代表的有关“何谓人的好的生活”的问题的理解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至于他们不能容忍苏格拉底,要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
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466a4-468e2这一演说家与僭主段落(orator-tyrannts-passage)中将当时的政治家和演说家心目中所向往的“好生活”的样式展露无遗地揭示出来。在波鲁斯(Polus)的眼中,“好生活”在于自己能够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演说家与偺主就是这种好的生活的代表,因为他们都有权利能够将人们认为最为不幸的事加于那些他们想要惩罚的人身上,剥夺他们的财产,甚至可以将其置于死地。苏格拉底通过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与做自己喜欢或显得好的事情之间进行区分而批驳了这种观点,因为演说家与僭主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或对他们显得好的事情,但他们并不能做他们在意志上真正想做的事情。真正的好生活是正义的生活,一个违反正义的事情虽然可能是令他喜欢的,但并不是真正的善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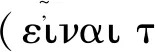
雅典人啊,尽管我与你们是朋友,并且热爱你们,但是,我更愿服从神而超过你们,只要我一息尚存,还能做事,就绝不会停止追寻智慧,都会用我一惯的说法向你们提出警告,且向你们证明,无论碰到你们中的任何人:哦,最为卓越的男人,作为来自一个以智慧和力量而著称的最伟大的城邦的雅典人,如果你只渴望尽力获取最多金钱,声名与荣誉,而不追求智慧与真理,也不关心如何使灵魂成为最好的,你难道不会为此而感到羞耻么?如果你们中有人否认这一点,而认为关心这些事,那么,我不会让他离开,我自己也不会离开,而是询问他、考察他、检验他。如果我发现,他并不拥有德性,而说自己有德性,我会给他指出,他将最为重大的事情视作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将较差的事情看作是较高贵的事情。对我遇到的每个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年青人,是异乡人还是本地人,我都会这样做,对你们我更要这么做,因为你们是离我最近的同乡。你们一定要弄明白,是神命令我这样做。我相信,在这个城邦里还没有过比我对神的侍奉更大的善(Apo.29d-30a)。
苏格拉底为了能呼吁雅典民众关心灵魂和欲求德性,在这里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因为他会询问、考察和检验任何一位他所遇到的人,如果发现对方声称自己拥有德性,但实际并不拥有德性,那么,他就不会放过他,因为他将最为重大的事情视作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将较差的事情看作是较高贵的事情。苏格拉底的虔敬在这里也显露无遗,因为他认为,是神命令他这样做。苏格拉底自感肩上的使命源自于天授,因此,他更不畏惧权贵的刀剑与巧舌如簧的诡辩。无论如何,苏格拉底指出了雅典的那些政客、能工巧匠与诗人或演说家都基于对自己的技艺的娴熟程度而自认为在那些极为重大的事情上也是拥有智慧的。恰恰是这一错误,遮盖了他们认识到何谓真正的“好的生活”,因为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极为重大的事情”就是指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局限于自己的技艺之内而失去了走向另外一个更高的层面进行哲学反思的机会,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就像精通专门的技艺那样也很精通人应该如何生活或何谓德性的问题,然而这正是雅典人的最大错误:
你们雅典人啊,都会些能工巧匠们在我看来似乎犯了和诗人们同样的错误,因为他对自己的技艺掌握的相当娴熟,于是,每个人意愿自己在那些极为重大的事情上也是最有智慧的。这一错误遮盖了他们拥有的智慧(Apo.22 d)。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那些“极为重大的事情”就是指有关何谓正义的和好的生活的问题,这关乎到人的德性以及人在城邦里的教化。苏格拉底对此并没有直言不讳地认为自己具有智慧,认为自己对于这“极为重大的事情”了然于心,他只是确切地认为,僭主、辞令家或演说家、智术师与能工巧匠们所主张的生活方式与他所认为的“好的生活”或“正义的生活”有着本质上的天壤之别。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认为,阿波罗神庙的神谕之所以坚持认为无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是因为只有苏格拉底明白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毫无价值。这种区分是源于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的,而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
三、“好的生活”与自我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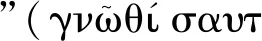
我至今都不能按照德尔斐神谕认识自己,连自己都还不认识就去探究(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对我来说,显得好笑。所以,我把这些东西都搁置一边,人们习惯上是怎么相信这些东西,我就信之若素,而不去探究这些事物,而是探究我自己,看看自己是否碰巧是个什么怪兽,比百头怪还要曲里拐弯,还要形象可怖,抑或是个更为温顺而且单纯的动物,天性上带有几分神性,而非百头怪(Phdr.229eff.)。

对于第一个转向,苏格拉底实际上并没有一开始就专注于对不可生灭的超越感性的形而上学世界的探究,并没有一开始就以认识自我为终生之旨趣,而是在年轻的时候沉迷于探求自然的智慧,忘情于对外在事物的研究而浑然不觉:
我啊,刻贝斯,年轻时候就欲求那种叫做“探求自然的智慧”。毕竟,当时在我看来,这种智慧甚是美妙:知道每一事物的原因,即每一事物何以产生,何以毁灭,何以存在。我不断反复思考,对这样一类问题,困惑不解。就如有些人主张的那样,是否热与冷引起的发酵就会产生出动物的组织?我们是否借助血、空气、或火来进行思考?或者这些都不是,而是大脑给我们提供了听觉、视觉和嗅觉、而记忆与意见就源自于这些感觉,知识则是源于记忆与意见的确定状态?(Phaedo95a-97a)



四、“好的生活”与技艺的类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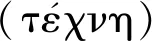

五、“好的生活”与智慧
基于技艺类比,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人的优良或卓越,也就是有关人的伦理德性的知识是一种不同于技艺的知识,有关人的善好生活的知识并不是通过制作外在的产品表达出来的,而更多地在于我们的分辨能力,即决定我们应当选择何种目的以及应当将我们的才能与禀赋运用到何处才能帮助我们过一种苏格拉底所说的“善好生活”的知识。这种知识并不是天赋于我,而是需要实践经验与理性的反思。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一方面,他宣称自己并不具有这种知识,也不能教授这种知识,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对那些自以为知道何谓德性或何谓善好生活的对话者无情地加以口诛笔伐,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德性的真实本性,他们只是自以为知道,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有关人的善好生活的知识并不是一种技艺性的知识,而是一种智慧(17)John M.Cooper用非常精炼的语句表达出了这种智慧的特性:“Wisdom,then,is a permanent,deeply settled,complete grasp of the total truth about human values of all sorts,in all their systematic interrelationships,primed for ready application to all situations and circumstances of human life.” See:Cooper,J.M.,Pursuits of Wisdom,Six Ways of Life in Ancient Philosophy from Socrates to Plotinus.Princeton:Princeton Univ.Press 2012,p.46.。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苏格拉底所说的“好的生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第一,苏格拉底将“人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视为自己的伦理学的基本视域或核心问题,一切的哲学关切都是与探寻何谓“好的生活”关联在一起的;第二,苏格拉底反驳了僭主、演说家和诗人对“好的生活”的理解,他不遗余力地呼唤人们转向德性,因为“好的生活”必然是正义的、符合德性的;第三,“好的生活”或德性始于对自我的认识,而本真的自我是理性,所以本真的自我并不存在于生灭不定的感觉世界或生成世界之中(Werden),而是存在于建基于理性之上的实存世界或本体世界中(Sein),换言之,苏格拉底的自我认识是从一种对身体的关心转向到对灵魂的关心,即对德性的关心;第四,苏格拉底对于“好的生活”的理解或者对于德性的知识并不是一种技艺性的(technical),因为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技艺都是价值中立的或是两面性的,即一门技艺根据人的意愿既可以被运用到好的目的也可以被运用到坏的目的上,而有关德性或“好的生活”的知识一定只能被运用到好或善的目的上来,德性一定是好的,因此,对于德性和“好的生活”的知识不是技艺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