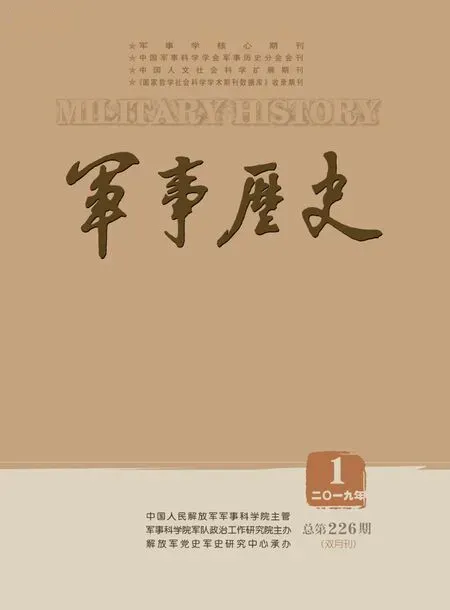情怀、思想和方法
——评《中国兵学思想史》
★ 高润浩
由黄朴民、魏鸿、熊剑平三位学者撰著的《中国兵学思想史》一书,于2018年3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作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著“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的一种,对中国兵学思想史进行了新整理和再阐释,是近年来中国兵学思想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最新成果。
我有幸与本书的3 位作者都非常熟悉。第一作者黄朴民教授,是我18年前在军事科学院学习时的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魏鸿博士,是我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时同一办公室多年的同事;第三作者熊剑平博士,是朴民师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后带的博士生,虽入师门晚于我,称我为师兄,但他刻苦勤奋、治学严谨、成果很多,学问胜于我,乃同门翘楚。因我的个人经历及与本书作者的特殊关系,所以我对兵学思想史研究、对本书内容和作者撰著本书情况比一般读者了解得多一些。也正因为熟悉和了解,想说的话很多,限于篇幅,我主要从情怀、思想与方法三个角度谈一些感想,与读者朋友们分享。
一、令人感佩的学术情怀
学术研究需要对学术发自内心的热爱。没有深沉的学术情怀,很难写出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当今社会注重市场、强调经济效益,从事思想史研究,没有学术情怀是沉不下心、坐不下来、很难做出像样成果的。兵学思想史研究更是如此。同其他思想史研究相比,兵学思想史研究还存在研究者少、课题立项难、缺乏学术平台等制约学科发展的诸多问题。
正如本书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军事史从本质上讲,是历史与军事两大学科彼此渗透、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这一属性,决定了兵学思想史其实也是军事史与思想史的综合与贯通。这一学术特性,对研究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他们最好能具备历史与军事两方面的专业素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复合型队伍自古至今似乎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与儒家、道家、佛家乃至墨家、法家等诸子学术的研究相比,有关兵学的研究显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成果为数不多姑且不论,质量上乘、体系严谨、见解独到之作更是凤毛麟角。
因此说,从事兵学思想史研究,更需要一种热爱、一种情怀。所谓学术情怀,就是学者在特定专业领域表现出的对探究过程及其结果的价值判断和对自身学术存在价值及承担社会使命的自觉意识。具体地讲,学术情怀主要表现为:一是坚定的学术热情和学术理想;二是严谨的学术精神与学术操守;三是自觉的学术责任与学术担当。本书三位作者,都是既有历史功底又精通军事的复合型学者,这为他们撰著本书提供了深厚基础和极大便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兵学研究都有着深厚感情和学术期待,这为他们撰著本书提供了高远目标和质量保障。
学术情怀不是天生的,是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培育和加深的。以朴民师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他从山东大学博士毕业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对军事、军队都可以说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对兵学研究的学术情怀。学术情怀的形成来自学术薪火的传递和前辈的示范引领。军事科学院是一个人才荟萃、藏龙卧虎的科研机构,严谨治学之风和学术报国之志是科研人员的优良传统。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朴民师组织并参与了《中国军事通史》的编撰,这既是一个军事学术的积累过程,也是兵学情怀的培育过程。《中国军事通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全军军事科研工作“八五”计划课题,由军事科学院主编,军事科学院原战略研究部第三研究室承担具体的组织、撰写、编审和出版工作,约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华书局等地方学者参加部分卷册的撰写。该书上起原始社会末期,下迄辛亥革命,共分17 卷20 分册,800 余万字,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以断代为序编撰的大型中国军事通史,获得了1999年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部煌煌巨著有40 多位军地军事史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历时10年完成,培养造就了一批中国军事史专家,如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吴如嵩、秦汉军事史专家霍印章、唐代军事史专家于汝波、宋代军事史专家刘庆、明代军事史专家范中义等,也影响培养了一批青年学者。
学术情怀不仅表现在对学术的热爱与追求,更表现为自觉的学术使命与学术担当。这一点,在兵学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朴民师在个人文集《刀剑书写的永恒》序言中说到:“军事史虽然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之一,但更是军事科学整个学科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表面上看,它的基本宗旨仅仅是叙述总结以往的军事活动陈迹,揭示军事历史上准备战争与实施战争的一般性规律,与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等直接服务于现实军事斗争需要的学科相比,似乎不怎么显赫与重要。尤其是在整个社会被急功近利心态与氛围所包围和充斥的今天,军事史研究更有意无意地被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可有可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不尊重自己的悠久军事文化传统,不善于从以往的军事历史中借鉴得失、启迪成败,那么它就没有资格侈谈什么军事理论创新,也不能建树真正有价值的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更遑论在世界大变局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施展自己的影响了。一句话,不珍惜传统,肯定不会有光明的未来;漠视历史,迟早会受到历史的惩罚。”①黄朴民:《刀剑书写的永恒》,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 页(自序)。
他们对兵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还来自对西方中心主义谬论的冷静思考。如美国人杰弗里帕克在他那部全景式的战争史著作——《剑桥战争史》中,罗列了发生在欧洲、美洲、非洲、中亚、南亚、东北亚、太平洋、大西洋等地区的所有重大战争,却独独略去了曾经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帕克还断言:“独立的军事科学遗产始自希腊。”众所周知,中国有“兵学圣国”之美誉②据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现存著录兵书有3380 部,23503 卷;存世兵书2308 部,18567 卷。,春秋时期《孙子兵法》诞生之时,西方尚未有一部像样的军事著作。面对这种不公正的言论,单纯的义愤无济于事,简单的反驳也难以服人,正确的态度还是“径自讲述我们自己的军事历史,去让世界了解,世界自有公断”。朴民师说:“假如我们撰著的《世界战争史》能打破帕克之辈《剑桥战争史》的西方中心观,客观全面反映世界军事发展的真实面貌,难道不同样是政治与思想文化斗争的胜利?”③黄朴民:《刀剑书写的永恒》,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 页(自序)。这种深沉的学术情怀,是他们从事兵学研究的不竭动力和思想源泉,为他们坚持研究并最终完成《中国兵学思想史》的撰著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有思想”的思想史
台湾学者韦政通说:“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是思想史的主体;但如能辅之以其他领域的知识和观点,可以使主体部分看得更清楚。一部接近理想的思想史,最好是做到内外兼顾,尽可能充分注意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④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册,台北:水牛出版社,1986年,第6~7 页。
“思想史”不只是纯粹历史的描述,不只“说事”,也要“谈理”,应该有思想、有历史。一部好的思想史著作,必定是有特点、有个性、有鲜明思想特色的,必定要体现作者对思想史的研究和理解。但是,做到有历史相对容易,有思想则很困难。这需要作者对该思想领域有长期深入的研究,对研究现状与不足有清醒认识,对思想史基本问题有全面把握、深刻理解和独特思考。
过去的中国兵学思想史著作,大多是以兵书和军事人物思想为主体,兵学思想研究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兵学演变的外部影响不明确,兵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不清晰。究其原因,是兵学思想史中的“不见思想”。本书作者努力突破这种现状,改变习以为常的研究范式和陈陈相因的研究逻辑,从3 个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一是研究重心的转移,将以研究军事人物思想、兵书典籍理论为主导,变为以研究战法与思想共生互动为宗旨。二是在围绕“武器装备——作战方式——兵学理论”这一主线与结构展开叙述的同时,尤其注意对兵学思想发展上的阶段性特点进行概括与揭示。“区分不同时期兵学思想的鲜明特征,探索产生这些特征背后的深层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原因,观察和说明该时期兵学思想较之于之前的兵学思想传承了什么,又改变或增益了什么,而对于其后兵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产生了何种影响,真正把握兵学思想的历史演进趋势和文化个性风貌。”①黄朴民、魏鸿、熊剑平:《中国兵学思想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 页。三是在具体的研究思维模式、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加强努力、开辟新的道路。
他们在撰写过程中,自觉地确立了三种意识:一是研究对象与范围的确立上贯彻综合系统意识,不仅仅从军事方面研究中国兵学的发展,而且也从社会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政略政策、哲学思想、地理地缘、民族文化等多领域研究其对中国兵学发展的影响。二是研究理念和方法运用上的科学创新意识。三是研究价值与功能的转换上反映借鉴启迪意识。
从本书目录就可以看出这本著作与其他兵学思想史的不同。以第一章“夏商军事与兵学思想的萌芽”为例,分为“从血亲复仇到部落争雄”“原始兵器与原始防御体系的形成”“原始社会后期的战争指导思想萌芽”“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兵学雏形”四个部分。本章从原始社会血亲复仇和部落冲突这种战争雏形讲起。原始人类为了争夺生存条件发生的武力冲突,就是战争的萌芽。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血缘相近的氏族结成部落联盟,部落内部、部落之间发生许多武力冲突,这都是萌芽状态的战争。当时的兵器是从生产工具发展来的,由于格斗的需要,这些生产工具的体形和刃形不断改进,逐渐分化出来成为作战工具——兵器。原始兵器以石、木、骨为主,有钺、矛、匕首等格斗兵器,单体弓等抛射兵器和藤甲、皮甲等防御装具。原始社会初期的战争基于狩猎的经验,是对人的围猎。随着战争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到原始社会后期逐渐出现原始的战争指导和战术运用。这在涿鹿之战、尧舜禹攻伐三苗之战等战争中都有体现。甲骨卜辞中关于当时战争的有关记载,是原始兵学萌芽的集中反映。
这样的写法,相较于以兵书、军事人物思想为主体的兵学思想史研究有了本质的进步。本书各章节的撰写都遵循从社会发展、战争形态演变、军事技术变化到兵学思想的发展等几个方面,把影响兵学思想的内外部因素进行系统总结,在此基础上对兵学思想进行研究这一思路,既见局部、又见整体,既见历史、又见思想,既见兵学共性、又见时代特征。这是本书的最大特点,也是它的成功之处。
三、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
蔡尚思先生在《中国思想研究法》中提出:“研究学术,以方法为首要。”林存光先生说:“任何一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都需要方法的指引,需要遵循正确而适当的方法,拥有一套系统而高度自觉的方法论理念乃是一个学科成熟水平的重要标志。”②林存光:《得鱼在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天府新论》2015年第4 期。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等专门思想史研究要比兵学思想史研究成熟得多,这些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可以为兵学思想史研究提供借鉴。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开山奠基之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已有系统论述并总结为三:一为问题的研究法,二为时代的研究法,三为宗派的研究法。对此,刘泽华先生作了更进一步的细分,主要划分为如下六种研究方式和方法:一是按思想家或代表作进行的列传式研究,二是对流派的研究,三是对社会思潮和一个时代重大课题的研究,四是关于政治思想的重要概念、范畴如礼、德、法、刑、仁、义、爱、赏、罚、势、术等的研究,五是对各种政治思想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六是对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关系的研究。
本书借鉴吸收思想史研究的成功做法,汲取既有兵学思想史研究著作的经验与不足,力图整合军事与历史、军事史与思想史,从军事的角度解读思想史,从思想史的角度解读中国兵学。“改变长期以来军事与历史两张皮,思想与实践相割裂的弊端。在中国兵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过程中,既充分运用历史方法,又尽可能地借助军事的范畴、概念与方法,注重从军事的角度考察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回归历史,回归军事,超越过去僵化的模式和平庸的论调,而把握住深化兵学思想研究的新的发展契机。”①黄朴民、魏鸿、熊剑平:《中国兵学思想史》,第8 页。
军事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与思维模式上有很大差异。一般地说,思想史研究是通过史料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地考察分析,揭示思想史各现象与事实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而军事史研究注重从军事学的角度,运用军事学的概念术语与相关理论对历史进行解读,旨在揭示战争与军事发展的规律,探索历史中的军事谋略与智慧。
思想史与军事史的研究方法可以相互借鉴,研究成果可以相互启发。军事史研究为思想史研究提供思想线索和资源,战争形态的发展、军事制度的演变以及作战指导思想的革新等,都可能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关键背景,使思想史研究更丰富、更生动;思想史研究可以为军事史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和大量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加深军事史特别是军事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认识,而且可以从思想文化层面考察军事文化现象,为深化军事史研究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本书将思想史研究与军事史研究相结合,开创了兵学思想史研究的新方法与新领域。
由于中国兵学思想史时间跨度长、上下几千年,涉及兵书多、浩瀚几万卷,不同历史时期兵学思想的既有研究成果参差不齐,有的朝代成果丰硕,有的时期则鲜人问津。因此,本书各个章节在篇幅和研究深度上也有差异,有些章节在研究上稍嫌不足,有些章节内容显得单薄。
本书作者对此有清醒认识,他们在序言中明确指出:“面对兵学思想研究中的(这些)瓶颈,如何突破?怎样超越?这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学术积累上,还是研究能力上,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都远不具备完成转型、实现升华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而放弃探索、不思进取。恰恰相反,我们必须直面这些问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尽可能进行必要的尝试,起到铺路石的作用,为今后兵学思想史研究的进展与成熟,打下一定的基础,提供足够借鉴的经验。”应该说,他们的努力是可贵的,他们的尝试是成功的。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中国兵学,共同推动中国兵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管理思想史》评析
——徐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