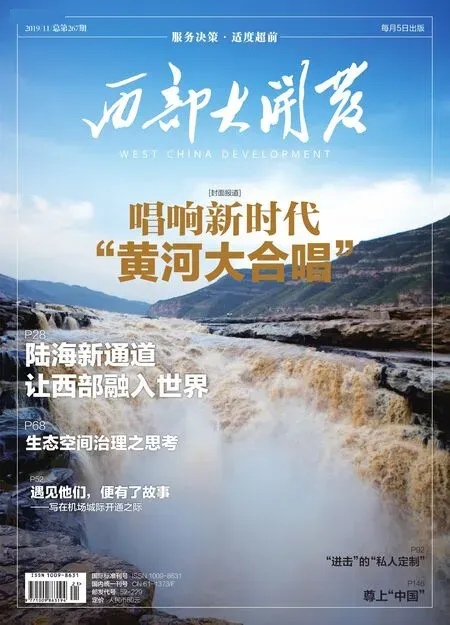水土火捏合成象征的内空间
——析读凌晓晨的诗文本和诗观点
文/沙克

心灵的水面——凌晓晨诗集《水荒》作品研讨会
生活在黄土高原渭水岸畔的人,对于土质的感受是抵实的,对于水源的珍视是刻骨的,对于火的信仰是恒定的,他们居土思根,饮水思源,引火思生,成为西北区域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理念,凝为区域文化中具有沧桑感、道德观和价值性的水土火意象与活命象征。
在西北咸阳出生、居住半个世纪有余的诗人凌晓晨,沉浸于诗意水土30年,对于诗歌圈曾经离而又复归,对于火一样的诗性精神则坚定守持,这使得他聚土成丘、积水成潭、集火成势,近些年先后出版了《黄土色泽》《水荒》两部诗集,将要出版诗集《火眼睛》。他在三本诗集中把水土火的理念外化内凝,把农业文明的基本意念渗透进细微的水土火分子,修为繁复的现代诗形式重置于词语关系之中,捏合塑形成生和思的内空间,升华为形而上的意象叙述和象征抒情。
内观诗集《黄土色泽》的抒情素材,是形而下的具体物“黄土地、丘陵地带、沟壑、窑洞、破屋、河流、树木、庄稼”,这些引号中的纷繁事物是诗集中的种种诗题。给我的感观是,形而下的抒情起于生存经验,止于想象空间的美善意境。例如《沟壑》《荒草地》两首诗,前者“一高一低的阶地,你涌上来/就到无垠的地面上躺下/成为切近手掌的纹理/顺脊梁上的汗水而下,你的深度/让人难以置信”,地理形势的沟壑是形而下的艰难处境,“成为切近手掌的纹理”是近距离的抒情链接,“你的深度/让人难以置信”则切入形而中的沟壑内瓤;后者“根在那里纠结,不死的手指/面对绝对的边界呼唤/真理无边无缘,膨胀如同宇宙/光速是一种假想的角度”,荒草的求生状态就是“不死的手指”,类似于人的形而下的尴尬生存,不得不根植于形而中的有边界的土壤,却又假想着光速的角度和蔓生向宇宙的真理抒情。
这部诗集的文本对于意象结构的塑形技艺,多有形而中的具体物和意念物的虚实互生,是对抒情素材的逐步提炼净化,譬如以“灰烬、激流、鹰、景色、一杯水的容积、寻找梦境”等等为题的诗作大体如此。我的感观是,形而中的塑形技艺其于文化经验,止于信仰空间的普遍象征。《灰烬》里呈现着“瓦罐在边缘地带打碎,猎尽鸟类/煮沸的水声,随河水而逝/……/残存的灰烬,冉冉不息/……/缓缓热流,气贯冲天/遥对恒星的位置”,具体物的瓦罐、鸟类、河水,与意念物的灰烬、水声、热流交互感应,遥对虚实皆可的高远处的恒星——存在感、存在观、存在价值的召唤。
诗的解析常有两个途径,一是指向诗文本,二是进入诗人的内生空间。凌晓晨诗集《黄土色泽》的诗文本如前所述,它的形而下的抒情起于生存经验,止于想象空间的美善意境,形而中的塑形其于文化经验,止于信仰空间的普遍象征。凌晓晨技巧地使用了语言工具,实现了抒情表意的效果。下面来阅读《黄土色泽》的自序,凌晓晨开启了内心的柴扉,“黄土地深厚而宽广,沟壑纵横,千姿百态,水珍贵而稀少,穿越在沟底的河流仿佛生命的灵魂一样,吸引着我无数次奔向她。”这是他对生存处境的感性聚积,成为他写诗的机缘与外因。“有那么一天,我躺在晾晒的麦子旁边,看到阳光直射下来,仿佛颗颗麦粒,落在我身上,落在我的周围,堆起来形成物质,融入我的身体,构成我的生命,构成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这是他对生活状态的质感自悟,成为他写诗的酝酿过程。“在我的精神上,我觉得黄土高原是一片海洋,我把生活作为戏剧,但实际上生活就是信仰,就是自信的欢乐,也是失落的哀伤。我的心中就是这黄土风,一直在吹。”这是他的理性辨析,成为他的写诗实践与认知。“我为自然景象创造的奇迹而感到荣幸,为追求完美的语言,忘记了自我的扭曲或者缩减的情感……”这是他的精神状态,对视觉形式和语言形式的着意探求。

凌晓晨与大学生分享关于诗歌创作的丰富经验
哥本哈根学派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认为,语言的内在结构是一个由各级要素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形式”是结构关系,“实质”是体现形式的语言外的实体。任何诗人包括凌晓晨都脱不了语言、结构(解构)、要素关系、实质实体,那么在诗歌写作过程中久久追索现代性的凌晓晨处于什么状况,我以为,机缘与外因,酝酿过程,实践与认知,自觉与追索,发韧成了凌晓晨不断垒砌的诗意空间和值域坐标,产生了凌晓晨的诗文本和诗心内,逐渐发育扩增其诗学的关联性空间。
第二本诗集《水荒》是另一种抒情和叙述,起于语言,止于方式。在诗题为“一滴露珠的原因、秦朝瓦当、最深的井、水域、水声、秋天的课程”等等诗作中,诗人以内视角的敏感直觉从不同的物性存在中提取意象语言,水到渠成,赋形为诗,赋性为流淌漫溢的象征体,其中尤以《一滴露珠的原因》《最深的井》《秋天的课程》为佳。那些脱离物形的诗性存在,具有诗人赋予的“自身构造”,类似诗题为“水的存在、一滴水内的时间、水自然、水域、水系之外”等等诗作,让生存经验与想象能力腾跃起来,交融为水土的造化行势,升起了文化经验与普遍象征并且互为骨血,这里的语言不仅是诗的工具也是诗的性质。
凌晓晨在诗集《水荒》的后记中开启了内心的多向门窗。
“汉语的每个字都是具有神性的,最初他们都是通神的符号。……赋予诗体的是语言,而诗却是在语言之外能够感觉的东西,所以语言的张力和伸展,以及叙述和分行,都在显示这种语言之外的精神、意志和灵感的来源。”这是对语言的一份觉悟,虽然没有否定语言的工具性,已经把汉语言当作神性的存在。
“诗的抒情根植于想象,诗歌的经验是感觉自身的陌生,忘我而为他,以及对原始经验的阐释,一种诗化生活的追求,一种想象世界中……对美好形式的热血赞颂。”到了此时,凌晓晨体认到了基于生存经验和文化经验的写作经验,用想象来陌生化自我的存在感,必然也会陌生化他人的存在感,试想独立出自身的文本风格。
“思维仿佛雷雨中的闪电,灵魂游走在雨滴击打的水面上,这种感觉时常让我的行动无法落脚,我的诗神在哪儿?”这是从形象中抽象出本质的思考。“长期以来与水结下不解之缘。……水所包含的意义,以及日常生活的点滴,都是水的意象,造就了我目前如何写作的模样。”这是运用水文化经验写作的阶段性小结。
沈从文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说过,“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水。我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以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的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沈从文在《自传》中进一步诠释他与水的命脉关系,“我的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于我有极大关系。”沈从文在湘西之行的船舱里写信给张兆和赞美故乡的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验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
凌晓晨水土乡情的体悟,或许受到过沈从文观点的暗暗濡染。水土生命、水土文化、水土思想、水土美学,写作成凌晓晨的水土诗文本。
在《黄土色泽》《水荒》两部诗集的基础上,凌晓晨即将出版最新的诗集《火眼睛》。诗人叶延滨为之作序,凌晓晨写了一篇对诗歌认知和诗歌写作的观点文章《关于边界和底线》代为后记,将对于自我经验的解释转变为对诗意和诗学的阐释。待版诗集《火眼睛》从外在扫视其结构感比较强,有着内在关联的层次性和系统意识,“生火、火力、火势、淬火、火光及火引”,六辑构造层层递进,尽显诗人多维度的预设空间。与外观的结构感、系统意识对照,诗集内的组成篇什是怎样的,《火炬》《本身:断面》《镜面》《火语》《梵高之眼》《一片葱地》《祈福自我》等等单个文本,比较契合诗集预设的初衷。
我明显地觉得,《火眼睛》与前两部诗集《黄土色泽》《水荒》相比,多了形而下、形而中的生活化题材和内容,纯粹的想象力似乎不占优势,本质的象征性趋弱,而是以具体的生存经验为源,以具体的现实思考作势,以对人生现场的淬炼作能,程序化地产生文本。也许,这部诗集是一架脚踏实地的实用桥梁,为诗人未来的转身与行动作外在过渡。然而,诗集《火眼睛》里的那首纪年式的组诗《沉默切割的碎块》,确是生存经验的升华本,其中包含文化经验的胚胎,写作经验的火引。
凌晓晨用戴望舒式的诗学随想《关于边界和底线》叙述观点:“诗人应该是视通万里,思接千古的人。”从诗人素质而论,等于说诗人的精神无边界。接着他从诗的文体特征而论,“诗的边界是明显的,是不以物性的表达为基础 ,而是以想象、意象、象征为边界的 。”究其论理内质,关键所在是,“诗的底线就是诗人意识的生活经验,他对过去的经验、现在的经验、未来的经验的一种诗化表达。”这里说的是,诗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以现实土壤为起点、以精神升腾为终极。
我经常强调,诗人必须精细地修辞炼句,此为入门原则,也是最高尺度。凌晓晨努力在理性、知性、抒情性之间交互把持,放在纸上的众多诗文本,优处自优,熠熠闪光;而在细微的修辞炼句的功夫上时有怠意,稍稍流于粗疏。比如诗集《火眼睛》的开首诗《潮流》,有“淋滤春夏秋冬和季节变幻”,动宾组合看似无碍,实似有恙;“春夏秋冬”的词组含有了季节转换,作为并列宾语的“和季节变幻”,不如作为春夏秋冬所修饰“的季节变幻”更为连贯切意。细一步挑剔,承接“春夏秋冬”,何须用“季节的变幻”,直接用“变幻”更为简练。我认为这句诗可以写成“淋滤着春夏秋冬的变幻”,加个“着”,语感顺畅些,语义利落些。
诗歌写作是关涉自身生命系统和客观环境系统的真功夫,是个体小世界内时空与外部大世界的无缝对接,也是自我修炼的慢功夫、细功夫、软功夫。我从凌晓晨的诗文本和他的诗观点中,体察到了他的积淀之现实,思考之朴实,笔意之虚实,表现为对既定生存方式的适应、平衡,对陈旧观念的怀疑、对峙,以及用新生经验和文化信仰来与之抵抗的态度。
通过对凌晓晨三本诗集《黄土色泽》《水荒》《火眼睛》的阅读,我得出一份总体的读后感,他是一位深植于现实主义而又意欲超现实的浪漫抒情诗人,他的诗文本是抒情素材、意象结构、塑形技艺合成的象征体。他处于形而下的具体空间,起于生存经验,从文化经验中磨练形而中的塑形技艺,拔向美善意境和信仰空间。
凌晓晨既认为诗的语言文字是“通神的符号”,便在诗观点中表达了对守旧、僵化写作的反对立场,就像诗人们反对不把诗当成语言的花蕊一样。可是,反对归反对,到底自觉不自觉,做到做不到做得怎么样又是别样的情况。在浩繁的当代诗文本中,词句老化、表意陈旧、结构松散,主题先行、抱死农业主义价值、道德教化、分行思想文章,意象转换脱节、焦点未明、象征混杂等等,是普遍存在的触目即是的大问题。写诗既久的凌晓晨,应该也察觉到了当下诗歌写作的种种弊病。如果假以时日细磨精练,提纯语言,着力聚焦,趋入本质;如果淡化旧式道德、实用道德和一己道德,强化诗学的大道大德;如果宁为精思考,不作泛抒情,宁为真个性,不作零抒情;如果在写诗经验上保持与自身和外界的陌生化立场,那么我肯定地期待着,凌晓晨将会在万众诗人中拔尖而出,形成自我风格的“通神的符号”。

凌晓晨诗集《水荒》与《火眼睛》
深植于现实主义而又意欲超现实的浪漫抒情诗人,比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现实主义诗人更适合当代中国的土壤生态,作为前者的凌晓晨,未必因诗而成仙,势必为诗而成就。凌晓晨把生存、劳动,写诗、遐想,把水土火捏合成生命象征,塑形成生活方式的内空间,不停地回归诗性与真性,逐层地跃动、飞驰生命,呈现一颗美善的灵魂存在,已经让所谓的物质贵族和精神贫者艳羡不已,令各种各样的人间神仙嫉羡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