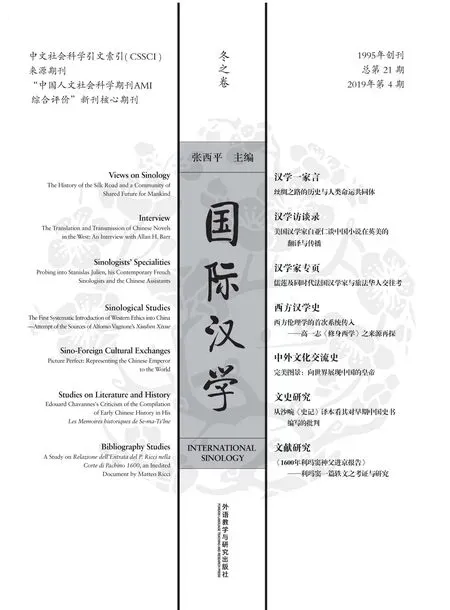美国现代作家史耐德的中国之行与他的生态政治观
□ 张 剑
一
然而事实是,金斯堡在中国创作的十余首诗歌和史耐德在中国创作的二首诗歌,以及他们后来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似乎都暗示了这次访问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在北京,美国作家代表团与中国作家一起举行了一次关于创作源泉的研讨会,史耐德在会上发言说,他的创作灵感来自高山、森林和土地,他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我们知道,他在美国西部内华达州的大山中生活了多年,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因此他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把大自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生态诗人。
史耐德在发言中引用了中国唐朝诗人杜甫的《春望》一诗,来说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说:“我们在这个社会,有什么狗屎舆论没关系,山河在就行,那就是国家,那就是爱国,那就是我们爱的东西,那就是起点。”也就是说,他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著名诗句解读为“国破”无所谓,只要“山河在”就可以,从而暗示了大自然的重要性大于国家的重要性。
可以说,史耐德对杜甫的引用是一种典型的挪用,因为他的引用改变了杜甫诗歌的原意。杜甫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两句诗歌中,表达了一种亡国之痛,说明他对国家因战乱而破败感到无限悲哀,因此才有了后面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史耐德把爱国说成是爱一个国家的山山水水,而不是爱这个国家的政权或统治者。对于一个生态诗人来说,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大自然是他强调的重点:朝代可以更迭,但自然不可以。
钟玲批评史耐德断章取义,扭曲了杜甫诗歌的原意,①钟玲:《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可能正是史耐德想要的效果。他对杜甫诗歌巧妙的误读,使杜甫的诗歌产生了他想要的意义,不能不说充满了智慧。但同时在他的解读背后我们又可以发现一种特别的政治含义,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态政治”,或者“垮掉的一代”的叛逆:国家不重要,山河更重要。这也许就是一种政治观,它在国家和生态之间做出了选择,一种带有颠覆性的重新评价。这也许就是史耐德的生态政治观的核心。
在访问中国期间,史耐德还写了一首诗歌,名为《柿子》(The Persimmons),其中表达的观点与他解读《春望》时表达的观点大致相同。诗歌描写了美国作家代表团去长城和十三陵参观的经历,北京郊区的柿子的丰收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车、农用车、人力车将柿子运往城市,沿着街道川流不息。他说,那些柿子有着“落日的深红色,每颗果实都是夏季留下的一缕阳光”。②Gary Snyder, No Nature: New and Selected Poems.New York & San Francisco: Pantheon Books, 1992, p.352.让他感到新奇的是,路边全是卖柿子的农夫,绵延数公里。他在路边向一位大爷买了一些柿子,吃得很开心,因此有了一些感悟。
史耐德的基本观点是,皇帝终究会死,但是柿子树不会。那些曾经统治这片土地的皇帝已经躺在十三陵的地宫中,但是柿子树仍然繁茂,在十三陵四周生机勃勃地成长。他说,那些曾经消费柿子的皇帝已经不在,“柿子比他们寿命更长”。帕特里克·默非(Patrick Murphy)评论道:“由于这种果实的历史比中华帝国的历史还要长,因此它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更有意义的标志,超过了史耐德被带去看的长城和十三陵。”③Patrick D.Murphy, Understanding Gary Snyder.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2, p.151.
笔者以所在学校为个案,开展了英语听说隐性分层教学的实证研究,目的在于验证隐性分层教学对提高学生英语听说水平和学习情感态度影响的有效性。
诗中有这样一行诗句被重复了两次,值得我们思考。在诗的中间和结尾,史耐德写道:“人们和柿子树永存”④Gary Snyder, No Nature: New and Selected Poems, p.353.,意思是,代表国家的皇帝已经死了,但代表大自然的柿子树及普通人将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耐德的《柿子》一诗不仅与他对《春望》的解读一脉相承,而且与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对国家与土地的理解也可有一比。在《在“列国分裂”之时》(In Time of “The Breaking of Nations”)一诗中,哈代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格兰乡村和在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的农夫,感叹道:“虽然国家改朝换代,但这个景象将持续。”只是,史耐德比哈代走得更远,在认为最重要的是河山,而不是统治这片河山的某个王朝的同时,他几乎否定了对国家的忠诚,以突显对山河的忠诚。
二
史耐德1984年访问中国时所表达的观点有两个层面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层面是这个观点的叛逆性和颠覆性,第二个层面是他对中国材料的处理方式。也许读者不一定能够识别史耐德思想的叛逆性和颠覆性,因为它并不那么明显,而是隐藏得比较深。它需要我们对它的历史背景进行梳理,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历史还原,才能把其中的颠覆性挖掘出来。另外,他对中国材料的处理方式不是一种引证,而是一种挪用。通过对中国材料的误读,或者对中国材料的扭曲,使之能够表达他所想要表达的生态思想,从而为他的生态政治服务。
我们先看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层面。虽然史耐德的生态政治观显得比较温和,不像金斯堡的“同性恋”和“吸食大麻”那样令人发指,但是,如果我们将它放入其历史语境中,也许它的叛逆性和颠覆性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孱弱。史耐德的逻辑是国家不重要,因为国家就是政权,政权可以改变,而承载这个国家的土地,即他所说的“河山”,就不一样了,它将永远存在,即使政权不在了,这片土地还将永存。在这个逻辑的背后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忠诚于这片土地比忠诚于这个国家更重要。
“垮掉的一代”是美国现代诗歌的一个叛逆团体。作为“垮掉的一代”的一员,史耐德的叛逆性主要来自他的生态观点。他没有写过类似于《嚎叫》(Howl,1956)的诗歌,没有吸食大麻的嗜好,也没有尝试过做一名同性恋者。他的叛逆性来自于他的生态立场,来自于他为维护生态而对社会和政府进行的批判。他批评工业化,批评城市化,批评西方文明对生态的破坏。他崇尚佛教和东方文明,抛弃基督教和西方思维模式,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叛逆。说土地更重要,土地上的国家不重要,这就是对造成生态退化的西方文明和人类治理体系的拒绝。
然而,在1984年的中国,史耐德用这样的观点想说明什么呢?他是否要将矛头直指中国的国家政权呢?我们认为,那倒未必,因为他对美国政府的批评也同样尖锐。在来到中国之前,史耐德发表了《致所有》(For All, 1983)一诗,描写了美国洛基山地区的自然景色:“九月中旬的早晨”“赤脚趟水”,在阳光照耀下,溪水“欢唱和闪耀”,卵石发出特别的“味道”等等。诗歌结尾将美国人要成为公民必须立下的誓言改写为:“我发誓要效忠土地,龟岛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居住的所有生灵。”史耐德在诗集的题解中写道,“龟岛”(Turtle Island)是印第安人对美洲大陆的古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州和县,都是人为地和不准确地强加于现实土地上的地理概念。”①Gary Snyder, No Nature: New and Selected Poems, p.204.
史耐德所追求的公民身份,不是美国国家的公民,而是美国生态圈的公民,他认为后者“比政治秩序具有更深远的有效性和持久性”。②Timothy Gray, Gary Snyder and the Pacific Rim: Creating Counter-Cultural Community.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06, p.285.1980年,他在一个采访中说,他将要寻求改变自己与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要研究他居住的这个生物圈,包括气候、植物、地貌、水系、文化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让心灵打破政治边界的束缚,以及其他一切习惯性和传承性的地区边界概念。”③Gary Snyder, The Real Work: Interviews & Talks, 1964—1979.Ed.William Scott McLean.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0, p.24.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阅读史耐德的《柿子》一诗,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诗里隐藏的具有颠覆性的政治观点其实是他的“生态政治”的一部分,它对土地所表达的超越国家的忠诚,与他通常表达的生态观点没有什么两样。
再来看问题的第二个层面,即史耐德对中国材料的处理方式。我们前边说过,“挪用”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另有目的的引用,史耐德不仅引用中国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且扭曲引用的材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挪用是一种后现代的批评手段,其中掺杂着戏谑、戏仿和反讽的因素,而不是简单的引用。在批评的同时,挪用者希望建立起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史耐德对《春望》的挪用并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在这之前,他多次使用过“挪用”的方法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理念进行改写和改编,从而达到建立他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的目的。在《革命中的革命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1969)一诗中,他挪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来说明农村是受压迫、受剥削最为深重的地方。他说,“最强烈的革命意识往往存在于/受剥削最深重的阶级之中”。他所说的“受剥削最深重的阶级”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农民和工人,而是自然中的“动物、树木、水、空气、青草”。④Gary Snyder, No Nature: New and Selected Poems, p.183.
在诗歌中他还引用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观点,来说明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一场生态革命。他首先将文明与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等同起来,把它们都定义为“压迫者”,然后将工人与自然等同起来,将它们定义为“被压迫者”,表达了一种朴素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在诗中写道:“如果文明/ 是剥削者,那么群众就是自然。党就是/ 全体诗人。”①Gary Snyder, No Nature: New and Selected Poems, p.183.他认为诗人应该像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剥削一样,旗帜鲜明地反对人类文明对自然的剥削和压迫。
史耐德所说的“压迫者”还包括理性,他说:“如果抽象、理性的思想/ 是剥削者,那么群众就是无意识。党就是/瑜伽练习者。”②Ibid.我们可以看到史耐德将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从社会延伸到了文明和心理层面,即理性思维是压迫者,无意识是被压迫者。我们应该从这几个意义上来理解他题目中的三重革命。第一层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第二层是自然意义上的生态革命,第三层是个人心理意义上的无意识革命。
当然,史耐德的革命重点是生态革命和无意识革命,他的革命武器是瑜伽和佛教,“力量来自吠陀经祈祷文中的音节”③Ibid.。与马克思主义相同的是,他的最终目标也是推翻剥削阶级,从而让被压迫者获得自由和解放。但他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他所要实现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他称之为“天人合一”(Communionism)。
三
以上只是史耐德的当代中国书写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如果我们看他的其他诗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主张的生态思想的表达路径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都是采用对中国材料进行挪用的方法。《致中国的同志们》(To the Chinese Comrades,1967)一诗看上去是描写中国当代政治,但是实际上也是他的生态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这首长诗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描写毛泽东其人其事、中国政治和中国生态,第二部分描写史耐德自己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的看法。那么,两个部分如何连接起来呢?
诗歌第一部分以中国政治开始,特别是中苏的矛盾,两国的军队20世纪60年代在边界对峙,战争一触即发。毛泽东提倡勤俭节约,归还苏联的贷款,为中国争了一口气。诗中也谈到西藏问题,达赖喇嘛集团逃亡印度、中印边界的领土之争。诗中还谈到香港,在新界的松树茂密的山上,史耐德眺望中国大陆,他看到的是一片“树桩的原野”,暗示了树木都被砍掉的荒凉景象,“大量的泥土流失,山脉变得荒凉”“山丘光秃”“来自鄂尔多斯的沙尘暴”“延安的黄土”“冰川萎缩和消失,像夏季的云”等等。④Gary Snyder, The Back Country.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8, pp.187—188.
毛泽东也许是史耐德实现生态理想的一个希望。“翻过这座雪山/ 我们就将见到毛主席!”⑤Ibid., p.187.诗歌将毛泽东塑造成为一个生态英雄,着重渲染了这位中国领袖在长征和延安时期的简朴生活,如粗布衣衫、油纸雨伞、土制饭碗、古旧的公文包、随风飘逸的头发、自制的烟卷、窑洞等,这些细节都将毛泽东塑造成为一个大山里的人,与中国古代的寒山类似,当然也与史耐德自己类似,过着史耐德想要的那种简朴生活。
诗歌第二部分主要写史耐德自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大山中的一些经历。毛泽东在长征中翻雪山、过草地的时候,史耐德只有四岁。1951年,他在大学时期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和美国的印第安文化,学习中国的书法,以及如何使用筷子。他在大山中与伐木工人为伍,吃粗面包,住简朴的工棚。由于他有中国情结,对米饭和酱油情有独钟,伐木工人有时候拿他开玩笑说:“史耐德,你他妈就像是一个中国人。”⑥Ibid., p.189.史耐德感觉那些大山好像就是释迦牟尼曾经逗留过的地方。
史耐德还回忆了他的一段难忘的恋爱经历。他与她曾经在梨花树下漫步、接吻,傍晚手拉着手漫谈列宁和马克思,“我的手伸进她的上衣,解开了她的胸罩”“她馨香的呼吸,在五月太炽热了”。⑦Ibid.他与她在绿树、鲜花、清泉之中,犹如一对亚当与夏娃。恋爱中的史耐德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以爱心彼此相待,而不应该有前面提到的那些对抗和战争。但是后来她去了北京,仿佛把他的爱也带到了遥远的东方。
在这里,史耐德个人的爱与事业的爱汇合到了一起。中国与他的那个她合二为一,变成了他的恋爱对象。最后,他呼吁毛泽东不要抽烟,不要生产炮弹,不要理会那些西方的哲学家,而要多种树,坚持农耕,在河里游泳,穿粗布军装。①Gary Snyder, The Back Country, p.190.这样他就会成为史耐德生态理想的化身,他们就能够一起去喝酒,成为朋友。
我们可以看到,史耐德所谈的政治最终都会回归生态。他把年轻时政治上的激进倾向运用到了生态诉求之中,使他的生态政治也增添了一份激进。他说,“我们需要一场生态革命”。金斯堡的激进主义主要是反对社会对个性的压制,反对资本主义的泛商业化对创造力的吞噬。史耐德的激进主义主要是反对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反对人类在自然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傲慢,不管这种傲慢是来自西方,还是来自东方。
总体看来,20世纪60—70年代的史耐德与那个时代的激进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他继承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关于中国革命是道家思想在当代的延续的观点,认为道家的“齐物论”思想从根本上讲是反压迫、反父权的平等思想,它“跨越了铁器时代的声音障碍,原封不动地从另一头传出来”②盖瑞·史耐德:《山即是心:史耐德诗文选》,林耀福、梁炳均编,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65页。。他赞扬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植树造林,但不赞同中国进行的“灭麻雀运动”。③Gary Snyder, The Real Work: Interviews & Talks, 1964—1979, p.127, 129.从这些细节看来,马克思主义对史耐德来说,不仅仅是“关于人与人平等的科学”,而且也可能是关于人与自然平等的科学。
四
史耐德1984年访问中国期间还写了一首诗叫《枫桥边》(At Maple Bridge),诗歌描写了他去苏州城外寒山寺的游览经历。在寒山寺,他想起了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想起了其中描写的江枫渔火,以及来自寒山寺的钟声。他在《枫桥边》一诗中除了误将“寒山寺”当成寒山出家的寺庙外,还描写了正在搅拌沙石和水泥的工人们,他们显然是在修建旅游设施。他仿佛听到寒山寺的钟声,飘过浪花拍打的古渡口,飘过太平洋,“石阶渡口,空无一人,浪花拍岸,钟声悠扬,跨过大海。”④Gary Snyder, The Gary Snyder Reader: Poetry, Prose and Translations 1952—1998.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 1999, p.544.
钟玲对这首诗歌的解读几乎已经成为理解这首诗的标准答案:这一钟声跨越古今、横越东西,具有一种“文化混杂性”,将中美两国的诗歌连接在一起。“工人正在进行造桥的工程,史耐德在这一辑译中也筑成一道坚实美观、中西合璧的桥梁,以跨越东西方文化的鸿沟。”⑤钟玲:《史耐德与中国文化》,第46页。但是,史耐德引入中国材料的主要目的可能还不在于表达对中国文化的敬意,而在于书写保护古代文化与发展当代旅游业的矛盾。沙子和水泥这些现代建筑材料与古韵十足的寒山寺和古渡口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反映了“史耐德对迅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中国日益拥抱市场经济、忽视藏传佛教和实施非生态政策等所持有的怀疑态度。”⑥Jonathan Stalling, Poetics of Emptiness: Transformations of Asian Thought in American Poetry.New York: Fordham UP, 2010, p.119.
史耐德的生态政治观是他批判现代社会的强大武器,可以帮助他与伤害自然的行为作斗争。《地球母亲:她的鲸鱼们》(Mother Earth: Her Whales)创作于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期间,后发表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诗中列举了地球上受到人类威胁的动物:猫头鹰、蜥蜴、麻雀等。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史耐德没有避讳,甚至有相当犀利的批评。他说:“麋鹿/ 两千年前曾经生活/ 在黄河的滩涂上,其家园后来变成了稻田。洛阳的森林在公元1200年/ 就被砍伐,造成了泥沙流失。”⑦Gary Snyder, No Nature: New and Selected Poems, p.236.
史耐德认为,这次联合国环境会议的参会各国不是来谈贡献,而是来谈利益,不是来谈拯救地球,而是来谈瓜分地球。日本不思考如何保护鲸鱼,而是思考哪一种鲸鱼可以猎杀,它像传播淋病一样向大海倾倒甲基汞。这个“佛教国家”做出这样的事情,让史耐德倍感失望。巴西对亚马逊流域的自然资源进行大规模开发,并将此视为“主权”内的事情。中国的麋鹿、东北虎、野熊、猴子都变成了“去年白雪”,杳无踪迹,肥沃的土地变成了“5000辆卡车的停车场”。①Gary Snyder, No Nature: New and Selected Poems, p.236.美国和加拿大对北美大陆生态圈发动的“战争”也被纳入了他谴责的范围之中。
在这些例子背后,史耐德谴责的是“几乎所有现代文化的哲学基础:人类中心主义”②Patrick D.Murphy, Understanding Gary Snyder, p.121.,即诗歌中所说的“人是最宝贵的生物”。然而,谁能够“为绿叶说话?为土壤说话?”“第一世界的强权与科学家政府?第二世界的帝国主义与资本家?第三世界的男性共产党官僚?”他认为,他们都不能。因此,史耐德号召蚂蚁、鲍鱼、水獭、狼、麋鹿“站立起来!”号召直立的树、飞翔的鸟、游弋的鱼、“两条腿和四条腿的人们,团结起来!”③Gary Snyder, No Nature: New and Selected Poems, p.237.既然人类不可能为它们说话,它们应该自己为自己争取权利。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站立起来”(Rise)和“团结起来”(Solidarity)在史耐德创作该诗的年代都是革命词汇,它们充满了革命的含义。《国际歌》的歌词是这样说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因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在这里,史耐德再次挪用了当代的社会政治话语,将“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运用到他的生态诉求之中,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们需要一场生态革命”。
我们认为,史耐德的“生态革命”的核心就是“农村包围城市”,至少在1984年之前是这样的。欧洲和美洲的“城市化”在后工业时代已经发展到了极致,美国大概有80%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并且“城市化”还在向无人的荒野蔓延。史耐德在《前线》(Front Lines,1974)一诗中将城市与荒野的边界比喻为双方战斗的“前线”,将开发商、伐木企业比喻为“癌症”,他们不断毒害和侵蚀森林的边界。他呼吁人们划出一条界限,阻止电锯和推土机对大地母亲的“强奸”。④Ibid., p.218.
史耐德号召人们融入到荒野当中,去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他自己的生活就是这种“荒野理想”的一个范例。如果具有“荒野理想”的人群增加到一定程度,那么可以推测城市会萎缩,乡村会扩大。这不但可以逆转城市化的蔓延,而且还能够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初衷。艾德温·福尔森(L.Edwin Folsom)评论说:“史耐德宣布要重新开放疆界,努力向东推移,逆转美国西进运动的历史进程,促进荒野向文明地区进发,从而将深藏于人们心底的能量释放出来。”⑤L.Edwin Folsom, “Gary Snyder’s Descent to Turtle Island: Searching for Fossil Love,” 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 15 (1980):109.也许这就是史耐德所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