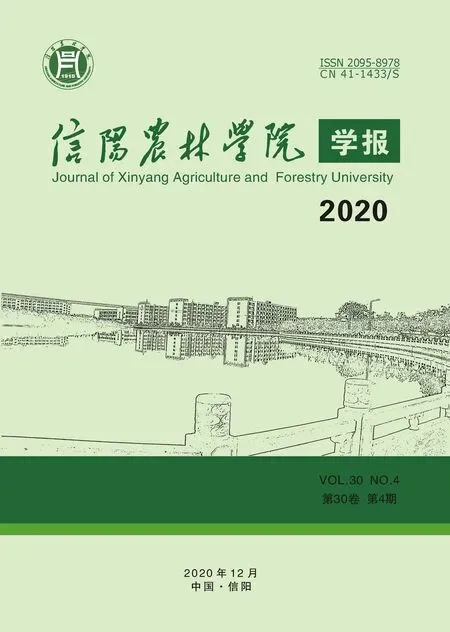狐狸文学母题的形成根源及其文化心理考察
黄露莹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仙(天)界、人间与幽冥共存,无数鬼魂、精怪游走其间。这样荒诞而诡谲的世界被封存在诸多古代文学作品中,如《太平广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以及《子不语》等等。这些作品有更为概括性的名字——志怪小说,“志怪”内容庞杂、种类多样,但都不出一个字——“怪”。卡西尔曾在《神话思维》中指出:“世界的各部分被指称为各种神,物质实在和人类活动的特殊领域被置于诸神的卫护之下,与此相应,世界变得更易理解。”[1]70这里指出的是神话思维在原始社会的解释功能,它为人类提供一种理解和解释世界的途径。在这种思维模式主导下,精怪(神魔)形象应运而生。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人类不再单纯通过混沌不自知的原始神话思维而是通过具体可知的思维观念实体——精怪来认识世界。这类渗透着社会化认识、社会化情感的形象积淀下来,进而成为了留存集体无意识的艺术形象,其中尤为突出的便是狐狸。
狐狸作为历代文学家们特别青睐的创作对象,已经不仅仅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产物,而是长时间历史积淀下的文化产物。这种长期反复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人类精神现象和基本行为,通常被称为“母题”,其中很多源出于或包含着在荣格那里被称为积淀着“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或原型”。作为后来发展为母题的原型或原始意象,它凌驾于个人无意识之上,扎根于无垠的民族历史记忆中,又由于遗传而留存在每一个个体的心灵深处。它“是一个不断地在历史进程中重现的形象——无论它是一个妖魔、一个常人或一种过程。每当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时,它就会出现”[2]。与此同时,荣格又指出:“它们展现了一幅一般的心理生活的图画,并且被分解为和投射入本民族神话中的众神的多种多样的形象之中。”[2]狐狸形象同样有积淀着集体无意识之原型的内涵,它不是某一部作品中的某一个形象,而成为混融了多重文化心理的母题类型。“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情势,就会有多少种原型。无止境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刻进了我们的精神构成之中,但是并不是以充满内容的形象的形式,而是首先仅为没有内容的形式,仅仅表征某种感知与行为的可能性。”[3]这种“没有内容的形式”会随着具体历史语境的激活而被确定,如果对其进行历史时期的分段式分类很容易侧重于各个时代的文化个性。因此,笔者欲从狐狸母题的最初形态开始,以狐狸形象的不断丰满和内涵的不断丰富为研究路径,从中提炼出共性的形成根源和深层的文化背景。笔者认为狐狸母题的产生源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本能、人类心理调节的需要和人类审美猎奇的渴求。
1 人类认识世界的原始本能
狐狸文学母题的诞生源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本能。狐狸在远古作为高媒神存在,这是母系氏族社会人类生殖崇拜的一种表现。原始人类对于狐狸的认识是:“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家成室,我适彼昌。”[4]21这段话寓意多子多福、家庭美满,与《诗经》中的“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5]是同一个意思。这种用动植物来启示人类社会福祸现象的做法在原始社会非常普遍,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结果。
首先,原始时期人的愚昧认知。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有限。人类没有产生自我意识,渺小的生命力和有限的认知力使人类将自我与世界混为一体,将自身属性投射到周围所有事物上形成了“万物有灵”的意识。其他生物进行的与人类似乎无异的繁殖、捕猎、社交活动也给予了人类灵感,于是人类开始审视自身的生产生殖活动。九尾狐寓意多子多福从而成为对大禹婚姻的吉祥启示就是这一思维的产物。人们不知道生殖的奥秘,又力图对此加以探索,于是这种启示逐渐成为当时的科学认知。当多子多福与九尾狐的联系被固定下来,九尾狐就在一定时间内代表着繁盛的生殖力而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此时,狐狸被象征化、观念化为生殖图腾,已不再仅是涂山氏,而是一个生殖神,体现着原始人类对神秘生殖的认识。
其次,进阶的认知渴望。当人类加深对自然界的了解后,人类意识到自己与周围的生命体不同。此时的人类有了主体意识,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建立了人类为“万物之灵长”的意识,人类应当也有能力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于是我们开始与自然(认知客体)形成对立格局,并企图为它们建立一个科学的认识系统。而此时许多人类无法解释的现象限制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于是人类将这部分认识盲区归结到一些所谓的神秘力量上,如鬼魂、精怪等。通过这样,人类自认为对世界的了解更进一步,与此同时,也在通过描绘战胜神秘力量的故事来获取自我力量的确证。于是无数狐狸作祟的故事被创造出来,这些故事又无数次地以狐狸被驱除的结局收场。九尾狐的地位在后来慢慢衰落也顺理成章,因为人类对生殖有了一定的科学认识,便不屑于将自身与兽禽混为一谈。最重要的是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狐”多产的母性体征已经不太适应父系崇拜的格局,多产暗示的一妻多夫制挑战了父系权威和逐渐建立的父系道德伦理。于是后羿之妻纯狐玄妻已不再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而成为淫荡不洁之妇,并且作为一个母题类型衍生出无数淫荡的狐狸形象,例如阿紫、妲己、胡媚儿等。
最后,形象思维的盛行。原始社会的人们主要通过形象思维而不是抽象思维思考问题。当人类将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归结于神秘力量时,这只是认识的第一步,还需要为莫可名状的神秘力量找到一个具体形状。卡西尔曾提出三种神祇,最原始的瞬息神指人们将当下瞬息震撼到自己的力量当做神来崇拜。卡西尔指出:“人人尊崇这个力量,而人的崇拜又赋予这个力量越来越确定的形式。”[6]这便是一个形象化的过程,狐狸在早期生殖崇拜时期呈现为九尾也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李建国指出“雌狐阴户临近尾根,所以兽类交配叫交尾。因而这里显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含义,尾多则阴户多,阴户多则多产子,结果是子孙昌茂,氏族兴旺。这里九尾尽可理解为九阴(阴户),是女阴崇拜的曲折表现”[4]27。于是神秘生殖力量具有了九尾狐这一实体形象,并且在往后还有了人类与其接触的故事。除此以外,如天界、冥府等神秘领域也被形象描绘为有人去过的真实图景。当这些东西都被形象化后,神秘力量才随着实体形象而被人认知、驱赶或战胜,此时才意味着人类真正掌握了探索未知、征服世界的能力。
2 人类心理调节的需要
从源头上说,人类具有渴望认识、理解、掌控并征服世界的野心,而当人们遇到无法认知的领域时,往往会受到打击并产生自我怀疑,于是狐狸精等神秘力量的形象实体被创造出来。这种方式如同卡西尔在《神话思维》中提到的:“现在,人们不仅以一种新的精神形式理解世界,而且首先以这种新的精神形式理解自身。”[1]186因此,笔者认为将无解现象归结于神秘力量的方式不仅源于人类认知世界或理解世界的本能,同时也源于人类心理调节或理解人类自身的需求。
首先,性压抑的心理宣泄。这类想法在创造性淫类狐狸母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刘仲宇称人们由于“性欲得不到发泄而导致心理失衡,于是产生了在梦境和想象的幻境中与异性恋爱、性交的病症”[7]。在生理欲望禁锢森严的时代,人们寻求一种发泄途径来获取心理舒适。迎合这类愿望产生的淫狐母题既能让人类发泄欲望又能让人类实现自我安慰——是狐淫而非我淫。对性的讳莫如深使得人类难以科学认识“遗精”、“生理需求”等概念,当个体无法克制进行意淫和自我安慰时,表示他(她)遇到了认知难关和心理关卡,此时“淫狐吸精”的概念便顺势而出解决人类的难题。精神自制力差、体质不佳而极易造成萎泄的病症被人们归结于狐狸作祟,连癔症等精神错乱的疾病也被认为是“狐媚”之症。此时,人们既解决了合理解释病症的难题又隐藏了内心难以启齿的欲望,于是在心理宣泄后人们也两全其美地获得了内心的极大满足。
其次,恋畏女色的心理安慰。从以上分析出发,亡国祸水的淫狐母题就是一种更为极端的自我催眠。诚然女色误国有它一定却极为有限的真实性,但到底是统治者不自制产生的影响大还是女色的诱惑力大呢?妲己作为这一形象的典型代表为我们作出了解答:就算是像纣王一样的统治者,自身文武兼备,前有比干等忠臣贤将辅佐,后有姜皇后等娴后淑妻陪伴,但他倾覆一个帝国的根本缘由却在于妲己。妲己形象正是古代很多人进行的一次集体精神安慰。有人将这种心理根源解释为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恋畏情结”:“狐狸精大多美丽迷人,象征了男性对于女子在感情上的追求与爱恋;而她们又害人杀人,象征了男性对女子在理智上的自我警告和约束。”[8]狐狸的魅惑力可以大到迷惑帝王以致祸国殃民,也可以小到诱惑文士以致耽功业误人生,但本质上或绝大多数时候它却不过是人类进行心理安慰的替罪羊。
再次,贤妻尤物的心理平衡。排除会带来祸事的媚狐,更能获得心理满足的是狐人相恋母题中的美狐。这种“美”不仅是相貌美更是心灵美,因此她们既可以让人们宣泄欲望还不会为人们带来恶果。此时的故事很多成为大团圆的才子佳人型故事,这时的狐狸是符合无数文人心理需求的佳人伴侣。它既拥有“尤物”的美貌,让人保留有心理放肆的空间;又拥有“贤妻”的品格,让人维持自我端庄的形象。这无疑是一种幻想出来的两全其美,实际上多数为的就是文人的心理平衡。
最后,为善去恶的心理补偿。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报恩报仇类的狐狸母题。它们是因果报应的观念体,启示着人们今生要积德行善而不要为非作歹。尽管许诺的是虚幻的来世幸福,但其出发点却极为现实;虽然是迷信性质的伪科学,但它却是苦难时代的人们苟延残喘的“强心剂”。其实“报应”阻拦不了真正作恶的人,但此类母题书写所发挥的“心理补偿”能遏制一部分作恶苗头,燃起一部分为善星火。
3 人类审美自觉与猎奇
狐狸从自然生物界进入到人类文化领域后,狐狸文学母题就诞生于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的怀抱,发源于《山海经》等早期作品中。之后狐狸经历了人类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改造,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文学加工。自此,自然物狐狸开始频繁地作为各类文学形象出现,并随着文学的发展而日渐内涵丰富、形象鲜明。在这种不断地被塑造和被添加新内涵的过程中,狐狸成为文学母题,历经复杂的审美历程,亦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
其一是审美自觉化。“志怪”曾长期隶属于史部,直到宋代欧阳修等撰《新唐书·艺文志》才将其归属于子部小说家类。小说在古代也长期处于“饰小说以干县令”的定位而没有成为一个文学类别被独立出来。志怪之“志”原义便是偏向于指记载和记录,因此“志怪”一直到后期都保有搜罗各种民间故事和传闻再记录在册的写作传统。陈文新在《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中将志怪小说分为“博物”体、“搜神”体和“拾遗”体三类[9]。第一类的代表作《山海经》的很多故事就是将“怪”记录在册,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山海经》中“怪”的文化性质是“不具备人格化和人形化的‘怪物’”[4]35。第二类的代表作《搜神传》则在记录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仙、鬼、怪的系统。这两类都与史书的结构类似,将帝王、英雄等人物记录在册,并为他们构建一个系统。第三类的代表作《拾遗记》已经进入到文学自觉的魏晋时代,更多是作家自觉地加工创造,它也被认为少记载而更近于后来的唐代传奇。于是自传奇体志怪小说脱离史传窠臼后,一部部不符合历史真实而有传奇色彩的文学作品被创造出来,《任氏传》就是其中的代表。没有历史人物作为依据的“任氏”身上满载传奇色彩,她为人称道的故事更是文人“有意为小说”的成果。小说曾作为稗官之野史存在,“有意为小说”的观念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富于文学性的作品,它还带给我们自觉认识文学地位、文学本质和文学规律的意识。我们不仅发现了如何写小说,我们更发现了什么是小说。龚鹏程曾提出:“神话与幻想经过若干变迁之后,依然和历史的写实精神紧紧结合着,成为文学的基本结构。”[10]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可忽视史学传统的影响,志怪小说从原始神话中孕育出来也曾与史书不分你我,但在文人自觉创作、文学自我独立的过程中,志怪也一起被重新认识。
狐狸从最初的神话图腾到民间信仰里的狐仙再到聊斋式的美狐,这一转变历经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学者将这种转变分为“民俗宗教态”、“民俗审美态”、“文学审美态”三种态势[4]112,并认为:“并不是说文学中的狐不能以妖祟人,把民俗宗教中的狐妖创造为一种邪恶意向,其实也是一个文学审美过程——‘审丑’也是审美,但是,我们是在用审美手段对狐进行审美理想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学审美化这一概念的,这是因为美狐的创造更富于审美意义和文学意义,文学创造的价值所在是对真善美的把握,创造美好事物是文学的基本追求。”[4]299这里讲述的其实就是伴随文学自觉化进程的审美自觉化,从宗教图腾到淫狐再进阶到“美狐”,正是由于文学审美自觉在狐狸母题产生和发展路径上的作用力。
其二是审美猎奇化。狐狸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他者形象出现的,人们对其充满了认知的好奇心,这种认知好奇心也极易转变为审美上的“猎奇心”。叶舒宪在《原型与跨文化阐释》中提出:“对荒怪事物的关注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现存事物的反思,产生某种‘陌生化’的效果。而这种空间转换和价值转换有利于观念上的去蔽和更新。”[11]于是正统诗歌文学趋于僵化的时候,人们便选择了狐狸这一处于“人物之间”、“幽明之间”、“仙妖之间”[12]的边缘事物来参与小说的创作,狐狸的边缘性和灵异性都能够极大激发文学潜藏的活力。国外有学者指出:“人类的秩序已经扩展到甚至包含了那些原本是外来混乱化身的生物,但狐狸保留了它的矛盾性质,暴露了秩序倒退到混乱的倾向,使熟悉的人再次变得陌生。”[13]文学世界里的狐狸是人性和妖性的矛盾统一,这使得它既能贴近现实又能产生陌生化的文学效果,因此诸多非神怪小说体裁的文学作品也会加入神怪情节来增强文章的新颖性、激发读者的兴趣度。继而随着历史延续,当狐狸二字所指称的文学内涵被极大多数人共同内化的时候,它就从最初文学作品中的新奇意象转身成为了中国人信息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密码——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内涵高度一致的母题。
与强调母题之陌生化稍有不同的是,加拿大学者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则说明文学母题具有集体性的一面,从而从另一层面有助于我们理解狐狸母题的审美内涵,虽然他赋予神话原型不少神秘性意味。弗莱认为最基本的文学原型就是神话,在文学循环发展的历史长途中,其余文学类型或多或少受到神话原型的渗透。神话原型体现着人类集体久远的历史记忆和精神想象,又表现为有限而重复的模式。他指出:“原型是联想的集群,与符号不同的是它是复杂可变的。在这一复合体中常常有大量特殊的、靠学习而得的联想,这些联想是可传播的(communicable),因为在特定文化中的好些人都对此很熟悉。”[14]正如弗莱所提出的“可传播性”,这种特性使得文学中的狐狸形象,能在风云变幻的岁月中唤起人们对它的认知感受。“狐狸”这一母题已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使用的内涵相通的语言符号,并在时间的积淀下成为一个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皆可理解的文化标识。因此,尽管狐狸母题常表现得不无荒诞、无理、扭曲之处,但却在文学园地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