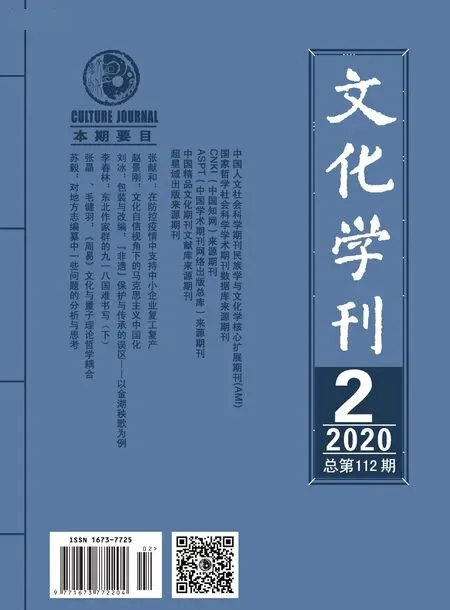清寒的当代浮世绘
——《应物兄》的色调解读
刘牧宇
2019年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公布,《应物兄》名列其中。这部十三年磨一剑、出版以来就饱受争议的作品终于取得了自己的位置。李洱曾说此生只打算写三部长篇,分别写给历史、现实与未来,立足现实的《应物兄》故事其实十分简单,即济州大学对儒学研究院的筹建以及儒学大师程济世的归国还乡,这个“象牙塔围墙”中的小事却借由主角的生活轨迹,串联起一幅浮世绘,在其中延展着枝干,围墙也被逐渐淡化,指涉向更广阔的世界。虽然题材形式与《花腔》截然不同,但字里行间依然隐伏着李洱独有的智性和机趣,由此在多个层面为作品添上了清寒的色调。
一、冷幽默反讽下的崇高消解
“让荒唐变得合情合理是一种本事,让‘相反的念头互相撕咬,互相吐痰又互相献媚’是一种别样的智慧。”[1]将反讽精神作为小说的建构底色不是李洱的第一次尝试,《花腔》中的反讽使用就曾是极富魅力的闪光点,而《应物兄》在描摹当代知识分子群像时的戏谑很难让人不联想到《围城》。钱钟书对讽刺运用堪称妙笔,才情才气与文学修养不露声色地在字句中渗透,诸如“肉上一条蛆虫从腻睡里惊醒,载蠕载袅”的金句俯拾皆是。《应物兄》则选择以知识碎片的填充和拼贴形成一种特殊的反讽结构,作品中大量精心设计的知识陈列一面填充着细节空间,一面实现了对人物和主题的深入。应物兄在和弟子讨论珍妮的论文时,众人煞有介事地旁征博引,把驴和儒学之间的关系论述得头头是道,甚至得出黔之驴有“我佛之大智、大忍、大善”的结论。为了争取到安全套生产基地的落户,邓林给它安上了出自《论语》的“温而厉”一名,还由此引发了一场“涉及深奥国学知识的性文化大讨论”。这些看似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更像是打着知识旗号的荒诞表演,创新异化成了标新立异,而对待学术的随意和不严谨深入肌骨地被剖开呈现。李洱的高明在于这一切都含而不露,没有对任何人物显示反感,也未建立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只以适度、宽厚的智性言语去记录熙攘本身,成为一种更深刻和内敛的冷幽默。
《应物兄》的反讽不再局限为文字修辞,而是一种总体性的反讽,在人物言辞同行为的脱轨和命运的不可控中体现反讽的力度,“它揭示的是生活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无可避免的悖谬:所有人物的行动都被自己所不知道的无意识力量支配,因而,他们既是被审视、嘲弄的对象,又是被同情、怜悯的对象;他们未必是无辜者,却一定是无助者”[2]。程济世最忌讳“无后为大”,偏偏私生活混乱的儿子生了个怪胎;华学明本以为足以获诺奖的成果却被野生济哥的苏醒摧毁,自己也疯了。如斯的阴差阳错流淌在作品的每个角落,有意义发展成了无意义,悲剧丧失了崇高内核,而学术、儒学等事物也就此消解,跌落神坛。《应物兄》把不动声色的冷幽默与反讽晋升为观察世界的方式,潜藏着对当代学人精神荒芜和当下文明困境的思索,在这个层面上,它不输于《围城》。
二、冷色笼罩的众声喧哗
应物兄的名字源于经学家王弼的“应物而无累于物”,他像一只劳蛛,在以自己为中心织就的大网上虽然做到了“应物”,却未能“无累于物”,勾连着政、商、学等界的七十多个人物,游走于复杂交错的关系之间,呈现出“学术江湖”的浮世绘。围墙之外,由于程济世声名在外,筹建工作复杂微妙了起来,校长亲自操刀,各界全力参与,当程济世多次谈及回忆里的济州,筹建也牵一发而动全身,引来了酒店老板、养鸡大王、内衣大王等利益攫取者粉墨登场,最终演变成旧城改造、引进外资的“大事”。程先生的弟子黄兴,一个将安全套捆绑上古典词牌名兜售的“当代子贡”,他到访济州一段是丑态的集中揭露。争夺“敬香权”时,邓林以权谋私的手段堪称高明,善于溜须拍马的他还以典故为栾长官母亲的排便问题建言献策;慈恩寺大和尚释延安是在物质和宗教间走钢丝的好手,他的绝活是把笔绑在“那话儿”上作画、写书法,因此润格远高于他人。连一校之长葛道宏也张口便是“我也接触过不少省部级大员,像您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有没有?有!但不多”之类的高妙奉承。
而回到学界,作品着重刻画了三代学人。老一代的代表是济大四位博导,他们身上多数时间体现出对专业知识、奉献精神和理想信念的坚守,但在时代的推波助澜下也难免迷失在功利化的道路上,“总是被一群学者簇拥着,从这个会到那个会,究竟是什么会议,姚先生都搞不清楚,也懒得搞清楚”[3]。乔木宣扬了一生立命担当、老来却满是明哲保身的酸腐气息,常训斥应物兄“你这个人,够机灵,却不够精明”,把学术与厚黑混为一谈,活成了“人精”。应物兄、华学明、文德斯这一代人则体现了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变迁中的分化,华学明之流自恃取得了傲人成果,便自称“华先生”,儿子也荣升“华公子”;而芸娘、文德斯则保持了难得的理性与克制,目光澄澈地旁观一切。到了他们学生一代,则完全淹没在了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大潮里,学术成了经营关系的名利场,甚至爆出“用力过猛牛X,肾虚手抖傻X”这种惊世骇俗之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对其最好的注解。个性鲜明的众生相与他们的熙攘喧哗让小说“读来哑然失笑,冷汗直流”,一步步落入“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荒凉。
三、闪烁的暖光:“一切诚念终将相遇”
程济世作为各方期待的灵魂人物却始终居于暗处,他的返乡的确隐喻着儒学传统从西方向中华的“回归”,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这一决心的落脚点不过是记忆里的“仁德路”“仁德丸子”和“济哥”。于是原本为“儒学精神”而筹建的研究院,重心立马转向旧址的探寻和济哥的寻找培育,精神上的“仁德”则不再重要。而大费周折之后,野生济哥根本未灭绝,层层考证出的仁德路位置也是假的,至于程济世本人的回归直到结局也未有一丝征兆。《应物兄》出版之初,就有“几代作家向《红楼梦》致敬的重要收获”的推荐语,尽管过誉,但这场最终沦为“等待戈多”的荒诞闹剧确有了几分《红楼梦》的悲辛酸楚。所幸李洱狂欢化叙述铺陈出的寒凉并没有成为唯一的色调,毕竟此类风格的作品极易在向滑稽或讥讽的高歌猛进中降低了格调,“对历史或者现实最难的呈现方式是正剧,单纯的喜剧和悲剧都是相对容易的”[4]。后半部对双林父子、芸娘等人物的内心深入使作品终于闪现出难得的暖色。物理学家双林院士将毕生献给了国家建设,深藏大漠数十载,甚至不知妻子去世和儿子去向,一直得不到双渐的原谅。但在双林意识到大限将近,动身祭奠同事亡灵而行踪不明期间,双渐开始体谅父亲,双林也把对儿子缺失的爱倾注在孙辈身上,义务讲课,资助失怙儿童,希望在年轻一代身上传承学人精神。还有端庄睿智的芸娘,何为教授评价她:“她说话,人们就会沉寂。嫉妒她的人,反对她的人,都会把头缩进肩膀,把手伸进口袋里。”最懂应物兄的也是她,她提醒他要张弛有度,下蹲是为了蹦得更高;让他读二三流作品和枯燥的史料文献,学会避开沸点。应物兄对芸娘的感情也十分深挚,在负责筹建工作后最担心芸娘对此不满,但知晓芸娘支持他后,“所有的阳光都扑向了雪”。他们身上凝聚了作者对学人应具有的情怀和品质的期望。
赵汀阳说:“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时代要多,但我们丢失的东西也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少。”[5]应物兄也不无担忧地自嘲:“到了21世纪学术就是个饭碗。”他自己不得不在“应物”的过程中迷失,内心所秉持的情操正如他在浴室的状态一样,太过“赤条条”而难被容纳,象牙塔的失守和书桌的无处安放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那我们是否还能做些什么?李洱的答案始终肯定。应物兄最终在棚户区找到了张子房和曲灯老人一直坚守的仁德路,尽管在终章他遭遇车祸,但精神恍惚之际他对自己的发问“你是应物兄吗”得到了清晰的回答,“他是应物兄”,意味着他实现了自我的找回和确认。由此,李洱留下了最温暖的色泽,“一切诚念终将相遇”。
四、结语
《应物兄》的争议并未因获奖而停歇,多数源于出版营销带来的反噬,如果没有为读者的阅读期待附加“挪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地图的坐标”“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等话语,它或许会受到更为公正的评价。《应物兄》确实带着试图飞跃“经典”的野心,从布局设计到世道人心的试探,李洱都展现出了技艺的成熟,但也如评论者所言,“凭一己之力写尽世间百态,实在是个充满暧昧诱惑但难度系数实在太高的指标。”[6]毛尖称其“就是我们这三十年的生活和对这段生活的反思,是我们狗血但也是血的世界,是我们世纪末又世纪初的人生,是我们既抒情又反讽的当代生活”[7]。如此看来,《应物兄》至少作了“砍向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的斧头”,也隐约窥见了当代文学创作的应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