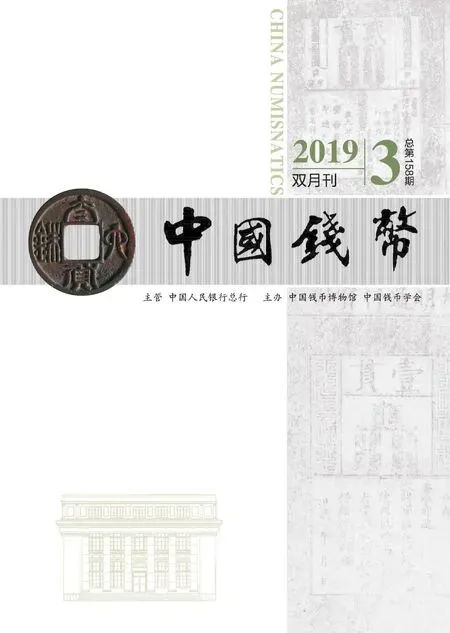明代九边军镇铸币考论(下)
张 冬(重庆)
四 陕西战区铸币
明代的陕西省幅员辽阔,包含现今陕西、宁夏、甘肃三省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九边中有四镇都在其中,延绥镇、宁夏镇和甘肃镇共称为西北“三边”,另还有一个固原镇(也称陕西镇),陕西三边总督驻地就在固原镇城。
明代由于缺铜,总体铸钱数量不高,陕西省内出产铜矿,是当时铸钱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陕西军镇铸币始于崇祯三年的甘肃镇,延绥镇在崇祯时期也有开设钱局,宁夏镇和固原镇是否铸钱未见有明确记录。
1、甘肃镇
至若甘镇从来亦无所谓鼓铸也,鼓铸自饷司郭应响始,允其请而见为救时裕边委资鼓铸者,今陕西督臣杨鹤也。[1]
甘肃镇位于明长城最西端,东起兰州,西至嘉峪关,占据河西走廊,是明九边中最早设立的军镇之一,该镇总兵和巡抚驻地都在甘州(张掖)。
杨鹤是明史中一个悲情人物,他于崇祯二年上任陕西三边总督后,主张对省内的农民起义军进行招降安抚。皇帝最初很支持他的政策,并于崇祯四年正月下诏书,命御史吴甡携十万两帑金前往陕西赈济。然而几个月后,曾经受抚投降的义军首领纷纷复叛,杨鹤的绥靖政策彻底失败,他被捕入狱受到戍边的处罚。
郭应响,字希声,福建福清人,崇祯初任户部督理甘肃、固原两镇粮储员外郎,他所管理的机构称甘固饷司,驻地位于甘肃镇内紧邻固原镇的兰州。崇祯三年,郭应响筹集了白银一千六十二两七分二厘,其中包括他自己捐出的二百四十两,用于购买铜料、鸠集工匠。甘固饷司钱局六月十九日开炉,至九月末停炉,一季共铸崇祯通宝金背钱1152000文,作价每8 文准银一分,共值银一千四百四十两,除还工本外获利银三百七十七两九钱二分八厘,利润率约为35.6%。[2]当年十月钱局再次开炉,至十二月末停炉,第二季用铸本银一千九十两一钱二分,共铸钱1170000 文,值银一千四百六十二两五钱,获利银三百七十二两三钱,利润率约为34.2%。[3]
据郭应响自述,甘镇所铸铜钱每文重一钱,一季共铸六十五炉,每炉用红铜六千六百九十五斤,每斤值银九分八厘,用窝铅(锌)二千四十七斤八两,每斤值银一钱一分六厘,铜与锌的配比为7.66:2.34。甘肃铜价与京师相比偏低,而锌的价格更高,采用高铜低锌的铸材配比更为合理。

图9 崇祯通宝背“户”【秦版】
甘镇每季铸钱数量不及宣府十分之一,利润率却远超后者。崇祯四年五月宣府钱局被下令关闭时,甘镇钱局仍在继续铸钱。[4]之后不久,郭应响调任延绥镇榆林兵备道佥事,钱局或因此而停罢。现今甘肃境内出土崇祯通宝数量颇多,涉及的背文品种繁杂,其中有一种秦版崇祯背“户”钱,结合史料、出土和钱币特征分析,它们应该就是崇祯年间位于兰州的户部饷司钱局出品。
2、延绥镇
延绥镇地处陕西北部,东临府谷黄河岸,西至定边花马池,境内长城一千余里。延绥是延安、绥德两地的合称,最初的镇城设在绥德,成化年间镇城迁移至榆林,该镇因此也被称为榆林镇。
崇祯四年八月时,陕西境内只有省属钱局仍在开炉,巡按李应期上疏称铸钱有厚利,建议各抚道一体开铸。工部回复称:“秦中为产铜之乡,则鼓铸之兴不容稍缓,况称所铸千钱其本止须四百,利过于本可谓极饶,此京铸所不能得者,自应俯从所请,听其支本省堪动银专官开铸。”[5]户部尚书毕自严对李应期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之前陕抚刘广生上报的铸息每年只有六七千两。他覆疏建议甘肃、宁夏、延绥三镇“酌量机宜,从长商榷,”果真有利即行鼓铸,感觉不便也不要勉强。皇帝认可工部的提议,对毕自严的答复表示不满,说他“空言塞责”。[6]
此事后续未见记录,但至少延绥镇可以确定开设了钱局,证据就是陕北地区出产的崇祯通宝背“榆”钱,这里“榆”指的是榆林。它们在黄河对岸的山西境内也有过批量出土,或与当时渡河的农民起义军有关。

图10 崇祯通宝背“榆”【标准式】

图11 崇祯通宝背“榆”【太平手】

图12 崇祯通宝背“榆”【新手】(江苏王承藏品)

图13 崇祯通宝背“榆”【官手】(江苏王承藏品)
崇祯通宝背“榆”钱版式本文列举有四种:标准版、太平手、新手、官手。标准版工艺相对规范,存世数量也较多。另外三种怀疑是借用了秦版崇祯背“太平”、背“新”和背“官”钱改范翻铸,少数样品“榆”字周边还能清楚看到模具改造留下的痕迹。
五 秦版崇祯通宝背文释读
崇祯时期对铜钱背文的管理尤为混乱,各地自成一派。陕西古称“秦”,当地所产明钱古泉界称为“秦版”。秦版崇祯钱常见背文有八种:“户”、“榆”、“新”、“官”、“兵”、“制”、“奉制”、“太平”,另外老谱上还有一枚背“新钱”。“户”和“榆”之前已有介绍,是陕西军镇钱局所铸的记地(局)钱,后面几种含义比较模糊,史中未见有明确解释。本文主题是讲九边军镇铸币,秦版崇祯钱因其产地特殊,很多品种都被怀疑出自军镇系统钱局,以下是笔者个人关于这些钱币背文的解读,正确与否有待检验。
1、新与新钱(图14-19)
崇祯通宝背“新”有南京版和秦版之分,前者是南京户部新钱厂所为。后者多出自西北地区,目前已发现有多种子类,似乎不是同一个钱局的产品。标准式背“新”是崇祯通宝中数量最多的背文品种之一,西北各处都有出土,其面文风格与在西安大量发现的李自成永昌通宝较为接近,可能是当时设在省府的布政司钱局出品。
丁福保《历代古泉图说》中收录一枚崇祯通宝背“新钱”,系崇祯钱中的大神品,马定祥先生批注为新钱局样钱,这还是与南京版的背“新”混为一谈。从拓片上看,这枚“新钱”面文书风与秦版“新”标准式几无二致,两者出处应该相同,前者大概是初开炉时的样式,后者是大量铸行的正式版本。
明代地方民政系统铸币多是以省为单位进行管理,各省钱法事务由巡抚总体把控,布政司具体主管,相关府、州、道协理,这个体制大约是在万历年间确立,并一直沿用至启祯时期。各省之中钱局往往不止一处,例如与陕西相邻的四川省在崇祯年间就有五所铸钱局。陕西省铸钱局万历年间已有设置,天启二年再开,据陕西巡抚练国事疏称:“自天启二年起,至崇祯四年止,十年间只动过本银一万二千四百余两,陆续获息银十一万七千八十两零。”[7]崇祯四年八月,陕西巡按李应期上疏称铸钱有厚利,建议各抚、道开炉铸钱,[8]此后陕西军镇、民政两个系统的钱局数量或都有所增加。
明代文献中常会提到三个名词:制钱、旧钱与新钱,这里的“新”、“旧”并不是崇祯钱上背文的由来。制钱是明朝各年号官钱的统称,旧钱又称古钱,泛指唐宋以来留存的历代钱。嘉靖年间御史阎邻说:“国朝所用钱币有二:首曰制钱,祖宗列圣及皇上所,如洪武、永乐、嘉靖等通宝是也;次曰旧钱,历代所铸如开元、祥符、太平、淳化等钱是也。”[9]新钱本意为新铸之钱,常被用作本年号通宝钱的代称。《明史》载:“庄烈帝初即位,……以御史王燮言,收销旧钱,但行新钱,於是古钱销毁顿尽。”[10]此处古钱即旧钱,新钱指的是改元后新铸的崇祯通宝,新钱和旧钱从面文上一望而知,没必要再做背文标识。
另外,还有人说崇祯通宝上的“新”、“旧”是指铸钱所用铜材的新与旧,此说也不成立。明朝由于国家整体缺铜,官方利用旧钱及旧铜器熔化铸钱的做法一直存在,旧铜与新铜铸钱在流通中的价值没有分别。
秦版崇祯通宝背后的“新”字实际代表新饷,它们并非军镇铸币,而是出自地方民政系统钱局。
案查臣部建议,非督抚重臣驻劄处所不许铸钱,其利本薄,而强民求息者皆罢其役,惟陕西、云南二省密云饷司见在举行,俱解充新饷之用,宣府、甘固二饷司见在举行,俱解充旧饷之用,大同抚臣自行鼓铸以充军前之用,其余似不便再行开端以启径宝矣。[11]
以上这段话,是崇祯三年十二月户部尚书毕自严对各地铸钱做的一个总结。晚明时期,政府应对财政危机最直接的举措就是加税,这是当时唯一能够立竿见影筹集大量经费的办法。增税的名目有三种:辽饷、剿饷和练饷,史家称之为“三饷加派”。辽饷的加征分为三个阶段,先是在万历末年连续上调田赋,每年总计增加税银五百二十余万两,天启年间加征了关税、盐课,并且大肆搜括各种杂项银,崇祯四年再次上调关税、盐课和田赋,每年的辽饷数额最终达到一千余万两。[12]
新饷就是新近加征的辽饷,九边原额的军粮称为旧饷,它们既是加征于民的税收科目,也是数十万边军赖以生存的军费支出科目。明末新饷与旧饷是国家财政管理的核心内容,最初由户部山东、山西司带管,之后户部又在十三司之外专门成立了新饷司。这两项经费从征收开始就分别统计,存放于不同的库房,按规定它们的用途也不相同。崇祯初“京师杂支与九边年例原属旧饷,关宁军兴及蓟、密、津、通等处新兵援兵原属新饷。”由于九边军费亏欠太多,这两项也“不得不为新旧通融之计”。[13]
崇祯二年三月,原户部侍郎南巨益上疏称,延绥、宁夏、固原三镇额粮(旧饷)缺至三十六月,当地军民穷则思乱,大盗蜂拥而起,请求朝廷发饷三十万以避免边军叛乱。[14]皇帝同意他的请求,命将陕西省应上缴的二十万新饷存留使用,另外再凑发旧饷十万两。[15]新饷原本是朝廷专为明金战争加征的税收,主要用于辽东和京畿周边军镇,至此陕西新饷资金暂改为本地军镇发饷。

图14 崇祯通宝背“新”【秦版·标准式】

图15 崇祯通宝背“新钱”(《历代古泉图说》第2054 品)

图16 永昌通宝【西安版·参考品】

图17 崇祯通宝背“新”【秦版·小字】

图18 崇祯通宝背“新”【秦版·稚书】(浙江贾文波藏品)

图19 崇祯通宝背“新”【秦版·久头通】(浙江贾文波藏品)
催征和输送新饷是各省布政司的职责,地方铸钱也是由布政司主导管理,两者在铜钱上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毕自严说陕西省铸钱解充新饷之用,秦版崇祯通宝背后的“新”与“新钱”应是新饷用钱之意。从实物版式特征来看,这些铜钱的铸地或不止一处,除了位于省府的布政司钱局之外,还有其它的府、州、道钱局参与其中。
2、太平、制、奉制(图20-22)
秦版崇祯通宝背“太平”、“制”和“奉制”,从数量上看都是流通正用品,它们的背文含义一直存在争议。“太平”前人说是指甘肃太平监,不知所云为何处,明代陕西省境内的镇、府、州、县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地名。“制”全称制书,秦汉时已有之,本意是指古代帝王颁布的法令制度之书。明代所有记录皇帝命令的文书都可称作制书,“天子之言曰制,而书则载其言者,如诏、敕、札、谕之类”。[16]“奉制”为承奉制书、遵命奉行之意,“制”在穿上“奉”在穿右的布局体现对王命制书的尊崇。
以上这三种铜钱背文,既不是传统的产地、钱局标识,与经济也没有直接联系,更像是一些政治宣传的标语。
明末天启年间陕西遭遇罕见大旱,一些饥民暴动抗拒征粮,引发省内多地大规模农民起义,这场动乱最终席卷全国,摧毁了帝国的统治根基。政府应对农民起义主要措施有三种:赈、抚、剿。赈济灾民和招抚叛军都是利用经济手段花钱消灾,往往一体施行。崇祯年间陕西大规模的赈抚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崇祯四年,由总督杨鹤倡导、御史吴甡主持,主要针对陕北延安府以及延绥军镇所属区域,包括中央拨款和地方捐输共计花费白银十三万七千余两。[17]第二次是在崇祯十年,由当时的总督孙传庭主持,皇帝亲发御前银,加上太仆、光禄二寺拨款共计白银六万两,“西安、凤翔、延安、平凉、兴安、汉中、巩昌六府一州所属兵荒州县逐一详酌,分别应赈、量赈。”[18]
明政府招抚义军的政策不可谓不热情,“给赏花红,鼓乐引导,造花名册,给予路费钱。”但朝廷拨给的经费毕竟有限,暗中还有些杀降的狠毒招数,各路义军势力忽降忽叛,多数并未有效解除武装。据御史吴甡言,曾有唤作独头虎的义军首领诈降就抚,听闻朝廷大军前来,仓惶奔逃出韩城,潼关道臣胡其俊居然追上去送给他铜钱九十万文,美其名曰临行馈赠之“赆钱”。[19]此事在当日沦为笑谈,也由此可知,虽然上报的赈抚费用都是按白银计算,实际开销中仍有不少铜钱,地方政府因此具有铸钱的动机。
如果笔者推测无误,崇祯通宝背“太平”、“制”、“奉制”都是明末陕西地区专为赈抚所铸的铜钱,背后文字是安抚百姓、教化叛军,宣扬皇恩浩荡的政治宣传口号。两次大规模的赈抚行为,崇祯皇帝事先都曾颁布谕旨下达指示,铜钱背后的“制”与“奉制”或来源于此。至于它们究竟出自杨鹤还是孙传庭总督时期,有哪些地方或军镇钱局参与铸造,目前还无法判定。
3、官与兵(图23-29)
崇祯通宝背“官”版式类型有多种,形制大小和文字风格不一,其中的奉制手与崇祯背“奉制”风格极似,应为同产地、钱局所出。崇祯年间陕西铜钱私铸猖獗,陈仁锡说陕西“钱东不踰关、西不踰河,民间小钱概非官制,故民亦甚病之。”[20]秦版崇祯钱上的“官”字应代表官铸正品之意,这大概是当地官员想出来的制钱防伪手段,而且是多个钱局一体化联动的政策。

图20 崇祯通宝背“太平”

图21 崇祯通宝背“奉制”

图22 崇祯通宝背“制”

图23 崇祯通宝背“官”【小样】

图24 崇祯通宝背“官”【大样】

图25 崇祯通宝背“官”【奉制手】

图26 崇祯通宝背“官”【草点通】

图27 崇祯通宝背“官·下月”

图28 崇祯通宝背“兵”【大兵】

图29 崇祯通宝背“兵”【小兵】
崇祯通宝背“兵”背后文字书写有大小之分,面文风格和形制、铸工如出一辙。“兵”前人称是指南京兵部,当属不知产地的史料误读。此钱出自秦地,九边军费管理由文官系统把控,军镇不可能以兵部的名义设局铸钱。笔者推测,“兵”或是指兵备道或者兵粮道,属于军镇铸币范畴。明末陕西四镇中,延绥镇有和甘肃镇都有三个兵备道,宁夏镇兵备、兵粮道各一,固原镇有五个兵备道和一个兵粮道。[21]道是边镇军费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具有铸币权。宣大总督卢象升奏疏中说:“查宣府分守口北道职衔,从来有兼理铸钱字样。”[22]另外,辽东巡抚王化贞早年职掌宁兵备前道时也曾设法开炉铸钱。
六 军镇钱局的管理与运营
1、管理体制
圣旨:各镇鼓铸原非旧例,总在抚按道司规酌长便以裕边计,这宣、甘二镇行止事宜俱依议,钦此。[23]
九边军镇铸钱并非国家成法惯例,也没有什么自上而下统一的指令安排。军镇设立钱局通常由各镇官员先提出动议,获得总督支持后再向朝廷申请,批准之后方可开炉铸造。有些总督如王象乾、卢象升等人,本身就有很强的铸钱意愿,或者之前有过主持铸钱的经历。蓟辽总督王象乾是天启朝铸大钱的主要倡导者,他曾向茅元仪咨询铸钱之法,[24]后者是明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承宗统帅辽东期间的下属幕僚。宣大总督卢象升是户部主事出身,早年抚治郧阳时就曾“募商采铜铸钱”。[25]
各镇铸钱事务的奏疏都会交由户、工二部商议答覆,户部掌管边镇钱粮,同时还执掌钱法,某镇铸钱是否可行,铸本动用何笔资金,所获铸息作何使用,对于这些问题户部的意见尤为重要。万历末年王化贞在辽东铸钱时,所任职务为宁前兵备道(其后升至辽东巡抚),在此之前他曾担任户部派驻广宁的饷司郎中,户部对他的铸钱动议也颇为支持。王化贞这两重身份,正好对应着明代军镇钱局管理体制的两种类型。
九边军镇钱局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各镇的抚、道官员监督管理,例如辽东的宁前道钱局、山海关钱局,蓟州的遵化钱局以及大同镇钱局;另一类是由户部派驻的管粮郎中(或员外郎)负责管理,例如密云饷司钱局、宣府饷司钱局、甘固饷司钱局。天启年间工部在密云短暂开设的钱局,主管官员由工部派出,严格来讲不属于军镇铸币的范畴。边镇钱局管理体制与军费管理系统密切相关,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中说:
明代九边军费管理机构可以划分为两个系统:以户部派出机构管粮郎中为代表的中央系统,以巡抚和各道为代表的军镇系统。从明代历史变迁看,其军费管理经历了由武官到文臣的转变,尤其在巡抚和郎中广泛设立于各边镇之后,以总兵为代表的武官系统便不得染指钱粮管理。明代九边军费管理形成以管粮郎中为核心,其他机构为辅助的犬牙交错、彼此罗织的复杂体系。[26]
如上所述,至明中后期,九边军镇的军费管理主要由文官系统把持,正是由于军费短缺的压力,促使他们向上申请铸币权,试图获取铸息来进行贴补。各镇钱局主管既有中央系统的管粮郎中,也有军镇系统的抚、道官员。具体负责日常事务的是一些下级官僚,如山海关钱局的兵部主事林翔凤,以及宣府钱局的都司经历华起龙等等。军镇武官被隔离在军费管理体制之外,当然也不能染指铸钱事务。崇祯六年,一名临洮武官受到惩处,罪名之一是收买铜矿砂交与钱匠带铸私钱。[27]东江总兵毛文龙是否铸钱仍有待考证,当时皮岛孤悬海外高度自治,朝廷很难对其实施监控。另外,还有人曾提出监军宦官参与铸钱的猜想,目前来看没有任何资料可以佐证。
2、运营模式
铸出制钱即以搭放军粮,扣回钱价随给官商买铜接济,周而复始生生不穷。[28]
购买铜材铸成铜钱对外发行,资金回收后再投入购铜成铸,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构成明代钱局的日常。开炉铸钱需要成本,钱局的开销包括购置铜材、购买工具及辅料、修造炉舍、工匠工食等等。明末国家财政状况窘迫,中央政府虽然同意将铸币权下放至边镇,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各镇只能自己想办法筹措鼓铸所需资金。蓟辽督师袁崇焕算是一个特例,在他上任之初朝廷批给他十万两白银作为铸本,但当这笔钱被用于安抚叛军之后,再要就绝无可能,他也只能去打盐引换铸本的主意。
筹集铸本的手段之一为“通融那借”,就是从其它项目的军费开支中借用,铸成之后再行抵还。宣府饷司荆之琦先是从军饷银中借用了一万八千两,之后户部同意他扩大规模,从京运年例和民屯银中借支五万两作为铸本。密云饷司和于朝先后试图借新饷银和督抚军需银未果,最后从河南、山东班军的皇赏银中借用了四万七千二百二十二两。手段之二为“搜括清汰”,就是搜集平时不使用的经费,以及清理节约不必要开支。这种方式效果很有限,甘固饷司郭应响搜括各种杂费,清汰书吏工食,加上自己捐献的俸银,才勉强凑够铸本银一千六十二两七分二厘。
铜钱铸成后按官方定价发行,钱价制定会考虑铸造成本和合理利润,官价通常要比市面流通的钱价更高一些。崇祯初,朝廷规定崇祯通宝每文重一钱二分五厘,[29]六十五文折银一钱。[30]宣府镇新钱的发行价为六十到六十五文,市面上流通价七十二文折银一钱。甘镇所铸每文重一钱,发行价八十文折银一钱,与京师钱制相比减重和减价的比率相当。
军镇钱局铸成铜钱基本都用于发放军饷以及各种军需之用,户部管粮郎中主管的饷司负责边镇钱粮收支与军饷发放,在筹措铸本金和投放铜钱方面无疑更具有优势。宣府饷司钱局的操作手法最受青睐,“始借饷以铸钱,旋用钱而给饷”,[31]铸本来源和铜钱去向在账面上属于同个会计科目,资金的调拨与销算都极为便捷。饷司铸钱的模式看上去似乎很完美,一经提出户部就试图在各镇进行推广,直到崇祯十六年大厦将倾之时,仍有户部官员上疏建议“各边饷司皆许动支铸本一二万开局鼓铸。”[32]
3、铸材供给
地方有产铜不产铜之殊,民间有行钱不行钱之别,不产则费巨而息微,不行则法穷而难施,恐非在在可开,在在有利也。[33]
明代自嘉靖朝以后铸钱多采用黄铜,成份为铜锌合金。当时最主要的产铜区域是云南省,以及周边的贵州、四川部分地区。从遥远的西南边陲运至北方,铜的价格自然水涨船高,启祯时云、贵、川三地爆发土司叛乱,也让运铜之路更加艰难。锌在明代称作窝(倭)铅,或者直接简称为铅,此前主要产自湖广荆州、衡州等地。北方地区铸钱用锌一度比较短缺,崇祯初山西阳城、河南济源等地获批开采炉甘石(菱锌矿),情况才得到缓解。[34]
明时陕西、山西两省出产铜矿,对所在军镇乃至京师铸币都有所裨益。陕西是云南之外另一个产铜大省,号称“全陕出铜。”[35]天启年间主持铸钱的工部侍郎董应举说:“陕铜产于镇虏、兰州,聚于三原。”[36]崇祯初山西太原、汾州二府铸钱用铜需从陕西购买,价昂路远得不偿费,不得不申请停罢,[37]同时期大同、宣府两镇钱局情况应与之类似。崇祯四年,已经升任宣大总督的张宗衡请求开采山西绛、盂、垣曲、闻喜等州县铜铅(锌),[38]在工部大力支持下,他的申请获得批准,[39]朝廷命在京钱局“一体採买以裕鼓铸”。[40]此后山西平阳、潞安两府相继开炉铸钱,[41]大同、宣府两镇也申请钱局复开。山、陕铜矿一直到明亡仍在开采,崇祯十五年,宣大总督白贻清建议在“山西之绛、盂、五台,陕西之泾阳、三原产铜处支解京银办铜抵销。”[42]随后两年中陕西、山西落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之手,再往后是入关的满清,这两个政权在两省都有开炉铸钱,应当也得益于当地的铜矿资源。
辽东、蓟州、宣府三镇铸材多从外来,王化贞曾委托南京户部代买铜材,袁崇焕盐引换铸本后也试图招商买铜,荆之琦派人到山西、陕西、荆州、衡州等地收买铜铅(锌)。明末全国上下大铸钱的政策导致铜材十分紧缺,即便是两京的中央钱局也常会因为缺铜而停炉。明政府尝试过各种办法,无论是委官还是召商采买,都难以保证铜材及时送达,拖延、逋欠时有发生,甚至铜商卷款潜逃的事情也不鲜见。户部钱法侍郎李成名总结铸钱难以获利的原因说:“本亏于商役之欺骗,息耗于铜铅之多缺”。[43]九边军镇地理位置偏远,铜材供给困难更加突出,各镇钱局相互争抢铜源,还要面临来自地方民政系统钱局的竞争,铸钱效益自然无法保证。
4、成效与弊端
军兴旁午,计饷转穷,借生息于圜府已是削针之举,採铸本而乌有竟同缘木之求。[44]
钱局发行铜钱,回收的钱价扣除成本,剩余部分即为铸息,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铸币税。孙承宗主持辽东四年,盐、钱两项共获利三万四千余两,其中煮盐的收益应会更多一些。郭应响的甘固饷司钱局投入铸本太少,铸息折算到一年只有一千四百八十两。荆之琦的宣府饷司钱局借用五万两铸本,所获息银平均到每年只有七千余两,铸钱利润率仅为14%,显然没有达到预想的规模。该镇崇祯初年的京运年例银约为三十万两,铸息贴补军费效果难称显著。[45]张宗衡的大同镇钱局具体数据不详,据户部评价,该镇铸钱与宣府一样“俱无厚利”。总而言之,明代九边军镇铸钱效益普遍不佳,距离很多理想主义的官僚设想相去甚远,便如毕自严所言,铸钱取息助饷“是可以暂行而不可以常试者也。”[46]
除了铜材供给困难之外,铸本筹集不易也制约着钱局的规模与效益。理论上投入铸本越多赚取的铸息也就越多,然而以当时的财政状况,可供钱局直接动用的款项实在有限,类似郭应响在甘固饷司的做法,开炉铸钱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军镇钱局要想获取更多铸本,只能从其它项目的军费中挪借,铸成铜钱后抵还原借款项,接下来的铸本又没了着落,维持运作惟有不断的拆墙补墙借来还去。如此操作极大考验管理者的能力,既要懂鼓铸原理又要能调配大笔资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荆之琦获得升职嘉奖,他的继任者却视铸钱为畏途。
购买铜材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长途运输过程中充满了拖延与风险,边镇某项资金一旦被钱局占用,至少短期内无法正常开支,这反而会加剧军费匮乏的困局。宣府饷司“借饷铸钱、以钱给饷”的模式看上去完美,但资金周转的效率无法保证,每年的铸息(可能还无法持续)和占用的铸本比起来也实在太少,铸钱并没有立即给饥饿的边军带来好处,反而拖延了他们得到军饷的时间。边镇环境相对封闭,经济规模较为有限,所铸铜钱难以向腹内省份扩散,最后会导致当地通货膨胀。官方坚持铜钱发行高定价,以此来维持钱局的利润,市面上银与钱的比价上升,军队不但要忍受军饷的拖欠,拿到手里的铜钱还会贬值。虽然有一定的比例限制,以铜钱代替白银发饷的做法仍会招致军人们的不满,甚至还可能酿成兵变,这也是明代军镇铸钱难以长期持续的原因之一。
注释:
[1][3][4][23]《度支奏议》边饷司卷七·题覆宣甘二镇鼓铸行止事宜疏(明)毕自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483·史部·诏令奏议类
[2]《度支奏议》边饷司卷五·覆甘固饷司月饷新旧兼支疏(明)毕自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483·史部·诏令奏议类。
[5]《藏钞本崇祯长编》卷五十·崇祯四年九月 己丑条(清)汪楫,上海书店出版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明实录》附录之四。
[6][8][33]《度支奏议》山东司卷五·覆陕西抚院李应期条陈屯盐鼓铸疏(明)毕自言,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483·史部·诏令奏议类。
[7]《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八·户部四 戸部尚书侯恂条陈鼔铸事宜(清)孙承泽,吉林出版集团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史部36。
[9]《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一·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条,上海书店出版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明实录》。
[10]《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 钱钞(清)张廷玉等,中华书局。
[11][31][46]《度支奏议》边饷司卷五·题覆边饷堂条陈十六款疏(明)毕自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483·史部·诏令奏议类。
[12]《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1983 年·明末三饷加派 郭松义,江苏人民出版社。
[13]《度支奏议》堂稿卷一三·军兴繁费弘多新旧二饷分局疏(明)毕自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483·史部·诏令奏议类。
[14]《明季北略》第五卷·崇祯二年已巳 南居益请发军饷(清)计六奇,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440·史部·杂史类。
[15]《度支奏议》堂稿卷五·题覆会议边饷议单十二款疏(明)毕自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483·史部·诏令奏议类。
[16]《大明律集解附例》卷第三·制书有违(明)刘惟,学生书局。
[17]《柴庵疏稿》卷之七·钦奉圣谕疏(明)吴甡,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业刊》史部第51 册。
[18]《孙传庭奏疏牘》卷一·奏报赈过饥民并发牛种银两数目疏(明)孙传庭,浙江人民出版社。
[19]《柴庵疏稿》卷之八·查明流寇旋抚旋叛情形疏(明)吴甡,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业刊》史部第51 册。
[20]《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漫一·钱法三秦(明)陈仁锡,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1381·集部·别集类。
[21][26]《明代九边军费考论》第四章·第一节 明代九边边镇系统军费管理机构 王尊旺,天津古籍出版社。
[22]《卢象升奏牍》卷七·宣云鼓铸事宜疏(明)卢象升,浙江古籍出版社。
[24]《石民四十集》卷六十五·上王霁宇制府书(明)茅元仪,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1386·集部·别集类。
[25]《明史》卷二百六十一·卢象升传(清)张廷玉等,中华书局。
[27]《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一六·为奉旨审理毛一鹏案情事(崇祯六年)原文首尾缺失作者不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8]《度支奏议》边饷司卷二·题覆宣府饷司荆之琦铸息疏(明)毕自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483·史部·诏令奏议类。
[29]《藏钞本崇祯长编》卷四十·崇祯三年十一月丁酉条(清)汪楫,上海书店出版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明实录》附录之四。
[30]《藏钞本崇祯长编》卷十四·崇祯元年冬十月戊子条(清)汪楫,上海书店出版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明实录》附录之四。
[32]《痛史本崇祯长编》卷一·崇祯十六年十月丁丑条(明)佚名,上海书店出版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明实录》附录之四。
[34]《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二·题覆钱法孙侍郎条议钱法疏(明)毕自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483·史部·诏令奏议类。
[35]《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六·天启五年十二月丙子条,上海书店出版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明实录。
[36]《崇相集》疏二·鼓铸急需切要疏 天启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明)董应举,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业刊》集部第103 册。
[37]《度支奏议》新饷司卷四·议停南部新厂并山西鼓铸疏(明)毕自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483·史部·诏令奏议类。
[38][42]《古今治平略》二·明食货志钱钞(明)朱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756·史部·政书类。
[39]《藏钞本崇祯长编》卷五十二·崇祯四年十一月戊寅条(清)汪楫,上海书店出版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明实录》附录之四。
[40]《山书》卷五·疏通钱法(户部钱法侍郎刘重庆疏)(清)孙承泽,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367·史部·编年类。
[41]《藏钞本崇祯长编》卷六十二·崇祯五年八月壬午条(清)汪楫,上海书店出版社《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明实录》附录之四。
[43]《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三·题覆钱法堂谨抒一得疏(明)毕自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483·史部·诏令奏议类。
[44]《度支奏议》新饷司卷三·密镇官军皇赏疏(明)毕自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483·史部·诏令奏议类。
[45]《度支奏议》堂稿卷三·召对面谕清查九边军饷疏(明)毕自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483·史部·诏令奏议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