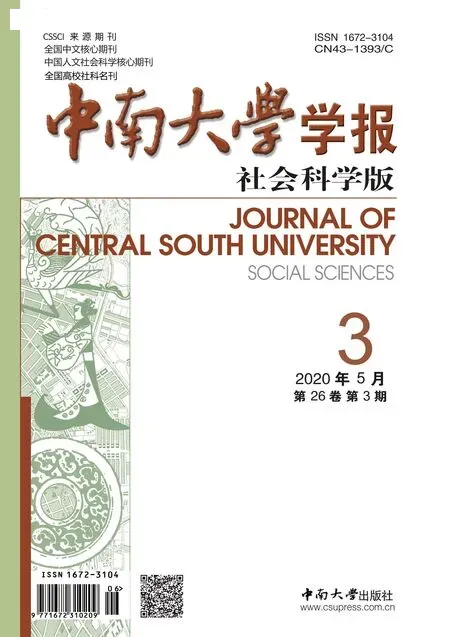社团的政治性与社团性政治
——政治社会视野下的中古晚期英国城市政治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关于中古晚期英国城市政治史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工作开始于19世纪史学职业化和专业化时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中古晚期英国城市政治史研究将焦点放在与自治市(borough)相关的法律、惯例以及政治体制问题,而不涉及其他未获得“自治”这一法律身份的城市,更没有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研究[1−6]。这一状况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有所转变。首先是城市这一主体范围得以扩容,除开“自治市”外,还包括其他非自治市;其次,社会史、经济史以及文化史研究在此之后渐渐成为中古晚期城市史研究的重点。
随着史学范式的转变,英国中古晚期城市史研究在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问题。虽然英国中古晚期城市史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政治话题被弃置一旁。到了90年代,有学者开始关注城市政治史,然而情况并不乐观。D.M.帕利泽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仍在呼吁不要忽视英国中古晚期城市政治史研究,他提醒“如果不分析城市政府和机构,不分析城市惯例和法律,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古城市”[7](7)。另外,依照新史学的理念,历史本身是一个由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元素糅合而成的整体[8](3−4),因此相关研究不应顾此失彼。然而,作为新史学中的一个构成部分,20世纪最后30年的英国中古城市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却偏离了上述主旨。
有学者在谈到经济社会史研究相对纯经济史研究所具有的优势时指出:“全方位、长时段、整体描述社会的经济—社会史比单纯的经济史更富有解释力,无疑也更有魅力和前途。”[9](11)类似地,政治社会史研究相对于纯政治史或纯社会史研究具有同样的优势[10](113−115)。
由此种种,为了更清晰地认识英国中古晚期城市政治②,我们何不将这一时期城市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做一番分析呢③?
一、社团的政治性:政治视野中的城市社会
中古晚期英国城市社会生活纷繁复杂,要从政治角度去审视它,理应对其社会本位有所认识。
一方面,从语义层面出发,中古晚期英国“城市”无论是在历史语境还是在现代界定之中都具有鲜明的社团特征④。
关于英国中古历史语境中的“城市”,研究英国中古城市史大家苏珊•雷诺兹(Susan Reynolds)在其著作中认为,中古英国城市居民常常用“communitas”(community)来称呼自己所在的城市。在对历史语境中的“community”一词进行一番研究之后,她指出了该词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态:“人们参与公共活动……共同体成员之间是一种互惠互利、多方且直接的关系,而不是要通过官员或统治者去进行协调沟通的间接关系。”[11](2)从这种历史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英国城市居民习惯将整个城市称为一个“共同体”,而他们自己则为共同体的一员。
关于英国中古“城市”,当代西方史家所普遍接受的概念同样能够让我们窥见彼时英国城市的社团属性。学者们认为英国中古居民点只要满足下面两个条件便可称为“城市”:其一,一座城市是一个永久的其大部分居民从事非农职业的聚居地,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口脱离农业劳动靠工商业谋生是“居民点”成为城市的必要条件;其二,居民有着明确的不同于乡村居民的身份认同,这包括自我认同与他我认同,即城市居民能够肯定自己与乡村农民不同,同时乡村农民也认为这些城市居民与自己不是一路人[12](ix-x)[7](5)。由此可见,在中古晚期的英国,居住在“城市”这一定居点中的群体具有社团四大特征之一——“明确的认同感”。众所周知,群体认同感的培养和形成必定离不开群体成员之间持续的交往和互动。由此,从支撑城市这一概念的具象的历史氛围去看,英国中古城市具有鲜明的“社团性”。
另一方面,在事实内容方面,中古晚期英国城市社会功能和经济管理同样能体现城市较为鲜明的社团特征。在社会生活层面,城市离不开各种社会团体:日常信仰方面的工作由宗教团体来承担;慈善接济方面的工作主要依靠行会、教堂以及其他宗教团体;城市居民言行的管控往往也依赖上述行会和宗教团体。社会团体作为城市的有机部分彰显了城市在社会功能方面的社团性。经济方面,作为工商业者聚居地,商品的生产和交易无疑是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韦伯指出“城市永远是个‘市场聚落’;它拥有一个市场,构成聚落的经济中心”[13](3−4)。如上文所述,这一时期英国的城市居民大都依靠工商业为生,因此保持手工生产和商业贸易有序进行便是城市在经济层面最重要的职责。这些职责的履行离不开彼时城市享有的工商业特权的支撑,比如辖区内市场的独占权和经营权以及组建行会的权利。这些权利涉及的核心问题常以经济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使得后人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常常过于关注经济元素,自然也就发现不了城市在履行经济职责过程中所具有的社团性。中古晚期,城市大都依靠辖区内部的行会践行其经济职能:监管商品生产和交易的职责常由手工业行会和商人行会⑤承担,商品产销场域中工商业者及其雇工和学徒的非经济事务的管制往往也交由行会。换言之,中古晚期英国城市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事务的管理重担往往都会落在市府之外的行业团体身上。身为非政府组织的行会在经济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足见彼时英国城市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社团属性。
由上可见,中古晚期英国城市社会无论是在语义层面还是在事实内容方面,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社团性,这些城市可谓是一个个典型的包含着诸多小社团的大社团。
然而在诸多社会群体参与的中古晚期英国城市社会生活中,亦存有蕴涵着政治属性的行为关系。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广义上的政治指的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其付诸实践的活动”。它具有以下特性:因为是活动而呈现动态性;政治因为“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而具有强制性或命令性,其基本要素便是权力,“不运用出自权力并且可以推行权威性法令的强制力量,就不可能有任何决策(或任何决议)”;集体性,换言之,政治是在两人及以上的集体中产生的,“至少要有两个个人共同作出决策,否则就谈不上政治”[14](583−584)。广义政治的外延不仅仅包括国家机关的运作,还包括符合这些必要特性的共同体活动。由此可见,广义政治的内涵和外延是一种泛化界定⑥。在上述百科全书中,狭义政治被定义为“一群在观点或利益方面本来很不一致的人们作出集体决策的过程,这些决策一般被认为对这个群体具有约束力,并作为公共政策加以实施”。该定义中的政治包含以下特征:非共识性,即当群体成员之间的“共识没有达到而有关的群体又需要集体行动时,政治就产生了”;非暴力性,集体决策过程中不得夹杂暴力胁迫;权威性,决策一旦形成便具有不可抗拒性;强制性,决策执行时异议者也必须或主动或被动配合,不得违背[14](584−585)。狭义政治外延有特定所指,它仅仅包括国家机关的相关活动,其他团体活动则不在其列⑦。
具体到中古晚期的英国城市社会,其既有广义政治的韵味又有狭义政治的余影。一方面,城市家户、作坊和行会内部都存在着广义上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中古晚期乃至近代早期,英国都是一个父权社会[15](9−10)[16](93−98),城市也不例外。父权在家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家庭日常生活方面,夫与妻、父与子、户主与仆人虽非对立关系[17](59),但也不可能全然平等。作为家庭的支柱,男性户主在家庭重要事务方面有着较大决定权,比如作坊或商铺的打理[18](276)、家庭收支以及子女教育等,与此相应,家庭其他成员在这方面的权利或多或少会有所欠缺。在作坊内部,师傅或雇主地位优于学徒或帮工,师傅或雇主对学徒或帮工少不了指派、训斥甚至是苛责,他们之间的关系绝不可能完全平等。行会之中,亦有会长与会众之别,大的行会中甚至还有执事等职,行业监管和行会章程的施行也具备一定的强制色彩。可见,在城市“小社团”中存在着社会差异,这种不平等催生出了广义上的政治行为和关系。
另一方面,在狭义政治视阈中,身为工商业者聚居地的城市也是一个对其辖区负有行政治理职责的单元,是地方行政链条上的一环。城市政府统辖整个城市,尽管在日常事务方面需要依赖内部的一个个小社团,但在重大事务方面还是能做到亲力亲为。城市政府与工商业行会之间的关系亦可折射出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性。商人行会以及后来出现的手工业行会在诸多事务上受制于市政府[14](28−29)[20](32,37,47−49,53−54,57),比如行会已制订或已修订的章程唯有报请市政府批准之后才能在相应行当的管理中实施[20](30,65);行会选出的行业督察员通常只有在市政府首肯后才有权巡查行会师傅们的生产或销售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享有市民权的居民亦是某一行会的会员,熟悉城市政治活动的市民在行会中扮演行会师傅这一角色时,不可避免会将政治属性带入行会[21](97)。
中古英国城市社会的“政治性”源于这样一个现实,即城市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领域的核心角色系于“市民”一身。市民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在家庭中,他是户主,是丈夫、父亲以及主人;在作坊之中,他是师傅和雇主;在行会中,他是行会成员;在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中,他是城市市场的主要参加者和管理者;在城市政府活动中,他是官员或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和监督者。男性户主、行会师傅以及政治活动参与者等多重角色汇集于一身,对市民而言,其身份可谓“多位一体”。因此,即使从狭义政治的角度观之,在其角色转换中,市民往往也会或主动或被动地将政治性的内容带到政府活动以外的城市生活中去。
概言之,在英国中古晚期城市内部,政治不可避免地浸润着社会生活,城市社会画卷因此多了几分政治色彩。
二、社团性政治:城市政治中的社团色彩
中古晚期英国城市社会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反映出当时城市政治对城市社会的渗透,可见彼时城市政治对于以市民为中心的社会群体而言并不陌生甚至是可触碰的。一般而言,相对于社会生活的亲和,政治更显肃穆。然而细究之下,中古晚期英国城市对内外重要政治事务的处理方式却同我们熟悉的近代欧洲政治有所出入。这些差异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种差异呢?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将前文中的视角与研究对象作一对调,即从社会生活角度去审视中古晚期英国城市对内外政治事务的处理方式。
政府官员的生成是中古晚期英国城市内部政治活动的核心构成部分,故而政府官员的生成⑧过程是我们窥探彼时英国城市内部政治特征的理想窗口。先来看城市议员的生成。在中古晚期,城市公众议会和上议会是结合在一起的,统称为市议会。它由市民共同体直接选出,代表市民的利益。15世纪末16世纪初,公众议会与上议会分离开来。公众议会仍旧由市民直接选出;上议会成员则多出自高级市政官群体,常被称作市府参事,任职终身。市府参事因亡故或其他原因出现空缺的,通常经由其他市府参事共同推选而产生[22](56)[23](19)。再来看其他官员的生成。市长往往经由市议会和其他市民团体推选而成。比如,中古晚期伦敦市长是由现任市长、市政议员、公众议员以及其他的市民共同体代表共同推选而产生[12](174−176);温切斯特市市长则由该市24人议会与其他市民共同选出。15世纪40年代赫尔市自治特许状关于该市市长等一些市政官员的生成办法的规定颇具说服力:
市民与4位市政官……从市民之中推选出1人担任司法官……,市民从市民内部推选出13人,尔后再从上述13人中选出1人担任市长,剩余12人则为市议会议员……,假如市议会议员之位因亡故或其他原由出现空缺,那么市民当从市民群体之中推选出1人以填补之。[24](571−572)
由此可见,中古晚期英国城市官员生成模式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和平等性。
另外,尽管重要官职往往由市民上层来担任,但在处理城市主要事务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其他市民置于一旁。帕利泽认为,在较大的城市里,虽然部分市民管理着城市,但是其他市民也会积极参与决策的制定。在1421年,林肯市有239位市民对该市多项重要决定进行了表决[25](142)。坎特伯雷市的一份记录记下了该市市民的诸多权利,其中有“自由人可以出席市政务会,在那里他可以发言……”的文字[24](569)。同一时期,伊普斯维奇的特许状规定了市政官员当由市民共同选出。
进一步而言,在中古晚期英国城市之中,尽管市民在占有财富方面存在多寡之别,然而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却显得较为简单和平等,中下层市民也有参与日常事务处理的权利,经常与上层市民共同议定城市大事[17](171−172)。比如,温切斯特市(Winchester)大约从1275年开始,其部分较低级别的官员便一直由市民和市议会共同指派;高级别官员虽非如此,也少不了市民的参与,如市政官的4名候选人虽然由市议会与市长推荐,但最终哪两位能担任,还是由市民投票决定。在13世纪的南安普顿,市政官、书记官和法警的选举工作虽然由12人议会负责,但这12人议会是由市民共同体选出的[26](188−189)。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在15世纪初期发生的一桩征税风波更具说服力。1416年12月的一天,什鲁斯伯里市的市民认为估税员和征税员相互勾连,私加税额并从中获利,使得该市实缴税额远大于应缴税额。我们不妨看一看该事件的由来及最终的解决方式:
在该市市民收到税收令状之前,征税员已然挑选了6位评税员,他们和这6位评税员所定税额远多于令状所定之总额,它损害了该市居民的利益。于是前述市政官、富人和市民共聚市政厅,经商议,他们一致认为前述评税员和征税员所作所为不当且有害。他们一致同意:自今日(1416年12月11日)起,当征税员收到税收令状后,他们应将令状呈递到市政官那里,依照令状之规定从该市市民中选出4到6人担任评税员。前述市政官、富人以及市民一致认为,被选出的6位评税员应当向全体民众起誓,发誓根据每一位居民的财产公平公正地一丝不苟地估算人们应缴纳的税额,同时他们还要秉公估算那些在城中享有产业的城外人以及那些承诺要为本市缴纳税收的外市市民所应缴纳的税额;这些税收的总数要同税收令状所定税额一致,即94镑7先令12便士;另,评税员履行职务时,征税员应当回避;尔后,市政官应将富人和其他市民召集到市政厅,在那里,选出6位富人核实评税员所估算的税额,以确定所征税收总数是前述之94镑7先令12便士;征税员……在审核员核算所有税收后,要将缴税名册呈递给市政官,……,以便该市所有应纳税的男人和女人查对他们的税额;市政官也应认真审核税收账册……以确保账册上的税额总数不多于94镑7先令12便士。
待所有工作完成之后,征税员方才获准将所征钱款上交给王室政府……[24](562−563)
什鲁斯伯里市征税风波及其解决方式表明:该市全体市民享有征税监督权,他们有权质疑赋税的评定和征收;全体市民有权根据税收令状之规定推选评税员,有权要求评税员为恪尽职守而宣誓;应缴税额在上缴给王室政府之前还要再经历数重审核。从这些方面,我们可窥见什鲁斯伯里市市民之间较为简单和平等的政治关系。
综上,官员的生成以及市民的政治参与反映出:在狭义政治层面,市府与市民通常依据一定规则,或集体或环环相扣进行持续不断的互动。它折射出中古晚期英国城市的内部政治具备一定的平等性。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中,城市市民较多时候是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这种特性也折射出彼时的城市政治活动具备一定程度的社团气质。
众所周知,中古晚期英国城市通常以一个整体同外部威权主体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当遇到城市外部权威干涉时,全体城市市民乃至非市民为了维护城市的工商业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便是常有之事[27](79−80,201−202)。
中世纪中晚期,英国城市可分为三类:王室城市、世俗领主城市以及教会领主城市。这三类城市在同各自领主打交道时,所拥有的政治空间依此递减:王室城市通常享有较为充分的自治权[7](281);领主城市享有一定的自治权[28](52);教会城市自治空间最小。虽然领主城市和王室城市在政治经济权利方面存在区别[7](194),但对于国王和教俗领主而言,将城市所辖区域内居民和不动产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是最为方便的一种做法。正因为如此,这种做法在城市领有者与被领有城市之间的政治互动中最为常见。比如,国王自1200年开始就赋予王室城市格洛斯特自治权,条件是后者每年需向前者缴纳65英镑赋税。王室与格洛斯特市共同体之间所确立的这种政治经济关系一直持续到近代[29](154,157−158)。
就城市而言,在涉及与城市整体利益相关的重要事务时,无论是王室城市还是领主城市,通常都是以共同体身份同其领有者打交道的。
那些从国王那里获得自治特许状的城市均有资格选派代表参加议会下院[30](42),这些城市被称为选区城市。绝大部分王室城市为选区城市,议会成为它们与国王博弈的重要平台。每一个选区城市可以选派两名代表参加议会⑩。在下院议员的选举中,选民是全体市民或者是市政府官员,法定候选人必须是常住市民。尽管中世纪晚期已经存在“乡绅入侵”的现象,但城市议员中乡绅所占的比例比16世纪的要小,在1422年接近50%,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平均为66%[31](75,82)。换言之,选区城市通常都能选派一名城市居民参加议会下院。这些城市代表往往会利用议会赋税批准权、下院请愿权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立法权同国王周旋。自13世纪末期,英国就已经确立了国王征收赋税必须得到议会批准的原则。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演化,在14世纪90年代以后,议会的赋税批准权由“经上、下两院批准”变为“在征得上院同意后,下院批准”[30](47)。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有助于下院地位的提升。平台地位的提升增强了城市代表为各自城市主张权益的信心。此种关系诚如刘新成教授所论:“在议会,上议员仅代表个人,下议员则代表社会。下议员在议会同意的决定,他所在地区的国民应该服从,这是一条既定原则。赋税是向国民征收的,所以国王首先要尊重下院的意见,否则便没有征收赋税的可能性。”[30](47)自1310年“贵族立法团”建立后,议会中的骑士代表和城市代表开始享有请愿权[30](34)。请愿分为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书面请愿和根据口头叙述由议会书记官撰写的请愿状被称为议案[30](48)。请愿往往由下院议员提出。15世纪中叶以前,下议员的请愿书常常被国王及其追随者篡改。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下议员请愿书被直接提交给下院秘书,议会也渐渐明确了国王和上院对下院的请愿书只可表示同意与否,不得加以改动的原则[31](132)。在议会立法的过程中,下议员的请愿是议会法的蓝本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议会立法机构地位的确立实际上提高了下院的地位。
非选区城市同其领主博弈的途径有两条:暴力的与和平的。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城市与外部权威之间的冲突多发生在修道院与其领有的城市之间[27](204−205)。世俗领主偶尔也会遇到城市的反抗。比如,唐克斯特市的市民在1365年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发起了反对其领有者玛格丽特女士的举动;农民暴动前夕,冈特的约翰(John of Gunt)也遇到过其领有的市镇的反抗[27](196−197)。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教俗领主城市对其领主的抵制大多依赖平和的诉讼方式——将纠纷诉诸王室法庭而非上述暴力行为[7](297−298)[27](207−212,220,222)[32](234)。此种情形的存在当与诺尔曼·庞兹指出的彼时英国“中央政权相当强大”有颇为密切的关系[33](66−67,91)。
当然,中古晚期英国城市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所遇到的外部威权主体除开各自所依附的领主或王室,还包括领有者之外的其他贵族或修道院院长或主教。与非领主性质的外部威权主体打交道常常是在诸多对外矛盾的集合中进行的。在遇到来自外部其他世俗贵族或宗教贵族的干预时,城市居民往往会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比如,部分王室城市虽然从国王那里获得自治特许状,但是特许状往往并没有划定各个城市确切的管辖范围,在这些城市周围还有其他权威实体,如世俗庄园或教会管辖区。王室城市同它们之间的界线如若模糊不清,那么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会同这些权威实体产生矛盾和纠纷。城市政府通常采取长期诉讼的手段来应对这种挑战。而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居民往往会站在政府一边,尽管这种解决方式颇费人力、物力和财力[32](205−235)[34](571−592)。
因此,从中古晚期英国城市与外部政治关系这一层面来看,一方面,城市及其领主在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时往往会有意识地将城市视为一个整体。这对城市而言,有利于城市居民形成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意识。虽然领主无意在城市培养一种有离心倾向的抱团意识,但其政治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有违他们的初衷。另一方面,城市在处理同外部非领主权威之间的关系时,其居民展现出来的一致行动的能力,既是抱团意识的体现,又是抱团意识得以强化的因素之一。
概而言之,中古晚期英国城市对市民参与处理城市内外政治事务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市民与市民持续的面面互动便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政治活动形式。这种政治活动对中古晚期英国城市市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社团活动中才会出现的体现一定平等的理念成为市民政治活动的规范之一;抱团意识以及紧要关头时一致行动的意识也得以加强。这一气质正是近代早期欧洲城市政治所欠缺的。若以社团的概念和特性来衡量中古晚期英国城市政治活动中的市民群体,我们会发现,当时由市民主导的狭义层面的城市政治活动亦有较为鲜明的“社团”色彩。
三、结论
以政治视角看中古晚期英国城市社会生活,其政治色彩相当浓厚,政府以外的世俗团体在日常行为处事方面也体现出一定的广义政治和狭义政治的属性,大有社会生活“政治化”之意。然而,当我们以社会视角去审视中古晚期英国城市政治生活时,会发现彼时的城市政治亦有较为浓烈的社会色彩。城市在处理对内对外政治事务时,更多地依靠以市民为中心所构建的社会体系或依赖社会团体,让其分担一部分管理职责,或依照社会团体的做法来解决一些相关问题。究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城市市民角色的多位一体化。市民在角色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将政治带入社会生活中,相应地,也会把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做法带入政治活动中。两个层面的考察实则揭示了彼时城市政治与社会的交融,从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发现英国中古晚期城市政治的面貌:一种市民广泛参与的、必要时整个城市居民协同合作的较为开放的非寡头化政治。
从长时段去审视上述主题,亦能隐见历史的连续性。上述“政治—社团”互动色彩较为明显的政治形态在中古晚期英国大多数城市中长期存在着,它在宗教改革后受到冲击,依照罗伯特·蒂特勒的观点,此后城市政治逐渐转向排斥性很强的寡头政 治[35](182−183)。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1835年的市政改革实际上否定了排斥性的“城市寡头政治体制”,再一次将开放性注入城市政治中。笔者不能妄言英国中古晚期城市政治和1835年后的英国城市政治之间有直接关系,但其政治实践中部分相似之处却又提醒我们,不能断然否定两者之间存有一定的联系。
注释:
① 文中“英国”仅及英格兰,不包括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
② 已有关于城市政治开放与否的研究多集中在市民群体。有学者认为城市政治对全体市民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开放的。参见:Carl I.Hammer Jr.Anotomy of an Oligarchy:The Oxford Town Council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1978(1):1-27 ;John T.Evans.The Decline of Oligarchy in Seventeenth-Century Norwich.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1974(1):46-76.也有学者提出相反看法,认为中古晚期英国城市政治出现了寡头化,即当时城市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到富裕市民手中。参见:D.M.Palliser.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Vol.I,600-1540.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310-312.那么,中古晚期英国城市政治对于市民乃至城市内部全体居民而言,是封闭还是开放,抑或是其他?倘若换一种视角去审视这一话题,会发现它并未像部分学者所说的那么封闭和狭隘。
③ 在下文中,笔者将引入社会学的“社团”概念,至于原因,详见文中相关论述。“社团”为“社会团体”(social groups)的简称,社会学中的术语,它指代的群体是社会学研究对象之一。韦伯界定“社团”为“一个基于同意的组织,若其明文秩序的效力仅及于那些依个人志愿参与的成员,则称之为‘社团’(Verein)”。参见:韦伯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0。查理·斯坦格(Charles Stangor)在其著作中列举了多位社会学家对这一词语的定义。言人人殊。参见Charles Stangor.Social Groups in Action and Interaction.New York &Hove:Psychology Press,2004:14-15.戴维·波普诺则将社团定义为“两个或更多的人,他们有共同的认同及某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对群体中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相同而确定的目标和期望”。参见:波普诺的《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73页。国内部分社会学研究者则认为社会群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会群体,泛指一切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类群体;狭义上的社会群体,指由持续的直接的交往联系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参见: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89-190。概而言之,以“社团”标称的群体存在着以下特征:(a)特定社团有明确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可以区分个体是或不是该社团的一员;(b)有大体一致的价值观念以及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范,社团成员在彼此交往中相互影响,天长日久便会产生或遵守一些共同的观念、信仰等价值取向,彼此遵循一些口耳相传或明文规定的行为规范;(c)有持续的相互交往;(d)有共同行动的能力,在群体意识和群体规范的作用下,社团随时可以产生一致的行动。
④ 当代东西方历史学研究非常注重专题考察中所涉及的核心词语的界定,遵循“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之原则,力求从历史本真出发去核定相应研究中关键词之内涵和外延。正因如此,某一历史事物的属性往往会在学者广为认可的相关历史术语中露出端倪。
⑤ 塞利格曼曾指出,在中古英国一些城市之中,商人行会包括所有的工商业人士,对外商贸者、小商贩甚至是手工业者。行会与市政组织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却从未平起平坐。在这个过程中,行会担当部分公共责任,在公共卫生和治安管理中成为市政府的得力帮手。详见Edwin R.A.Seligman.Two Chapters on the Medieval Guilds of England.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887(5):9-113。
⑥ 此种界定是将社会中所有不平等体系都囊括到政治范畴以内。这种广义性质的政治也得到政治社会学研究者和部分政治学者的认可。详见: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王大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15;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7-18。
⑦ 当代部分西方政治学者认为存在公共性政治和私人性政治、附属政治和组织内政治。政府和政党一类的公共组织的活动被称为公共性政治,而其他私人性的和组织内部活动被归入另外一类。有些学者不主张泛化政治,也即是说,将活动是政治与否的判定严格地同是否影响公共决策及公共管理联系起来。在他们那里,大多数时候政治仅限于政府和政党一类的公共活动。详见陈振明、陈炳辉的《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8。
⑧ 从整体来看,中古中期英国城市政府设有市长(mayor)、财务官(chamberlains)、司法官(recorders)、法警、警督以及书记员等职位。参见:Susan Reynolds.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Medieval Towns.Oxford and New York:Clarendon Press,1977:120-121.)到晚期,随着城市议会的出现,大城市以及部分中小城市相应地又有市议员一职。依功能而定,市议会属于代议机构。部分城市市议会具体又分为上议会(Inner Council)和下议会(Outer Council),后者后来演变为公众议会(Common Council)。参见:Susan Reynolds.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Medieval Towns.Oxford and New York:Clarendon Press,1977:173-174.
⑨ 市镇自治法人化(incorporation of boroughs)在13世纪晚期14世纪初期开始出现,并随后成为中古晚期英国城市政治形态之一。参见:James Tait.The Medieval English Borough.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36:236-237.自治法人特许状的五大特征(权利):永久承续法人团体的权利;永久保有土地的权利;使用法人公章的权利;依据法律发号施令的权利;在王国法庭上诉讼与被诉讼的权利。参见:Martin Weinbaum.The Incorporation of Borough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37:18.
⑩ 伦敦可以选派4名议员,威尔士各选区(Constituencies)只能选派1名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