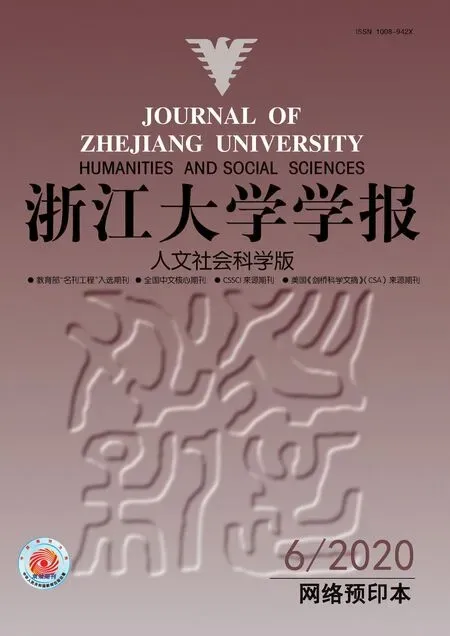叶德辉与诸桥辙次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
周 妍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与日俱增,学术交流也随之迎来一个高峰。一方面,政府官员、民间文人、留学生等大批中国学人赴日,将日本视作中国的发展参考,以日本为媒介学习西方知识;另一方面,日本学者纷纷到中国访问,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留下了大量的日记、游记。这些珍贵的资料为我们走近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域外视角,其文献价值也愈来愈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仅仅依据日记、游记等材料,并不能高度还原面对面的交流场景,而具有原始性与现场感的笔谈资料恰好与之形成互补。近年来,随着俞樾、吴汝纶、竹添光鸿、内藤湖南等近代中日一流学人间笔谈资料整理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笔谈资料在中国近代史、中日交流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章太炎、叶德辉、胡适、张元济等众多中国学者与日本学人间的笔谈资料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本文即以叶德辉与日本汉学家诸桥辙次的笔谈资料为例,分析20世纪20至30年代中日学人围绕经学与经学史研究展开的交流。
诸桥辙次(1883—1982),日本新潟县人,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任职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文理科大学等,曾向日本皇室进讲中国典籍,长期兼任静嘉堂文库长,因编撰《大汉和辞典》而蜚声国际。诸桥1918年4月首次访问中国,1919年9月至1921年8月在北京留学,此后又多次赴华考察,与各地硕学以笔谈的形式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叶德辉正是其中一员。1920年5月,诸桥游访湖南长沙时,前往叶德辉家拜访,与之进行笔谈,并将笔谈原稿带回了日本。1985年,诸桥辙次的弟子月洞让在《大汉和辞典月报》第11期中将此份笔谈原稿影印出版,并附有录文、翻译[1];1990年,国内学者王继如对月洞让的录文进行了修订[2];1999年,李庆又将此份笔谈收录至他的著作,并进行了注释[3]163-167,至此,资料整理工作告一段落。但是,这件资料的丰富学术内涵尚待挖掘。本文在历史背景下,梳理叶德辉与诸桥辙次的交流经纬,聚焦二人围绕康有为今文经学、颜元实学展开的交流,分析他们在经学与经学史研究领域的观点异同及其在近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意义。
一、 叶德辉与诸桥辙次的交流经纬
1918年以及1919年至1921年的两次访华期间,诸桥辙次的足迹遍及华北、华中、华东等地,他一路观览风景名胜、探访书院寺庙、考察古迹墓地、拜访各地硕学。途中见闻记载于纪行录《游华杂笔》,据此可以大致还原诸桥与叶德辉的交流经纬。1920年5月2日,诸桥从汉口出发前往长沙,5月3日下午抵达。5月4至14日期间,先后拜访了湖南省教育会会长陈锐、佛教会长吴嘉瑞(1)《游华杂笔》第128页中的记载如下:“吴先生精通佛学,曾为高师校长,现为佛教会长,年六十左右”,据“高师校长”“佛教会长”两点信息,推测吴先生为吴嘉瑞。以及左宗棠、曾国藩的遗族左念贻、曾广江、曾广钧等人,交流最多的是叶德辉。《游华杂笔》中的记述如下:“五月四日早九点在三井洋行安置后,向认识的人打听叶德辉,说他学问深厚但为人评价不高。查看《观古堂藏书目录》,叶氏藏书众多。前往叶宅,其子出门来见,进行笔谈,说今日父亲事多,可另择日会面。”[4]125再次访问的日期定在了5月12日。诸桥对叶德辉的印象是:“不到六十岁,没有胡须,龅牙,时而戴上时而摘下金边眼镜。一见之下,无气质之人。然而进行笔谈,学问博通,收获甚大。”此外,“叶德辉谈及五行之说始于《焦氏易林》,此说知者甚少,颇显得意”。5月14日,诸桥第三次拜访叶宅,当日“观看藏书。叶德辉说宋版书籍已多运至苏州。元版以下的书籍甚多。得章太炎、康有为的介绍信后告辞”[4]129。
在1963年以回顾诸桥辙次学术生涯为主题的座谈会上,诸桥回忆与叶德辉“在长沙多次见面,此前在北京也有会面”[5]278。有关二人在北京的交集,笔谈资料提供的线索如下:
诸桥:高名久仰之。晚生今次欲究潇衡之胜,游历到此地。曩在北京,请柯凤孙先生得介绍。会有为言者曰,先生既去沙在苏,以是不携其书,不图今日得请谒。晚生之悦,何以过之。
叶:自丙辰年到苏州,于去年中历十月始归长沙,本拟于本月内仍赴苏过夏,因事稽留。适逢先生莅止,得接清谈,欣幸之至。鄙人承贵国学士商家,相知二十余年,平时与贵国人交情亦更亲切。故贵国现时无不知有鄙人者,惜不能人人握手也。(2)本文对笔谈资料的引用基于月洞让、王继如、李庆的成果,文中不再一一标注。
从“曩在北京,请柯凤孙先生得介绍”一句中可知,二人是通过柯劭忞(字凤荪)的介绍相识的。而柯劭忞与诸桥辙次的牵线人很可能是原京师图书馆馆长江瀚。据诸桥回忆:“留学前在嘉纳治五郎的住所见到江瀚,抵达中国后立即前往拜会。在他的帮助下,身居北京的大儒基本都得以会面。”[5]276江瀚曾受邀主持湘水校经堂,抵湘期间结识了叶德辉等在湘学者[6]。综上可以推断,诸桥很可能是通过江瀚、柯劭忞的关系结识叶德辉的。
此外,叶德辉提及“自丙辰年到苏州,于去年中历十月始归长沙”。进入民国后,叶德辉因言招祸,为躲避逮捕,数次离开长沙;1916年4月底至苏州,其间钻研学问、发表研究成果;1919年10月中旬回到长沙,受到时任湖南督军张敬尧的礼待[7]5-10,607-609。据此可以推断,诸桥辙次拜访时,叶德辉不仅暂时获得了政治上的安稳,在学术研究上也有了充分的积累。叶德辉学问深厚,且十分自负,笔谈中豪言:“故贵国现时无不知有鄙人者,惜不能人人握手也。”从他指导过盐谷温、松崎鹤雄等人来看,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力确实不容小觑[8]278-283。所以诸桥慕名前来,在记录与叶德辉的交流时也感慨“收获甚大”。诸桥所言的“收获”具体来讲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有形的收获,叶德辉是近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大藏书家,诸桥辙次在叶宅阅览了大量珍稀古籍,叶德辉慷慨地将自己所著《经学通诰》赠予诸桥,并允许诸桥抄录自己为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写的批语[5]278。临行之际,叶德辉挥毫录了一首陈文述《留别秣陵》诗赠予诸桥(3)此份叶德辉手迹收录于单行本《游华杂笔》(目黑书店1938年版)。叶德辉当时选录陈文述的诗相赠,应与他欣赏舒位、陈文述所撰《乾嘉诗坛点将录》相关。,并为他写了给康有为、章太炎的引荐信。
其次是无形的收获,与叶德辉笔谈论学给诸桥辙次带来了知识的收获与精神的愉悦。二人的笔谈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叶德辉对自己学术渊源的阐述,向诸桥表明“鄙人学派与湖南不同”;二是叶德辉对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的梳理;三是有关张之洞《书目答问》、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具体问题的对话。笔谈以诸桥提问,叶德辉回答的形式进行,叶的回答占主要篇幅。鉴于此,下文首先提取笔谈中叶德辉的代表性观点,从历史背景把握二人在经学史研究上的思想交集。其次,参考诸桥辙次的论著,对他未在笔谈中展开的论述进行补充。在此基础上,分析叶德辉与诸桥在康有为今文经学、颜元实学等具体问题上的交流与论争。
二、 对经学史的认知与学术思想交流
笔谈中,诸桥辙次将叶德辉视为继曾国藩、王闿运、王先谦之后湖南学者的代表,不料叶德辉表明“鄙人学派与湖南不同”,并解释道:“鄙人原籍江苏苏州吴县,有清一代经学之汉学肇基于此地,即世称昆山顾炎武,吴县三惠(惠周惕、惠士奇、惠栋)是也。曾文正为古文家,王闿运为诗文家,王先谦为桐城古文家,皆非汉学家也。鄙人于三公皆不相同。”同时,叶德辉还强调“鄙人尚有阴阳五行之学,此皆曾文正、二王先生所不知者”。叶德辉的祖籍是江苏吴县,此地为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之地,目录版本、文字训诂等研究兴盛。然而,叶德辉生长于湖南,就读于岳麓书院,湖湘地域的文化传统是推崇义理之学、强调经世致用。出生地与生长地的不同造成了叶德辉在学术认同上的两面性:他一方面继承了湖湘地域的文化传统,视维护道统为己任;另一方面形成了明确的汉学意识,以接三吴汉学之绪为荣[8]14-44。
叶德辉的学术认同与他对经学流派的划分密切相关,而从汉学与宋学的视角梳理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问正是此次笔谈的精华所在,摘录原文如下:
中国学问,近三百年来分两派,汉学、宋学是也。汉学之中分两派,西汉、东汉是也。宋学之中亦分两派,程朱、陆王是也。西汉(王莽以前)之学为今文家(当时经师传授之本为隶书,故谓之今文)。此类书皆残缺不全,只有学说散见诸儒书中,并无正式经本也。康有为以之乱中国,故鄙人及张之洞、章炳麟(太炎)均痛斥之。王闿运即其祖师。王传之四川人廖平,廖传之康有为,今已消灭矣。东汉之学为古文家,今存之书,郑玄《三礼注》《毛诗传笺》、许慎《说文解字》。当初所传经本皆古篆籀文,故谓之古文。清国乾隆嘉庆以后,此学大昌,即曾文正亦为旁支。王先谦晚年亦专于此,但未精深耳。宋学以程朱为正宗,所传《五子近思录》为理学学说荟萃之书。清初陆陇其乃其嫡传也。陆最恶王阳明,凡所著书均痛驳阳明,以为异端邪说。据鄙人所见,陆子(九渊)天分极高,虽与朱子不同,尚从本原上立脚;王阳明全是有心立异,学无本原。现时中国学者,因贵国三百年来拜服阳明,亦靡然从风,群相附和,此最无识之事。盖人情畏难喜易,此中国人之大病,今日科学不能深入亦此病也。西汉学易,东汉学难;陆王学易,程朱学难。去难就易,无非为盗名起见,此类人何足与言学问。
关于经学流派的划分,不得不提到叶德辉的代表作《经学通诰》。该书初稿成于1907年,刊行于1915年,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梳理汉宋经学,揭示清代经学源流;二是梳理乾嘉汉学家的治经方法;三是标列书目以纠《书目答问》之弊[9]。《书目答问》被视为指导治学门径的著作,设经、史、子、集、丛书五部,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中分列汉学专门经学家、汉宋兼采经学家、理学家、史学家、经学史学兼理学家等14项,反映了清代学者采取汉学与宋学视角的论述方式。叶德辉对《书目答问》的修订继承了这一视角,《经学通诰》则分列汉代经学、宋代经学、清代经学三大派别,每种派别又再细分,列举代表性人物进行分析。对于经学流派的划分,叶德辉区分汉学与宋学,同时强调治经应“不分汉宋”,提出“尚汉学崇朱子”的主张,以此回应“汉宋兼容”“汉宋调和”之说[8]44-52[9]。值得注意的是,叶德辉在笔谈中指出,中国学人喜“西汉学、陆王学”为“今日科学不能深入”之根源。“科学”一词的使用侧面反映出围绕经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已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
对研究方法的思考也是诸桥辙次的问题意识之所在。1918年4月首次访问中国,诸桥就敏锐地察觉到传统经学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必须趁清末大儒在世时向他们请教学问[5]239,273[10]55。在各方协助下,诸桥如愿于第二年即1919年9月踏上留学之路。其间,他拜访各地硕学,而请教研究方法贯穿了他的交流记录。如前所述,诸桥手抄叶德辉为《书目答问》所写的批语,并在笔谈中提问:“程朱之学,以读何书属阶梯?”在拜访溥仪之师陈宝琛时,诸桥也询问了研究方法[5]240。而在与胡适的笔谈中,诸桥写道:“近年敝国人之研究经学者,多以欧美哲学研究法为基。条分缕析,虽极巧致,遂莫补于穿窍。弟私以为,东洋经术、西洋哲学既不一,其起原体系、研究之方法(Methode),亦宜有殊途。然而弟至今未得其方法,又未闻有讲其方法者。”[3]154由此可知,诸桥认为经学研究应立足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对以西方哲学附会经学研究的方法论抱有疑问,这基于他对日本汉学界的反思。
诸桥辙次认为,明治中期以后,日本汉学界受到清末学风的影响,分为汉学和宋学两派。在《对汉文学科的期望及其现状》(1935年)一文中,他指出:“近期以孔子的伦理观、朱子的哲学、天的思想、理的意义为主题的研究成果颇丰,此类研究基于科学方法,虽与汉学有几分相通之处,但仍以阐明义理为要务,总体上看可归入宋学派。相对的是,主张中国学问应置于中国发展脉络之中,阐明义理前首先要明确义理的依据,因此以确认文本、训诂考据为要务,与乾嘉以后的汉学派相近。东京帝大偏向前者,京都帝大偏向后者。”[11]417-418然而,在诸桥看来,“不论是汉学还是宋学,原为经学研究发展过程中的自然派生,无所谓有用无用。从做学问的目的来看,主张阐明大义的宋学派的观点无误。但为领悟大义而忽略方法,不精通文本、不问训诂则是站不住脚的”[5]249。诸桥致力于宋学研究,同时十分注重考据,其折中汉宋、得其要领的问题意识与叶德辉等同时代中国学人的学术思考产生了交集,反映了当时中日学者对经学史的认知以及在经学研究方法上的共同探索。
三、 对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认知与学术思想交集
诸桥辙次在听取了叶德辉对近三百年来中国学问的梳理后,抓住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提问道:“曰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其说虽奇,不过立异,不可以为正宗。高见如何?”对此,叶德辉回复:“康有为一切学说,鄙人所驳者,多在《翼教丛编》中,此书湖南、湖北、广东、云南均已有之,乱后少见传本。”1898年刊行的《翼教丛编》被视为顽固守旧派的一面旗帜。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成为新学宣传的中心,不仅政府官员积极推行新学,而且在舆论层面,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大力宣传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宣讲民权、平等、公法等新思想。为此,一批旧学人士奋起反击。1898年,王先谦的弟子苏舆汇总朱一新、洪良品、安维峻、许应骙、文悌、孙家鼐、张之洞、王仁俊、屠仁守、叶德辉、王先谦等人批驳康有为新学的文章,以《翼教丛编》之名刊行,书中叶德辉的论述占较大比重[8]53-84。笔谈中,叶德辉不仅将《翼教丛编》作为自己批判康有为学说的代表作,还特别强调了在“痛斥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乱中国”一事上,与张之洞、章太炎的立场一致。实际上,章太炎曾先后撰文《〈翼教丛编〉书后》《今古文辨义》发表在《五洲时事汇报》上,对《翼教丛编》中“腐儒”的态度进行了猛烈的反击。从政治态度来看,章太炎主张革命与叶德辉坚持守旧的立场大相径庭;但从学术立场来看,叶德辉强调古文经学在经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确与章太炎有共通之处。从龚自珍、魏源提出“经世致用”,到洋务派实践“中体西用”,以今文经学为主干的公羊学研究逐渐成为近代经学的主旋律;康有为后将其与西方知识相结合,章太炎与之公开对垒,引发经今古文之争。经学研究的前提条件是明确经的定义、经的领域、经与孔子的关系。古文学派认为经是一切群书的通称,经、传、论的区别在于书籍装订与版本、内容长短的不同,兵书、法律、教令、史书、地志、诸子乃至其他群书都时常称经;今文学派则认为经是孔子著作的专有名称,孔子之前无经,孔子之后也不得冒称经[12]17。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康有为先后避难日本,在寻求政治帮助的同时,继续宣传新学思想。日本舆论对康有为力图改革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总体的论调是对改革本身抱有同情和理解,但对于变法思想的过激、改革手段的粗糙以及对日本盲目的追随持怀疑、否定的态度[13]108-124。时隔20年,诸桥辙次关注康有为学说完全基于他的学术探求。如前所述,诸桥追求独立于“西洋哲学”的“东洋经学”的研究方法,然而康有为从儒学经典中提取民权、平等、公法等西学概念,明显有悖于其理想。虽然诸桥在笔谈中没有就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展开论述,但在《儒学的目的和宋儒的活动》中,他提及康有为的另一本著作《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4)据诸桥辙次的回忆,与康有为初次见面时获赠《新学伪经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康有为对《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各章做了详细的说明,希望诸桥回国后帮他进行宣传。,并做出如下评价:“因作者是《公羊》学者,十分认同董仲舒、何休之说,所以有一些基本的错误。”[14]131-132此判断基于诸桥对经与儒、经与孔子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
《儒学的目的和宋儒的活动》是诸桥辙次1929年向东京帝国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是其经学研究的代表作。论文旨在通过北宋庆历至南宋庆元160年间宋儒活动的历史事实,阐明以“修养”“正名”“经纶”三纲目相统合的儒学真谛。论文由三大编组成:第一编为“儒学之目的”,第二编为“儒学目的之分化与宋儒之活动”,第三编为“儒学目的之统合与宋儒之活动”。在聚焦宋儒的活动之前,诸桥首先就“何为儒学之目的”展开论述,而方法即是对“儒与经”“经与孔子之删述”两部分内容的考证。在“儒与经”一章中,诸桥首先阐明“儒”的意义变迁,指出“儒”起初作为术士、学者的代名词,后在《周礼》中专指教授道艺的特定人群“儒士”,再后来成为区别于杨墨的特定学术派别;其次,诸桥通过对比“传”的用法究明“经”的意义变迁,指出先秦时代儒家多用“传”字,诸子多用“经”字,而西汉以后,儒家以孔子删定六经以外的典籍为“传”。在“经与孔子之删述”一章中,诸桥指出“传所以述经”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源于孔子删述六经,并从删《诗》、序《书》、定《礼》、正《乐》、赞《易》、修《春秋》六个方面,对孔子删述的事实及程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得出“孔子删述六经仅止于小范围”的结论[14]25-160。
以上阐述是诸桥辙次对经学研究中核心问题的正面回应,从而与中国学界的探讨产生交集:一是诸桥指出先秦时代“经”多为诸子所用,而成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著书籍的专指是在西汉以后,此判断很大程度上与古文学派的描述相吻合;二是诸桥考证孔子删述的程度、分析孔子删述的初衷,一方面与今文学派聚焦孔子政治思想的出发点相近,另一方面又与新古史派从根本上否认五经与孔子有关的立场形成对立。诸桥从梳理基本概念出发,但不以考证为最终目标,吸取古文学派、今文学派的合理之处,是开拓经学史研究的一种尝试。
四、 对颜元实学的认知与学术思想碰撞
叶德辉与诸桥辙次的学术交流还见于笔谈之外,体现在对颜元学说的关注上。诸桥曾作《颜习斋的学风》(1939年)一文,而关注颜元的契机正是阅读《经学通诰》。他回忆道:“在中国时,我从叶氏那里得到《经学通诰》。翻阅一看,清朝学者中颜元居于首位。当时我还未读过颜元的著作,于是询问叶氏为何将颜元列为第一人,其学问是否如此深厚。叶氏答道,其实颜元的学问一般,只因当时大总统徐世昌提倡,为了迎合时局而已。”[15]83五四运动以后,徐世昌通过建立“四存学会”、创办《四存月刊》、编撰《颜李丛书》等一系列举措,大力提倡颜元、李塨之学,借此维系世道人心。然而,颜元的习行思想在梁启超、胡适等新学人士的眼中,又是与科学思潮相关联的。换言之,在新旧、中西思潮复杂关联的背景下,颜李学说得到了不同立场人士的共同推举[16]。
推崇颜学的风气以1869年戴望编撰《颜氏学记》为开端,与此同时,以朱一新为代表的宋学者展开辩驳,从而形成晚清学界表彰颜学与反对颜学的对立局面[17]。从维护宋学的立场上看,叶德辉对颜元学说或许并非真正推崇,这一定程度上符合他面对诸桥提问时的回答。而在批判康有为学说上与叶德辉立场一致的章太炎则为推崇颜学的代表人物,在与诸桥辙次的笔谈中,章太炎就表示:“清代讲宋学者,不过会萃成说,其是否,并无心得之妙。然如颜元(习斋)、戴震(东原)之徒,却有新义。”[3]118从传统经学诠释范围内的尊颜、反颜,到新文化运动后冲破传统经学研究范畴的尊颜,颜元学说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一个体现,诸桥以此作为把握清代学术、深化自身经学研究的切入口。在《颜习斋的学风》一文中,诸桥首先依据时间线介绍颜元的生平及学术,勾勒了颜元从信奉程朱之学到对宋学产生疑问,逐渐明确“学问不在理论而在实践”的过程。诸桥指出,“习行之学”至《习斋记余》达到巅峰,其晚年之作《存学篇》虽秉持批判宋儒的立场,但文中又处处可见对宋学的留恋。此外,诸桥还列举《存性篇》《存人篇》《存治篇》等颜元的代表作,逐一进行了介绍。
诸桥辙次对颜元学说的基本定位是“实学”。他指出:“清朝并非只有考证学,实学确实存在过。但遗憾的是,颜元、李塨以后只有二三门人,珍贵的实学没有被继承下来,再之后几乎被忘却了。”[15]82-83诸桥强调实学的重要性在于,他认为,清朝虽然学术发达,但经学研究沦为“为了考证的考证之学”,是在“抵达真正目的之前的彷徨”[14]6-7。所谓“真正的目的”即“儒学的真谛”,也就是诸桥在《儒学的目的和宋儒的活动》中所阐述的“修养”“正名”“经纶”三纲目之统合。诸桥认为,经学流派的分裂乃至对立源于“修养”“正名”“经纶”三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并从实现三纲目统合的角度确定了朱熹的历史地位。在诸桥看来,颜元实学也体现了“修养”“正名”“经纶”三纲目之统合的儒学真谛。在《颜习斋的学风》一文的最后,他明确写道:“一直以来,儒教是经世救民之学、修己治人之学,这既是先贤的定论,也是我的信仰。然而,学问发展至一定阶段后开始分化为各派,逐渐脱离学问的初衷,做学问和做事业分道扬镳的倾向逐渐显著。……当今社会多少需要此等学风,这出于将儒学与实际相结合的需要。”[15]81-83
诸桥辙次从经世致用的角度肯定颜元学说的重要性,并提出日本水户学派可能受到颜元学说影响的观点。他认为,颜元的“学以明伦”“教学治一体”等核心观点可以在藤田东湖《弘道馆记述义》、会泽正志斋《学制略说》等水户学派的代表性著作中找到相对应的部分[15]80-81。当同时代的中国学人在寻找中西思想间的关联性时,不少日本汉学家在中日思想间寻找联结点。诸桥的同乡前辈小柳司气太在《东洋思想研究》中论及颜元时,也指出颜元提倡的“言行一致”与日本儒学者山鹿素行的思想相似[18]195。实际上,诸桥早在1910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论文《诗经研究》中就将《诗经》与《万叶集》进行了比较研究[19]568-596。对他来说,阐述儒学真谛与探求东洋思想精华应是互为表里的,其晚年之作《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圣会谈》可为印证。新文化运动之后,探寻经学的作用成为中国学人不得不面对的难题[20],而诸桥辙次对儒学真谛具有普遍性的认知与探求,也可视作对此问题的思考与回应。
五、 结 语
本文以叶德辉与诸桥辙次的笔谈资料为线索,分析了两人在经学与经学史研究上的思想交集,阐述了两人围绕康有为今文经学、颜元实学的交流与论争。不论是康有为学说遭到批判,还是颜元学说得到推崇,两者皆反映了在东西、新旧思潮错综关联的背景下,近代中国学人面临的学术转型难题。日本的学术转型早于中国,中国学人以日本学界为媒介了解西方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日本学界的发展也始终伴随着东西、新旧的竞合,如何保留学术传统是中日学人共通的问题。诸桥通过与中国学人的交流,捕捉到了当时中国学界的焦点问题,了解到了中国学人的治学理路,加深了对中国学术的认识,在经学与经学史的研究思路上获得了新的启示。在研究方面他主张折中汉学与宋学的方法,在教育方面他提倡设立国学科,这些主张和提倡不同程度上与同时代中国学界的探讨有所呼应。
1933年,东京松云堂书店出版由诸桥辙次编辑,诸桥与安井小太郎、小柳司气太、中山久四郎合著的《经学史》。诸桥在序言中写道:“管见所及,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似乎还没有可借鉴的经学史。”该书正文由先秦至南北朝经学史、唐宋经学史、元明经学史、清代经学史四部分组成,对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多有参照(5)参看王应宪《日本“中国经学史”之译介与回响》,见张柱华主编《“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424页。。新文化运动以后,经学和经学史研究在中国学界淡出舞台的中央,然而诸桥辙次等日本汉学家在此方面的探索与同时代中国学人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追求形成呼应。叶德辉与诸桥辙次在经学和经学史研究领域的对话即是20世纪20至30年代中日学术交流的一个缩影,具有代表性与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