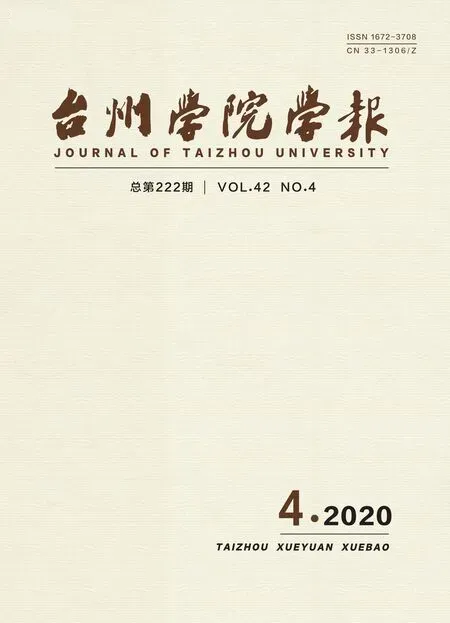试论《曾国藩家书》中的修身之学
於谋芝
(淮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作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无疑是晚清乃至近代历史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同时,在学术上,曾国藩也是晚清著名理学经世派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宋明以降的传统理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新,特别是融合儒、道、墨各家思想发展出独特的修身之学,抛弃了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陈腐学风,一反宋代以来理学“内圣”与“外王”分离乃至对立的倾向,真正实现了“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融合统一。其修身哲学的集中体现,便是《曾国藩家书》。作为对子弟修身的要求,《曾国藩家书》(以下简称《家书》)中的修身不再停留于理学内在的心性之学层面,而是强调身体力行的要求,使修身最终能够落实于现实生活,突出经世致用的倾向。这一由内而外贯通的修身之学,对宋明以降过分内化的儒学,是一次重要纠偏,也展示了儒学自我开新的生命力,对今天儒学的发展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曾国藩家书》中修身之学的思想渊源
(一)《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思想。从思想渊源上看,早期的中国哲学传统本身即包含刚健进取的传承脉络,曾国藩主张的刚健进取的修身之道,来自《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后世理学趋于内敛主静的修身倾向不同,《易传》赋予人生一种自强不息的活跃精神和张扬向上的乐观意识,所谓“生生之谓易”,这是一种积极主动、重刚行健的人生哲学。随着儒学在汉代以后日益庙堂化,在宋明之后转向心性之学,《易传》中的这一人生哲学日渐湮灭不彰,但在晚清实学中,在曾国藩为代表的经世派理学中,《易传》所体现的刚健进取精神,再度被发扬光大。
《易传》中强调刚健有为,但也反对将“阳刚”这一属性推至极致,否则会导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这种辩证精神在曾国藩的修身之学中,也有体现。曾国藩认为刚毅和刚愎自用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二者又很相似,“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1]28所以要时时注意,时时谨慎的内省自身。这一观点显然是《易传》“刚柔兼济”“刚中而柔内”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修身实践中,就是既可以刚健进取,也可以做到谦退自抑。
(二)宋明理学周敦颐、二程的“主敬”思想。曾国藩的修身学,有继承宋明理学“主敬”的一面,如提出敬之功夫为“内为专静纯一,外为整齐严肃”[2],并将“敬”列为日课之首。这与周敦颐、二程的由敬而静、居敬行简的修身之学一脉相承。为此曾终身坚持每日静坐一段时间,以求灵台清明;同时外貌要保持整齐,神情端正严肃,内心时时刻刻要警惕自己是否出现了闲杂或不良的念头。平日闲居无事时,要宁静安泰,不要想身体以外的事情,一旦投入工作中,就必须做到专心致志,不存杂念。自己要保持清澈明朗的精神状态,才能保持旺盛的生机,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
(三)道家老庄居柔守雌和光同尘的思想。在他成就不世功业后,为免于功高震主之虞,谦退自抑就成为他的重要处世准则,并经常以其修身原则训诫子弟。他曾经在家书中告诫自己的弟弟:“余近年在外,问心无愧,死生祸福,不甚介意,惟接到英法美各国通商条款,大局已坏,兹付回二本,与弟一阅。时事日非,吾家子侄辈,总以谦勤二字为主,戒傲惰,保家之道也。”[3]230曾国藩认为谦退是一种让家族兴旺的法宝,劝胞弟子侄务必谦勤,不可傲惰。但是他也认为不能过分谦虚,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过度地贬低自己。“不能过谦,过谦则下无敬畏之心。”[3]230曾国藩取得如此成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懂得韬光养晦,知道如何藏锋。湘军在攻打下南京以后,首先退去一部分兵权,裁撤了四万湘军,又把南京的防务让给八旗兵,这些举措,打消了主上的猜忌,无疑是曾国藩韬光养晦、谦退自抑保身之道的重要体现。这种明于世故的处世策略,在程朱理学熏陶下的俗儒那里是难得一见的,这使曾国藩的修身之学有着远超之前的儒家士大夫的处世哲学的智慧。这一修身之学,既有来自风口浪尖历练的切实人生经验,在学理上,也有着对道家老庄居柔守雌和光同尘的理论的借鉴。
二、《曾国藩家书》中修身之学的主要内容
修身在曾氏思想中占有核心地位,也是他劝勉子弟的重点,是其《家书》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读书人只有两件事是要记住的,一是进德求的是“诚正修齐,以图无忝所生”[4]48;二是修业修的是“记诵词章”[4]48的技巧,“以图自卫其身”[4]48。进德修业二事,核心都在于修身,即他所谓“修身为本”。《家书》中的修身之学,打破了传统修身之学的格局,其中既有曾氏个人在修身方面长达数十年的涵泳体认和经验积累,也有对其他学派在修身方面的重要思想的整合,特别是相对于宋明理学传统中的修身之学,表现出新的气象。而这一修身之学从其效果而言,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其作用不仅仅是福荫曾氏后人,使曾家历五代200余年,无一废人[5],也成为今人修身之学可资借鉴的重要经典。《家书》对宋明理学修身之学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现分别述之。
(一)修身的精神导向:从内敛主静到刚健进取。宋明理学的“主敬”思想的修身学到极致,势必要走向“废动而求静”,甚至追求“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状态,这显然是为曾国藩所不取的。他的修身之学,受湖湘学派王夫之等理论的影响,王夫之认为“致虚守静之学,以害人心至烈也”,要求抛弃专注静息修养的主静之学,主张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这显然与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更为契合。因此,不同于宋明修身学一味主张的内敛主静,《家书》对修身的要求,多了激扬奋发刚健进取之意,这也是曾本人性格为人的写照。“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6]107,“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需有二字灌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6]107曾国藩一生具有超强毅力,性格刚强,坚而不脆。男子要想自强自立,必须有倔强的品质,在曾看来无论是做任何事都必须具备这个品质,否则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功。曾的刚强,不只表现为行伍战阵的愈挫愈奋,屡败屡战,也表现在其他一切事情上的刚健务实,兢兢业业,还有不注重于口头的宣传而看重实际工作的“拙诚”;以及在遇到挫折时能够忍辱负重,坚毅沉着,迎逆境而上,最终成就大事。
(二)修身之法:在伦常日用中的自我砥砺。不同于宋明理学在修身之学上的高蹈和空疏,《家书》更强调在伦常日用中的实践。曾的祖父的八字治家格言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宋明理学的一个弊端是使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生产实践,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终身埋首故纸堆皓首穷经,而中国民间社会则奉行耕读传家理念,“男必耕读,女必纺织”的家庭教育,则一定程度避免了理学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荼毒。曾氏治家格言中的八件事中,都是极为具体的,能够于当下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修身要求。特别是其中有明确的对物质生产劳动的要求,这种极为接地气的对子弟日常行为的规范,使曾氏修身学具有强烈的实践理性特征,这是以往偏重心性修炼的理学修身学中所没有的。
《家书》对子弟的修身要求,继承了其祖父治家规范中的这种实践理性特质,往往体现在每天的伦常日用中。他对子弟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如遵守祖辈的耕读家风,不要有官气,出入不许坐轿,不许让下人伺候,要拾柴收粪,学习农活,男子汉要种田养鱼,女子要做鞋纺纱等。将农业生产实践放在修身的重要位置,这在之前的宋明理学修身之道中,无疑是比较少见的;又如对早起的要求,这既是对子弟谆谆告诫、反复叮咛的修身规范,也是曾国藩自己身体力行、一生坚持的实践。“居家以不晏起为本”,“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与身体大有裨益。”[7]可见曾氏修身学,一个重要特点即是从细微处入手,从行止坐卧的日常生活进行要求,培养勤奋自律的品质。
早起以养勤,勤作为品质,往往被视为底层劳动者的品质而被宋明儒学知识分子较少谈及。但在早期中国哲学传统中,“勤”作为修身原则也曾被墨家学派着力强调,墨家之徒,“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6]127。曾国藩的修身之学,无疑是对古代先贤的这种勤苦自律精神的继承发扬。他视勤为治家之本,“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行军,皆以勤字为本”[6]127,曾氏本人更是注重对子弟的以身作则和言传身教:“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6]127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即五勤是他将勤具体化的几个方面。相较于宋明理学空谈义理的风气,曾国藩的修身之道,显然具有更务实的可操作性。
除了勤,还有俭,也是曾氏修身学的核心要求。在给其弟的书信中,曾国藩写道:“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4]131在其日记中,曾国藩也写出自己的忧虑:平时都是教别人节俭,可是最近感到自己的生活太奢侈了。“昨闻魁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1]346在曾家成为显赫的达官显贵之族,曾国藩深深忧惧子弟在安乐的环境中会养成骄奢淫逸之风,所以在治家中力戒子弟奢靡,在衣食起居诸方面要求子弟保持勤俭朴素家风,在家书中,殷切提醒后人虽然家族已经呈现鼎盛之势,但是也不要忘了贫寒时的家风,后辈子弟一定要戒傲戒惰。通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子弟勤俭品质的养成的重视。
勤俭不仅是必备的修身途径,也是培养克己自律,进而养成其他德性的重要途径。曾国藩的修身之学,极重个人自我约束,他本人在一生中也无时无刻不在监督自己的言行,不断警示和检讨自己,视慎独为修身第一自强之道。只有严于律己方能服众,方能成就坚卓大志,曾国藩的自律克己,不只是对自己的胞弟子侄有示范作用,更有带动一方风气,改变社会的功效。近现代以来湖湘地区出现诸多影响历史的人物,如毛泽东、田汉、沈从文等,无疑与曾国藩对这一地域民风与文化的示范和影响有关。
(三)修身的落实:经世致用。宋代湖湘学派立派之始就想要“通晓实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自宋至明,理学逐渐走向空谈而不问国事的时候,湖湘学派依然秉承着经世的思想,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生活,这成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特点[8]。清代包世臣、陶澍、汤鹏、魏源等为首的经世学派,继续传承了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倾向。
生长于湖湘学派这一文化圈中的曾国藩,虽然也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但也深受湖湘学派地域文化的熏陶浸染,这使他的修身之学,比正统程朱理学多了经世致用倾向。这使他一方面成为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也有超越这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格局的方面。作为正统儒家知识分子的一面,体现在他一生潜心研究学问,成为有清以来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学术兼综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不分汉学宋学的门户,在儒学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同时,他的经世致用倾向,又使他得以远远超越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格局境界。正是这种倾向,使他不再局限于程朱理学教化出的那种不通世务的“俗儒”。经世致用的思想成就了他日后务实的优良品格,从而能够使他出将入相,赢得中兴名臣的美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锋。
曾国藩极重经济之学与经世之术,并一反宋明理学对二者的轻视,将其归于孔门正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政书,及吾世掌故皆是也。”[9]经世致用思想体现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便是积极有为,重事务实,“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3]137这“五到”就是《家书》中所强调的修身,“五到”的精髓就是脚踏实地,不厌烦琐,不怕艰难的埋头苦干,这无疑是曾国藩务实精神的突出表现。正是这样的务实精进的作风,让他后来极力倡导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主张中体西用,成为洋务运动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和支持者。
《家书》中的经世倾向,对于传统理学的修身之道也是一种纠偏。理学的修身之道,宋以后逐渐被奉为士人修身圭臬,其后果是整个知识阶层有明以来的沉沦,即所谓的“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无力面对现实的难题。其后果正如顾炎武所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0]传统理学往往重理不重事,以理为先,鄙弃事功,曾国藩则突出重事务实,以事为先,强调有为。对宋明理学不重实务,不讲事功,空谈心性,流于空疏的弊端,《家书》中的修身学做出了有力的反驳,将内省修身与经世致用有效结合,一反理学脱离实务的倾向。这无疑是曾氏修身之学补益于后世的最大意义。
三、曾国藩修身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注重家风和家庭教育,是修身的基础。家庭教育是孩子道德教育的起点,人生的第一任老师是父母,曾国藩一向重视家风和家庭教育,不让家人因为自己的威望和特殊地位搞特殊化,也不为家人谋取任何私利。曾国藩要求家庭中每一个人要学会劳作,学会耕耘,不要好吃懒做,养成勤劳和节俭的好习惯。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风貌,弘扬优良家风是道德教育的重要过程,对于提升个人修养有着重要作用。家风好,则家庭和谐美满;家风差,则家道衰败,贻害子孙。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11]现代道德教育必须注重家风和家庭教育。家长必须把美好道德观念及时地传播给孩子,在他们健康成长的道路上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品德,而家庭教育就是修身的基础。
(二)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修身的基本要求。曾国藩提出的“十二条戒律”就是对自身修养严格要求的体现。曾国藩一生对自己要求很严,要求自己要经常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过失,从而弥补自己行为中的不足,达到提升自身修养的目的[12]。要求自己及面对任何事情必须心平气和,不可操之过急。曾国藩对他人却很宽容,要求做人要有君子胸怀,不要过分计较个人的得失,虽然自己在朝廷威望很高,而对于不同政见者却以礼相待。现代人往往心浮气躁,对自己不能严格自律,对别人要求却很严、很苛刻,不符合修身的基本要求。现代修身方法强调要严于律己,对别人要宽容,必须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找出自己行为的不足,省察克治,改正错误,才能使自身修养不断地提高。
(三)把修身融于生活实践中,是修身的重要方法。传统的宋明理学容易使人流于空谈,不与现实生活相联系,让修身脱离了生活实践,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曾国藩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突破了传统修身思想的局限,提出把个人修养融于日常生活实践中,成为现代人修身养性,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修身是提高个人修养的过程,良好品德的养成,是水滴石穿的功夫,通过生活实践向人民群众积极地虚心学习,不断提升自身品德,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现代修身思想要把道德理论的学习和道德实践紧密结合,不能脱离生活实际来空谈道德理论,要通过日常行为不断历练,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认知,形成良好的品德,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宋明理学人格美育论》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