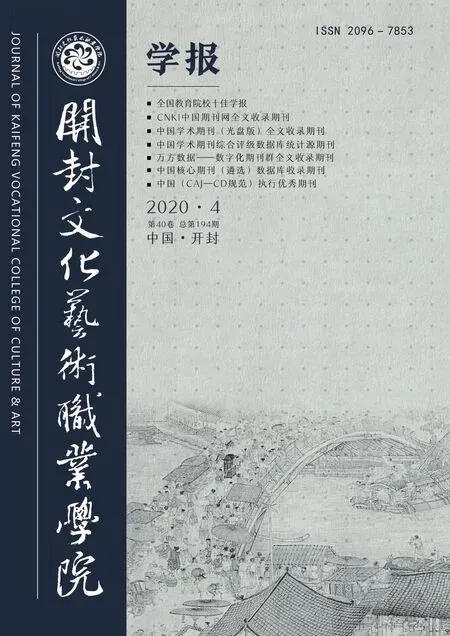潘年英《河畔老屋》的原生态叙事
陈 洋
(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 黔南 551300)
潘年英是新时期贵州侗族代表作家之一,因求学、工作等原因,他经历了从侗乡到城市,从依山傍水的美丽村寨走向城市喧嚣的人生轨迹,无论身在何处,故园永远是他最牵挂的地方,文学创作中的“盘村”就是以故乡盘杠村为原型而创作的。2018年,继“故乡三部曲”(《木楼人家》《故乡信札》和《伤心篱笆》)之后,《河畔老屋》经由王铭铭、安妮·居里安、刘再复、韩少功等人联袂推荐,这一心血力作得以问世。
一、“老屋”的叙事与个体身份的确认
中国是传统的以农业立国的国家,中国人有着深厚的恋土情结,历来十分注重“居者有其屋”“安身立命”“叶落归根”等。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房屋不仅仅是居住的场所,更是安身立命之所,是人的根之所在。正如列维纳斯在《整体与无穷》中所说:“房子最与众不同的作用就是,它不是人类活动的终结,而是人类活动的条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是人类活动的肇始。”[1]
在《河畔老屋》中,潘年英按个人成长经历和家庭搬迁轨迹描写了4处房屋,作品采用倒叙的手法,通过居住房屋的变迁,展示家庭、房族的代际更迭,折射出侗民族文化和生存状态的变化,窥探时代文明的新貌。
“半岛老屋”,因房屋矗立在一处半岛一样的巉岩上,故此得名。从时间上来看,“半岛老屋”承载了潘年英进省城读书直至现在的时光。作者在半岛老屋居住时间较久,感情较为深厚。从生产队时期修房写起,有火塘间的温暖,有推开窗看到的缤纷世界。潘年英在作品中写道:“而自从那次分家之后,我们那一个曾经让人艳羡不已的大家庭,也由鼎盛开始转入衰败。”[2]25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树木被砍,水田荒芜,坪子荒草萋萋,那个曾经诗意与美好的家园,早已破败不堪,写出了作者深深的无奈。
“竹林老屋”,因门口茂密的竹林而得名,是典型的吊脚木楼。从时间上看,竹林老屋承载了潘年英从童年到进省城读大学的生活时光。正如作者所言:“竹林老屋于我的记忆有许多昏暗而暧昧的细节,其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模糊褪色,反而是越来越清晰而鲜活了。”[2]72竹林边终日流淌的盘江,推开窗就可以触摸到的竹叶,有和姐丹、姐小“办家家”的游戏,有大黄狗,有小花猫,有发酵的甜酒,有父母温暖的怀抱,有捣谷子的劳作,也有父亲的书,还有青春期的忧郁与叛逆,时间的脚步在这栋老屋留下了深深的痕迹。现在的竹林老屋只剩下一片竹林了,令人伤怀的不仅仅是竹林老屋,还有时光的无情,更有曾经熟悉的面孔,而现在早已物是人非了。
“食堂老屋”,因被生产队用作公共食堂而得名。从时间上看,食堂老屋承载了潘年英从出生到读小学的生活时光。“我”虽在食堂老屋出生,但因在此生活时间不长,加之年龄较小,更多的细节多靠母亲的转述和年长后的重访,故对食堂老屋没有什么较深的细节记忆。虽然作者此后也曾在食堂老屋读过几年书,但更多是阴森恐怖的记忆和不懂新课程带来的恐惧与绝望。潘年英在食堂老屋经历了人生的巨大磨难,虽保住了一条命,却留下心理的创伤。作品用不少的篇幅讲述了盘村的家谱,食堂老屋有作者一家的变故。
“河边老屋”,因距离盘江河比较近而得名。从时间上看,河边老屋是潘年英父亲及其爷爷主要生活的居住场所。河边老屋本是一座气质高雅、卓尔不群的房子,是青砖瓦的木楼,有精致的雕花,有宽敞的房间,处在盘江河边,孟岚寨的桥头边上。但后来因为爷爷的问题,导致父亲和“我”都受到影响,父亲成了一个时代的“弃儿”,“我”也从未佩戴过一次红领巾。河边老屋经转手卖给地主子女,最终被大火吞噬。
在人的内心与外在之间的交流中,房屋是最深沉的隐喻,成为人灵魂的栖身之所。“老屋”的际遇就是作者的际遇、家族的际遇和民族的际遇,在它的身上,集中反映了一个家庭、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作者将家族故事、民族发展和时代进步融入“老屋”的叙事中,既体现出故事的丰富性,也再现了作者人生轨迹的曲折。“我”对“老屋”的向往,实质是对家园的追寻,如今“老屋”或是被父亲变卖,或是被损毁,或是被遗弃,这些都是作者无能为力的,没有了“老屋”,其实就是一种无根的状态,没有了人生归属感,没有了精神寄托,个体身份的焦虑与困惑随之而来。
二、“父亲”的叙事与家族身份的断裂
在中国,家庭是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是通过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庭关系中,每个人有明确的职责和身份。换言之,每个人的身份,是通过父母的身份和家庭的存在得以证实的。
在一个家庭里,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亲的关爱和教育。《河畔老屋》中,关于“父亲”的一生,作者大致通过父亲的身世、父亲的形象和“我”与父亲的关系几方面向读者全面展现。
爷爷去世后,父亲主动退学,肩负起家里的重担。在那个阶级仇恨异常惨烈的年代,父亲成为一个时代的“弃儿”,被强行赶出家门,投靠同母异父的兄弟,也被拒之门外,遭受了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打击。作品中多次提到“父亲是一个极有生活创造能力的人”[2]29,或许是生活所迫,或许是出于无奈,父亲掌握了多种生活本领和技能,他乐观向上,相信自己的努力与付出终会换来幸福的生活。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的形象一直都是肃穆而严厉的。除了有因砍伐树木遭到的斥责,还有生牛痘时被父亲抱在怀里,感觉到他那宽厚而温暖的胸膛,也有因“我”偶然考了一个好成绩,让父亲激动不已,半夜把“我”摇醒。念了高中,“我”性格开始叛逆,也不再听从他的召唤。他教会“我”想吃李子就自己去栽李子树,否则就永远吃不到李子。
父亲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向往,他对待生活的坚毅乐观令人敬佩,“我”渴望得到父亲的关爱与认可,他的精神是“我”一生宝贵的财富,但父亲的逝去,不仅使我失去了与家的联系,还使“我”感受到无根的人生状态,“我一直觉得,只有在我父亲和我的几个堂哥都还在世的时候,我们那个房族才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房族。而如今的房族,则早已名存实亡”[2]20,进而产生了对家族身份的焦虑与困惑。
随着至亲家人的离世,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出现断裂,人的记忆也会慢慢消逝,人的身份也将荡然无存,这对人类来说是最为可怕的灾难。
三、“火塘”的叙事与民族身份的维系
人类对火的使用具有重要意义。侗族作为少数民族之一,火在日常使用中必不可少。在侗家人民的生活中,火塘不仅具有烹饪、取暖、照明、会客、保存火种、维系亲情等功能,而且还具有象征生产生活、家庭伦理、族群关系、宗教观念、社会制度等功能。火塘有团结人心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带来了欢乐祥和的生活景象,是侗家人民互相交流、延续久远的民族文化。
在《河畔老屋》中,作者对火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传统的侗乡建筑是没有会客厅的,火塘间就是侗乡的会客厅。火塘维系着人与人的关系,维系着族群的命运,延续着家族的生命。
人的一生都在火塘边转悠,火塘是人一生重要的生活空间。作者及其祖祖辈辈,因火塘获得温饱,延续生命。“火塘”的叙事,向人们展现了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人们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性。火塘与民族的生活习惯,以及家族之间的紧密关系,是作者对那个温暖的家园的向往和留恋。
由于和侗家生活联系紧密,火塘已然成为侗家人民独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成为漂泊在外的侗族儿女寄托对故乡无限思念的象征,是确立一个人民族身份的重要依据。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城市文明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也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使火塘的功能逐渐弱化。“文化变迁是指一个社会或群体中大多数成员逐渐放弃旧的行为选择标准体系而接受和形成新的行为选择标准体系的过程,是社会变革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结构的重新组合。”[3]面对火塘的逐渐消逝,我们在为侗族火塘文化惋惜的同时,也要看到这是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改善人类居住环境的必然。
四、身份的失落与追寻
潘年英曾言:“不瞒大家说,我是一个生活在农业时代的人,我的感情和思想依然停留在农业时代,我只对乡村、泥土、自然感兴趣,而对于城市,对于工业或后工业文明,我是很隔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确是太不与时俱进了,太落伍于这个时代了。”[4]261
因离家在外多年,故乡已然没有自己当年生活的痕迹,而那些逝去的人生历程只能留存在记忆的深处。当“老屋”不在,“父亲”逝去,“火塘”改变,“我”试图想去维护这种关系,寻找自己在故乡的“身份”。在作品中,“我”展开了三次身份的“寻找”。
第一次是关于父亲的三幅画像,第一幅是当地土画家画的炭画像,“我”觉得一点也不像,但是母亲却说这个是最像的一幅;另一幅是“我”早年给他拍摄的照片,但所有看到照片的人都说“太不像”;还有一幅是油画,大家看了也说不像,尤其是母亲,她坚决否认这画上的人是父亲。当所有人都质疑的时候,“我”由此产生深深的挫败感,“我”与家族的断裂显而易见,这种身份的追寻显然是失败的。
第二次是二弟几次想把老屋卖掉都被“我”拒绝,作者认为他的兄弟们已经在感情上遗弃了老屋,其实作者害怕的不是在情感上遗弃老屋,而是“我”怕被遗弃。因为老屋伴随着作者的成长,而作者已经离开家乡多年,害怕再也看不到老屋,没有了情感的归宿。
第三次是“我”决定回乡修建风雨桥,可是却意外遭遇乡亲的阻挠,再次遭遇身份确认的失败。后来,家里的屋基被别人霸占修建房子,“我”想重建竹林老屋也以失败告终。
潘年英远离故土,却又未能在城市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所以他不停地往返于城乡之间,“一有空,我就从城里驾车千里迢迢往老家赶,目的就是想在那灶房上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我就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令我心安的地方了”“使我疲惫的身心倍感温暖,感到灵肉均有所皈依,进而对之无限依恋和挂怀”[2]157-158。
五、故园追思与民族记忆
所谓故园,一方面指血缘和族亲的认同,即地理环境或行政区域上的家园;另一方面指文化和价值上的认同,即精神家园。
在《河畔老屋》中,潘年英突出了一种难以割舍的诗意化的故园情怀,通过自然、真诚的原生态描写,向世人展示了盘村原生态文化的和谐美好。他曾在《故乡信札》中写道:“我要说‘故乡’于我是难以超越的,那个生我养我哺育我成长的盘村家乡,是我认识世界和生命成长的摇篮,也是我全部学术和文字的支点。”[5]4王铭铭在评价潘年英的《在田野中自觉》时曾写道:“潘年英将他的故园想象成‘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他的很多文章表达了他对他的家园的爱,我以为这种深挚的爱并不多见,是这个嘈杂世界的心灵残存。我欣赏这种深挚的故乡之恋,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表达对它的向往。”[6]
乡村文明的没落是全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事实。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迅速波及,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发生了新的改变。在对“原生态”文化的认识方面,具体表现为,以前被看作是“原始”“落后”的文化习俗,现在被认为是自然的、纯真的、原生态的,反而被视为现代文明下仅存的文化精华。
潘年英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民族叙事特点,他笔下的“老屋”“火塘”“父亲”,除了有作者的人生经历外,还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潘年英和他的侗族同胞作家一样,从山村来到陌生的现代城市,用汉语的文字来陈述自己的故事,结束了侗族没有文字而沉默或者被他者表述的境地,同时又竭力不使本民族的文化消融在他族的文化传统中。”[7]“火塘”边侗家人的生活场景,“老屋”里的家族故事,“父亲”与我的人生轨迹,这些都是作者对城乡文明冲突的思考,对故园的追思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对文化之根的追寻。现如今,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全社会的关注,现代城市文明对乡村的“入侵”越来越严峻,如何保护好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文明,如何留存好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真正实现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需要全社会共同思考,共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