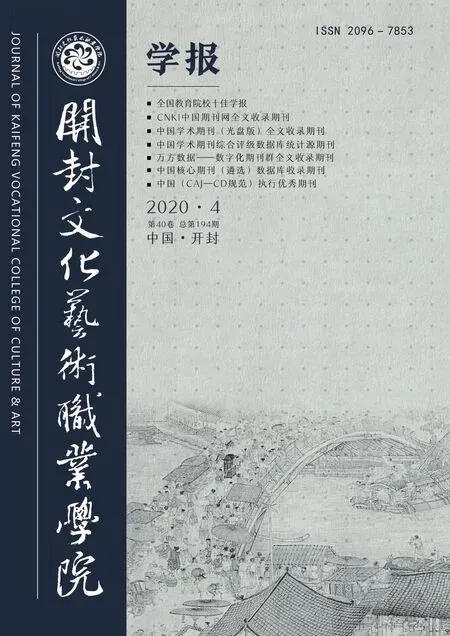浅析《高濑舟》中的叙事学问
陈颖妮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一、叙事视角的分析
(一)视角转换
作为一篇历史小说,《高濑舟》采用第三人称叙述、选择性的全知视角无疑是较为贴切且客观的。文中既有人物视角之间的转换,又有叙述者与人物视角之间的变换,视角多次变化的运用使得人物、情节、环节在修辞效果上产生了差异。
开篇故事背景的简介采用了“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1]129-130无聚焦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除此前7段文字之外,文中的一些环境描写、庄兵卫的家庭情况等也均为全知视角。这样全方位的叙事,“叙述者无所不知,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2]107,完整且直截了当地向读者补充了故事内容,并将作者的观点和理解传达给了读者。
森鸥外对于视角转换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自第8段引出重要人物庄兵卫后,作者暂时放弃了全知的观察角度,自然而然地切换到了庄兵卫的视觉角度,仅以这一人物的有限视角引导读者体验事件的发展,使得小说人物成为读者探索故事进展的唯一途径。这增强了读者的主观感受,却又不突兀,还暗暗设下了对喜助这一人物的悬念,让喜助的出现更加引人注目。在主人公喜助正式登场之后,随着叙述的需要,小说故事正式进入主题,此时单一的人物有限视角不足以有力地呈现喜助兄弟相依为命的画面,作者便以两人的问答形式不断改变聚焦者和视角。但在转变视角的过程中,叙述者仍然主要聚焦于庄兵卫。值得一提的是,回忆弟弟死去的场面时并未使用主要聚焦者庄兵卫的表述,用了喜助与弟弟这一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助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画面回放,“通过变动时态等手法使自己目前的视角与过去的经验视角相重合”[3]257,将弟弟艰难死去的画面展现在读者眼前,给人以跌宕起伏的冲击感。此后,故事再次回到庄兵卫的视角,直到最后的结尾处再次变为外视角。这种聚焦者和视角不停转变的多视点的转换式内聚焦的叙事方式,使得整个故事画面更为饱满、丰富、具有活力。作者在文中来去自如的视角转换正如一部流畅成熟的微型电影,镜头的切换与衔接浑然天成。
(二)视角转换带来的效应
没有视角的转换,即便读者获取到了信息,也无法明确地从中读出作者想要突出传达的思想。人物视角通过人物言行举止的描写带来直观的感受,有了代入感,读者便会深入体会人物的思想、作者的价值观,也更易接受。在必要时转换叙述者视角正如直路口的弯道路标,提醒读者、唤起读者、暗示读者去挖掘文中故事变化背后的真正原因和社会问题。
视角转换也带来了伦理效应的变化。从喜助的视角出发,街坊婆婆以及周围处理事务的人们对待安乐死执行者行为的看法便代表了社会众人的伦理看法。而以庄兵卫的视角来看,他对此问题的存疑,即使叙述者并未明确指明,但从真实作者森鸥外有着“医生”的身份、又有女儿的不幸遭遇以及多年的留学经历等方面考虑,不难猜测这似乎代表着森鸥外对于安乐死有着不同于众人的另一种伦理追求。对于主题“安乐死”相关的伦理问题,作者将视角与视角转换所带来的伦理效应有机融合,也将这一现实问题抛给了社会。
二、叙事进程的巧妙推进
(一)叙事结构技巧的融会贯通
小说将两条故事线融汇在了一起。从庄兵卫的角度来看,该小说情节按照从庄兵卫在船上见到喜助开始再到两人交流、喜助回忆这样的进程展开,喜助回忆这段插叙对于人物的塑造和刻画以及主题的揭示至关重要。若从第二条故事线喜助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喜助兄弟故事的开篇呈现的喜助已然是一个因杀害弟弟而获罪的罪犯的形象。这作为此故事的结局被作为一个悬念放置于最前,然后再引出喜助为何杀害弟弟(即导致此结局的主题“安乐死”)的故事。喜助兄弟这一故事的写作方式也可视作一种倒叙,是喜助的倒叙,这样一种“设置悬念→探因解疑→解疑明旨”的悬念式写法超出了简单直接的叙事开篇。若是换作从喜助和弟弟相依为命的生活写起,再到上高濑舟遇到庄兵卫,虽然对小说的主题并没有产生影响,却使读者丧失了对结局起因的探寻,没有悬念,索然无味。当然,结局前置确实也磨灭了读者对结局的期待,但其所带来的趣味性对情节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了本身。
(二)人物塑造的多元
文章中约有10段文字描写人物庄兵卫的心理活动,不仅在字里行间透露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性格,从中也反映出作者“注重人物内心活动、强调人物性格的一种认识倾向”[2]54的“心理型”人物观的叙事学观点。作者笔下的人物并不是“扁平”单一的,服从权威的庄兵卫也抱有新的反抗意识;哥俩兄弟情深却有离别的勇气;喜助生活困苦却不消沉自哀;押送犯人的解差也有柔软心肠……对于这些“圆形人物”的塑造,作者又交替使用了直接和间接的人物塑造法。小说对喜助不似寻常罪犯阿谀奉承等一系列姿态进行了直接叙述,又从语言、外貌、动作等多维度对不同人物形象进行了间接描写,最终使得人物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也利于向读者传达人性和生活的复杂与真实。
(三)场景描绘的反差
场景描绘是小说中讲述情节的一种戏剧性的表现手法。森鸥外在该作品中多用反差的叙事手法来描绘场景,以此突出主题意象。故事背景与京都这一繁华无比的首都息息相关,作者将故事设定在了京都,却不以京都兴旺发达的景象来开篇叙事,而以京都高濑川上满目疮痍的罪犯之船“高濑舟”为着手点,以如此黑暗、悲惨、不和谐的一面来打破京都看似繁华实则虚有其表的景象,意在让读者细品繁华旖旎之下的萧条冷肃,以反差渲染全文凄凉的氛围。小说中也明确介绍了故事的具体时间“宽政年间”。当时正值昌盛年代,作者笔下勾勒的却不是蓬勃生机,而是已然盛开的春日樱花随着夜幕钟声慢慢飘零的场景;春末夕阳风光正好,却因出现的犯人而失去了色彩,纷华靡丽之后江河日下、日暮穷途,不禁让人长吁短叹。此外,森欧外刻意添加了一段风平浪静只闻船头水声的描写,似乎也在冥冥之中暗示着背后的暗流涌动。作者这样的安排看似不经意,实则有意,作者意在通过反差把问题放大、使读者的感官敏锐化,提醒读者,同时让读者思考,引出光鲜亮丽的背后不为人知的沧桑与凄凉、社会动荡和当权者压迫下下层人民的生活困境。
三、叙事交流的实现
(一)叙事层次的交流
何志勇、张卫娣在《日本名著赏析》中指出:“小说《高濑舟》为我们揭示出两个令人深思的主题。实质上,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如果对原作稍作改动的话,《高濑舟》完全可以成为两篇微型小说。”[4]45的确,小说的两个主题似乎并无关联性,但若把“知足常乐”(即“庄兵卫遇喜助”的故事)这一框架层和“安乐死”(即“喜助兄弟”的故事)这一嵌入层之间的关联性独立开来,作者便无法使得框架层的庄兵卫借助嵌入层的喜助实现叙事效果。很明显,庄兵卫借喜助的“知足”来反思自身的“不知足”,借喜助与弟弟的故事反思自身以及社会对“安乐死”的看法,甚至引发读者对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以及社会问题的忧虑。实现庄兵卫的讲述目的也就能引发、改变或深化读者的认知进程。可以认为,作者实现了各层讲述者的叙事意图及叙事效果,这两个层次并不能分开而论。
(二)隐性进程中作者与读者的交流
文中多处放置了隐性进程。显性情节围绕庄兵卫的“不知足”展开,对其内心反应的描写则作为隐性进程隐隐透露出庄兵卫所代表的下级武士的自尊心。再者,显性情节上通过庄兵卫妻子的身份引出“士农工商时代的身份之差”,却又以庄兵卫的反权威意识这一隐性进程引出“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显性情节突出喜助坐牢却知足常乐让庄兵卫钦佩,而喜助头顶放出亮光——庄兵卫崇拜过头的隐性进程也透露出社会众人难以知足的病态。显性情节上描写富有人情爱的解差、满含兄弟情的喜助,又以爱无法改变身边人结局的隐性进程暗示残酷世界带来的压迫。通过显性情节与隐性进程的交汇不断引发读者的思考,实现了与读者的交流。对于“安乐死”“反权威”等现实问题,就最后庄兵卫人物的内心表现来看,显然隐含作者仍是迷茫的。因此,以上隐性进程需要读者站在真实作者的立场上,考虑其生平历程,如留学经历和“高官”的身份地位,才能体会隐含作者的这些选择性叙事中真实作者所无法明说的主题意义以及对社会的反讽性。
结语
森鸥外除了作品内容上的开创,其在叙事层面也有他的独创性。以往对于《高濑舟》主题、思想的探讨研究众多,却忽视了其在叙事学上的杰出成就。本文从叙事学的视角出发,分别从叙事视角、叙事进程、叙事交流层面对该小说进行了再次探讨,以新的叙事审美艺术进一步解析了小说背后的现实问题和价值问题,有助于弥补《高濑舟》叙事学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