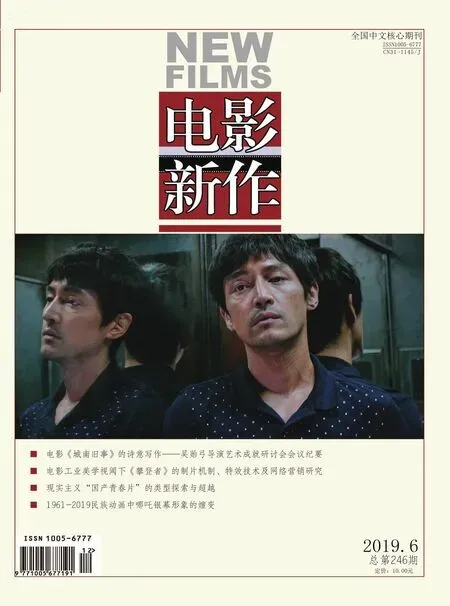1961-2019民族动画中哪吒银幕形象的嬗变
彭慧媛 李柯颖
中国动画电影鼻祖万籁鸣先生曾在《闲话卡通》中说“要使中国动画事业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必须在自己民族传统土壤里生根”。中国民族文化深厚的文化资本所孕育的民族风格在动画艺术领域大放异彩,自1941年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诞生之日起,民族动画创作者们就坚定着追寻和探索民族风格的文化自觉,不断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汲取力量。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中国动画学派为领军,确立了民族动画的美学范式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动画最杰出的成就——民族风格。
哪吒,作为中国神话故事中经典人物和民族文化符号,自出现以来,不断被文艺创作者进行民族化取用、创造,在多种样态的艺术化过程中承载着民族情感和价值认同。从1961年到2019年,我国文化语境、社会风貌经历了近60年的巨变,哪吒形象也以民族动画的形式为载体,相继经历1961年《大闹天宫》、1978年《哪吒闹海》、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三次典型的银幕演绎,呈现出视觉形象、叙事结构、价值诉求的差异性,代表着各自时代里中国动画的民族风格最高典范,折射出我国民族动画的审美特质和影像嬗变历程。
近年来国内动画电影相继出现《大鱼海棠》《大圣归来》等多个现象级热潮,2019年暑期爆款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下文简称为《魔童》),以近50亿元票房的成绩,成为中国最卖座本土原创动画,“国漫崛起”的赞誉不绝于耳。“叫好叫座”或多或少都能反映出观众对影视作品的文化需求和审美倾向,以及动画生产和工业水平取得了突破性成绩,然而反观这些影片,会发现他们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题材表面化、主题同质化、唯技术论,以及过度借鉴等弊端。在全球化和国内主流文化在恰当的历史路口,我们该如何开掘民族传统文化和神话题材的同时又葆有民族核心精神内涵,中国动画的民族性如何寻找创新的活力,成为亟待探索的时代课题。
一、哪吒银幕形象的演变历程
民族集体将对信仰与向往付诸于文学艺术的特定主体中,凝聚成民族精神的标志——神话,不同时代的艺术创作者和民间智慧共同创造着文化形态和集体想象,周而复始地在不同“讲述神话的年代”里重新呈现“神话讲述的年代”。梳理哪吒形象的演变首先要基于中国历代造神过程、宗教思想和民间力量的共同作用,经过传说、小说、戏曲、话本的通俗艺术形式演绎,哪吒形象由“哪吒护法神”形象日趋通俗化为“哪吒英雄神”形象。
哪吒的最早记载源自中亚佛教:“忽若忿怒哪吒,现三头六臂。忽若日面月面,放普摄慈光。”哪吒的佛教原型三头三眼六臂,威猛凶悍,作为护法神、夜叉神,辅佐毗沙门天王(李靖原型),忠诚卫护佛法,扫除邪恶,这一基本形象固定至北宋初期。南宋时期,人们将佛教故事进行了本土化重塑,哪吒成为毗沙门天王李靖之子,正神形象被广泛认定下来。明代“儒释道三家思想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也互相斗争。在这种形势下创造的哪吒神形象也有三教混一”的特点,此后明代的通俗小说、曲艺,以及后来的《封神演义》《西游记》基本形成了我们目前人们所熟知的哪吒儿童形象框架。有关哪吒的故事讲述,都必然要与原记载、此前版本进行比对,凝练和创造出新的形象与叙事特征,而时代文化语境决定了语义关系和改变,哪吒形象的再书写、再创造,显示了中国动画自己的独立品格。
(一)《大闹天宫》中的神勇战神形象
1961年这个时间点,属于十七年电影和“中国动画学派”兴盛的时期,万籁鸣导演领衔制作的《大闹天宫》是中国动画黄金年代里的集大成之作。影评家凯恩·拉斯金曾赞誉称“这部影片可以和《圣经》中的神话故事以及希腊民间传说相媲美,他们同样是充满了无穷的独创性、迷人的时间、英雄式的行为和卓越的妙趣,影片通过杰出的美术设计而成为一部拥有强烈感染力的作品”。
本片讲述孙悟空不满天庭招安,与天兵天将在花果山大战的故事,哪吒作为天庭派出的一名天神,与猴王斗法,哪吒的故事角色是执行神勇天将忠诚战斗的叙事功能,反面角色哪吒,造型脸谱化、性格单一化,用以衬托孙悟空的集猴性顽劣、人性善良、神性法力为一身的丰满形象。形象很大程度上依循了《西游记》原著第五十一回“额阔凝霞发髻髽。绣带舞风飞彩焰,锦袍映日放金花。环绦灼灼攀心镜,宝甲辉辉衬战靴”的描述,结合了民间艺术的传统美学元素,“三头六臂”“玉面娇容”“身小”的外在特点,年画里红肚兜、双发髻的胖娃娃样式,创造性地采用京剧白脸元素,三角眼略带阴狠,脚踏风火轮,手擒乾坤圈,突出“奋怒”“凶恶”的性格和勇猛刚强的“斗士”角色设定,通过精美的工笔画描绘,实现了神采奕奕、神勇无比的外形和个性的鲜明塑造,十分贴合人设内涵和叙事需求—天威强权的代表,孙悟空正义行为的反抗对象。
(二)《哪吒闹海》中的悲剧英雄形象
《哪吒闹海》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献礼影片,由严定宪总导演,王树忱编剧等动画界精英集体制作,在短短65分钟内施以浓墨重彩的宽银幕长篇动画。承袭了《大闹天宫》在工笔重彩美学技艺和高超的意境化处理手法,《哪吒闹海》整体风格灵动隽永,艺术性成就极高。
与前作取材不同,本片故事源自《封神演义》神魔小说体系,叙事核心集中在“哪吒”人物上,在审美倾向上更有“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道家美学意味。剑眉星目,正气凛然,灰白色长上衣,素褐色长裤,用自然简淡的笔触和大量留白的画面勾勒人物所处的环境,呈现天人合一审美意境。经改编后,哪吒成为反封建反黑恶势力的正义形象,红色飘带飘扬,手持乾坤圈的造型,十足的小英雄。完全脱离《大闹天宫》中的单一面貌,从面露凶相的“战神”,转变为血肉丰满的“人神”,宣告中国动画界重归传统文化。
2003年,中央电视台《哪吒传奇》系列动画片,可视为1978年《哪吒闹海》在电视剧中的延续,“少年英雄小哪吒”人物设定和正邪对立不变,塑造“我们的朋友小哪吒”的亲和形象,开启新时期哪吒的序曲,奠定此后一大批哪吒影视一轮轮的新讲述。
(三)《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魔童形象
新编的人物、完整的叙事、吸睛的特效、成功的营销,是《魔童》成功的四大要素。它的出现,打破了长久以来“孙悟空”“西游”IP在中国动画题材的垄断局面,启迪影视创作者向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传统文学里开掘新故事、新人物、新素材。
故事讲述“天地灵气孕育出一颗能量巨大的混元珠,元始天尊将混元珠提炼成灵珠和魔丸……太乙受命将灵珠托生于陈塘关李靖家的儿子哪吒身上,然而阴差阳错,灵珠和魔丸竟然被掉包。本应是灵珠英雄的哪吒却成了混世大魔王。调皮捣蛋顽劣不堪的哪吒却徒有一颗做英雄的心。然而面对众人对魔丸的误解和即将来临的天雷的降临……”串联起了哪吒亲情、友谊、自我追寻和反抗命运的故事。
人物形象塑造也伴随故事新编而颠覆。因循前作深入人心的“哪吒”人物基本元素:儿童身形、红肚兜、双发髻等相关符号之外,大胆创意“丑哪吒”形象,打造了一个黑眼圈、血盆大口,穿萝卜裤,双手插口袋的叛逆少年形象。充满现代感的台词,玩世不恭的表情姿态,颓丧的语调,恶作剧行为,都贴合“魔”“恶”的特点。随后在哪吒化身战神时又出现“三头六臂”的成人身形、超能力英雄形象,当回溯神话哪吒神形象时,既满足了观众的偏爱新鲜感的审美享受,又超出了观影期待,让人热血沸腾。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以上三部动画电影中的哪吒形象由民族风格突出、形式感强、脸谱化的神形象,转化为情感饱满、贴合时代诉求的英雄形象,到今天脱胎为一个当代少年与超级英雄混搭的魔童形象,哪吒形象和寓意从传统定义走向了更开阔的表达空间。
二、哪吒银幕形象的民族风格变迁
以1961年、1979年、2019年三部涉及哪吒的动画电影为代表,笔者将民族动画分为了以三个阶段:《大闹天宫》为代表的民族风格浓郁的美术片时代,《哪吒闹海》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动画风格的成熟时代,《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代表的多元融合的动画时代。中国动画也从民族风格的顶峰,逐渐步入全球化大众文化形态影响下的民族风格弱化和多样变革中,如今动画技术信息化更带来写实风格的提升,呈现动画产业在近20年低谷后的上升姿态。
(一)艺术手法:从传统美术到现代技术
早期国产动画电影人是一批优秀的中国美术继承人,他们不仅贡献出宝贵的艺术作品,更将对中国传统美学与诗意文化的理解全数灌注于创造,“美术片”正是在这样文化情怀中诞生。移植与运用中国传统美术工艺,如水墨、剪纸、蜡染、版画、皮影等,强调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化价值,传达独特的民族情感。而“动画”概念,是由钱家骏在1946年《关于动画及其学习方法》一文正式提出的,面对这种外来文化,中国动画先驱们尝试赋予其信达雅的文艺理想和民族内涵,为我所用,成为承载中华文化的新的艺术形式。
《大闹天宫》是当时耗资百万的大片投资,色彩瑰丽的工笔画卷,整体形式美强烈,突出中国传统艺术景物处理虚实结合的手法,呈现想象丰富的装饰性设计。万籁鸣团队历时四年,考察各地建筑、陶器、手工艺品,选用了如意头云纹样式,设计出变化莫测的云朵和中式楼兰亭阁;参考敦煌壁画,绘制了蟠桃园仙女衣裳轻盈浮动的状态,人物形象均稍做夸张变形;空间环境设计在鲜明的民族化意味中区别了花果山晴朗明净、天庭富丽堂皇两个不同空间。本片开创了动画音乐制作新的表现手法,即大胆采用了京剧、民乐、昆曲等形式配乐,“在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时则配以轻盈的乐器从而将人物内心世界的忐忑不安与情绪的复杂多变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同时鼓点节奏配合动作,用不同的音乐段落进行剧情转接,全片动画视听异彩纷呈。
《哪吒闹海》手工绘制七万幅珍贵水墨原画,同样运用了多样化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和民族元素,融合其中,并推陈出新,简化环境。强调人物而自然地写意抒情,最典型的是哪吒死前一幕,作一种超现实处理,小鹿在蓝色幕布里伴着琵琶声轻盈跳跃,哪吒泪眼与双手交替特写,线条柔软,水波似有若无,形成流动的视觉美感。哪吒出生,以轻快活泼的鼓点进行定场亮相,展示可爱的性格和灵活的形态。
前两部影片同为美术片范畴,在人物造型、景物造型、环境空间等传统美学元素上有很高的相似性,通过三维动画视听再造了“四项变化无穷之妙”的美妙幻境。意境美为观众留下无限想象空间,但也引发不同的审美想象,《大闹天宫》镜头语言强调“形”,夸张造型和设计构成强烈的舞台感,《哪吒闹海》则强调“神”,在“有”与“无”营造寂静空灵的情绪,镜头平缓移动犹如定点立足,目光远眺,符合中国画散点透视的创作方式和静观方式。
《封神演义》原著的一大精髓在于“奇观”,《魔童》作为首部IMAX国产动画电影,从视听设计、表意空间、镜头设计、观众参与度上与前两部作品有极大差异性。通过3D技术将该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现代感十足的奇观的堆砌、吸睛特效,都已经成为商业类型片的必要元素。山河社稷图的包罗万象的空间、万龙甲汇成时的美轮美奂,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通过技术具象为视听盛宴。科技发展带来了哪吒微微抖动的小肚子,龙王细腻流动的须髯和盘旋的躯体,细节写实更生动真实;皮克斯风格的电脑绘画、丰富的场景转换,太乙真人“七彩仙莲”指纹解锁、“指点江山笔”时空穿越等流行元素提高观影距离和代入感;在动作设计和景别选用上,相较于前两部,电影语言更明显,而民族化的美学特征远不如前。
此外在配乐上,必须提到《小刀会序曲》,自1962年推出以来,被诸多影视作品采用于高潮情节点的气势营造,从胡金铨《龙门客栈》到周星驰《大话西游》《功夫》,再到2015年《大圣归来》,音乐一旦出现,就能立即唤起观众对振奋的情感参与和热切认同。时至今日,对众所周知的曲调沿用仍是一种安全的燃情套路,更遗憾的是我们的影视作品配乐创作匮乏而保守,这么多年来竟然没有出现更多有新意的作品来被观众认可。
(二)叙事模式:从戏曲样板到美日模式
哪吒动画形象发展至今,美术片影像创意与传统叙事方式、情节程式化的艺术手法式微,而具有现代感的好莱坞经典三模式剧作结构、日本漫画情节模式成为全球通行的影视法则,对我国当前的动画作品有诸多影响。
1.叙事策略与人物塑造
《大闹天宫》采用中国传统的戏剧式结构,保留原作章回体小说形式,采用主动式单线性叙事方式,“叙事过程中常常以绘画性的平面镜头语言以生动的、声情并茂的对话图解文学故事,并辅以戏曲式的表演推动剧情发展,在叙事空间表现上呈现出绘画性、表现性、意境性等艺术美学特点,呈现出一种戏剧性空间”。《哪吒闹海》是经典改编案例,在故事上延续了哪吒相关人物关系图谱和“陈塘关-龙宫-天庭”的故事构架,将哪吒生性顽劣、恶意杀龙,改为:龙王欲求童男童女,危害百姓,哪吒为保护乡民才杀死敖丙,四海龙王布雨威胁索命,哪吒为救一方百姓,自刎谢罪,节节攀升的冲突,不断推动悲怆感提升。
在剧本结构上,将《封神演义》原著中的灵珠子设定,改为混元珠,从《哪吒闹海》的主角哪吒、反派敖丙,变成《魔童》“哪吒-敖丙”双雄结构,是对前两部最大的结构更新,是符合当前市场和受众观影偏好的选择。“在肉眼可见的双雄结构之下,哪吒-鸣人、敖丙-佐助、太乙-自来也、申公豹-大蛇丸、龙族-宇智波一族、陈塘关-木叶村……从人设、性格、背景设定以及最终对决,《魔童》与日本动漫《火影忍者》有着清晰的人物对应关系。”
其次,好莱坞经典三幕剧结构的成功运用促成了《魔童》的流畅叙事,同时符合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理论结构。第一幕,建制。通过交代陈塘关背景和混元珠来源,引出申公豹调换双珠,魔丸降生破坏力极强,将面临天劫,李靖求天尊解咒,哪吒作恶惹是生非被太乙真人带入山河社稷图,听信自己灵珠转世后拜师修行;第二幕,发展过程。修炼两年,逃出山河社稷图,擒拿海夜叉,解救女孩,与敖丙相识,却遭百姓误会,敖丙得知自身重任,诛杀哪吒才能建功立业拯救龙族,哪吒邀请敖丙赴宴,哪吒得知真实身份,并获得武器装备,解开乾坤圈咒语,大开杀戒;第三幕,解决问题。太乙真人控制哪吒威力,再次化身童身,得知命符。敖丙身份暴露,决定活埋陈塘关,冰火双方斗法,遭受天劫,哪吒敖丙共抗天劫,七色宝莲保住灵魂不灭,留住魂魄后完成救赎,被百姓认可。也有学者指出与日本动漫的燃魂四步结构也有相似之处,虽说中国起承转合与经典三幕剧结构有相似之处,运用经典的商业类型结构,可以快速获取受众欢迎的方式,但《魔童》无论是上述哪种叙事模式都大有借鉴、套用之嫌,且与中国民族化艺术创作方式相差甚远。
2、情节设置与借鉴问题
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依赖于角色表演动作、对话与台词,在美术片时代的显著民族特点表现为对传统戏曲、样板戏的程式化借鉴和使用,在时代气息中与动画影像贯通融汇。《魔童》存在着情节拼贴感和经典影视情节借用学习的问题。作者饺子,非科班出身的天才型动画创作者,他在前作感谢了手冢治虫、迪士尼等动漫名家,在大量学习和借鉴了日本漫画、欧美的优秀影视作品中吸取灵感、习得技巧,在此我们通过具体的文本细节梳理,观察对比情节设定的相似之处。

表1.《哪吒之魔童降世》与其他影视作品情节对比
影片大量使用港片搞笑桥段、动作设计、低俗笑料,通俗大众文化少有全新的风格,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也不可能有全新的影视创新,对日本动漫的模仿导致了相似度高,本土原创性不足,没有新意,虽然在技术上有所提升,但对动画民族性的理解、继承、结构、立意上还很空缺。
(三)文化价值:保守-开放-回归
民族动画的文化价值通过具有强烈民族性特征和内涵来建构,从神话故事中提炼出稳定明确的人物精神内核,在时代环境中勾勒切合文化大众化思潮的故事主题。现代社会已与神话讲述的时代大不相同,在哪吒动画的改编进程中,主题深度从深刻悲壮到浅显大众化,神话象征意义的功能性已经转变为电影叙事的符号功能,哪吒故事原初的文化价值在银幕演绎中已经大大改变。
1.原型反叛的消解
我们讨论从神话取材时,是在认可所选取人物以及他的核心精神,两者合一的前提下进行的。在传统神话中哪吒精神核心是“反叛精神”,与之密切相连的行动集中用强烈的“自我伤害”的情节作为反叛的能指。《封神演义》中的“刮骨还父”,《哪吒闹海》中的“举剑自刎”,而《魔童》中对自我伤害只是撕去命符纸条,哪吒反抗力度逐渐缩减,不只是儒家文化孝道对其的改造,也是顺应时代文化品格的调适。
《哪吒闹海》中的哪吒,发展至今天已经成为流行文化中一个反叛精神的符号。它在片中的反叛表述有三个步骤:第一,把龙王从无辜受害改成吃人的大反派,给予哪吒大闹龙宫的行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正义动机。第二,删减了哪吒的作恶段落,从邪恶的反骨者变成正气凛然的反叛者,增加了大众对哪吒的接受度。第三,将神魔小说中“刮骨还父”以“举剑自刎”的形式替代,自杀前“程式化”系列动作,极力渲染了对抗的决心和绝望感。那是在特殊变革时代里,人们需要英雄,来寄托革陈除旧、热血牺牲的精神和决心,成为人们心中独特的记忆。
《魔童》中的哪吒,将“自刎”改成“撕纸条”这样的温柔处理,意指“哪吒自杀”,把以往的大悲化解掉,把自残、弑父,改写为父与子换命符、撕命符的相互牺牲,将“反面角色”消解为“正邪合一”,把此前抗争对象由具象化的“父”“恶”转变为抽象化的“命运”和“自我”。纵然叙事流畅、人物出彩,但失去了反骨的哪吒还是真哪吒吗?而哪吒的矛盾过早通过内在“爱”化解,总是处于问题被解决的局面中,被“天劫”“父爱”所推动的,同时,哪吒和敖丙的动机不强,转变太快,也造成反叛也不够彻底,最后的大团圆结局更趋近于主旋律和谐的价值观,片尾处已经丢失了片头所谈的“不信命”的议题。
2.宏大母题的日常化
伦理关系,这个宏大母题伴随着哪吒故事的变迁,哪吒父子关系的文本溯源,有几个重要环节。宋代慧洪《禅林僧宝传》记载问“哪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化身于莲花之上,为父母说法,未审如何是太子身”。《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在此前通俗文艺形式的基础上明确了哪吒“投胎童身”“怒杀龙王”“杀石矶子”“析骨析肉”“莲花化身”“天帅之领袖”的重要设定, 但“剔骨还父,割肉还母”之举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中国儒家孝悌思想大相违背。将道家的舍生取义,以及儒家孝文化融入对佛教的本土化改造,融入繁荣开放的文艺创作中,于是明后期,《封神演义》增加了“父子和解”,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哪吒动画中父子关系的文学发源。
哪吒作为反权威的图腾,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反对父权。在动画世界中这个父权不仅仅是李靖本身,还被引向了更多的表意中——“天命”。1979年版与2019年版,都提到这个词,正是两部影片的叙事驱动核心。
《哪吒闹海》的天命理解为“权威”,当兴风作浪的龙王发难时,李靖只敢屈服于上级天神,并指责儿子的正义行径,在君臣等级和骨肉至亲之间说出了“天命难违啊”,懦弱的他继续担当一个秩序维护者。当哪吒大喊“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抒发一种对父辈的绝望的时代情绪。正如蒋勋评价哪吒“这个角色在过去饱受争议,大家不敢讨论他,因为在百善孝为先的前提之下,他是一个孤独的出走者”。哪吒自刎的方式表达对“子道”的反叛,但这种叛逆一定是在主流文化框架以内的,莲花化身后重获新生,也重拾了亲情。
《魔童》成功将我们时代的情感融入神话新编的过程。哪吒的口号:“我命由我不由天”,“天”成了一种抽象的压力,现代人的情感呼喊。基于“我命”的自我问询,我是谁,是魔丸还是灵珠。缺席的长辈是现代家庭关系疏离的写照,留守儿童哪吒被禁闭在家、社会偏见、孤独成长这些来自现实主义的境况,让年轻观众产生代入感,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是陈塘关的百姓,而我们都是哪吒。《风语咒》《大圣归来》《魁拔》等,均与《魔童》“我命由我不由天”有类似的议题,2000年的《悟空传》喊出“逆天改命”,《魁拔》也有“只要还活着,就绝不认输”的台词。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和伦理关系被重构,宿命反叛者经历自我追求后,家庭与社会认同是最好的归属,成为这个时代的共同话题。
此外,创作表达不足导致了主题模糊、浅显。前半篇幅提出了“逆天”的大议题,但前面铺垫娱乐性太多,不足以撑起如此厚重的议题,难以表达反抗的悲怆感,甚至在打斗戏中穿插笑点桥段,他们再次进入山河社稷图,被捆绑在一起却用低俗“屎尿屁”梗,让前面蓄积起来的壮阔激烈顿时消散,不断破坏了命运的节奏,紧接着通过煽情点转而变为父子和解的温情,彻底地转移了故事的核心矛盾。影片前后的表达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力量去抵达初衷“逆天”的大议题,唯有落脚在亲情、友谊,并以此化解矛盾来收尾。
三、哪吒形象嬗变的反思
哪吒形象的演绎有着复杂性与多义性,这三个时期的哪吒文本形成一种跨时代互文,形象上的差异也昭示出政治话语、文化逻辑、产业等多方面的因素纠葛。《铁扇公主》用带有迪士尼模仿痕迹的形式,呼喊反抗侵略的号召,成就自己民族的一套独立语言。20世纪50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提出“走民族风格之路”的口号,探索民族动画创作之路,万氏兄弟提供了独立于好莱坞之外的另一种动画创作的可能性,中国动画民族化是时代规律的必然要求。
80年代改革开放后,大批优秀国内动画人加入了日本、美国的动画代工厂,造成本土动画行业的人才流失;追求经济发展的追逐中,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发展缓慢,美术、动画教育匮乏,从社会历史情况上局限了动画发展。如今《魔童》所张扬的“燃”文化——并不属于中华文明的精神范畴,而是一种现代人对激情、速度、强烈感的呐喊,那不是中华民族精神原有的、根源性的民族性格。当一个个取材于传统文化的人物精神流失后,套用“舶来”的叙事方式、精神内涵,源头故事和形象的符号就成为变异物,民族性淡化、幼齿化、低俗、借鉴痕迹明显,是中国动画在今天的缺点,对此我做出以下思考。
第一,尊重民族文化,正确地从民族文化中取材,开掘传统故事题材是最优路径。“我们不得不面临因习以为常而常常忽略的两个危机:在借取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化的过程中如何避免电影性和当代性的失落。这意味着首先,对神话等文化资源的挪用、改造和创造,需遵循电影叙事的内在法则,造型、人物、意象、仪式、情节、故事等叙事要素的选择必须遵循电影叙事的特殊性;其次,电影的立意和价值传达需充分注意神话等传统文化资源的移位置换功能,投射出精神价值充沛的当代品格或超越性内涵,切实改变该类型浅表化、符号化、技术化的当下创作状况。归根结底,如何利用神话、传说等民间资源对神怪片进行组合创意,是该类型获得良性创作土壤,成为具有无限潜能的可持续发展的国产优势类型电影的关键。”传承独特民族艺术风格,用东方美学的表达方式与当下的动画电影技术结合,开发传统艺术,比如水墨画、皮影等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寻找在当今可以相互契合的技术呈现方式。
第二, 理性面对国外动画的影响,合理借鉴。广泛学习借鉴是没有错的,它是成长的必经过程,只有当我们珍惜宝贵的文化资源,从古代典籍、现当代优秀文学里吸取养分,寻求到自己的特色,吸取精华,辩证地借鉴,将各国动画优势容纳到中国文化体系内,民族文化的根源才不会断绝。假借他人的模式和风格,不是长久之计,在阶段性的进步和发展局限中,是有效果的,借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本民族的动画产业和文化趣味是否合适那些已经卖座、已经被接受的模型,是否可以再进一步突破,突破可以到什么程度。
第三,寻找突破口,提升动画产业原创动力。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计划经济年代,没有市场压力,精工细作投入巨资,不计回收的《大闹天宫》时代绝无仅有。中国当前的动画市场同时存在着产业分散和文化内涵浅薄的困境。打造优质IP,以“封神宇宙”系列动画的开发为突破口,鼓舞中国动画业向传统民族文化找出路,将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四,深挖民族心理,引导和培养受众观影。国漫复兴,既是口号,也是我们中国影迷和动画迷的期望。受众与创作者都出于同样对本民族文化和艺术的热爱为每一部优秀国产动画喝彩。民族情感和文化自信心,必须经由我们自己去独立思考、独立发展,中式审美与当代思想文化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国民族动画与传统文化交融、与市场接洽、与观众对话,希望看到中国动画真正崛起,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热情所在。
少数影片的成功爆红,远不足以扭转整个行业的现状,中国动画面对着丰沛民族文化资源和有限的动画发展局面,如何将传统文化与动画艺术交融,用中国人自己的影视语言和特色去影响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是目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