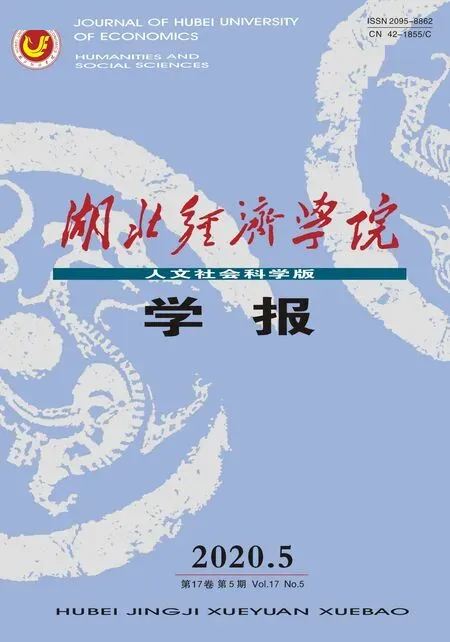《一九八四》汉译比较研究
——以董乐山与刘绍铭译本为例
周宝航(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一、引言
《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four)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长篇政治著作,于1949 年由塞克尔和沃伯格公司(Secker & Warburg Company)出版。乔治·奥威尔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出过多本著作,他曾写过多本小说、文章和评论文章,被誉为最具重要并且具有影响力的作者之一。小说通过对未来预言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假想的极权社会,表达出浓厚的政治寓言气息,体现了对极权社会淋漓尽致的讽刺。
起初,《一九八四》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并不顺畅,其直到1979 年才首次在《国外作品选译》刊登,发行形式还为“内部发行”,仅有少数人可阅读。到1988 年,花城出版社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一九八四》才得以公开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作为《一九八四》的首个中文译本,董乐山翻译的《一九八四》一经发行,便带给中国读者以思想的震撼和心灵的启迪。《一九八四》是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影响了包括王小波在内的一批中国青年作家,其还在2008 年入选“改革开放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 本书”,但关于这样一部作品,其译界的研究成果却比较薄弱,对其研究还比较欠缺,这与其在文学、思想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译者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核心”,在翻译的“文化转向”中,译者作为翻译中文化内容的解读者和翻译文本改写的操纵者,获得了翻译学者和专家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翻译研究在不知不觉间实现了从“语言”到“文化”再到“译者”的研究转变。《一九八四》自董乐山首次引进中国后,广受好评,其译本也获的了广东地区的优秀翻译奖,董乐山因此收获了名誉与认可,也为其之后的翻译实践打下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九八四》在中国的译本逐渐增多,在全国各地甚至出现了近十部译本。本文选取《一九八四》董乐山的大陆译本与刘绍铭的台湾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在译者主体性视角下译者对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选择的主动性与能动性。
二、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长期以来,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语言层面的探讨,从“语文学”时期强调以美学为基础的译论,到“结构主义”重视语言学基础的翻译研究,再到后来“后结构主义”提出的“多元系统学说”和“翻译的文化转向”,译界对于翻译的研究逐渐从忠实原文转到重视语用功能和宏观的语境,对译者的主导行为有了更多的重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视野逐渐转向翻译研究的交际功能,关注翻译的媒介作用。对翻译的研究逐渐超出语言的范畴,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其中还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与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有时因为译者的误读,甚至产生文化的缺省与补偿,造成文化的错误传达(王东风)。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译者作为翻译中文化解读与改写的操纵者,获得了翻译研究更多的关注。译学研究悄悄实现了从语言——文化——译者的研究转变,实现了由本体到主体,又一元到多元的跨越(袁莉,2002:398)。译者的身份也逐渐从幕后的隐形,到走向舞台的显性,译者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肯定。
英国著名学者兼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改写理论(Adaptation Theory)提出“操纵”着译者价值取向的几种因素,包括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虽然该理论对翻译文化和文学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用这种“历史文化决定论”来描述翻译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译者的主体作用。作为某个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翻译者,译者的行为既是“自律的,也是他律的”。对于主体文化的翻译规范,译者不仅有“被操纵”的一面,即翻译为了帮助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与认可,接受并遵守主体文化的“规范性”;与此同时,其还有“操纵”的一面,即译者“叛逆”的创造性翻译,自觉地改造目标语言文化的行为。
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所进行的翻译活动需要尊重原作作者,然而译者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为实现某种翻译目的,有时也会表现出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即我们常说的译者主体性(查明建、田雨22)。译者主体性表现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展现出的翻译策略的独特性和个体性(刘军平53),其还表现为一种主观的能动性,即一种自觉的创造意识(许钧120)。译者主体性的建构,集规范性与主体性于一体,是一个辨证的过程。翻译也不是单纯、单调的语符之间的互换,其是一种复杂的融合着译者自身的情感、审美和经历的艺术生成物(朱献珑、屠国元a 108)。
译者不仅是原作作品的鉴赏主体,其还是译文文本的创作主体。译者对于原文的理解和译文中所使用的语言措辞、方式表达决定着译作的面貌,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具有其自身的创造性的特征(张迎春xii)。译者的翻译风格和翻译策略受制其所处时代翻译思潮的影响,之外,其还受自身的个性、情感、人生经历和人生追求的制约,这种翻译个性和翻译的主体性常常表现为译者译前关于文本的选材和翻译过程中译者翻译策略和风格的决定(朱献珑、屠国元b 124)。
译者的主体性是指在尊重客观翻译的基本前提下,在充分认识和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的文化需求下,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结合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知识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主观能动性。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因此,译者为了满足特定的翻译目的或者翻译群体的需求,必须要尊重原作然后进行再创作。因此译者也是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群体。译者的主体性具有主管能动性、受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的特征。
三、翻译文本选择的主体性
《一九八四》首个译本的译者是董乐山,其于1924 年生于浙江省宁波市,董乐山是新中国最重要的翻译家、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和作家之一。他学识(博、译著丰硕,共翻译文学、政治、历史、文化、新闻、社会等方面的作品20 余部,总字数超过400 万字,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翻译作品有《一九八四》(独译)、《西行漫记》(独译)和《第三帝国的兴亡》(合译)等。可以说,董乐山在翻译领域中取得了很多成就,译界也称其为“翻译家中的翻译家”。
原作《一九八四》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创作的长篇政治讽刺小说,讽刺的是极权统治,其书于1949 年由塞克尔和沃伯格公司(Secker & Warburg Company)出版。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刻画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社会,在他笔下的世界,人们没有自己的情感,人性被扼杀,自由被剥夺,思想受到严酷钳制,人们的情感只剩下对“老大哥”的热爱和对敌人的憎恶。人们的生活异常艰难,特别是对于下层阶级的人们来说,生活整日就是浑浑噩噩,毫无新意,只能挣扎于生存线。这部小说与英国作家赫胥黎的著作《美丽新世界》以及俄国作家札米亚京的著作《我们》并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
《一九八四》问世30 年后,在1979 年才以“内部发行”形式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首次以中文的形式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其译者董乐山选择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译成中文,是由于自身对于日本和德国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的右翼极权主义的极度痛恨(陈勇105)。董乐山对于作品翻译的选择有较大的主观能动性,翻译的很多任务都是由他自己选择。而董乐山选择翻译《一九八四》,还体现出其对作者奥威尔的崇敬和认同,他们都是忠实的社会主义者,并将本职工作视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冯翔92)。
《一九八四》的另一个译者刘绍铭(LAU Shiu-ming, Joseph)于1934 年生于香港,刘绍铭自幼因父亲患肺癌突然离世,为帮贫困的家境分担经济压力,小学没读完就去该校的印刷所当学徒,后来又转到香港荷里活道的民生书局当售货员。刘绍铭在业余时间自学中文和英语,之后于1955 年入读北角达智英文专科学校,翌年参加香港中学会考取得及格成绩,后被台湾大学外文系录取,至1960 年毕业。刘绍铭就读台湾大学期间与台大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历程。1966 年,刘绍铭取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然后开始任教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知名大学。刘绍铭学贯中西,著作颇丰,尤其擅长中西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其行文舒徐,语言富有幽默感,位列香港散文五大家之一。
刘绍铭翻译《一九八四》时,正是在1984 年。介绍这本书给刘绍铭的人,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夏济安。在台湾大学读书期间,夏济安老师告诫他要多读书,并且对于一些书,不仅要自己阅读,而且还要传播给其他的人。那一年,刘绍铭还受香港《信报》林山木(作家、媒体人林行止)之邀,每天在《信报》上连载两千字。在老师推荐和朋友邀请的情况下,刘绍铭开始了《一九八四》的翻译工作,并在译后感慨道:《一九八四》是改变自己一生的著作(刘绍铭 135)。因为刘绍铭的处于多种文化背景下,他对于小说《一九八四》也有诸多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因此,他更希望用自己的理解将文本翻译出来,他希望人们都能够通过这本书意识到自由和权力,因此,他对于这本书的翻译风格可能会更加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四、翻译策略选择的主体性
从文章的整体语言风格上来看,董乐山翻译的版本更加忠实原文,无论是语句的使用还是词语表达上,都跟原文十分贴合。刘绍铭的翻译版本则添加了更多的译者本身对于文本的理解,语言表达也更加直白,更加符合中国人的话语习惯。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董乐山的翻译标准非常简单并且实用,他更注重译者对源语言,也就是原文的理解,认为只有透彻理解原文,才可以找到恰当的中文表达。由于历史语境的原因,董乐山所处的时代正是“信、达、雅”翻译标准普遍推崇的时代,所以那一时期的翻译更加强调对原文的忠实,而较少有译者对于作品感受的创造性翻译。譬如:在“Eastasia, smaller than the others and with a less definite western frontier, compromises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to the south of it, the Japanese islands and a large but fluctuating portion of Manchuria, Mongolia and Tibet.(Orwell 193)”中,董乐山直译“Manchuria, Mongolia and Tibet”为“满洲、蒙古、西藏大部(153)”,其译文忠实于原文,并没有过多的删减或改译。而刘绍铭则将其笼统译为“中国”,淡化了小说的政治因素,避免了因为复杂的历史政治原因而去解释“满洲”等敏感政治地名,便利了译文读者的阅读;但“Manchuria, Mongolia and Tibet”并不代表中国全境,将其笼统称为“中国”会有些地理方位的指代不明,使其表达不够明确。
在对于原文的忠实度上,可以从两位学者对于数字的翻译中也可以看出差别。例如,“6079 Smith W!Hands out of pockets in the cells!”(Orwell 226),董乐山也是采取直译的方法,翻译成“6079 号史密斯!在牢房里不许把手插入口袋!”(206),而刘绍铭则翻译成“六零七九号史密斯!手不许插在口袋里!”(216),对于人物的号码的翻译,董乐山直接按照原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法,而刘绍铭用中文大写的方法,首先,在中文中,按照中文的数字表达更有一种正式感。其次,人物的号码被喊叫的时候,更像是一个犯人,作者也更加希望传达出一种当时人物如同犯人一样的处境。
这种对于翻译的忠实度上,也体现在董乐山和刘绍铭对于词语和句型结构的选择性翻译上。董乐山更加希望传达出文本的原汁原味,但是刘绍铭更贴合于中国人对于词语的使用和句型的日常用法。譬如,在“Well, perhaps not exactly that. But from your general appearance–merely because you’re young and fresh and healthy, you understand–I thought that probably„”(Orwell 121)中,董乐山直译为“嗳,也许不完全这么想,但是从你的外表来看,你知道,就只是因为你又年轻,又肉感,又健康,我想,也许„„”(109).刘绍铭则翻译成“也差不多了,你站在我的立场看看。你的外貌、一举一动—就说你的青春、健康、活泼这些特质好了—都使我不禁想到你可能-”(115)。在这里原文是一段对话,董乐山非常直白地按照原文翻译,甚至连语气词都翻译出来。对于插入语的表达,原文的表达其实在中文中非常少见,因为这并不符合中国的传统口语表达习惯。因此刘绍铭则将原文的插入语,例如“But from your general appearance”以及“I thought that probably”直接换了语句表达的顺序,使之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口语说话习惯,以及补充指出了更多信息。而对于词语的翻译选择上,对于“young and fresh and healthy”的处理方法,二者也是有很大差距的。刘绍铭的“青春、健康、活泼”表达的更加隐晦,而董乐山的“又年轻,又肉感,又健康”则相对表达比较直白,这个也是受译者个人的主体性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翻译风格的选择。
在文章句式的语气表达上,两位译者也表现出了对文本不同的理解,根据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给出了不同的翻译。例如,对于“In front of him was an enemy who was trying to kill him: in front of him, also, was a human creature, in pain and perhaps with a broken bone.”(Orwell 105)。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第二部分的开头,两人第一次遇到的场景,彼此怀疑;董乐山对于这句话是这样处理的:“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要想杀害他的敌人,然后也是以一个受伤的,也许骨折的人”(95),而刘绍铭的翻译则大大不同:“站在他面前的不正是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敌人吗?另一方面,她也是人哪,忍受着痛苦的折磨,说不定骨头已经断了”(101)。刘绍铭的翻译加入了语气强烈的反问句,尝试表达出当时社会形势下彼此对立的紧张局势,而且用“她也是人哪”传达原文对于“human creature”的使用。在这一点上,刘绍铭对于文本的处理更加细腻,并且语气词的使用,也更加直白。
对于外来名词翻译的问题上,董乐山把外来名词的翻译和解释区分开来,认为翻译是用一个或几个词进行的对等和转换,而用几句相关的话尝试把意思简明说清楚的是解释(董乐山 286)。譬如:在“Between the frontiers of the super-states, and not permanently in the possession of any of them, there lies a rough quadrilateral with its corners at Tangier, Brazzaville, Darwin and Hong Kong, containing within it about a fifth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earth (Orwell 195)”中,董乐山直译“Tangier, Brazzaville, Darwin and Hong Kong”为“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和香港(154)”。而刘绍铭的译文则多有自身对于原文的理解与解释,在此句中,刘绍铭增加了四个地名的所在的国家,将其译为“摩洛哥的丹吉尔、刚果的布拉柴维尔、澳洲的达尔文和南中国的香港(177)”,对一些不太了解这些城市的读者而言,这种译法便利了他们定位这些城市的地理位置。
再如原文中的一句反复出现的话“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Orwell 1)”,董乐山将其直译为“老大哥在看着你”(3),“看”是多音字,不同的读音力道完全不同,其同时具有注视、凝视、看守和看管的意思,甚至还有照看和偷窥的含义。结合原文语境,我们可以发现“老大哥”的“看”更多为“看守”和“监管”的意思,所以刘绍铭的译文“老大哥在看管着你(3)”更精确一些。
在翻译拟声词时,为了再现原文形象生动的描写,董乐山选择保留原文表达和加注释相结合的翻译方法,以使其更符合情景语境和读者的审美期待。譬如:在“rhythmical chant of “B-B!„„B-B!”- over and over again, very slowly, with a long pause between the first “B”and the second(Orwell 17)”中,董乐山保留了“B-B!„„BB!.”的表达,通过加注释的方式解释这句的意思,其译文为“B-B!„„B-B!(注释)他们叫得很慢,在第一个B和第二个B 之间停顿很久(B 为英语‘老大哥’Big Brother两字的第一个字母)(14)。”刘绍铭同样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选择归化策略,以使拟声词的表达更加地道和自然。刘绍铭把“Big Brother”译为“老大哥”,而把“B”译为“老大”,其译文为“‘老大哥!老大哥!„„老大哥!’„„先念‘老大’,然后顿了顿,再叫‘哥——’(16)。”
历史语境对于译者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受特定时期翻译思潮的影响,还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譬如:在“La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re were the totalitarians, as they were called. There were the German Nazis and the Russian Communists (Orwell 265)”中,董乐山将“the German Nazis and the Russian Communists”译为“德国的纳粹分子和俄国的共党分子(210)”。需要提及的是,董乐山翻译时期,中苏关系正处于紧张阶段,所以董乐山将俄国共产党与德国纳粹党统称为“分子”,给人一种不好的联想。而刘绍铭的翻译相对比较客观,将其直译为“德国的纳粹党和俄国的共产党”(241)。
受历史语境及所处时代翻译思潮的影响,董乐山的翻译方式相对保守,着重于保持与原文内容一致,但在某些字词的翻译上,却也富于创造力,相对灵活,注重追求译文的文学美感及流畅。譬如:在“There was bribery, favouritism, and racketeering of every kind, there was homosexuality and prostitution, there was even illicit alcohol distilled from potatoes(Orwell 237)”中,董乐山将“homosexuality”“prostitution”译为“玩弄男色”“出卖女色”。又如在“an imaginary world beyond the grave(Orwell 211)”中,董乐山将其译为“冥界”。在古希腊神话中,冥界为人死后的去处,与人界和神界共同组成希腊神话的世界。冥界中除了本来的神之外,一些人类特别是一些英雄死后也成为冥界特殊的存在。与译为“坟墓外面的想象世界”相比,译为“冥界”更加符合目标语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
对于原作中的偏口语表达和粗俗语等极具特色的文体形式,董乐山尊重原作,选择相对应的口语表达,尽可能地再现话语的语境与情景。譬如:在“He confessed that he was a religious believer, an admirer of capitalism, and a sexual pervert(Orwell 253)”中,董乐山将“a sexual pervert”译为“老色鬼”,其语言表达不仅准确忠实,而且偏口语、接地气,符合说话人的话语习惯。刘绍铭的译文“在性行为上有堕落嗜好的人”则显得略有生硬,颇有些学术解释的味道。又如在“We didn’t have these bleeding litres when I was a young man(Orwell 91)”中,原文中的老人用词比较粗俗,语气粗鲁,董乐山将其译为“我年轻的时候可不用他妈的公升(72)。”表达出老人的不满与不耐烦;而刘绍铭的译文“什么一升半升,我们年轻时没听说过这种鬼东西(83),”语气则平缓许多,没能表达出老人的抱怨与粗鲁。
因此,在文本翻译的忠实度上,董乐山和刘绍铭对于 文本有各自的理解,无论是词语和句型结构上,通篇的翻译风格都大相径庭。而对于外来语名词的选择上,更体现了两位译者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对于文本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政治背景毋庸置疑也对文本翻译有很大的影响。至于文本中的其他翻译,例如数字翻译和拟声词的翻译等等,更是译者各自不同主体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选择性翻译。
五、结语
董乐山主动顺应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翻译思潮,翻译以异化为主,但又兼顾归化,其语言质朴、流畅,而且更为口语化,力求对原文的忠实。董乐山译作中体现出的翻译风格对我国翻译文风从欧化到中国化的转化有示范作用。刘绍铭翻译《一九八四》比董乐山稍晚一些,其翻译方式相对灵活,更注重译文的文学美感和幽默感。开展译者主体性视角下董乐山、刘绍铭《一九八四》的翻译研究,我们发现两位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翻译风格的“操纵”不仅取决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读者需求,而且还取决于其个人因素。译者是翻译过程的操作者,是翻译的主体,译者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翻译思想必然对其翻译有所影响,而译文则是译者翻译过程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