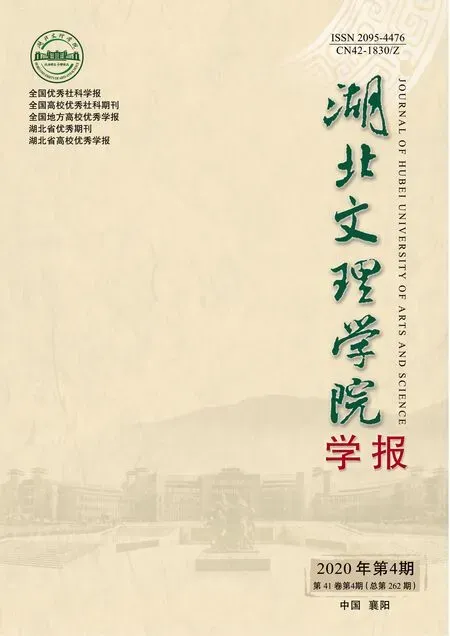重庆、湖北三国文化遗存调查及相关问题探讨
郭的非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四川 成都 610041)
2018年11月10日至12月17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全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组对重庆、湖北的部分地区三国文化遗存进行了为期近40天的调查工作。主要涉及区域包括重庆渝中区、北碚区、彭水县、长寿区、忠县、万州区、云阳县、奉节县;湖北恩施(巴东县、恩施市)、宜昌(猇亭区、点军区、宜都市、西陵区、夷陵区、远安县、当阳市、枝江市)、荆州(荆州区、沙市市、公安县、石首市、监利县、洪湖市)、荆门(掇刀区、东宝区、钟祥市、京山市、沙洋县)、襄阳(宜城市、保康县、谷城县)、十堰(张湾区、武当山风景区)。
本次调查为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项目组成部分,是在前期完成云、贵、川、甘、陕五省调查的基础上,对重庆、湖北两地三国文化遗存调查的第一期工作,旨在摸清调查涉及区域三国文化遗存分布及保存情况,以期深入研究。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调查涉及区域三国文化遗存相关发现
本次调查共记录点位95处(1)详细调查报告尚在整理之中,本文选取较有代表性点位举要分述。,现举要分述如下:
(一)墓葬
调查涉及区域内明确为三国时期的墓葬较少,较有代表性的有彭水山谷公园蜀汉墓群、忠县将军村墓群、忠县涂井崖墓等。
山谷公园蜀汉墓群,位于重庆市彭水县山谷公园内,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现两座砖室墓,据公园管理人员讲述出土有陶罐、陶俑等器物,保存情况较差。关于其墓主,民间传说十分丰富,传其为庞宏、长孙无忌、黄庭坚以及当地某状元的都有。当地文物部门将其初步定为蜀汉时期墓葬(2)此结论为彭水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杜继臣口述,尚无发掘简报。。
忠县将军村墓群,位于重庆市忠县乌杨镇将军村,由10个墓地组成,共发现汉至六朝时期墓葬257座。其中,枞树包墓地被认为是三国蜀汉大将严颜的家族墓地[1]。于该墓地发现的大型石阙构件,复原后被命名为“乌杨阙”,现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有研究认为乌杨阙可能是东汉末至蜀汉时期石阙,为严氏家族墓地的墓阙(3)此结论来源于李大地、邹后曦、曾艳《重庆市忠县乌杨阙的初步认识》一文(《四川文物》2012年4期),但尚存争议,罗二虎《重庆忠县汉代乌杨阙再研究》一文(《考古》2016年8期)认为乌杨阙年代应为东汉中期偏晚。。
忠县涂井崖墓,位于重庆市忠县涂井溪,共发现墓葬15座。墓葬形制包括崖墓常见的单室、双室和多室,出土器物近3600件,其中铜钱3000多枚,并以蜀汉钱币最多。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排比,报告将这批墓葬年代定为东汉末至蜀汉时期(4)此结论来源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简报(《文物》1985年7期),尚存争议,钟治、韦正《忠县涂井崖墓的时代及相关问题》一文(《东南文化》2008年3期)根据墓葬结构、建造方式、随葬品排比、时代背景以及地方墓葬特色延续性等方面,认为该墓群年代应为蜀汉至六朝早期。。
此外,重庆各区县还发现大量年代被定为东汉至南朝的崖墓。如此大的年代跨度,一方面由于崖墓这种墓葬形式开凿时间长、多家族合葬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已有明确年代为蜀汉时期的墓葬过少,可比对材料不多,不免存在蜀汉墓葬无法被区分出来的情况。
调查中还发现,湖北宜昌、荆门、荆州等三国文化名城,其地市级博物馆在其地方历史文化陈列中,也均没有专门的三国时期陈列。经访问后得知,这些地方的相关专业人员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将三国时期的文物从东汉至六朝的体系中独立出来,缺乏一定的标准,亦具有相当的难度。
(二)纪念性建筑
1.墓葬这一类墓葬与前所述诸墓葬有明显区别,基本未经考古发掘,甚至现已无法分辨出较明显的遗迹现象,多是根据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配合名人故里建设而打造的纪念性建筑,冠以墓葬之名。较有代表性的有关陵、甘宁衣冠冢、刘璋墓等。
关陵,位于宜昌市当阳市关陵路,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关羽之墓,民间素有“头枕洛阳、身卧当阳”的说法。当阳关陵建有陵墓、寝殿、正殿、拜殿、神道、碑亭、钟楼、佛堂等一系列陵墓设施,每年举行祭祀大典和庙会,影响非常广泛,是这一类纪念性建筑中最为成熟的代表。
甘宁衣冠冢,位于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甘宁村,其衣冠冢现已无迹可寻,只能通过当地老一辈知情人描述找到大致方位。当地致力于打造甘宁故里,至今还能走访获知不少关于甘宁在当地的故事传说,可见其影响力。在甘宁镇万州大瀑布景区内,还有为配合景区打造而建的甘宁像和甘宁墓。
刘璋墓,位于荆州市公安县章庄镇荆红村。该区域的地势平坦,此墓为一土台,未发现明显遗迹现象,“刘璋墓”之名为当地百姓所传。受此影响下,当地至今留下一特别习俗,逢丧葬之事,无论死者生前姓氏,墓碑上均冠以刘姓。
2.祠庙三国人物的纪念祠庙是本区域三国文化遗存数目最多一类,其中又以关帝庙和张飞庙最为常见,较有代表性的有云阳张飞庙、恩施武圣宫、荆州关帝庙等。
云阳张飞庙,位于重庆市云阳县盘龙社区狮子岩,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张飞,民间素有“身葬阆中,头葬云阳”的说法。现张飞庙是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由云阳老县城飞凤山原状搬迁至此,号称“巴蜀一胜境,文藻一胜地”。
恩施武圣宫,位于恩施州恩施市城乡街60号,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宫内已无塑像,建筑保存情况尚好,核心区域为正殿一院,正殿对面为一戏台。这种形式在西南较有规模的关帝庙中十分常见,正殿祭祀,戏台用于表演历史剧目,是一地百姓获知并再创造三国历史故事传说的主要认识来源。据当地文史专家考证,武圣宫所处位置为恩施老城最为繁华之处,其建筑格局最晚在唐代便已形成,是官方举办大型活动的重要场地。与其相对应,最晚在20世纪90年代,恩施老城还有石关庙、石像宫,各区县有十余座关帝庙(5)恩施市文物局研究人员周学聪口述。。
荆州关帝庙,位于荆州市荆州区爱民路48号,原为清代建筑,后于抗日战争期间损毁,20世纪80年代重建。核心区域为正殿、结义楼,塑有关公像和刘关张三人列像,每年举办大型庙会,是荆州地区关羽崇拜和关公文化的重要标志。
此外,这一类祠庙有时并非作为单独建筑存在。受民间崇拜、宗教文化以及地方各类历史文化工程打造的影响,常见其与其他建筑并存共生的情况。如宜昌黄陵庙中有关羽祠、武侯祠;宜昌玉泉山风景区内有小关庙;武当山风景区中有关帝庙;十堰三义宫中既有三国人物像,也供奉道教人物;长寿区桓侯宫中还供奉药神、财神和佛教人物。这些现象植根于民间,从另外的角度反映出三国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方式,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3.楼阁这一类建筑相比于祠庙类规模往往偏小,多数是有一间或一小型独体建筑,其纪念意义也不在于某一个特定人物,常见纪念某个历史事件或因历史事件而衍生出的民间传说。如春秋阁,位于荆州市沙市市中山公园内,原春秋阁建于清代,民国时移于现址。传关羽镇荆州,于此挑灯夜读《春秋》,故有此名。
4.历史事件发生处关于这一类遗存备注有二。第一,所谓“历史事件”是个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也包括根据历史事件而改编甚至夸张化的民间故事,还包括出于民间崇拜、个人信仰等因素完全虚构的一些情节。第二,历史事件发生的精确所在地基本难以考证,现存所谓“发生处”,多是寄托了当时人们某种特殊的情感。
关公显圣处,位于宜昌市当阳市玉泉山风景区内,现存两块石望表,一年代为明万历年间,上书“汉云长显圣处”;一年代为清代,上书“最先显圣之地”,由清大学士阮元敬题。此地渊源于《三国演义》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与相邻珍珠泉、关公磨刀石、小关庙组成三国文化遗存群。
张飞擂鼓台,一处位于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古战场风景区,一处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三游洞景区内,两处均建有张飞擂鼓雕像,渊源于张飞擂鼓操练水军一说。
回马坡,位于宜昌市远安县洋坪镇蔡家沟村罗汉峪,现存碑亭和碑廊,为清同治年间所建。当地有民谣“走进罗汉峪,四十八道溪。草鞋磨破底,脚板磨破皮。”传关羽败荆州,逃于此地,吴军层层设阻,终捕杀之。后人感念关羽大义,不记其败绩,反说关公回马于此,吴军未得其人。主碑上背面刻关公赤兔青龙像,正面书“呜呼此乃关圣帝君由临沮入蜀遇吴迴马之处也”。
此外,宜昌境内还发现有汉寿亭侯点军碑(6)位于宜昌市点军区江南大道海底世界前,现存碑为清光绪年间所立。、“张翼德横矛处”碑(7)位于宜昌市当阳市环城东路、311省道交叉口,现存碑为清雍正年间所立。,也均为这一类遗存之代表。
可以看出,这一类遗存主要依据于历史故事,或以历史故事衍生出的民间故事,其与后所述“民间故事与传说”一类遗存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一类遗存在历史故事、民间故事之后,均存在一定数量的真实遗存,以碑刻居多。“民间故事与传说”类遗存则以故事传说这样的非物质形态遗存为核心,多附会于自然景观或现代建筑之上,这些自然景观和现代建筑受到民间故事传说的影响,改变了其命名或性质,成为了非物质形态遗存的载体。
(三)城址
调查区域内未发现明确为三国时期的城建遗存,基本为依据明确史实、民间故事传说而带有浓厚三国文化因素的城址。较有代表性的有江州大城、奉节白帝城、万州天生城等。
江州大城,为蜀汉李严自永安还江州后所规划建造,利用长江和嘉陵江南北并流的天然地势,于今鹅顶岭前筑城相围,基本形成今重庆主城格局。后南宋、明清重修重庆城,均是在蜀汉江州大城基础上修补或略有扩展,即南宋重庆城,其城垣基址基本因袭蜀汉大城,明清重庆城的范围也基本是南宋城之范围[2]。
奉节白帝城,位于瞿塘峡口白帝山、鸡公山、马岭山范围内,现所谓白帝城泛指这一范围内发现的古城遗迹。白帝城所处位置为江汉平原进入四川盆地的交通要地,考古发现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这一区域便有人类活动、居住痕迹,至迟至战国便建有关隘。“白帝城”之名,文献可追溯至《后汉书·郡国志》,载:“南郡,十七城,……巫西有白帝城。”[3]3479经多年考古发掘,现已基本复原南宋白帝城即抗元山城的基本面貌,并找到了其下叠压的唐城和汉城的线索[4]45-46。
万州天生城,又称小石城、天子城,位于万州区周家坝街道天生城社区,现存遗址以南宋抗元山城为基础,清代有所重、改建。传说刘备伐吴曾屯兵于此,故又名天子城。这一传说自古有之,《蜀中广记》:“建安二十年,先主分朐忍……其西四里天子城,相传昭烈驻兵于此,常璩所云小石城是也。”[5]291这样的说法至今仍然存在,并受到当地人广泛认可。
(四)古道路
调查区域内所涉及古道有一些共同特点,基本未被开发或开发程度较低;路面未有专门修缮,处于随时代变迁自然变化状态;至今仍为当地人所使用。关于其与三国文化之关系,一类为受当地民间故事的传播影响,以三国因素命名,未有明确史料或实物支撑,如张飞古道。一类为有一定史实基础,受地方文化宣传影响而命名(或确定),但缺乏更多证据支撑,如华容道。
张飞古道,位于重庆市北碚区东阳镇西山坪大沱口。当地广泛传说为张飞于此地行军所拓修使用,现整条古道仍为当地使用,基本沿江而行,长近10公里,路面间或残存铺地石块,石料应为就近山体所取,未发现明确遗迹遗物,始建年代不明。开发程度较低,仅有少数几处当代石刻题记。
华容道,位于荆州市石首市至湖南省华容县东山镇大旺村省界,横跨桃花山。现存全长约3公里,为华容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界处有隘口,当地人称释曹口,应为依据历史故事附会。另有一华容道,位于荆州市监利县上车湾镇华容道村,有当地政府部门以“三国遗址”为名所立碑,指碑前现村道,长度不明。两处华容道均无明确遗址遗迹,且华容道具体位置、走向至今仍存争议,文献无明确信息,亦无相关考古发现佐证。但当地民间故事传说的传播现状及方式,以及地方政府及文化工作者宣传本地特色文化的立场和方式值得关注。
(五)民间故事与传说
本次调查的区域是三国故事传说极为丰富的地区,尤其是湖北,湖北三国传说已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括人物传说、地名传说、地方风物及习俗传说等。各地为此进行了大量工作,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民间故事传说辑录、研究的成果(8)较有代表性的有:程地宇、赵贵林、雷庭军著:《奉节文化大观》,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高仲著:《从远古沧桑中走来的郁山》,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印,2011年;东宝区文化体育和广播电影电视局、东宝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东宝民间故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文化当阳》编委会编:《文化当阳》,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2016年;熊远桂、熊永编著:《诸葛亮荆州传说》,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2015年;董乐义著:《古当阳》,湖北辞书出版社,2000年;鲍传华:《长坂坡》,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政协荆门市掇刀区委员会编:《掇刀文史》,2015年等。。
这些故事传说纷繁复杂,还多有变体,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一是由真实历史故事或遗址遗迹衍生出来。以真实史实为基础而衍生出的,如诸葛亮掌握气候规律开发种植技术的故事,即是根源于其布衣躬耕的史实;以三国遗址遗迹为基础而出现的,如猇亭古战场“虎牙”“望夫崖”“遗恨洞”等故事(9)猇亭古战场遗址,位于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6号,现为当地打造景区,景区内按收录当地三国故事打造了相应景点。;以其他时期遗址遗迹为基础而出现的,如荆州换帽冢、系马冢、落帽冢等处的关羽相关故事,据当地文物部门调查,上述几处遗迹本为战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因当地关羽崇拜风气,关羽于其地换帽、系马、落帽的故事流传十分广泛,已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地名。
二是民间故事传说附会于自然景观或现代建筑。如宜昌玉泉山风景区珍珠泉,相传关羽殉难后,赤兔马长鸣于此,刨出此泉,眼泪落入化为珍珠。此外如荆门京山新市镇马刨泉、荆门掇刀街道马跑泉、荆州八岭山镇龙山社区马跑泉等处,均有类似故事且具相当传播范围。
三是一些民间故事已广为人知,但并不依附于任何遗址遗迹或自然景观,亦很难找寻其产生源头和时代。这一类故事传说数量在上述三种类型中为最多,并且随时代推移,其具体内容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最直观反映了民间故事传说作为非遗一种形式的发展变化过程。
二、相关问题举要
三国文化遗存尚且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三国文化遗存研究也属于一个尚未被专门化的课题,关于其中的基本问题、基本方法尚在摸索的过程中,需要更广泛的调查、更多的材料以及更细致的思考。在调查过程中及材料整理阶段,我们针对本次调查点位、调查过程,以及过往已完成的调查工作总结了一些三国文化遗存调查、研究相关问题,虽不能以偏概全,但望抛砖引玉,引起关于如何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如何把这一课题系统化等更深入的讨论。
(一)三国文化遗存的定性
要解决何为“三国文化遗存”的问题,首先涉及的就是何为“三国文化”的问题。对于“三国文化”概念的研究,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应属沈伯俊先生之观点[6]。笔者也曾专门撰文,综述了以往对“三国文化”概念研究的不同观点,并提出了个人的意见[7]。暂且不论沈氏观点与拙文观点之差异对错,即无论三国文化应定义为综合性文化(详见沈氏三层次论)还是由三国历史产生和衍生的人类物质精神财富总和,从“三国文化”概念到“三国文化遗存”的定义,我们都面临着更实际的问题,即判定一个点位为三国文化遗存的标准问题。
在实际调查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即面对一处非三国时期的遗存,其三国文化因素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被定义为三国文化遗存?目前常用的办法是看三国文化因素是否影响到了该处遗存的命名和主要用途,或是看当地人们对该处遗存性质的普遍认知。如前文提到的落帽冢、系马冢,它们都不是三国时期的遗迹,但由于当地三国文化民间故事的广泛传播,其名称已经不代表它们本身的内容,且被当地人群所接受。然而,明显可以看出,这样的方式主观性太强,标准不够稳定。
另外,前文已经提到,一些民间故事和传说是以自然景观或现代改建、重建建筑为载体的,过往的调查中,我们一般是以这些景观和建筑的名称作为三国文化遗存点位名形成记录。那么,这些景观和建筑算不算三国文化遗存呢?一方面,从年代和现存遗迹遗物方面讲,它们本身当然不能算作文化遗存,真正的遗存是依附于其上的民间故事传说;另一方面,它们和那些故事传说又是一体的,不仅是其载体,更是其故事内容的表现。这一问题本质上反映出三国文化现象和三国文化遗存紧密联系,但界限还很模糊。
(二)三国文化遗存调查的定性
从目前调查所得材料可以看出,三国文化遗存的类型是极为多样且复杂的。从实际材料出发,很明显三国文化遗存调查不可能是一般的考古学调查。比如,一些点位本身的保存情况极差,甚至没有明显的遗迹遗物痕迹,更没有勘探、发掘的条件和必要性;一些点位本身需要大量史料及其他背景材料支持;加之面对民间故事传说、地方风物、民族习俗等内容,考古学本身的学科方法无法满足,还需介入民族学、社会学以及口述史的方法。
从调查目的出发,面对繁杂多样的材料,三国文化遗存调查最基本的目的是通过材料的累积,建立起对“三国文化遗存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系统。通过对各处遗存全面信息的搜集整理,建立起三国文化遗存的基本标准。只有把这些材料真正作为一个整体,才有可能深入研究其年代、性质、族属,才能建立具体的类型划分标准,才能以一个整体去发掘它们更多的价值。
以这样的角度来看,三国文化遗存研究更应属于近年来兴起的文化遗产学研究范畴,三国文化遗存调查更接近于文化遗产调查。虽然文化遗产调查目前尚未有明确的系统化方法论,但遗产学的一些概念,如遗产分类体系、遗产价值认知等,可以为三国文化遗存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三)三国文化遗存的年代和类型
三国文化研究毕竟是以历史学为基础的,因此,三国文化遗存的年代判定是对其研究的一大基本问题。可以明确的是,三国文化遗存的年代并不仅在于三国时期,这是基本的共识。而在对这些遗存年代问题的研究中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
其一,将非三国时期的三国文化遗存年代确定下来,并不代表对其研究的结束,反而是对该遗存与三国文化关系探索的开始。以我们过往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本次调查所获材料举例,攀枝花营盘山古军营遗址(10)营盘山古军营,位于攀枝花市仁和区啊喇乡,当地文物部门和百姓俗称“诸葛营”。和打箭岩(11)打箭岩,又名四川岩子,位于攀枝花市盐边县永兴镇,当地传为诸葛亮南征“一箭定岩(盐)边”射到石头上的箭。两处点位,我们给出了对其年代、性质的看法[8],但更应进一步考虑的是,它们是如何从与三国毫无关系演变为三国文化遗存的,那些起决定作用且流传至今的故事传说是如何产生的,甚至于该区域的诸葛亮崇拜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样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动因。再如,此次调查所见的张飞岍石刻(12)张飞岍石刻,位于重庆市彭水县太原乡花园村九组,当地传为张飞路过时所刻,年代尚不可考。、荆州偃月城等,在解决它们年代、性质问题背后,也都有故事如何生成类似的问题。这些视角和方法其实并非新颖,也已有成熟的相关成果(13)较有代表性的如杨爱国:《故事是如何生成的——以山东长清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9期。,但在三国文化遗存研究上尚较薄弱。
其二,年代问题固然重要,但只是基本问题之一,并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要依据所获材料实际情况而定。目前一些地方文化工作者,以及大量非专业三国文化爱好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探索有时太过执着,在历史考证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极端化的倾向。比如,仅因史书记载有其所属地区三国时期曾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便把一些非三国时期的遗址遗迹,以及不少现在的普通地点强行考证为历史事件的精确发生出,并进一步将该遗址(地点)年代上溯至三国时期,类似于“五月渡泸”之渡口所在地、华容道的准确走向、关公刮骨疗伤处等。然而,其中不少问题是依据现有材料无法解决的,甚至永远无法解决的。当然,他们对地方特色文化的热爱和宣传热情可以理解,这样的现象从社会学角度也值得关注,但于三国文化遗存研究而言,还是需要注意。
三国文化遗存的类型划分问题也是对其研究的一大基本问题。三国文化遗存是一个大概念,从考古学上讲,它跨越了极长的历史时期;从遗产学上讲,它包含了几乎全部的遗产种类。对其的研究不可能把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遗存混为一谈。同时,只有在存在细致、有效分类标准的前提下,三国文化遗存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才能体现出区域特色。比如,在调查中我们仅从认识层面体会到川南、云南地区有明显诸葛亮崇拜现象,有广泛分布的与诸葛亮相关的文化遗存,而荆州地区则更倾向于关羽崇拜;再如成都平原祭祀三国人物的祠庙基本为独立建筑,且祭祀对象专一于三国人物,而三峡地区此类祠庙则多是神仙、历史人物混合祭祀,还多与抗战文化相关联。调查中形成的这些大略认识,需要后期细致比对。在明确分类体系下,不同区域的地方特色在不同类别遗存上如何体现便能一目了然了。此外,完善分类标准,也反过来有利于三国文化遗存本身概念标准的完善。当前,对于三国文化遗存类型问题的研究还十分缺乏,分类方式还基本停留在以年代(三国时期、非三国时期)、性质(墓葬、城址、古道、手工业等)、形式(物质、非物质)、关联性(有史实依据、附会)等大框架的粗线条划分阶段。真正合理的类型体系,应该有明确的层级,什么可以作为第一级别标准,下面可延展出哪些次级标准,最终落脚于一个个具体的点位(文化因素),这些问题还需要具体研究。
(四)口述史调查方法的尝试
在过往调查中,尤其在三国文化故事传说较为丰富的地区,我们试图运用口述史学的方法作了一些调查、研究的尝试,且已有相关成果发表[9]。在重庆、湖北,我们继续利用过往经验,开展了口述史的一系列调查,涉及超过60%的调查点位,访问、随访相关人员60余位,保存影音资料超过1000分钟。口述史及其调查方法是近年来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讨论的热点,目前学术界对口述史学的定位、方法还有广泛讨论和争议,这里我们姑且搁置这些理论问题,主要谈谈从实际操作层面出发的一些问题和感受。
其一,调查者要充分了解点位基本情况和背景资料,制定访问提纲。首先,提出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指向性和目的性,并能随机应变。口述史的访问往往在非正式的环境下进行,访问气氛是轻松随意的,受访者虽作为讲述主体,但其讲述并不会严格按调查者所想来进行。调查者必须立足于对一处点位的基本认识,明确本次访谈要了解关于这处点位的哪些信息,是关于其名称来源,还是讲述人对其结构、历史、性质的认识,还是其衍生的故事传说等等。如何平衡既获得更多信息,又达到访谈目的,需要访问中了解讲述人文化程度、性格特点,把握时间、环境,适度掌握主动性。其次,提出的问题不能有过强的引导性。调查者必须始终是客观的,一些乡镇文化站工作者,以及当地居民,在宣传地方文化热情的驱动下,甚至仅仅是在热衷于访谈活动本身的热情驱动下,可能会对某些话题即兴发挥,甚至凭空捏造,这也是民间故事传说传播的基本特征。
其二,要增强对口述记录技巧性的认识。理论上讲,讲述人所讲内容,即口述材料,与记录、整理后形成的资料,即口述史料,二者是存在区别的[10]。即时的口述记录,尤其是文字记录,本身就是对口述材料的初次加工。讲述人的文化程度、立场、与点位关系要作为基本情况了解,同时访问过程中,讲述人的语气、讲述角度,甚至一个特别的眼神,都可能传递出信息。然而口述材料被文字化后,毕竟是平面的,表现(叙述)方式是客观的,我们既要求调查者站在客观的立场,又要求去深切体会讲述人的情感,这是互相冲突的,也是口述史学在操作层面上的局限,体现出口述记录作为一项精密的技术工作的难度。此外,不同地区的方言、风俗有时也会对访谈交流、记录带来困扰,为记录工作顺利进行,必要时调查组需要加入当地既懂民情,又懂专业的人员。
其三,要重视讲述人类型多样化。就讲述主体而言,不同职业、身份和文化程度的讲述人有不同的立场,有学者将其归纳为自我表功型、感恩赞美型、以史明鉴型、历史责任型、维护正义型、公益事业型、获取报酬型、辩诬白谤型等多种[11];就讲述内容而言,无论是口述材料还是口述史料,其历史真实是不可完全实现或证明的,但其动机真实是客观存在的。在过往和本次调查中,我们就某些条件具备的点位,往往兼顾访问政府行政工作人员、文博专业人员、乡村文化工作者、民间三国爱好者和当地居民,能够清晰发现不同类型讲述人有不同的讲述角度。同一处遗存的古往今来,可以被解读成政治文化的历史演变,也可能成为民间崇拜的载体,或也会有家族文化传承的塑造,甚至个体生活的理想图景。在一些少数民族集聚分布的地区,就还存在族群共同历史记忆的问题。因此可以看出,讲述人类型多样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