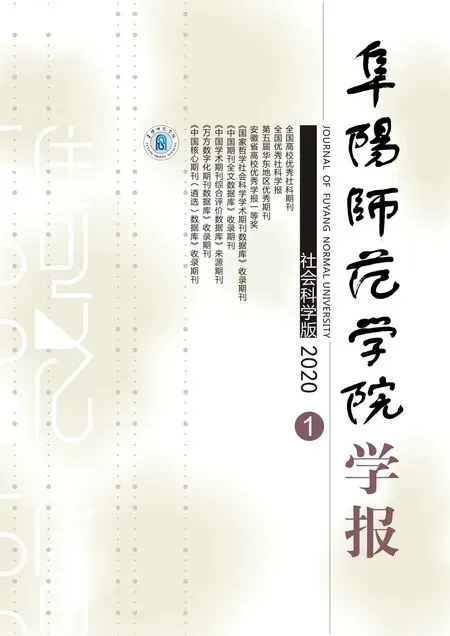信息论视角下中国典籍英译中的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研究——以《论语》英译本为例
徐光霞
信息论视角下中国典籍英译中的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研究——以《论语》英译本为例
徐光霞
(安徽外国语学院 西方语言学院,安徽 合肥 231201)
中国典籍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把中国典籍翻译成英语,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途径。但是,由于中国典籍英译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对于国内外译者来说,要想实现译文与原文完全地对等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欠额与超额翻译的现象。《论语》是中国典籍的代表之一,对中国文化甚至是世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论文主要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研究《论语》中出现的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此种现象主要是由于译文与原文在两级信息传输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信息、风格信息、修辞信息以及理性信息方面不对等造成的。
《论语》;信息论;超额翻译;欠额翻译
中国典籍博大精深,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哲学、宗教、法律、军事、天文、建筑等,而要想完全把中国典籍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翻译出来,译者不仅需要对原文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要拥有丰富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还需要具有很强的英语写作能力。因此,对于中国典籍的翻译,无论对于外国译者还是中国译者,要想完全地做到对等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在翻译中国典籍时,不可避免地出现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
目前,国内外对于中国典籍英译中存在的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的研究几乎没有。本研究采用信息论来研究中国典籍英译中出现的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基于此理论是因为翻译的过程就是理解与表达原文信息的过程。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就是对原文信息进行编码与再编码的过程。而中国典籍英译中出现的欠额翻译与超额翻译现象,即为译者在理解中国典籍后,用另一种语言进行表达这两个传输信息过程中出现的。本文以《论语》英译本为例,具体分析出现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的原因,即译者在理解与表达两种语言之间所传达的文化信息、风格信息、修辞信息及理性信息出现的信息失真所导致,译者应该正确对待《论语》英译本中所传达的各种信息。
一、信息论与翻译的关系
将信息论中相关理论知识与翻译领域相结合的是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在他的著作中曾从信息论的角度去阐释翻译行为。在翻译活动中,“翻译者肩负着原文的读者和译文的作者的双重身份”[1]260。信息论与翻译的联系在于以下几点:首先,利用信息论中的冗余理论研究翻译标准。人们之前在衡量译文是否忠实的时候,其标准仍需要对照原文作者的观点。后来爱德华兹认为译文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与原文最一致的感受”,即忠实的标准应该根据读者的反馈为主。其次,由于译语与原语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差异与失衡,而这类失衡主要来自于两种语言内部冗余度的差异。信息论与翻译的关系在国外的研究者主要是奈达,是他把信息论中的相关原理应用于翻译领域,拓宽了翻译研究领域。国内著名学者廖七一也曾在《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中详细地论述到信息论的相关内容,而方梦之在《译学辞典》这本书中也涉及到了信息论的相关内容,这些对于国内研究信息论是有利的。在中国知网上对信息论与翻译关系的研究进行搜查,大部分有关信息论的文章都是与翻译实践相关。例如,2002年,《中国科技翻译》中的一篇论文《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汉英翻译的冗余现象》,就是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待汉英翻译现象的。2004年在《中国翻译》杂志上的《信息理论与平衡翻译》,是利用信息论提出平衡翻译的概念,它拓宽了翻译的研究。另一篇论文《信息论对旅游材料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是利用信息论中的相关理论进行的研究;此类论文还有不少,这些主要是国内学者利用信息论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翻译实践的研究。
二、信息论视角下的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
由于中西方在社会、文化、语言、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的固有差异,两种语言在转换的过程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欠额与超额翻译的现象。译者所做的应该是探索出现欠额与超额翻译的原因,最终找出合适的策略去进行规避。由于翻译的过程是传达信息的过程,因此,可以运用信息论的相关原理去解释欠额与超额翻译问题。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是理解和表达的过程,是两级信息传输过程。第一级传输过程是理解的过程,也就是解码的过程,译者在解码中必须排除噪声的干扰;而第二级传输过程是表达的过程,译者需要正确使用译入语对原文本的内容重新进行编码。在这两级传输过程中,由于噪声的干扰,译者在解码与编码的过程中会导致信息传递的失真,进而产生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是译者进行信息解码与编码的过程。在这过程中,译者必不可少地受到噪声的影响。噪声会对译者所接受到的信息产生干扰,进而使译文与原文产生信息不对等现象。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的发生,则是由于译者在理解原文中出现的文化信息、风格信息、修辞信息、理性信息与译文中出现的相应信息不对等造成的。信息论与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之间的关系如下:
第一级信息传输过程:
译者解码原文本信息---->信号失真---->理解偏差---->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
第二级信息传输过程:
译者编码原文本信息---->信号失真---->表达偏差---->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
三、《论语》英译本中的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译者在进行翻译过程——对原文本信息进行解码与编码的过程,由于要全面考虑原文本中所传达的文化信息、风格信息、修辞信息、理性信息而导致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的出现,即由于译者在理解原文与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原文这两个信息传输过程中出现的偏差造成的,由于《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结晶,原文本中所传达的各种信息在现代社会来看,译者要想达到与原文本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可避免产生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现从《论语》原文本中传达的各种信息并结合理雅各、韦利与刘殿爵的《论语》英译本,探究《论语》英译本中出现的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
(一)文化信息
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人类进行交往与沟通时,必须用某一种语言来表现他们特有的文化。人类除了共同拥有一些文化的核心要素外,每个国家又由于其独特的气候、地理以及历史,保留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也正是由于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国与国进行交流时,就需要了解彼此文化的异同点。而国与国之间使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时,就需要译者进行两种文化之间的传递。此时译者能否了解彼此的文化异同点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在进行跨语际文化交流时,需要译者将不同的文化进行翻译整合,为译入语读者提供便利。但是对于译者来说,很难做到完全对等地把原文中的文化信息传递到译文中,尤其是翻译中国典籍。“翻译中国古代典籍与翻译其他类型作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典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而文字方面的难度是次要的。”[2]P1以《论语》为例,译者在翻译《论语》时,首先需要对原文所反映的独特文化背景知识进行理解,尤其是《论语》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如“君子”“小人”“仁”“德”等,译者往往由于处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无法真正完全懂得这些文化负载词内涵。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文化信息的正确传达主要存在于两级信息传输过程。在第一级传输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文进行解码,即正确理解原文中所体现的文化信息。由于中西方之间固有的文化差异,译者会受到噪音的干扰,此处的噪音主要在于再现文化信息方面的障碍,进而导致传输信号的失真,导致译者对原文中相关文化信息的理解出现偏差;在第二级传输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文本的文化信息进行编码。由于在第一级传输过程中出现了信息偏差,因此,第二级传输过程中也会导致传输信号的失真,译者无法正确译出原文的文化信息,最后导致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的发生。下面以《论语》相关语句作以分析。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理译:The Master said,“It is only the truly virtuous man, who can love, or who can hate,others.”[3]50
韦译:The Master said,“Only a Good Man knows how to like people,knows how to dislike them.”[4]P62
此句中,“仁者”是指有德行、有恩情的人。在佛教中,是对人的尊称。理雅各用 “perfect virtues man”来翻译“仁者”,即对“仁者”的翻译符合中国人对于“仁者”的定义,即译者在对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解码时,充分考虑了“仁者”在汉语中的意思,使“仁者”在原文中的含义在经过译者解码时,能够将“仁者”的文化信息传递到译入语中。而在韦利的译文中,用“good man”来翻译“仁者”,在英语中,“good”一词的含义较为笼统,用作形容词时,表示 “having desirable or positive qualities especially those suitable for a thing specified.”从该词的用法来看,似乎没有与汉语中“仁者”的意思相对应,即原文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并没有完全翻译出来,原文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产生信息失真,使译文的文化信息少于原文,最终导致欠额翻译现象的产生。
(二)风格信息
文学作品中的风格是指其表现出来的一种带有综合性的作品总体特点。随着翻译活动的不断盛行,一部文学作品译著风格的体现不仅仅与原文作者风格相关,而且也与译者风格相关。而译者风格受世界观、创作天赋与时代背景相关。因此,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风格再现过程中,在对原文的理解上会加入个人理解,在进行语言转换时,又会把自身的文学创作风格和语言表达习惯体现在译著中。由于不同的作者文化背景、情感态度以及生活经历、作者的表达风格与译者的表达风格不可能完全对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想完全对等地表达原文作者的写作风格具有一定难度。即对于译者而言,达到与原文作者相对等的写作表达风格很难。这时就会出现译文的风格信息少于或者多于原文作者的风格信息,最终导致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的产生。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风格信息的正确传达主要存在于两级信息传输过程:在第一级传输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文作者的写作风格进行解码,由于源语与译语作者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译者对源语作者写作风格的理解时,会受到噪音的干扰,此处的噪音主要在于再现风格信息方面存在的障碍,进而导致传输信号的失真,导致译者对原文中相关风格信息的理解偏差;在第二级传输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文本的风格信息进行编码。由于在第一级传输过程中出现了信息的偏差,因此,第二级传输过程中也会导致传输信号失真,译者无法正确译出原文作者的风格,最后也会导致欠额与超额现象的发生。
《论语》著作具有独特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论语》中的语句表达言简意赅,但形式多样,尽管语句不长,但写作方式生动,可译性较强,灵活的句式以及多样的写作技巧可以体现其生动的句式。第二,《论语》中富含文艺色彩和情感语句。对于译者,尤其是西方的传教士们很难完全领会其中灵活的风格,而这些风格特征恰是可以直接反映孔子及其弟子的风格。同时,《论语》中有些语句的意境与现代社会中的意境有所不同,有些甚至大相径庭,中国译者在翻译时都会出现困难,更不用说国外译者。第三,《论语》中每篇章节都有不同主题,换言之,《论语》中每章节内容都被主题化了。下面以《论语》相关语句作以分析。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理译: The Master said, “A cornered vessel without corners. —A strange cornered vessel! A strange cornered vessel!”[3] 75
刘译:The Master said,“A gu that is not truly a gu.A gu indeed!A gu indeed!”[5] 82
此句中,“觚”是中国古代用于喝酒的器具。在现代英语来看,还没有相应的词汇进行对应翻译,在理雅各译文中,他采用了解释的方法来翻译这一器具,即在翻译时加入了个人对这一器具的理解,这是理雅各的翻译风格,在其翻译中,把“觚”翻译成 “A cornered vessel without corners”,读者在理解这种器具时,在脑海里会出现很多类似的喝酒器具,此种翻译却未能再现原文中孔子的写作风格,即表达这一特殊器具的风格信息。译入语的读者在阅读时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器具,即译语信息量大于原文信息量,从而导致超额翻译现象的产生。而在刘殿爵的译文中,则用音译的方法保留了孔子原文中对于“觚”表达时的写作风格,可以保留该器具的特征,从而可以让译入语的读者明白该器具实属于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器具,避免了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的产生。
(三)修辞信息
英汉两种语言在修辞的表达方面有许多相同的修辞手法,如拟人、排比以及讽刺等。然而,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习俗、社会环境以及美学体验的不同,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在修辞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了解英汉两种语言在修辞信息表达方面的异同点。《论语》中有许多哲理性的语句,同时,文中的表达也使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如明喻、隐喻、类比、排比等修辞手法,因此有必要指出两种语言在使用修辞手法方面的差异。人们在进行语言表达时,为了润色语言,通常需要借助一定的修辞手法。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表现在使用修辞手法上。在翻译过程中,修辞信息的体现则主要通过不同修辞格来体现。在翻译中修辞信息再现的障碍主要在于以下几点:首先,两种语言即使表达同一概念,但却往往使用不同的修辞格;其次,即使采用同一修辞格,但在修辞格使用的广度和深度却有所差别;最后,某些修辞格存在不可译性,即原文与译文之间在进行转换时,无法找到对应的修辞格进行翻译。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原文与译文在修辞信息传达方面出现不等值现象,进而导致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的产生。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修辞信息的正确传达主要存在于两级信息传输过程:在第一级传输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文进行解码,即正确理解原文中所体现的修辞信息。由于中西方在历史、文化、风俗等方面存在差异,即译者会受到噪音的干扰,此处的噪音主要在于再现修辞信息方面存在的障碍,进而导致传输信号的失真,导致译者对原文中相关修辞信息的理解偏差;在第二级传输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文本的修辞信息进行编码。由于在第一级传输过程中出现了信息的偏差,因此,第二级传输过程中也会导致传输信号的失真,译者无法译出原文的修辞格,最后也会导致欠额与超额现象的发生。《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尽管语句简短,但意思明了。不少学者曾总结了修辞手法在《论语》中的使用情况,发现对照与隐喻两种修辞手法在文内使用了近55次。因此,在翻译《论语》时,也需要用相应的修辞手法进行翻译,否则就失去了中国典籍的美学欣赏价值。由于译者与作者处于不同的文化与时代背景,译者往往无法真正地理解《论语》中相关修辞格的内涵,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即译者在第一级传输过程中,由于无法完全对原文本的修辞格进行准确解码而导致《论语》修辞信息的信号失真,从而也会影响第二级传输过程。最终导致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的产生。下面以《论语》相关语句作以分析。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理译:There were four things from which the Master was entirely free. He had no foregone conclusions, no arbitrary predeterminations, no obstinacy, and no egoism[3] 195
刘译:There were four things the Master refused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he refused to entertain conjectures of insist on certainty; he refused to be inflexible or to be egotistical.[5] 201
此句中,句子结构简短但意思深刻,由四个短语组成,每个短语都有一个“毋”字,从修辞手法的角度来看,此句是平行结构的句子。因此,在翻译时需要使用四个相同的平行结构来翻译。在理雅各的译文中,用了四个“no”的平行结构来翻译,很好地再现了原文中的修辞信息。而在刘殿爵的译文中,虽然也用了平行结构来翻译,但是却只使用两个平行结构,与原文的四个平行结构相比较,修辞信息在译文中变少了,即译文中的修辞信息少于原文中的修辞信息,会导致欠额翻译现象的产生。因此,采用同样的平行结构才能更好地再现原文的修辞信息。
(四)理性信息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理性信息是语言中由词汇、语法意义所限定的相对固定信息,它是信息整体的基础”[6]317。词汇与语法是所有语言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在翻译中,分析原作与译作中的理性信息是否等值,就需要充分考虑两种语言在词汇与语法方面的差异。首先,汉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词汇的使用方面。汉语中,经常使用双音节与四音节词以及叠词,这些词汇的重复使用现象,在汉语中主要起强调作用。而在英语中,很少出现两个相同单词重复使用的现象。而叠词与重复的现象在中国典籍中尤为常见,《论语》作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代表,其中不乏使用叠字与重复语句的方法。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充分考虑中英文在词汇表达方面的差异。其次,英汉语言的差异也体现在语法方面。在一个完整的英语句子中,必须包含三个主要的部分:屈折变化、次序以及功能词的使用。在英语中,屈折变化较明显的是名词与动词,可以在这些词加上前缀或者后缀构成一个新词。英语句子的语法关系也主要通过人称、数、性、情态与语态等屈折变化来实现,而汉语则不同。由于英语中存在屈折变化现象,因此,词序没有汉语灵活。最后,汉语多无主句的句子,而在英语句子中,则必须要有句子主语,否则,不符合英语语法规则。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理性信息是所有信息中最基础的部分。在翻译活动中,正确理解原文语句中体现的理性信息至关重要。《论语》中有许多语句大量使用四字成语、叠词以及重复表达的现象,这也构成了《论语》中理性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译者很难完全准确表达汉语叠词与叠句的使用现象,同样对于中国译者而言,用地道的英语来表达汉语的这一语法现象也绝非易事。因此,在翻译的两级传输过程中,就会出现因未能准确表达原文中的理性信息而出现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在第一级信息传输过程中,译者需要解码原文本中的理性信息,在解码过程中受到噪声的干扰,此处的噪声主要是指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语法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传输过程中出现信号失真的现象,译者出现理解偏差,导致理解阶段出现的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在第二级信息传输过程中,译者对理解后的原文理性信息进行编码,由于第一级传输过程中存在理解偏差,在第二级传输过程中,译者需要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文中体现的理性信息,由于理解不当,也会出现的表达错误,最终导致原文与译文中的信息不对等现象,即欠额与超额现象的发生。下面以《论语》相关语句作以分析。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
理译:The Master said, “Great indeed was Yao as a sovereign! How majestic was he! It is only Heaven that is grand, and only Yao corresponded to it. How majestic was he in the works which he accomplished!”[3]136
刘译:The Master said, “Great indeed was Yao as a ruler! How lofty! It is heaven that is great and it was Yao who modelled himself upon it.[5]125
在《论语》原文中,孔子用“巍巍乎”与“荡荡乎”表达其对尧的赞美。因此,为了再现原文中的理性信息,在翻译时,译者也需要用相同的句式来翻译这两个短语。然而,由于英汉之间在理性信息方面固有的差异,译者很难再现原文的信息。此句中理性信息再现的难度在于两级信息传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即由于理解与表达的偏差,最终导致欠额与超额现象的产生。在此句翻译中,理雅各用“How majestic was he”来翻译“巍巍乎”与“荡荡乎”,此种翻译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者的赞美之情,但是译文中仅用一词 “majestic”来翻译“巍巍”与“荡荡”这两个叠词,同时在译文中也没有体现出“巍巍乎”与“荡荡乎”这两个短语的区别,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译文的信息量小于源语的信息量,由此,会产生欠额翻译现象。而在刘殿爵的译文中,用了“How lofty!”来翻译“巍巍”与“荡荡”这两个叠词,也未能把汉语叠词的强调特点充分展现出来,因此,要想规避由于翻译叠词而出现的欠额翻译现象,译者需要在正确理解这两个叠词的基础上,用两个不同的英语单词对应叠词,这样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使译入语的读者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结语
中国典籍是中华民族甚至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而《论语》作为我国最早和最可靠的有关孔子生活和学说的材料来源,对中国文化甚至是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论文主要从信息论的角度分析《论语》中体现的文化信息、风格信息、修辞信息以及理性信息,并对比不同译本,比较其中因缺乏考虑上述信息而出现的欠额与超额翻译现象,以期在以后中国典籍英译的过程中,译者能够充分重视原文中所传达的各种信息,进而更好地翻译中国典籍。
[1]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60.
[2]汪榕培,王宏.中国典籍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01.
[3]孔丘.论语[M].理雅各,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4]孔丘.论语[M].韦利,杨伯峻,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5]孔丘.论语[M].刘殿爵,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6]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317.
Under-translation and Over-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under Informa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Versions of
XU Guang-xia
(Western Languages Department, Anhu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efei 231201, Anhui)
Chinese Classics is the aesthetic wealth for the whole worl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status in this world,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is the best approach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s full of challenge; it is sometimes impossible to achieve full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ranslated text. As a result, under-translation and over-translation will inevitably appear.,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ese Classics, has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and even the world culture. This thesis mainly analyzed under-translation and over-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Theory, and shows that this phenomena are due to the non-equivalence of cultural, stylistic, rhetoric and conceptu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he translated texts in the process of two level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 Information Theory; Undertranslation; Overtranslation
2019-11-12
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信息论视角下中国典籍英译中的欠额与超额现象研究——以《论语》英译本为例”(SK2017A0793)
徐光霞(1987- ),女,汉族,安徽合肥人,硕士,安徽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10.14096/j.cnki.cn34-1044/c.2020.01.07
H059
A
1004-4310(2020)01-003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