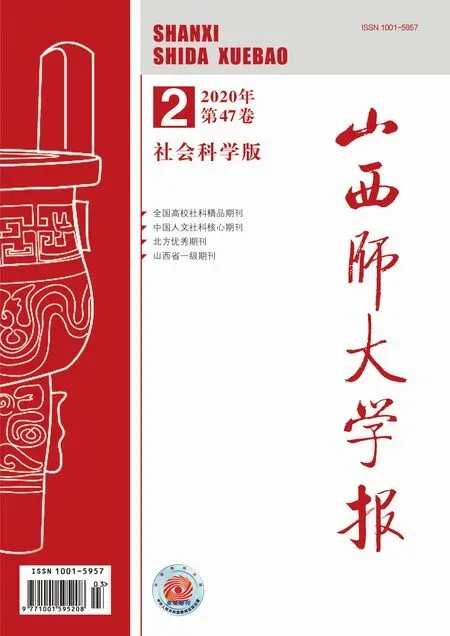“思想市场”观念辨析
谢加书,刘苗苗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640)
一、“思想市场”观念在我国的形成与传播
近年来“思想市场”观念在我国学术界和社会舆论场传播,引起较大争论,逐渐形成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出发,需要我们系统梳理“思想市场”观念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形成原因,为辨析和引领思潮奠定基础。
首先,“思想市场”观念形成的背景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泛滥。“思想市场”观念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直接来源是新自由主义。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发生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受到挑战,经过修正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应时而生。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为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滞涨危机,先后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政策指南,从而实现了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走向政治实践,并成为推行全球化、西化的重要工具,其高潮是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及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主张“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 自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广泛传播,在我国理论界、媒体中影响很大,成为一股有影响力的新自由主义思潮。
“思想市场” 观念秉承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自由化、市场化等核心理念,强调思想观念在自由竞争中优胜劣汰。1974年,科斯在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中提出了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指出“思想市场”内含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里的内容。此后,科斯在阐述中国问题时进一步指出:“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地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1]作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科斯在我国影响较大,其“思想市场”观点也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观念。
其次,“思想市场”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持续发酵过程。“思想市场”在我国经历了从学术界内部研讨到逐渐影响社会舆论的过程。从学术影响来看,“思想市场”日渐成为多学科研究对象。以“思想市场”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中搜索,发现有90多篇相关文献,文献发表的时间跨度从1993年到今,内容涵盖经济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法学等学科,包括学位论文等。此外还发现著作多本,如《思想市场论》等。搜索结果表明,“思想市场”已经成为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对象,既包括肯定性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批评性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社会影响来看,“思想市场”从学术研究到影响社会的关键是科斯的讲话。科斯在2011年12月《财经》年会视频致辞中提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1]他认为思想市场是解决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钱学森之问的关键,并在此后的《变革中国》中进一步强调。作为著名学者和有影响力的舆论领袖,科斯的话在我国引起了较大反响,有人甚至认为“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中国未来”,同时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批评。
最后,“思想市场” 观念在我国传播有复杂的国内外因素。从国外因素来看,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始终没变。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变种成为西方分化、西化中国思想界,最终影响乃至颠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思想武器。“思想市场” 观念强调多元思想自由竞争,必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曾任科斯学术助手的王宁在2013年指出:“思想市场,应该是我们下一轮改革的指明灯。”“思想市场是中国改革绕不开的坎。”[2]这观点显然与坚持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相左。从国内因素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泛化对思想领域影响深远,市场交易原则渗透进思想理论领域,少数人热衷于传播思想市场等观点,认为单纯的市场可以推动思想传播的优胜劣汰。
二、“思想市场”观念评析
思想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自然科学技术的思想,它只涉及真伪,强调主观与客观是否一致,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二是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道德、政治法律思想、文学艺术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虽然部分意识形态也可能是科学的,但思想本身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其评价标准是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等。在科斯看来,其思想市场所指的思想既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思想,如产业属性的知识、技术及各种创意,也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科斯曾指出:“为简明起见,我将演说、写作及宗教信仰活动称为‘思想市场’。”[3]63从其实质来看,“思想市场”观念强调的是多元思想自由竞争,客观上迎合了部分国家分化、西化我国的政治需要,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一)“思想市场”的立论基础不成立
“思想市场”观念的立论基础是思想自由传播,但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平等的自由传播权利和传播机会。“思想市场”观念坚持“自由化”“市场化”,认为群众在思想传播方面具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可以通过自发的市场调节形成思想领域的优胜劣汰。事实上,思想的自由传播受两方面限制:一方面,自由不是任性放纵。从哲学上来看,自由是对必然的自觉认识和依据这种认识对世界的能动改造,即按规律办事。从根本上看,政治与法律权利意义上的自由是建立在对必然认识基础上的,不能违反客观规律。自由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受到人类认识、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文化传统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存在任性放纵的自由。自由是规律的、自律的自由,是具体历史的自由,是遵守本国本地区法律的自由。因此,思想自由传播的基础是要遵守一定的宪法和法律,并受到本民族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制约,不存在完全自由的思想传播。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群众缺乏实质意义的自由平等传播权利,没有实质平等的传播机会。资本主义社会中思想的传播载体受到资本控制,思想传播遵循着资本逻辑,谁掌握了资本谁就掌握了“思想市场”。表面上思想自由传播,事实上思想的传播广度和深度受到了传媒资本家的控制,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传播思想的平等权利和平等机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市场,如近来在香港暴乱中美国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和Twitter等大规模封禁介绍香港真实情况的账号,配合美国政府干预香港局势。“由于媒体的垄断与集中,美国媒体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其所属利益集团话语权的延伸。存在共生关系的社会各种强势集团,会对媒体刊播的新闻进行过滤,将其他文化和不同见解边缘化,向公众传达他们选定的信息。”[4]
(二)“思想市场”观念模糊了两类思想的性质差别
“思想市场” 观念忽略了自然科学技术思想和意识形态这两类思想性质上的差别。这两类思想性质上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其在“市场”中的传播方式。自然科学技术思想是客观的,不具有阶级性,是为人类服务的。部分具有产业属性的自然科学技术思想,与价值无涉,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让受众自由选择最适合他们自己的思想产品来“消费”,形成“思想市场”。当然,自然科学技术思想也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传播的,发达国家通过严密手段控制特定的自然科学技术思想,以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家利益。即使是作为思想结晶的知识产权,市场在知识产权配置中也并不是完全起决定性作用,有的国家在一定范围进行了干预,如美国长期对华实施高新技术出口管制,限制中国留学生学习某些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等。部分自然科学技术思想不具有产业属性,但对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人类文明传承有重要意义,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进行有效传承,单纯的市场机制也无法承担普遍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重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通过政府和社会支持资助自然科学技术思想的传承和人才培养。
意识形态在任何国家都不存在完全自由传播的“思想市场”。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价值立场,存在着为谁服务的问题,部分思想传播还受到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制约。从世界各国来看,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般通过教育、宗教、大众传媒、政党活动等进行传承。虽然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禁止立法设立国教或侵犯思想自由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通过资本家把控的媒体等得到保障,边缘化其他思想,即压制性宽容,以其形式上的自由掩盖了实质的不自由。
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倡行“思想市场”。社会主义国家捍卫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仍处于弱势,西强东弱的态势没有根本改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传播优势,加大和平演变力度,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挑战性因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传播技术和传播载体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如果推行所谓的自由“思想市场”,其结果是西方力推的思想观念在全世界畅通无阻,破坏他国的意识形态治理秩序,必然会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三)“思想市场”观念没有正确理解政府治理与市场传播之间的关系
思想领域不同于经济领域,思想传播绝不能简单套用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国际公认经济领域单纯的市场调节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思想传播更不能简单套用市场机制提倡思想市场。事实上,思想市场的倡导者也承认思想领域不同于经济领域,但在如何运用市场调节方面,多数思想市场倡导者坚持完全市场调节,强调市场是检验思想真理性的标准,少数则主张政府要进行合理的治理。科斯认为:“像所有社会制度一样,思想市场是远远不够完善的。举例而言,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招致更坏的结果。”[1]简单以市场为标准,在利润导向下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黄赌毒等必然会蔓延,低俗、庸俗、媚俗的思想观念、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等必然会泛滥,这将严重影响公民的肉体和精神健康,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降低社会文明程度。从这点来看,需要政府自觉管理、适当管理,与社会组织等一起鞭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其从未有过真正的思想市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把危害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其“思想市场”是虚伪的。如冷战时期美国麦肯锡主义盛行,共产主义者受到残酷迫害。至今,美国等发达国家允许在可控范围内有不同思想出现,维持虚伪的思想自由,以营造虚假的“思想市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思想自由充其量不过是通过‘压制性宽容’来维持的装饰品。”[5]另一方面,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外宣传积极干预他国“思想市场”。冷战时期西方国家等通过“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鼓吹西方是自由世界,抨击社会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鼓动社会主义国家的群众叛国投敌、颠覆本国政府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美国长期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控制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流向,资助对别国的意识形态渗透、颠覆等活动。冷战后,西方国家对外宣传策略重视信息技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推行网络自由等政策,以渗透乃至颠覆他国。2016年美国通过《波特曼一墨菲反宣传法》法案建立基金,培训和资助有关方面,使之成为美国政府对外宣传的“马前卒”。
从我国实际来看,加强思想领域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思想领域的斗争事关意识形态安全,是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前沿阵地。奉行思想市场必然导致将意识形态领导权拱手让人,放手让敌对势力来争夺我国群众,争夺我国青年一代,势必破坏国家的长治久安。如2011年,美国政府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以网络言论自由、网络信仰自由和链接自由为工具,通过支持“压制性国家”的网上活跃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等,名为推动网络空间自由,实为传播美式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事实上,党的十八大前,我国网络空间曾出现较严重的造谣蛊惑、抹黑党和政府、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等现象,在网络空间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可见,国内外的意识形态斗争迫切需要我们党和政府加强思想领域的治理。
三、引领社会思潮的对策
面对“思想市场”观念等社会思潮在我国的传播,我们要积极应对,加强对社会思潮的分析和引领工作。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武装工作和科学素养的提升工作,通过系统的工作努力解决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提高中国思想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积极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首先,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武装工作和科学素养的提升工作,积极占领思想阵地。一是积极推动自然科学技术思想的广泛传播,推动科普工作。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渠道积极推动现代科学思想的传播,压缩封建迷信等不良思想滋生的空间,化解伪科学谣言等,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6]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更充分均衡地满足群众的思想理论需求。加强理论武装,加强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以关键少数带动多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等融入群众美好生活追求中。面向基层开展文明创建活动,通过宣传社会公共文化产品和群众自治的村(居)规民约,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日常生活。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形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长期抓、经常抓的有效机制,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为广大群众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牢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不断提升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
其次,注重分类引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6]要合理区分上述三类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治理对策。对于政治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不能模糊、妥协和退让。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原则,以科学的说理引领思潮;对于思想认识问题,要注意精准推送,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翔实的事实、严密的逻辑论证、科学的结论说服群众;对于学术观点问题,在学术范围内鼓励学术争鸣、鼓励理论创新,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推进学术研究,使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多层面加强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和引导。一是要从学术层面加强对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抽丝剥茧,厘清我国社会思潮与西方社会思潮的渊源关系、发展脉络等,加强学术引导,进行正确的学术争鸣;部分社会思潮在传播过程中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三者兼而有之,这需要我们综合引导;对于借学术之名行政治图谋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二是要从政治层面分析社会思潮的政治本质。以国际视野、中国立场解读社会思潮的政治本质,引导群众充分认识该社会思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揭露其服务对象。三是要从传播层面加强对社会思潮传播过程的分析和治理。从传播者来看,多数社会思潮的源头来自境外,社会思潮境内广泛传播的关键是有影响力的学者或舆论领袖的扩散;从传播过程来看,一般是境外炒热,部分境内网络媒体跟风,伴随着争论,国内更多学者和报纸杂志参与其中。这要求我们抓住社会思潮传播过程的关键要素和环节,及时引领社会思潮,积极化解和防范社会思潮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同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强化媒体自律制度,压缩不良社会思潮传播空间。
最后,提高中国思想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断加强和改进中国思想的传播,尤其是要着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增强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是建设全面覆盖的传播载体,这是加强我国思想传播的前提和基础。要针对不同类别思想的特点,加强规划和建设相关的传播载体,如建设适合专业性质的学术思想传播载体和宣传性质的社会思想传播载体,还要加强对各类传播载体的领域和内容分工,完善载体体系,全面覆盖群众生产和生活空间,进行多落点、多形态传播,从整体上提高思想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二是要发挥以党政组织系统为核心的组织内政治学习和以国民教育和党校为依托的思想教育的主渠道作用,进一步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压缩邪教、宗教极端势力、封建迷信思想的活动空间;以党的宣传系统为核心,结合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革,提高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载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夯实社区思想文化平台,建设基层图书馆等传播载体,让科学思想深入群众生活领域;适应信息技术发展新形势,充分运用三网融合契机推动思想传播,精准传播,点对点推送到群众手中,进一步提高思想传播的实效性。三是要采取有效策略,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面对思想传播的新趋势,加强思想理论的数字化、视频化形式转化。精选中国思想理论的最新成果,以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形式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图文并茂的作品,让不同群体喜闻乐见;通过声光电等形象具体的视觉展示,让群众动心动情,引发受众深思;以新潮的语言获得更多群众的理解和认同。通过有声有色有味的形式吸引群众,接地气,聚人气,提升中国思想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感染力、向心力,增强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