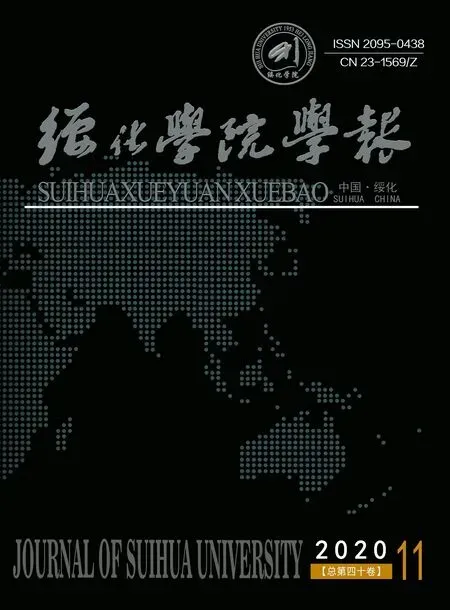胡风与茅盾的论争探析
魏邦良
(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马鞍山 243002)
胡风与茅盾早年在日本有过一段交往。回国后,他俩在政治和文艺领域都曾共过事,同时与鲁迅的关系非同一般。按理,两人交情匪浅,即便文艺观不同,理应求同存异,相互包容。但令人困惑而又惋惜的是,他俩的关系极为糟糕。
一、“茅盾会说阔气话”
1934年,鲁迅向茅盾提议,办一个专门刊登译文的杂志,杂志名称就叫《译文》。茅盾当即同意。后来,茅盾还向鲁迅推荐了黄源,负责跑书店和印刷所,做些杂事。黄源工作认真,赢得了鲁迅的信任。《译文》出第四期时,鲁迅决定由黄源主编。不久,生活书店换了新经理。新经理不信任黄源,要撤换他,让鲁迅来编。9月17日,生活书店请鲁迅、茅盾等人吃饭。宴会刚开始,新经理就提出换编辑。鲁迅对这种“突然袭击”的方法很反感。之后,鲁迅和生活书店闹得不欢而散。《译文》只得停刊。
对于此事,茅盾的态度颇为暧昧,作为鲁迅的朋友和《译文》发起人之一,他当然不便替书店方面说话;但同时,他也是生活书店老板邹韬奋的朋友,所以他也没有完全站在鲁迅这一边。一方面,他委婉地批评生活书店换编辑,不该不事先和鲁迅商量好;另一方面,也体贴地为生活书店辩解,说他们当时在经济上确有困难,所以才想借鲁迅的名声打开销路。茅盾的这一看法鲁迅想必不会同意。因为鲁迅认为,《译文》停刊,背后捣鬼的是郑振铎。胡风在其回忆录中采纳、认同了鲁迅的看法,“郑振铎起意排除黄源,是从私意出发的。鲁迅不能屈服,是由于作家和编辑不能听凭书店随意处置的原则立场。”[1](p564)
而茅盾却直截了当为郑振铎鸣冤叫屈,认为《译文》风波与郑毫无关系,是鲁迅不明白情况,“鲁迅怀疑这次《译文》事件是振铎在背后捣的鬼,并从此与振铎疏远了,而且拒绝把《死魂灵》第二部的译文继续在《世界文库》上发表。这当然冤枉了振铎……”[2](p97)
茅盾为什么要替郑振铎叫屈,读了胡风下面这段话你就明白了个中缘由:“郑振铎们的做法,茅盾是同意的,但又不敢公开说出来。可以说,茅盾一直支持郑振铎。茅盾有个特点,他喜欢替书店方面说话,不愿替作者说话。鲁迅了解这一点,有时也会忍不住批评一下,说‘茅盾会说阔气话’。”[1](p564)
从以上所引的胡、茅文字中,可看出他俩对鲁迅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茅盾对鲁迅不可谓不尊敬,但内心已有隔阂,而胡风对鲁迅则是衷心的爱戴。正因为胡风对鲁迅有一颗赤诚之心,茅盾对鲁迅的怀疑在胡风眼里恐怕就是大不敬了,而在《译文》停刊风波中,茅盾的“骑墙”态度,胡风自然也不敢恭维。
胡风耿直,爱憎分明,有话直说,难免得罪人;茅盾圆滑,左右逢源,想两面讨好,也往往力不从心。两人性格差异如此之大,相互看不惯自在情理之中。
从鲁迅逝世后,胡风和茅盾的不同表现也可看出他俩对鲁迅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鲁迅逝世后,胡风为主持丧事累得如同大病一场,而当时的茅盾正在乌镇写作,未参加鲁迅的丧礼。对此,胡风当然不满:“鲁迅逝世,国民党的孔祥熙和上海市长都送了挽联。郁达夫也从外地赶来参加葬礼。茅盾却在家度假,他的住处离上海近,坐火车三小时即到。丧事办完几天后,茅盾才回上海,看了一次许广平。”[1](p58)而茅盾的解释是,他当时痔疮发作,才未能赶往上海。
可以说,茅盾和鲁迅充其量算相互尊重的同道,而胡风和鲁迅则是心心相印的密友。
二、“两个口号”论争中,茅盾对胡风的无端攻击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鲁迅认为,作为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国防文学”明确、深刻。鲁迅认为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同时,鲁迅也指出,周扬派主持的《文学界》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
鲁迅批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笼统且含糊。茅盾却辩解道:“我并无另提一个新口号的意思,我原则上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只要给以正确的解释,是可以用的,它有它的优点。”[2]158茅盾的言下之意,是不必另提口号,但鲁迅却坚持提出一个新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认为,从阶级立场看,“国防文学”这口号不明确,从创作方法上看,这口号不科学。而且,鲁迅也明确告诉茅盾:“提出这个口号和雪峰、胡风商量过。”[2](p161)
由此可知,后来胡风撰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时提出这个口号,是遵鲁迅之命的。茅盾同意了鲁迅的意见,但对胡风这篇贯彻鲁迅指示的文章却吹毛求疵,大加指责。说胡风这篇文章没提到鲁迅。那意思是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正确的,但只有鲁迅配提这个口号,胡风不配提。鲁迅提这个口号,就可补救“国防文学”的不足,胡风提这个口号就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这说得通吗?
胡风文章发表后,遭到“国防文学”派的猛烈攻击,胡风本想回击,但冯雪峰劝他说,沉默是最好的回答。他只得服从。
“国防文学”派的攻击越来越猛烈。冯雪峰代替鲁迅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作为回击。冯雪峰把两篇文章拿给茅盾看,茅盾看了鲁迅的文章,认为第二篇太简略,因为没有批评“惹祸的胡风”。茅盾一方面认为这个口号本身没问题,另一方面对提出口号的胡风却死揪不放,一批再批。
对口号的商定者鲁迅、冯雪峰,茅盾不提意见;对“国防文学”派的肆意攻击,茅盾要么不提,要么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反而一味批评胡风的“宗派主义”“不团结”,这只能说他对胡风的成见太深了。
为了弥补鲁迅文章的不足,茅盾撰文《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附在鲁迅文章的后面,这篇文章除了重申鲁迅的观点,还增加批评胡风的内容。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讨好“国防文学”派。然而,“国防文学”派却不领情。所以,《文学界》虽然发表了茅盾那篇千字文,但在文后却附了八百字的《附记》,直接否定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茅盾这一回不得不承认:“从这里,我直觉地感到了宗派主义的顽固。”[2](p169)
在和冯雪峰谈及《文学界》的“宗派主义”时,茅盾批评周扬时,又毫无理由将矛头指向胡风:“胡风他们有宗派主义,而周扬他们又以宗派主义回敬”。你看,他追根朔源,把《文学界》的宗派主义归咎于无辜的胡风。冯雪峰实在听不下去,就提醒他:“我看目前主要是周扬他们的宗派主义。”接着,冯雪峰要茅盾写篇文章,抨击周扬他们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茅盾同意了,但他表示身体有恙,短期内无法完稿。一旁的孔另境(茅盾妻弟)自告奋勇帮他起草。第二天,孔另境就写出了初稿。茅盾接下来的这段文字,很好地说明了他对胡风和周扬的态度还是亲疏有别的:“另境的稿子,基本代表我的看法,但不该严厉批评周扬,也不应点徐懋庸的名。我对他的稿子作了改动,加重了对胡风的批评,主要针对他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当然对周扬犯的同样错误也做了批评。”[2](p171)
茅盾明明答应冯雪峰写篇文章抨击周扬他们的宗派主义,孔另境当时在旁边根据他们的谈话草拟了稿子。但孔没想到茅盾只是口头应付冯雪峰,并不真想批评周扬。所以茅盾才会不满孔在文章中对周扬的批评“严了一些”,修改时,加重了对胡风的批评,减轻了对周扬的批评。然而,茅盾虽加重了对胡风的批评,但周扬这次依旧不领情。于是周扬再次撰文批驳茅盾此文。冯雪峰看到了周的文章,就去找茅盾,对他说,你现在应该清楚了,目前周扬才是不团结的因素,他的那一套才是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冯雪峰还强调:“胡风有错误,但他接受了我的批评。而周扬谁的话都不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正确。”[2](p172)
有人曾造谣胡风是“内奸”,鲁迅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
其实茅盾也曾在鲁迅面前造过胡风的谣,鲁迅同样回他一个冷眼。茅盾一再说胡风人品有问题,但从不给出真凭实据,那么,不管是鲁迅还是旁人,又怎样相信他的话?
茅盾一直指责胡风“不是一个团结”的因素,并想当然地认为,胡风影响了鲁迅对某些问题真相的看法。他认为,胡风向鲁迅介绍情况时带着偏见,而鲁迅又十分信任他。于是,胡风某种程度左右了鲁迅的看法。从茅盾的话中,明显看出他对鲁迅的不满与失望。
接下来茅盾举了一个例子证明鲁迅对胡风的“信任”:“那是一九三四年秋,我从得知胡风在孙科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内领津贴,每月一百。胡风‘中山文化教育馆’只是翻译一些国际政治经济资料。工作很轻松,月薪却高达一百元。但孙科一向严防左派人,没有人担保,他不会聘用胡风。胡风是怎么获得对方信任,进入这个机关的,他对此讳莫如深,令人生疑。我曾和鲁迅谈过此事,他却很不愉快。我也就不好再提了。”[2](p156)
鲁迅沉下脸,“顾左右而言他”,其实很给茅盾面子了。因为,茅盾这番怀疑胡风的话,是故意说谎了。其实,胡风通过什么关系进了“中山文化教育馆”,别人可能不知情,而茅盾却是了如指掌的。因为,胡风是在征求了茅盾的意见后,才决定进入这家“教育馆”的:
“组织工作决定了以后,我需要找个职业养活自己。只好搬出朋友的家。这时,中山文化教育馆刚刚成立,这个机构的后台老板是孙科。出版部主任是陈彬和,主编《时事类编》半月刊,刊载所翻译的多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时论。韩起的朋友在那里做秘书。韩的这位朋友邀我去中山文化教育馆任职,主要工作是翻译文章。我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茅盾、周扬他们赞成我去。这样,我就去了中山文化教育馆,担任日文翻译。”[3](p301)
茅盾说,胡风进“中山文化教育馆”,“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保了密”;而胡风则说:“我在书记处报告了这个情况,茅盾、周扬他们都主张我去。”双方各执一词,孰真孰假?好在另一个知情人吴奚如在《我所认识的胡风》中替胡风作证,说“胡风进入文化教育馆当编译,事先是得到‘左联’党团批准的”[4]。
茅盾主张胡风去“中山文化教育馆”编《时事类编》,但在鲁迅面前,他却装作不知情,告胡风的状。以鲁迅的睿智和对胡风的了解,他自然知道茅盾在说谎。
三、文学观不同带来的意气之争
茅盾在开始写作时,就注重观察,强调反映现实,《谈技巧、生活、思想及其他》一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文艺观。在此文中,茅盾强调,倘想写出成功的作品,光观察当然不够,你的观察还必须深且广。另外,茅盾还指出,文坛的贫血症,主要还是由于思想深度的问题。他认为,一个作家思想深度不够,就免不了要迷惘自失。
在胡风看来,茅盾的话似乎有些隔靴搔痒,没说到点子上。
胡风认为,作家能否写出好作品,与作家的主体精神密切相关。胡风没有直接批评茅盾的文艺观。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一文中,胡风批评郑伯奇、罗荪的文学主张。因为郑、罗两位的文学观与茅盾极为相似,所以,胡风这篇文章也可看作是与茅盾的“隐形交锋”。
茅盾、郑伯奇、罗荪的文艺观,概而言之,就是强调观察,概括,综合描写,创造典型。胡风认为,这种论调,完全抛开了作家的对待对象(题材)的态度,作家的主观和对象的联结过程,作家的战斗意志和对象的发展法则的矛盾与统一的心理过程。
胡风认为,如果按照这种解释,而所谓典型也就势必成为一种七拼八凑的、图解式的、死的东西了。
胡风指出,由于茅盾的文艺观不理解文学活动的主体(作家)的精神活动状态,不理解文学活动是和历史进程结着血缘的作家的认识作用对于客观生活的特殊的搏斗过程,于是,茅盾的见解就从文学的道路上滑开了,把文学变成了非文学,也就让文学自己解除了武装。
茅盾的观点是,文艺家在创作时首先要如同社会科学家那样经过由具体到抽象,由表象到概念的过程。胡风同意,创作过程可能而且应该受合理概念的领导,限制,但同时,他又认为,文学还有它自己的道路,文学的认识作用要求作家的意识在特殊的方法上最高度地进行搏斗。
列宁认为,作家所描写的主题应是作者所非常熟悉,经历过的,深思过的,再三感觉到的。茅盾也主张作家要写自己“非常熟悉,经历过的,深思过的”,而胡风却特别看重“再三感觉到的”。他的理由如下:
“为什么必须‘再三感觉到的’呢?作家的认识作用是形象的思维。并不是先有概念再‘化’成形象,而是在可感的形象的状态上去把握人生,把握世界,这就必须在作家的意识上‘再三感觉到’。艺术的表现能力正是艺术的认识能力的一面,只有有艺术的认识能力才能有艺术的表现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充分估计作家的生活实践和他的主观精神力量。”[5]
茅盾强调观察,认识,看重作家的技巧;而胡风则认为,作家的生活实践和对生活的态度至关重要。由此可知,胡风与茅盾的文学观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原本属于很正常的事。观点不同,可以探讨,可以商榷。但两人不该上纲上线,把学术争鸣演变为意气之争,甚至乱给对方扣帽子,打棍子。
胡风讥讽茅盾的创作观是“客观主义”,而茅盾则咬定胡风之所以赞扬“主观精神力量”是因为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上。
1945年后,胡风的文艺观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一开始,胡风还能进行争辩,予以回击。但到1949年后,胡风的言论空间越来越狭窄。在这种情况下,茅盾利用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做总结发言的机会,对胡风频放冷箭。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说,容或有探讨和商榷的余地。但茅盾在发言中以不由分说的口气,将一个学术问题上纲上线到政治立场问题。他断言,坚持“主观战斗精神”,是因为没有放弃“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问题的实质是:文艺作家当然不能采取‘纯客观’的态度对待生活,但文艺创作上之所以形成种种偏向主要是作家太多地站在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上面?既然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思想与情调阻碍我作家去深入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那么解决这一问题,作家们就应该彻底放弃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立场,自觉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与人民大众相结合。”[6]
茅盾这番话把文艺论争演变为文艺批判。作为被批判者,胡风已失去了和对方平等论争的权利。
1929年9月,胡风和同学朱企霞一起去东京。一上船就看见秦德君。胡风认识秦德君。她是胡风以前的老师穆济波的妻子。秦德君告诉胡风,她和穆早已离婚,并和茅盾在东京同居,这次是回上海为茅盾讨版税。两人从东京回到上海后,在茅盾发妻孔德沚的眼皮底下还同居了四个多月,最终茅盾还是未能顶住压力,在秦德君第二次人工流产后不告而别,回到了发妻的身边。
对于和秦德君的这段感情,茅盾讳莫如深。而胡风正是茅盾这段感情经历的重要见证人。胡风在回忆录中他写下这段话:“茅盾和秦德君回上海后不久就分手了。他俩中的一人(记不清是谁)把他们分手的照片寄给了我。我和茅盾的关系后来有了很大变化,甚至发展到格格不入。他回忆录中有一些对我的不实之词。这一切应该有思想感情上的原因的。”[3](p296)
胡风这样说有些情绪化,事实上,胡风与茅盾的“格格不入”,根本原因还是文艺观的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