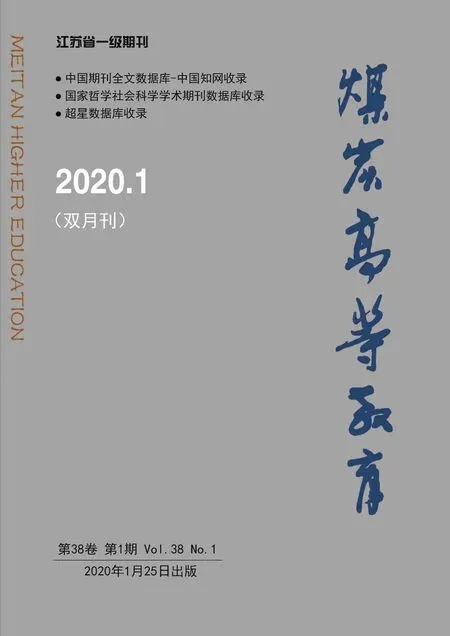大学学术自由的时代境遇
董 菁,李海龙
众所周知,知识探索需要自由就好比鱼需要水一般。那些顶尖大学无不崇尚自由探究的精神,并不断以追求真理的态度对自由权利进行佑护,近代科学也因此诞生。学术自由的存在需要三个决定性因素:理念是源头、制度是保障形式、变革提供动力。学术自由在制度上的衍生物是大学自治,二者共同造就了大学在理念与权利上的卓越。历史上,学术自由经历了时代的调和,不仅同大学和知识形成了亲和力,更融入了社会观念与国家意志中,变成观念共识。如果说科技是推动时代进步的第一生产力,那么学术自由应该称之为驱动科技发展的首席动力。正如罗马城并非在一天之内建成一般,学术自由理念和制度也经历了时代的锻造,如新鲜空气一般不断被注入大学中。到今天为止,学术自由已经成为卓越大学最值得被捍卫的精神领地,在制度与权利上都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
一、学术自由如何源起
1.从理念到制度的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从天然理念到形成制度体系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学界普遍认同的是:学术自由是一种源于西方形而上哲学的理念,从一开始就存在于知识探索的土壤中,到了今天则成为探究真理精神与权利的结合。然而任何理念都不是无源之水,纵使理念的知识与精神源头无比抽象,也有时代和环境为其打下的烙印,从理念到权利需要社会观念、规则与行为方式的长期塑造。“一个共同体内权力、地位、财富或特权的变化,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特征并不能轻易从生物学中衍生出来。”[1]大学是学者寄居的学术共同体,其自由探究的权利也经历了从学者群体扩散到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的漫长历程,正因为如此,对自由理念的向往才能成为所有大学共同的精神与知识认知。不论是“自由七艺”还是自由权利,如果没有理念种子在历史土壤中生根发芽,就不会衍生出权利与制度自由的茂密丛林。正因为知识向往自由理念,大学才能将自由视为精神内核。
今天学术自由的制度源头来自于大学出现之前欧洲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和行会制度。中世纪的欧洲宗教观念盛行,基督教教义以二元论理念来划分世界,精神世界中的知识探索活动不受物质世界的纷扰。“知识是对人类处境的理解,对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的理解。这样我们可以从物质世界的束缚下得到解放。”[2]学者和教士的职责一样,两者的精神活动都建立在超世俗的基础上。宗教本身的存在目的不是为了通向彼岸世界,而是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真理的启示,摆脱奴役。在物质世界中,自由以特殊权利形态被共享,在精神世界之外,自由、自治的特权被学者和城市市民所分享,这些特权可以维护不同群体各自的精神世界不受侵害。学者的自由权利则要依托西欧早期发达的社会分工获得发展。“西欧封建社会是在罗马奴隶制度崩溃和日耳曼氏族制度瓦解的基础上,由这两个过程互相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综合的制度。”[3]自由特权与自由理念的存在催生了分工和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一方面,这种社会制度使得社会成员的阶层分布更加具体化,分工所产生的生产力更发达;另一方面,让市民阶层成为一个独立的话语群体登上历史舞台,学者们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市民阶层。有了发达的城市和市民阶层,就有了城市自治下的行会自治制度,每个行会都拥有不受外界侵犯的权利和行业自由。也就是说,自由探索知识的权利和自由交易一样都是受保护的行会特权。而这种权利则是各种行会长期与外部斗争的结果,最终以特许状的形式确定下来。“事实上,自由和法治的特征都体现了一种契约观念。契约的特点在于双向性抑或权利义务对等,构成西方文明的理念,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典时代。”[4]基督教思想的二元世界观划分结合了行会制度,是构成学术自由理念和制度的重要来源。
2.早期学术自由的制度根基
自由之于学术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学术自由却不是肤浅的、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学术自由产生和发育的土壤与养料有着鲜明的普世性,这种形而上的精神气质伴随着人类的进化过程,也渗透进不同的国度成为时代和社会特征,学术自由的演进过程实际上是这些普世性价值的体现。
中世纪孕育出了大学这种特殊的社会产物,不论是学生们为了追随欧内乌斯学习辩证法而诞生的巴黎大学,还是研修民法而聚集起不同学者的博洛尼亚大学,特定的社会发展状态是大学之母。高等教育和高深知识的交流则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类主观需求的结果。教会、世俗君主以及贵族、市民阶层都需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理论,高深知识的拥有者得以拥有一席之地。与人们理解的黑暗中世纪有所不同的是,宗教力量还并未强大到一手遮天的程度。恰恰是基督教哲学中的宽容理念和普世价值才维护了自由理念。“它支持和传播了一种关于规则、一种高于一切人类规律的思想。它为了拯救人类,提出了这个基本信念,即在一切人类法则之上存在着一条法则,……它有时称为理性、有时称为上帝的法则。”[5]事实上正是因为教会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才让社会生活的运行步入正轨,对高深知识的需求才能由少数个体变为整个社会的群体化行为,没有基督教精神和教会的影响,大学的崛起时间只会被推迟。这种理性的精神力量为科学发展冠以明确的价值导向,并提供了充分的佑护,使科学的发展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欧洲的基督教伦理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相契合,最终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和学术。
3.学术自由的理性根源
按照早期西方知识探索的脉络来看,不论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经义解读,还是带有实用气息的律法研修,西方学者对于知识的加工与传播经历了一个由“理性—知性—人性”的过程。古代西方学者对于宇宙和世界的思考源于宇宙和真理都具备理性的属性,例如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自由归于理性之中,自由的知识被理性的人感觉和学习。这种知识的传播是为了使人自己认识外界。故而,自由知识需要探索的权利,需要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特权。
在人类认知能力相对落后的年代里,宗教被认为是通达真理的渠道,在基督教教义中,上帝的角色兼具神性、人性和理性,所以对知识的探索就是利用理性实现与神交流。理性知识是人与神的中介,而这种中介必须要予以实质性的自由权利才能发挥其效用,塑造理性认知成为了学术自由存在的知识基础。“在学术自由存在的合理性的三个方面中,认识方面的原因是最主要的。”[6]所以说,神性、理性以及人性构成了学术自由形而上的源头。以自由七艺学习的形式,可以达到认识自己和世界并且通达神性的目的。训练学者的方式除了对经典的解读之外,更在于培育学生敢于质疑、批判的自由气质,主要的手段是辩论和诘问经典。正如涂尔干所认为的:“如果从一种特定的角度来看,人文主义者为教育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恰恰是让学生们反思性地思考人事,至于经院哲学家们就更是如此了。”[7]虽然有人一度认为中世纪学术在宗教神权控制下无比黑暗,但教会、学者和这种理性的精神的传播不曾断裂,自由知识带来的权利以理性的名义却被尊重。
到了近代,随着宗教改革的完成,理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知识不再通往神性,而是直接为社会物质生产服务。比较突出的是德国大学的崛起。从表面上看,德国大学是威廉二世支持下建立并享有各种权利,实际上则要归因于德国本土成熟的古典理性传统所培植出的精神特质。个体的精神自由构成了整个民族自由灵魂的起点。而且国家应该保护这种个体的精神自由,从而保障知识探究的权利。对于这种民族理性的自由认知和追求是德国古典大学观现代化气质的源头。而英国新大学运动建立的学术气质则是由近代科学带来,这种自由的风气体现在打破了原有大学教籍、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反过来又对近代科学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高等教育的内涵被新崛起的大学重新定义。“‘高等教育’中的‘高等’理念意味着一种对既定意愿的超越(无论概念、理论还是行动上),而不是受制于它。”[8]超越与不断突破正是学术自由从近代科学精神中所提炼出的,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二、学术自由变革的驱动因素
1.学术权利的制度化
从进化史来看,人的自然天性崇尚自由,而社会角色则要求遵守律令,有效处理自由与规则之间的关系便成为整个人类历史都要面对的问题。两者似乎在表面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但现实中制度与规则不仅保护自由权利不受侵害,而且开辟了高深知识社会化传播的空间。“人的自我认知有限性,人的自我辩解本能(常常体现为特定阶段的科学结论)和强大的依赖心理则遮蔽了一个更为深层的现象,即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或控制手段,乃是人类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反自然的选择。”[9]在种种外界权威压制之下,知识天生的脆弱性表露无遗,故而学术自由的制度理应为知识的发展保驾护航。今天学术自由代表着双重意义:一是,学者思考和探究真理天然的自由权利;二是,有独立裁决学术事务不受外界干涉的权利。
学术自由从一种思想理念演变成一种成熟的制度,并且能够成为各方接纳成为一种价值共识,并不单纯是由于知识探索职业的崇高,还因为欧洲大陆逐渐形成的文化及法律土壤。中世纪之初,各种法人制度就成为规范行业和社团行为的依据,社团法人的地位平等。学者会并非是享有特许状的唯一群体,各行各业都拥有自己的法人地位。特许状代表了一种契约制度,同法人制度的结合成为今天西方大学学术权利的基础。“社团法人角色的出现在法律理论方面引起了革新,从而使一系列社团新形式和新力量的创造成为可能,……此外,社团法人这一法律理论还在宪政原则的轨道上确立了一系列的政治理念,如立宪政府、政治决策一致、政治代表权和法律代表权、司法审判 权,甚至自主立法权等。”[10]上 至教会、国王,下至贵族、市民能够达成制度上的共识,这就有效减少了外界对学术发展的掣肘,使自由理念能够以制度的形式被全社会接受。
启蒙运动之后,教会权威虽然瓦解,但神学伦理的权威仍然有效。在学者群体中遵守宗教戒律,坚持以一种无私利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不论是显得略有陈腐的英国古典大学,还是以接纳近代科学精神崛起的柏林大学,宗教性的自律成为每个学者维护真理价值的戒条。对基督徒来说,教义和自身信仰本身就是一部法律。信仰为知识探究与理性思考拓宽了空间,使得学术精神能够从中获得立足之地。从外部来说,由于法人角色同社会契约作为约定的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即使是取代教会的王权,也在遵守古代罗马《查士丁尼法典》的条文,在世俗和信仰世界中,法律的权威得到最大的尊重,并能保护个人的权利,这让知识探究的自由权利由理念成为正式的制度,也使得大学能够保持独立的属性,并能有创新与探究的场所。
2.知识理念的变革
学者们在大学建立之初,就始终以真理探索为最高权威,但这种真理权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功能的变革才能保证自由从理念到权利的延续。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预设了一个独立的理性世界,这成为知识唤醒自由的源头。由于理性启蒙的完成,人就会摆脱被自然奴役的状态。如果从事智力活动,则会获得高于体力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教育是后来学术自由中学习自由、教学自由的最初起点。到了大学建立的11世纪、12世纪,研究高深学问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学位、学衔制度使学者们得以立足成为一个行会的群体,“学术自由实际上是机构自由和个体自由的统一”[11]。学者们自由属于知识带来的天赋,而大学自治则来自于行会特权。学术自由特权的形成是随着知识自我合法化而实现的。
自由的权利来自于知识探究的理念,没有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基础,权利就会发育不全,大学精神权威也正是自由理念与权利驱动的结果。“确立大学地位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大学选拔和发展了拥有合适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品质的人才。”[12]在笛卡尔将物质与精神作了二元划分之后,康德完善了其思想,提出了理性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重世界观。真理的探索归于理性世界,并且学者在理性世界可以形成极高的道德修养。“知识即美德”即为学者们信奉理性世界的圭臬。理性世界的精神活动不受外界干涉,学者们是探究未知的使者,也是上帝在世间的权威,学者们心中的道德律令和头顶的星空一样宽阔。“人的真正目的在于最圆满、最协调地陶养其各种潜能,使之融为一个整体。而自由是这一修养的首要、必备的条件。”[13]这种知识理念是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参照准则。民族国家的崛起不在于武力,而在于武装了智力的国民和教授的大学。“知识的主体不是人民,而是思辨精神。……合法化语言游戏不是政治国家性质的,而是哲学性质的。”[14]在高深知识形成的“文化国家观”中,学者们和国家拥有共同的目的:通向哲学真理的圣殿。因此,国家必须在理念上和形式上保证学者研究、教学和学习的自由。学者和大学坚持科学、修养、自由和寂寞的准则,用智力财富回报国家,这也构成了影响至今的德国古典大学观。
3.学术自由制度的集体运作
如果说在欧洲大陆的学术自由有着较强的思辨渊源,有历史悠久的理念的话,那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术自由思想及学术权利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进化方式。“美国学术自由的主要矛盾相继经历了科学与神学、科学与财富、科学与政治的对立,学术自由斗争的主要任务分别解决理性与信仰、大学与政府、学术与政治的冲突。”[15]虽然在知识起源上,欧洲和美国有相似的地方,但美国学者在争取学术权利时,“斗争”和“集体”的味道则更要浓烈。
同欧洲部分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教育从建国以前就是分权制的形式,国家政治力量对大学和民众的影响远不及中央集权国家。民众和学者所秉持的是以自然法和习惯法为交往秩序,天赋人权,生而自由的法理观念在大学学者和民众身上表现的同样突出,这样一来的问题是学术自由与公民言论自由在法律界定上的困难。“在美国,刚开始,学术自由不是宪法和其他的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教师和学生的权利,而一般的思想、言论自由则是一种受到宪法保护的公民自由权利,侵犯公民思想、言论自由的行为可以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对待违反了学术自由的行为,则只能够企求于社会团体或个人的良知加以保护。因此,不同于宪法所规定的保护思想言论自由的机制,学术自由要求更为特别的保护。”[16]争取行会自治与自律的制度保障也成为了美国大学学术自由权利的最大特色。
在美国大学管理模式上,校外非学术人士所担当的角色非同一般。一方面,他们可以平衡学校与政府以及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董事会的存在也会干涉到学术生活,妨碍到学术权利的运作。故而,1914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组建就是为了弥补后者对学术自由的侵害,并起到监督作用。同时,终身教授制度保障了学者的职位安全,利用职位安全保障自由的权利。工会、AAUP、AFT(美国教师联合会)的集体行动成为了影响董事会、政府的主要力量。关键在于让社会认识到:“如果大学没有全面接受和贯彻落实学术自由的原则,那么大学就不能履行它的三大功能。从总体上看,大学是为社会而存在,任何限制大学教师自由的行为都将影响大学的效率,破坏大学的精神,最终损害社会利益。”[17]所以说,美国学术自由的集体特色引发的扩散效应更能得到各方关注。
三、学术自由的载体需要时代担当
时至21世纪,中国的大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岁月,作为一种舶来的产物,中国大学已经形成了世界瞩目的数量规模,在知识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随着时间演变,愈演愈烈的是学术腐败层出不穷,大学内部严重的科层化以及学者公信力的一再下降。看似是学术相关的道德问题所牵扯出的是民众对高等教育、对学术发展的失望与愤怒。实质上,则是学术自由失去了应有的载体,自由的权利在制度上缺乏有效制衡,缺乏理性的自由理念。
从学术自由的角度看待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可以发现,知识探究创造的自由理念其实远甚于西方。中国古代虽然以儒家一说治天下,在汉以后的历史中并未出现如西方社会中要为科学殉道的范例,尤其在面对科学的到来时,科学传播的途径更加通畅。正如涂又光所言:“对比起来,科学的兴起,在西方何等艰难,要以科学先烈的生命为代价;在中国何等顺利,有点成熟就会受到称赞和尊敬。想一想原因何在?专就文化而言,就因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多了一个道家。”[18]可见,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包容性的学术自由种子是存在的,况且20世纪初中国大学的辉煌和自由探究的学术之风盛行一时。然而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学术自由遭遇的危机与困境却逐日凸显。
保障学术自由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独立的制度,独立的制度运行的核心取决于学者们能否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拥有何种精神气质。现代性和学术资本主义的侵蚀所带来的影响固然不容忽视,但我们能否继承前人风骨,回归“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理性信仰才是要求权利的核心。现代社会中学术自由危机呈现弥漫的态势,当代美国也曾遭遇过“麦卡锡主义”和“忠诚宣誓运动”的威胁,但仍有学者为真理而斗争,不惜以被解雇的危险而争取权利。今天的学术自由更需要具有担当的载体,从精神到制度确立朝向真理的气质,在知识上坚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才能达致“大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