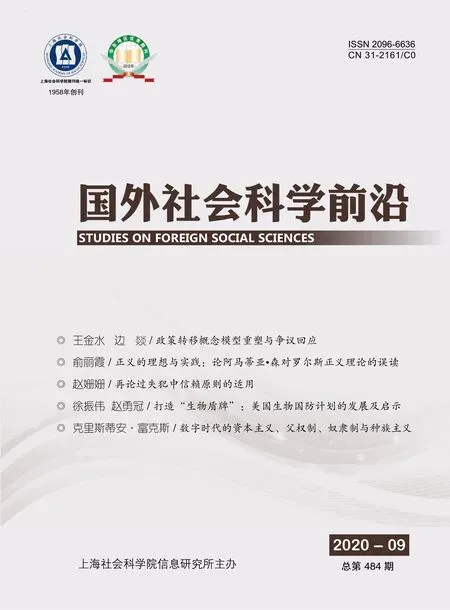再论过失犯中信赖原则的适用
——对深町晋也教授化解危险接受困局思路的扬弃 *
赵姗姗
内容提要 | 在新过失论的构造下,信赖原则是有关过失犯客观预见可能性的原则。这一原则,对判断现代社会中过失犯的成立与否具有重要价值。关于信赖原则的适用,日本深町晋也教授借助该原则剥离出危险接受案中具有刑法意义的过失的思路具有启发意义,但以“理性”为基础的经验法则因过于主观而不十分可靠。在对深町教授之见解的扬弃过程中,应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情,重构信赖原则的适用规则。即,将规范信赖作为事实信赖的依据,并针对危险接受案、监督过失案、交通事故案的具体类型,适用不同的处理路径,以判断是否成立过失犯。
一、有关信赖原则的观点聚讼与研究现状
(一)观点聚讼
所谓信赖原则(Der Vertrauensgrundsatz)的最初含义,是指“一切交通关系的参与者,在依据交通规则而信赖其他参与者会采取适切行为的场合,对于该其他参与者之不适切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不承担责任的原则”。1西原春夫 《交通事故と信頼の原則》 成文堂,1969,14页。首次适用该原则的刑事判例是德国1935年12月9日帝国裁判所的判决,2RG St 70-71.其后联邦裁判所在1952年7月8日的判决中最先明确采该原则。3BGH St 3-49.1959年,信赖原则经由西原春夫教授引入日本,并在日本1966年的判决中第一次被正面适用。我国台湾地区适用信赖原则的判决始于1981年,该判决称:“汽车驾驶人应可以信赖参与交通行为之对方,亦将同时为必要之注意,相互为遵守交通秩序之适当行为,而无考虑对方将偶发的违反交通规则之不正当行为之义务。”41981年台上字第6963号判决。其后,历经1985年判决对适用规则的进一步说明与诸判决的阐释,51985年台上字第4219号判决。我国台湾地区“信赖原则之适用,已无任何争议矣。”6廖正豪:《过失犯论》,三民书局,1993年,第206页。
关于信赖原则在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位置,学界见解不一,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主张:首先是,否定构成要件该当性说。该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过失犯中的客观注意义务由客观的结果预见义务与客观的结果回避义务构成,采纳信赖原则,是将客观注意义务的内容加以具体化的原则。7参见陈子平:《刑法总论》,元照出版公司,2017年,第222页。具体而言,有的学者认为,信赖原则关乎的是预见可能性。例如,学者指出,“信赖原则,是将客观预见可能性这一抽象标准进行具体化的原则”;1曾根威彦 《刑法総論(第4版)》 弘文堂,2008,176页。“ 旧过失论下,信赖原则在体系上无从定位。然而,作为预见可能性对象的行为不单是行为,而是对法益有实质危险的行为。……在信赖原则发挥作用的场合,行为人的行为便不具有实质危险性,从而便从预见可能性的对象中被排除。据此,信赖原则关联的是预见可能性问题。”2堀内捷三 《刑法総論(第2版)》 有斐阁,2004,130页。此外,一部分学者的关注点并不在客观的预见可能性,而是认为信赖原则关乎客观结果回避义务。例如,学者指出,“信赖原则,从行为危险性的角度来看,是限定结果回避义务的原则”;3山口厚 《刑法総論(第3版)》 有斐阁,2016,257页。“ 如果预见可能性仅有危惧感就足够了,那么,信赖原则并非是否定预见可能性的原理,而是免除风险负担、否定结果回避义务的原理。”4高橋則夫 《刑法総論(第3版)》 成文堂,2016,232页。上述两类观点以外,在否定构成要件该当性说中,有的学者并不从注意义务的内容上探讨信赖原则的机能,而将信赖原则的作用机理聚焦在因果关系上,认为适用信赖原则的场合会产生与因果关系的交错,并通过否定相当因果关系,进而否定构成要件的该当性。5参见岡野光雄 《刑法要説総論(第2版)》 成文堂,2009,199页。其次是,违法阻却事由说。主张此见解的佐久间修教授指出,“信赖原则具有决定如何在加害者与被害者间分配注意义务的侧面,与交通领域中危险分配的法理存在表里一体的关系。基于这一意义,信赖原则是将被容许的危险或适度的危险具体化的法理,左右着过失犯的违法性。”6佐久間修 《刑法総論》 成文堂,2009年,153页。再次是,否定或减轻责任事由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中,有的学者认为,“在有合理根据可以信赖对方能够采取适切行动的场合,否定行为人主观上的注意义务”;7神山敏雄 “信頼原則の限界に関する一考察” (西原春夫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編集委員会編《西原春夫先生古稀祝賀文集(第二卷)》,1998,成文堂),49页。“ 信赖原则的机能无非发挥在注意义务的领域……乃是否定作为责任要素的主观注意义务的原则。”8立石二六 《刑法総論(第4版)》 成文堂,2015,253页。但有的学者却认为,适用信赖原则并非是对主观注意义务的全部否定,而是“在新过失论中,适用信赖原则减轻了行为人的责任”罢了。9大 越 義 久 《刑 法 総 論(第5版)》 有 斐 阁,2012,141~143页。最后是,既否定客观构成要件该当性又否定责任说。这一立场的代表学者为林干人教授,其指出,“信赖原则既可以否定客观注意义务,也可否定责任,哪一方也无法一家独大。”10林幹人 《刑法総論(第2版)》 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298页。
以上聚讼源自学界对违法性本质认识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了学者对过失犯构造的理解。例如,立足于行为无价值的新过失论者通常认为,信赖原则应被定位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只是对该原则具体影响了何种要素(客观结果预见可能性、客观结果回避义务或因果关系)存在分歧。而结果无价值论者则分为两派:旧过失论者不承认构成要件的过失,故适用信赖原则的场合只能主张否定责任;而修正的旧过失论者因承认过失实行行为,故也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检讨信赖原则的机能。在部分修正的旧过失论者看来,过失实行行为是对法益具有实质危险性的行为,而所谓的“危险”意味着客观的预见可能性。11曾根威彦 《刑法における実行·危険·錯誤》 成文堂,1991,62~68页。既然适用信赖原则否定了这种预见可能性,自然也否定了实质危险,进而否定了过失实行行为的存在。
(二)当前理论研究的不足
溯究信赖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可以发现,其脱胎于被容许风险的法理所确认的风险分配理论,或者说与被容许风险、风险分配理论互为表里,承担着缩小注意义务的范围、适应现代发展需要的机能,具有进步意义。尽管关于信赖原则的体系位置尚存在诸多分歧,但是,既然学界承认该原则在体系上有所定位,则无异于认同其在限缩过失成立或减轻过失责任方面的价值。因此更多的学者主张,信赖原则可以适用于交通事故以外的其他领域。对于这一主张,早在该原则被引入日本之初,西原春夫教授即提出,“在过失犯的场合,特别是由第三人或被害人的行为惹起结果的场合,可将信赖原则广泛用于过失犯的认定。”1西原春夫 《交通事故と信頼の原則》 成文堂,1969年,14页。在后来的研究中,学界通常认为信赖原则可用于划定医疗过失、公害过失、企业灾害、监督过失中注意义务的范围。2参见苏俊雄:《刑法总论Ⅱ》,1998年,第494页;廖正豪:《过失犯论》,三民书局,1993年,第210~233页;佐久間修 《刑法総論》 成文堂,2009年,152页。但不尽人意的是,该原则虽曾备受关注,但在近四十年中有关信赖原则的研究却无突破性进展。对适用规则的归纳也主要局限于交通事故领域。例如,通说认为,在行为人本人违反交通法规、容易预见对方会违反交通规则、不能期待对方(如年老者、幼儿、残疾人、醉酒者等)遵守交通秩序、在道路有冰雪而事故可能高发的场合等,不得适用信赖原则否定过失。3参见岡野光雄 《刑法要説総論(第2版)》 成文堂,2009,197~198页。而在现代社会频发的医疗事故、公害事故、企业灾害、监督过失等领域如何适用“信赖”,至今并无公认的规则。在相关研究中,日本的深町晋也教授将信赖原则用于化解危险接受困局的思路具有启发意义。笔者将在下文引介这一思路,通过剖析其优势与不足,尝试构建信赖原则在不同领域的适用规则。
二、适用信赖原则的新尝试:日本深町教授化解危险接受困局的观点引介
(一)危险接受的归责路径之困
以信赖原则判断危险接受案件中过失的成立与否,可谓深町教授颇具开创性的见地。所谓危险接受,旨在描述被告人基于被害人的意思对被害人实施了危险行为,却违反了被害人的意思而导致法益侵害结果的场合。4参见山口厚 《刑法総論(第3版)》 有斐阁,2016,183页。也即,被害人已认识到他人行为的危险性,对该行为对自身法益可能造成的侵害存在认知,但仍基于自身意志置身于危险之中,以至导致了危险的现实化。5参见恩田祐将,2010,“危険引受けにおける承諾型と非承諾型の区別” 《通信教育部論集》 13:67~86。此类案件的难点在于,在双方事实上的过失导致了法益侵害结果的场合,如何对被告人的行为作出定性。对此,学界基本的立场是,危险接受中被害人接受的只是行为,而非结果,故危险接受的理论构造不同于被害人同意,从而无法将接受危险作为违法阻却事由。至于究竟如何解决对行为人的定性问题,学界亦是歧见迭出。当前较为有力的主张是在双方过失中确定一个具有支配性的过失,如果被告人的行为具有了支配性,那么其至少符合过失犯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对此,德国早已存在一个事实支配理论,以危险在事实上由谁支配来探讨归责——在被害人起支配作用的场合,德国的通说认为被告人在原则上不可罚;但在被告人起支配作用的场合,德国至今也未达成一致见解。6参见岛田聪一郎:《被害人的危险接受》,王若思译,《刑事法评论》2013年第1期。我国提倡该理论的学者为张明楷教授,其主张先基于一定的标准对案件进行分类,再基于分类适用不同的归责路径。划定分类的标准为事实上哪一方支配了结果的发生:在被害人起支配作用的场合,属于自我危险化的参与类;在被告人支配的场合,则归入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类。1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中危险接受的法理》,《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对于前者,张明楷教授认为,应以共犯从属性理论为依据,若正犯的行为不符合构成要件,那么共犯的行为亦不可罚,例如:
海洛因案:甲、乙均为吸毒者,甲称有海洛因,邀乙一同吸食,但提出由乙帮忙买注射器,乙同意。在二人使用乙购买的注射器各自注射后,甲因摄入毒品过量而死。2BGH Urteil vom 14.2.1984.
张明楷教授认为,甲明知吸毒危及生命仍选择吸食,居于侵害自身法益的正犯地位。鉴于当前各国皆否认自损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故甲不成立正犯。既然不存在正犯,那么根据共犯从属性原理,参与者乙则不成立共犯,从而乙也不可罚。
至于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类,按照事实支配理论,此类别中被告人的行为起了支配作用,在客观上该当了构成要件。在违法性阶层未保护更为优越利益的场合,则不存在阻却事由,从而成立过失犯。3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中危险接受的法理》,《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例如:
冰面驾驶溺水案:丙、丁在河畔游玩时,丙见冰面较厚,认为可以承载其车,遂提出驾车穿过冰面到对岸的建议,丁同意。当丙驾车载丁驶至河岔中心时冰面破裂,汽车坠入水中。最终,丁溺亡,丙得以生还。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中刑终字第1871号。
根据事实支配理论,甲作为汽车驾驶人,其过失起到了支配了作用,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
不过,在笔者看来,事实支配理论存在三点问题:其一,“支配”具有过失相抵的意味。也即,承认被支配方存在过失,只不过作用力过小,被支配方的过失所左右了。在此值得思考的是,这种带有过失共同正犯意味的“相抵”,在不承认过失共同正犯的我国刑法语境下,究竟有多大的适用空间。同时,“被支配”的过失毕竟在客观上是存在的,是否应当减轻支配方的责任;如果减轻,又如何量定其作用力的大小,事实支配理论没能解决这一问题。
其二,可能导致类别划分的暧昧。关于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张明楷教授另外提出,具有优越认知的一方居于支配地位。例如:
赛车同乘案:戊系赛车初学者,为得到行驶指导,邀请富有七年竞技经验的教练己坐在副驾驶座,并遵照其指示,使用了自己不熟悉的方法高速行驶。因减速不足,戊驾车撞上了防护栏,致使教练己死亡。
张明楷教授指出,相对于初学者戊,教练己具备驾驶赛车的优越认知,系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即便戊亲自操纵赛车,但只处于间接正犯的位置。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论断,本案应被划入自我危险化的参与类。而学界在探讨此案时,通常将其划入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类中。在笔者看来,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正在于事实支配理论对“支配”的判断略显恣意:如果着眼点在于无论戊是否遵照了他人的指示,其终究是具备正常判断能力的驾驶人,那么本案便可归入自我危险化的参与类;如果以优越认知为标准,便应归入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类。不可否认的是,现实生活中具备优越认知的群体多左右着事态发展的进程,但认为具备优越认知便应承担更重的注意义务,不免有以“主观说”判断注意能力之嫌,恐面临着“惩勤奖懒”的批判。
其三,并非所有危险接受的案件都能够划分清晰支配关系。在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事出偶然的场合,事实支配理论将面临困境。如“蘑菇案”:野外远足的情侣共同煮食野蘑菇食用,二人皆知晓其中可能混有剧毒的蘑菇,仍出于侥幸心理决定食用。在各自进食而一人死亡的场合,一般不存在过失犯的问题;在一方表达恩爱而给另一方喂食致其死亡的场合,是否应判定喂食的一方起到支配作用?如果是,对这种行为又有多大程度的处罚必要,值得思考。
关于危险接受案件困局的化解,日本学者提出了被允许的危险说、特别责任阻却说等主张,但这些主张多围绕体育竞技展开,并不具有普适性。1主张“被允许的危险说”的学者为须之内克彦教授,参见须之内克彦“スポーツ事故における同意と危険の引受け”(日高義博等編 《刑事法学の現実と展開:斎藤誠二先生古稀記念》,2003,信山社),115页;主张“特别责任阻却说”的学者为神山敏雄教授,参见神山敏雄“危険の引き受けの法理とスポーツ事故”,(《宮澤浩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第二巻》,2000,成文堂),25~26页。另有日本学者主张社会相当性说、否定行为危险性说、自我答责性理论2主张“社会相当性说”的代表学者为奥村正雄教授与十河太郎教授,参见十河太郎,1999,“危険の引受けと過失犯の成否”《同志社法学》 50(3):341页以下;奥村正雄,1999,“被害者による“危険の引き受け”と過失犯の成否” 《清和法学研究》 (6)1:105页以下。主张“否定行为危险性说”的学者为山口厚教授,参见山口厚 “‘危険の引受け’論再考”(日高義博等編 《刑事法学の現実と展開:斉藤誠二先生古稀記念》2003,信山社),96页以下。主张“自我答责性理论”的代表学者为盐谷毅教授,参见塩谷毅 《被害者の承諾と自己答責》法律文化社,2004,369页。等,针对学界对这些观点的批判,笔者亦表示认同,在此不再赘述。对于危险接受的论题,德国有学者认为,在被害人自我选择而进入危险境地的场合,被告属于未创设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刑法无需介入保护。3转引自陈璇:《刑法中社会相当性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62页。我国台湾地区的许玉秀教授也持这一见解。4参见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449~450页。既然被害人接受危险的场合非属被告创设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那么在客观归责理论中便排除了归责。这一思路也得到我国部分学者的认同。5参见王俊:《客观归责体系中允许风险的教义学重构》,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93页;马卫军:《被害人自我答责与过失犯》,《法学家》2013年第4期。在笔者看来,客观归责理论能够解决一部分危险接受的难题,但困局难言得到充分的化解。理由在于,究竟应如何理解“被容许风险”。如果从此概念产生之初的蕴意来看,应含有“社会有用性”之意。因为自卡尔·宾丁(Karl Binding)创制该概念后,卡尔·恩吉施(Karl Engisch)在1930年首先强调,其规范意旨着眼于对危险行为之“社会价值”(Sozialwert)的考量,需要考虑所追求目的之大小、发生范围、成功的机率以及法益侵害的大小与盖然性。6参见[德]Karl Engisch:《刑法における故意·過失の研究》,荘子邦雄、小橋安吉译,一粒社,1989年,第350页。换言之,被容许风险的合法依据来自将行为之有用性、必要性与法益侵害危险性进行衡量后的结论。7参见小林健太郎,2005,“許された危険”《立教法学》69:43~66。这一理解在日本得到了平野龙一、曾根威彦、前田雅英等学者得支持。8陈子平:《刑法总论》,元照出版公司,2017年,第224页。我国台湾地区的苏俊雄教授亦认为:“所谓‘冒险利益’乃属一种‘社会价值’的考量。”9参见苏俊雄:《刑法总论Ⅱ》,1998年版,第481页。那么,被容许的风险本身应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毕竟没有积极意义的“风险”并无被容许的理由),否则便与创制这一概念的初衷相悖。如此一来,将被容许风险用于危险接受中以否定过失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因为危险接受案多发生于一般生活场合,与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风险领域未必相关。此外,对被容许风险还存在另外一种理解,即,如果风险发生在社会伦理规范或社会相当性范围之内即可以被容许。这一理解并不包含利益衡量的色彩,可以将对社会无害的行为囊括其中。例如,克劳斯·罗克辛(Claus Roxin)教授所归纳的创设不被容许的风险表现为:(1)违反具体规范;(2)违反交往规范;(3)无信赖原则可以适用;(4)未尽询问义务与不作为义务;(5)于社会并无用途与价值等。1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716~734页。依据这些规则,任由他人接受属于自决权范围内的风险的行为未违反(2)之交往规范,故属于被容许的风险。不过细究罗克辛教授归纳的上述规则可以发现,其与新过失论中违反客观注意义务的情形并无二致。如果客观归责理论中的制造法不容许的风险等同于新过失论中对注意义务的违反,那么此时面临的便是对过失犯构造的选择问题。考虑到构建在行为无价值论基础上的新过失论更具有引导国民遵守一般准则的功能,笔者倾向采纳新过失论探讨过失犯的相关问题。
(二)以信赖原则化解危险接受困局的尝试
关于信赖原则的体系地位,深町教授认为该原则所影响的是客观结果预见可能性,且不必然局限于交通领域。关于如何影响预见可能性,深町教授借助了“经验法则”这一概念,认为危险行为所关联的结果之发生或不发生,是由多种次元的危险增加要素与危险减少要素所组成的。依据一定的经验法则,如果危险减少要素增加了,那么正常的发展逻辑是侵害结果不出现。同时,出现的结果即属罕见。既属罕见,便能够否定相当因果关系或客观归责。深町教授认为,在行为人信赖经验法则且在具体情形中无法预见存在打破经验法则之事由的场合,难言其对结果的发生存在高度的预见可能性。对于缺乏预见可能性的行为,自然无法作为过失定性,故过失犯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不成立。
关于“经验法则”的内涵,深町教授将之解释为“被害人的自我保护”。然而,问题在于,从危险分配的法理出发,通常情况下明确规定被害人“必须自我保护”的法规范并非普遍存在。对此深町教授的回应是,法规范不存在无法论证出经验法则不成立,“被害人的自我保护”这一经验法则在某些条件下仍可以得到肯定。因为一个“自律”的法益主体皆有自我保护的本能,面临对自身法益的侵害能够采取回避的举动。但深町教授亦认为,经验法则并非无条件启动,而首先有赖于法益主体的主观认知,或者可以说,是从“危险认知——本能地保护自身利益”这一过程里推断出来的。不过,对危险的认知仅是必要条件,即便被害人对危险有所认知,也存在经验法则不成立的情形。例如:(1)被害人缺乏答责能力;(2)被害人当时无法回避危险;(3)相对于被害人,行为人居于更易回避危险的地位等。2参见深町晋也,2000, “危険引受け論について” 《本郷法政紀要》9:121~162。深町教授用上述思路分析了“赛车同乘案”,认为教练已谙知赛车的危险性,相对于戊具备优越认知,并通过对戊的驾驶指导,在一定程度上有遏制危险的机会。由此判定,戊信赖己能够提供适切的指导。换言之,案中的己能够通过适切的指导以控制危险减少要素,故存在“己可以回避侵害结果(可以自我保护)”的经验法则。因此,戊对己的死亡不存在具体的预见可能性。同时,深町教授分析了“河豚案”。该案的基本案情为:明知河豚肝脏可能带有剧毒的顾客仍于某料理店食用了河豚肝脏,提供河豚肝脏的被告系取得河豚料理资格的厨师,尽管如此,最终顾客还是中毒身亡。3最决昭和55年4月18日判例 《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34(3),149页。在深町教授看来,面对已取得河豚料理资格的厨师,顾客可以对其抱有“能够提供安全食物”的信赖;基于此,厨师便无法对顾客适用“自我保护”经验法则,从而不能否定厨师过失的成立。
三、拿来的辩证:事实到规范的过渡
(一)深町教授观点的启示:剥离出刑法上的过失以回避“过失相抵”
危险接受困局的核心在于,在双方事实上的过失均对结果产生作用力的场合,如何剥离出其中具有刑法意义的过失。显然,在深町教授看来,适用信赖原则的场合一方对结果的发生没有预见可能性,故没有过失实行行为。也即,其中一个事实上的过失未被评价为刑法上的过失。这一观点令危险接受案的处理思路清晰些许。而在事实支配理论下,需从双方事实上的过失中找到起支配力的一方,那么“支配”的判断过程多少带有过失相抵的意味。毕竟过失相抵通常以“斟酌考虑受害者的过失从而限制加害者的损害赔偿债务”这一形式去呈现。1[日]圆谷峻:《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权行为法》,赵莉译,法律出版社,2008,第216页。但事实支配理论无法充分说明,既然双方过失均对结果产生作用力,被支配的过失是否减轻被告的责任;如果能够减轻,幅度又是多少。我国既有的判决虽未言明采纳了过失相抵,但事实上也带有这一色彩,处罚结果无非也是“各打五十大板”,难言能够划分清双方应承担的责任。例如:
田玉富案:田某之妻康某因违法生育第三胎,被计生人员带至计划生育指导站实施结扎。田某为让妻子逃走,用备好的尼龙绳系在康某胸前,将其从窗户吊下。途中绳子断裂,康某坠楼身亡。
法院认为:田某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却没有预见,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2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05)麻刑初字第111号。同时实务观点指出,案中二人均存在过失,但我国尚不承认过失共同犯罪,故无法将二者的行为进行整体评价,只能单独评价被告人的行为。在被害人有明显或重大过错的场合,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3杨建华:《田玉富过失致人死亡案》,《人民法院案例选(分类重排本)4·刑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第1777页。如此结论,显然是民法处理与有过失的逻辑归结。
所谓“与有过失”,亦为民法上侵权责任部分的概念,是指侵权人与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均存在过失原因力,乃双方过失造成了同一损害结果的情形。4参见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与案例评注·侵权责任篇》,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76页。与有过失的后果即过失相抵,在日本称为“过失相杀”。我国民法典中亦有过失相抵的规定,例如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我国的民法学通说,过失相抵的理论基础为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可以使损害在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得以合理分配。5参见程啸:《过失相抵与无过错责任》,《法律科学》2014年第1期。
虽然事实支配理论与实务的处理方式多少带有过失相抵的意味,但细解深町教授的主张可以发现,适用信赖原则的场合并未给过失相抵留下空间。因为信赖所依据的“被害人的自我保护”这一经验法则并非无条件地启动。在符合信赖条件的场合,一方的过失在刑法上得以被否定。这一理解也符合最早将信赖原则引入日本的西原春夫教授的观点。西原春夫教授认为,尽管信赖原则发挥作用的过程与过失相抵十分类似,但并未援用过失相抵理论。理由在于,过失相抵的法理以双方皆有过失为前提,被害人的过失并非减轻或否定加害人的过失,只是减轻加害人应偿付的金额罢了。而信赖原则的作用机理却是,在被害人有过失的场合,加害人基于对被害人的信赖否定了自身过失。在不存在双方过失的场合,始无“相抵”之余地。6参见西原春夫 《交通事故と信頼の原則》 成文堂,1969,24~25页。
在笔者看来,西原春夫教授的上述阐述仍未触及信赖原则与过失相抵间差异的本质。笔者认为,民事侵权可适用“相抵”,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民事侵权不排斥共同过失,这一点在日本与我国均有体现。例如,日本民法第719条(共同侵权行为)第1款规定:“因数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加害于他人时,各加害人负担连带赔偿责任,不知共同行为人中何人为加害人时,亦同。”此条文中的“共同”“加害”如果用置于刑法学领域,通常仅用于描述故意。但根据作为日本民法学通说与判例立场的客观关联共同说,只要两个(及以上)侵权行为间存在客观关联即可成立共同侵权,并不以共同的主观认识为必要。1参见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426页。也即,在双方均为过失的场合也可以成立共同侵权。从我国民法典第1173条(受害人过错)与第1168条(共同侵权行为及责任)等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来看,亦未明确否定过失共同侵权的成立。例如,第1168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未将共同侵权的主观方面限定于故意。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明确使用了“共同过失”之表述,其中第3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从上述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表述来看,民法上共同侵权的成立未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关于共同侵权的本质属性,虽然我国学界一直存在共同过错说、意思联络说、共同行为说、关联共同说等主张,但我国的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基本采纳的却是共同过错说。2参见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与案例评注·侵权责任篇》,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38页。亦即,“当一致行动的意思中含有侵害他人的目的指向时,便表现为共同故意;而当一致行动的意思中虽不含有这样的目的指向,但行为人可以预见共同作出的行为会导致他人损害,并且可以避免这样的损害发生时,便表现为共同过失。”3叶金强:《共同侵权的类型要素及法律效果》,《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关于接受共同过失的理由,民法学者指出,共同侵权行为及连带责任的立法基础之一在于“置民事权益受损害之人以更为优越的法律地位”,故“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69条没有表述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无可非议,只要规定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即可。”4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与案例评注·侵权责任篇》,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40~41页。换言之,民法乃调整平等私人关系的法律,侵权责任的最基本功能是填补损害,故主观心理状态究竟是故意,抑或是过失并无关紧要。民法上的故意与过失原则具有相同的价值。5参见叶名怡:《侵权法上故意与过失的区分及其意义》,《法律科学》2010年第4期;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9页。
鉴于现有的规范环境与理论基础,我国民法典关于过失相抵的规定,实则构建在承认侵权人与被侵权人成立共同过失的基础之上,只不过侵权责任中过失的对象一定是本人之外的其他人,故被侵权人的过失并非侵权责任中“真正的过失”。“基于权利的对世性,只有权利人之外的人才负有不侵害绝对权的义务……权利人对自己无义务,也不会有过失。此处的过失,只是为进行对侵权人责任的限定而由法律拟制出来的‘不真正过失’。”6满洪杰、陶盈、熊静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释义》,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8页。
然而,刑法的立场却截然不同。无论是结果无价值一元论,还是结果无价值暨行为无价值二元论的主张者,皆认同刑罚的机能在于报应与预防,而非被害人补偿。仅就报应而言,过失与故意反映出的主观恶性不同,处罚理应有所区别。既然刑法上的过失与故意并不具有相同的价值,那么刑法对过失共同正犯的成立也颇为审慎。在西原春夫等主张共同意思主体说的学者看来,欠缺共同意思联络的场合无法成立共同正犯。1参见内海朋子 《過失共同正犯について》 成文堂,2013,56~70页。从而才得出以接受共同过失为前提的过失相抵与信赖原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尽管日本最高裁判所在1953年开始承认过失共同正犯,但肯、否二说间的论战从未停休。2参见内海朋子 《過失共同正犯について》 成文堂,2013,52~101页。在我国,学界虽不乏肯定过失共同正犯的呼声,但就当前的通说与实务立场而言,对过失共同正犯的成立依旧持否定态度。因此,更宜回避带有过失相抵色彩的处理路径。适用信赖原则,在事实上的过失中剥离出刑法上的过失,避免陷入过失共同正犯的争议,是信赖原则化解危险接受困局的优势所在,亦是符合我国理论与实务现状的破题之路。
(二)深町教授观点之不足:有赖“理性人”概念的“经验法则”之困
以信赖原则化解危险接受困局有赖于经验法则的运用。也即,依据一定的经验法则,在行为人能够信赖被害人可以自我保护的场合,认为行为人对其危险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无预见可能性,从而否定构成要件该当性。此处的问题在于,赖以判断信赖的经验法则是否可靠。
所谓经验法则,原系围绕法官的内心认知所提出的概念,旨在描述人们在生活经验中归纳得出的关于事物属性或因果关联的法则。这一概念其后多在大陆法系的诉讼法与证据法中用于推定事实或认定证言。3参见张卫平:《认识经验法则》,《清华法学》2008年第6期。既然“经验法则并不是具体的事实,而是作为判断事物之前提的知识或法则。大凡人们在对事物进行合乎逻辑的判断时都必须以经验法则为前提。”4[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375页。那么,抛开诉讼阶段中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在案件的进行过程中,行为人依据经验法则来判断被害人的下一步举止亦无不可。然而,经验法则需以事物一般特征的正确性与有效性确认为基础,在意大利学者米凯尔·塔如弗(Michele Taruヵo)看来,适用经验法则时难以回避对“实质假前提”的担忧:如果一些法则既非基于科学上确认,亦非出自实证验证,而只是基于所谓的“经验”,那么人们便不知、亦无法知晓该法则参照了何者之经验及所得结论的认识基础,无法把握形成该法则的经验内容。如此一来,人们便不能掌握法则可能出现的错误概率,得出的结论可能既不具有逻辑性,也不具有认识和推论的基础。对此塔如弗提出,经验法则的运用需要更多的限制——在以自然科学或有效一般性常规为前提的场合,得到的判断便具有结论性,亦即属于被确证的事实;而在基于假的一般性常规或者原本不存在所谓一般性特征之表现的场合,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例如,一些经验法则可能只是依据非确证的可能性概率所得出的,一般表现为“通常会……”,“很可能会……”等,“这样一来实际上支撑经验成为法则的基础就只是所谓的‘经验’了。”5参见[意]米凯尔·塔如弗:《关于经验法则的思考》,孙维萍译,《证据法学》2009年第17卷(2)。此时的结论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深町教授提出的“被害人的自我保护”即偏属后者。对此不妨以实际案例进行说明:
防冻液案:王某与卢某在井下作时,看到吊机车上放有一瓶绿色液体。王某问卢某能不能喝,卢某称是防冻液,可以喝。王某不信,与卢某打赌称,如果卢某将液体喝掉就把手表输给他。卢某喝下后,中毒身亡。6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2014)新刑初字第337号。
对于此案我国有学者认为,谨慎的公民不会喝下不明液体,故不能认为卢某可以自我保护。1参见庄劲:《团结义务视野下的被害人自陷风险》,《月旦刑事法评论》2017年第5期。依据深町教授的见解应当也能得出这一结论。然而,“谨慎”的标准在事实上并不明确。相比之下,学理上更常使用“理性”代之。细究深町教授所提出的、“自律”的被害人在认识到身处危险时会自我保护的这一经验法则,实则来自康德提出的“理性——意志自由——自律”这一逻辑。2参见王啸:《自由与自律:康德道德教育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但是,“理性人”概念与自然法如影随形,且考量因素未排除习惯与道德,3参见张建肖:《法律上理性人刍论——源流、界定与价值视角的分析》,《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故法系间理解的不同导致了各国适用上的差异:英美将其用于刑事案件的认定;4英美刑法中首例适用并确立理性人标准的案件为R. v.Welsh(1869)案,R. v. Welsh,11 Cox C. C. 336(1869)。大陆法系的国家中却主要用于民事上的表见代理、外观主义、善意取得、权利失效等制度,以保护合理信赖等私法价值。我国部门法中尚无关于理性人的明文规定,学理探讨也主要集中在民法学领域。例如,有学者认为,民法上“善意取得”中的所谓“善意”,系“相对方的信赖是否合理。所谓合理,是指可被一般公众所接受,参照各国判例和司法实践,普遍倾向于以理性人作为其判断标准。”5张建肖:《法律上理性人刍论——源流、界定与价值视角的分析》,《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在我国有限的论及理性人的刑法学论作中,有学者主张将此概念用于过失犯预见能力的判断标准,6参见谷永超:《英美刑法的理性人标准及其启示》,《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4期。但在笔者看来,该主张本质上仍未脱离现有的折衷说,且对理性人的文化根基与在我国刑法环境中的适应性并无论证。甚至该学者自己也承认,理性人存在“标准模糊”“不合理”等缺陷。总体而言,相当于民法,我国刑法学界对理性人的研究尚欠缺深入、系统的探讨。
关于民、刑间对理性人关注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根源仍在于民、刑机能的不同。民法意在处理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故多以主观意思为准;而刑法的机能却在于法益保护、秩序维持与自由保障。7参见佐久間修 《刑法総論》 成文堂,2009年,4~5页。因此,刑法学者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是,在法益保护与公民自决权相冲突的场合,究竟以何者优先来判断“理性”。依据深町教授的见解,“自律”的公民应当自我保护;而在美国法哲学家乔尔·范伯格(Joel Feinberg)看来,完全正常的理性人为追求某些快感也甘愿自冒风险。8[美]乔尔·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三卷),方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47页。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我国部分学者的认同。9参见王俊:《客观归责体系中允许风险的教义学重构》,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96页。应当承认的是,理性是一种心理活动,行为人之理性未必是法律上的理性,个人选择自己接受风险或许是理性的,但对社会而言,将其作为标准却不合理。10参见张建肖:《法律上理性人刍论——源流、界定与价值视角的分析》,《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如果以具有理性人色彩的“自律”作为“被害人的自我保护”之经验法则的前提,恐怕需要社会成员整体具备基本的、平均的理性。且不言这一状态在地域发展不平衡的我国当前阶段难以实现,细究深町教授所主张的信赖原则,事实上也并未建立在基本、平均的理性之上,相反却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例如在“赛车同乘案”中,深町教授认为,戊信赖教练己可以自我保护的原因是对方具备优越认知,而非来自教练这一规范身份;“河豚案”中厨师之所以不能信赖顾客可以自我保护,并非缘自厨师应提供安全食物这一规范要求,却来自作为厨师不能信赖顾客采取自我保护。深町教授的论述中渗透着对规范要求的考量,但却没能论述透彻,似乎信赖与不信赖并无明显的界限,最终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综上所述,深町教授借助信赖原则剥离出危险接受案件中具有刑法意义的过失的思路虽然具有启发意义,但以“理性”为基础的经验法则因过于主观而不十分可靠。那么,在对深町教授之见解的扬弃过程中,如何划定一个符合我国实情的、客观上“应当信赖”的标准,并以此作为事实信赖的依据,或许才是我国学界从危险接受困局中实现突围的可行性路径。
四、一个符合我国实情的路径构想:事实信赖需以规范信赖为依据
(一)我国当前阶段应以规范信赖为依据
深町教授主张的“信赖”固然因过于主观而不可取,事实上,在危险接受的案件之外,当前学界所归纳的信赖原则在其他领域的适用也存在主观信赖与客观信赖的交织。例如,在交通事故中,驾驶人信赖其他驾驶人会遵守交规属于客观的信赖,毕竟取得驾驶资格的人经过专业的训练,社会有理由信赖其能够遵守行驶规则;但步行人的场合却另当别论。步行者能否遵守交规恐怕与其受教育程度和个人素养有关。如果有人愿意信赖其会遵守交规,那么这一信赖便具有主观性。同理,在监督过失中,酒店老板能否信赖被雇佣的焊接工可以安全作业,进而在发生火灾时借助该信赖否定监督过失,亦恐并非“愿意”便可构建。如果任由主观信赖去否定过失,可能导致实务中的被告人动辄以信赖原则脱罪。
诚然,日本从德国判例继受的适用规则呈现出了对主观信赖的接纳态度。在日本的交通领域,信赖原则的适用限制仅是,在行为人本人违反交通法规、容易预见对方会违反交通规则、不能期待对方(如年老者、幼儿、残疾人、醉酒者等)遵守交通秩序、在道路有冰雪而事故可能高发的场合等不适用信赖原则。可见,日本学者将老人、幼儿、残疾人、醉酒者以外的社会一般人拟制为具备同等社会认知水平的群体。但这一拟制无不依据。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日本的高中教育已充分普及,截至2018年,25~64岁人口中的半数接受了高中教育”,“80%的年轻群体完成了高中教育,日本是OECD(经合组织)中高中进学率最高的国家之一”。1《2019年版(カントリー·ノート:日本(PDF:1380KB※OECDのウェブサイトへリンク))》,https://www.mext.go.jp/b_menu/toukei/002/index01.htm。相比之下,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口仅占全人口数的11.8%,2《3-1 全国分学业完成情况、性别、受教育程度的6岁及以上人口》,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且各地区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比例从1.8%到32.29%不等。因人口基数大,即便在我国文盲率最低的地区也达到333098人,全国高达54190846人。3《1-9各地区分性别的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这些群体不仅集中于乡村,同时也在向城市转移。根据上述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乡村离开户籍地的省外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4《1-4c各地区分性别的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口状况(乡村)》,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这其中不乏对规则认知度偏低的群体。如果仅从机动车数的激增与道路设施的改良便认为我国已具备适用信赖原则的条件,那么在保证城市运转效率的另一面,可能难以保障因受教育程度所限而对规则认同度偏低的群体的权益。
危险接受中对信赖原则的适用应服从信赖原则的一般规则。鉴于信赖原则以常识的普及与规则意识的整体提升为前提,考虑到国民的受教育状况,笔者认为我国虽然可以借鉴这一原则,但应当设定更多的限制。总的原则是,主观上的事实信赖,需以客观、规范上的“可以信赖”为依据。这一限制的优势在于:其一,规范上的“可以信赖”缘于被信赖方的“特殊态样”,实则为社会成员对社会公认交往模式的认可,具备高度的可信赖性。“特殊态样”需获得国家公权力的肯定或许可,从而使特定社会成员的业务能力具备规范上的高度被信赖性。关于这一要求,诚如京特·雅科布斯(Günther Jakobs)所指出的:“对于已经设立的规范,个体不能够提出任何抗辩,不能提出他缺乏遵守规范的兴趣、不能提出他有更重要的事做、不能提出遵守规范给他带来的损害。”1[德]京特·雅科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冯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81页。例如,社会可以信赖取得执业资格的护士能够合规操作,但不应对未取得资格的实习生抱此信赖;路人可以信赖机动车驾驶员会遵守交规,但驾驶员不应对路人“一定不会闯红灯”抱有信赖,因此在通过交差点时仍需减速慢行。基于规范上“可以信赖”而信赖,避免了主观的任意性,更具有刑法上的探讨意义。其二,利于法定犯时代社会规范意识的内化。风险社会的深化推进了法定犯时代的到来,风险愈高的领域,法定犯的规定愈密集。风险领域的作业员作为掌控风险的主体,故不得在规范允许的范围之外信赖他人可以回避风险。如此可以避免不合理的风险分担,有利于敦促风险领域的谨慎作业。
(二)对信赖原则适用规则的类型化构想
由于过失犯存在多种态样,故信赖原则的适用也应根据类型区别对待。在本文看来,信赖原则主要被用于三类案件:危险接受类,公害、医疗、火灾等事故相关的监督过失类,交通事故类。
其一,危险接受类。此类案件的特点在于存在双方事实上的过失,故可能存在针对彼此的信赖。根据前述深町教授思路的启示,应借助信赖原则剥离出其中具有刑法意义的信赖,进而确定刑法上的过失。具体而言,可以将该类型再细化为两类:(1)一方具备特殊态样的类型。其中,具备特殊态样的一方并无信赖对方可以自我保护的规范依据,故其事实信赖不能否定对结果的预见可能性,从而无法否定刑法上的过失。与此相对,不具备特殊态样的一方在规范上有理由信赖对方可以保护自己(被害方)的法益,即便(无特殊态样的一方)接受了危险,但刑法仍认为其对危险的现实化无预见可能性,因此不成立刑法上的过失。以“河豚案”为例,顾客有理由信赖取得执业资格的厨师会提供安全的食物,因此可以降低谨慎选择食用。即便发生死亡结果,也可以判定顾客的这一事实信赖存在规范依据,故对死亡结果不具有预见可能性。相反,厨师因特殊态样而负有更多的注意义务,规范不允许其信赖顾客去自己我保护,由此不能否定厨师对死亡结果的预见可能性。简言之,案中只有厨师的过失被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过失。在“赛车案”中,学员基于教练之特殊身份,有规范上的理由去信赖教练的指点是安全的,从而对事故的发生没有预见可能性。与此相对,教练并无规范上的理由信赖学员可以安全驾驶,故只有教练的过失具有刑法上的评价意义。在导致教练死亡的场合,只能认定学员无罪,应由教练自我答责。(2)双方皆不具备特殊态样的类型。此类案件中,因双方皆不负有保护对方的注意义务,在基于合意接受了危险进而导致危险现实化的场合,因无法剥离出刑法上的过失,故只能由双方自我答责。例如,“冰面驾驶案”并非发生在交通领域,驾驶人这一特殊态样在此案中并无规范上的被信赖性,加之驾车驶过冰面系二者合意为之,故无法剥离出其中具有刑法意义的过失。据此笔者认为,本案应定性为民事案件,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则处理。
其二,在监督过失的场合,1此处的监督过失仅指对人监督,也即狭义的监督过失,一般表现为上级人员对下属的监督,不包括广义的监督过失中的管理过失。考虑到社会运行体制中监督义务的规范色彩,亦应区分为两种类型,以适用不同的处理规则:(1)对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间存在规范分工的类型,可适用信赖原则否定监督者的预见可能性。例如,甲对乙的作业负有监督职责,但甲之所以雇佣乙,是因为乙取得了甲所不具备的专业资格。此种场合,应允许甲信赖乙可以安全作业。但应强调的是,这一场合存在例外。即,在监督者明知法益侵害结果几近确定发生的场合不适用。因为,规范仅是社会一般经验的总结,未必能真实反映一切因果流程。在法益侵害几近确定发生的场合,基于对效益的考量,可能被侵害的法益应优位于原本贯彻体制运作的集体利益。2参见周漾沂:《反思信赖原则的理论基础》,《陈子平教授荣退论文集——法学与风范》,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第59页。( 2)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间仅存在监督关系,却不存在规范分工的场合,不能适用信赖原则否定监督者的结果预见可能性。例如,甲明知乙未获得乙炔切割的专业技术资格,仍雇佣其进行切割作业。即便甲深知乙具备多年的焊接经验,信赖乙能够回避风险,这一信赖也只是不具备规范依据的主观信赖。由于缺少规范依据,该信赖不能否定甲对结果的客观预见可能性。对于乙造成的法益侵害,甲至少符合监督过失的构成要件该当性。
其三,在交通事故的场合,仍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1)事故双方系机动车驾驶人与机动车驾驶人以外的人员之类型。此种场合,应以不适用信赖原则为原则,适用信赖原则为例外。理由在于,基于我国人口普查所显失的地域受教育年限数据及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的现状,应避免受教育程度偏低的群体分担过多的城市风险——故暂时不宜认为社会成员皆具备同一程度的规则意识。机动车驾驶人原则上不得以“信赖对方会遵守交规”为由主张对事故结果不存在客观预见可能性。但是,在与教育水平无关的场合可以例外地适用信赖原则。对此笔者赞同在我国城市快车道、国道、高速公路等领域适用信赖原则的主张。3参见谈在祥:《刑法上信赖原则的中国处遇及其适用展开》,《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4期。例如,在设有明显隔离栏的城市路段或封闭的高速公路所发生的事故,机动车驾驶人可以以“信赖无人会翻越隔离栏”而主张对事故不存在客观预见可能性。因为设有隔离栏的地段即以物理的方式明示告知“不得跨越”“不得进入”,受教育程度偏低的群体也可以领会。(2)对于事故双方均为机动车驾驶人的类型,原则上可以适用信赖原则。毕竟取得驾驶资格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可以拟制双方驾驶人均对交通规则存在认知,故被告方可以借助信赖原则否定预见可能性。但是,这一类型也存在例外。即当被告人明知对方无证驾驶的场合,不得肯定其信赖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