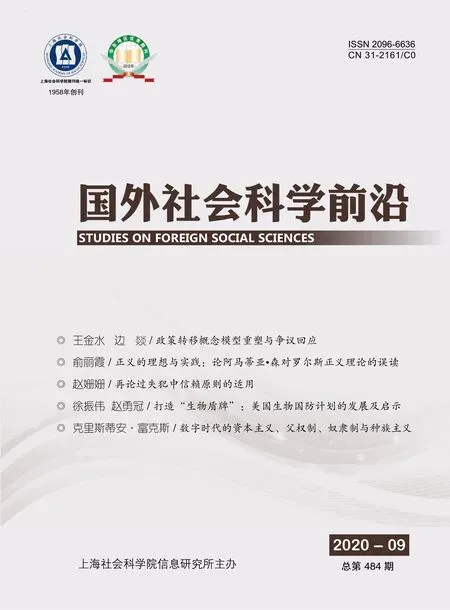日本2000年之后的刑事法动向:现状与课题 *
高桥则夫
内容提要 | 2000年之后,日本立法机关一改之前的沉默姿态,刑事立法的活性化凸显。处罚的早期化、扩大化、严厉化成为当下日本刑事立法的重要特征,刑事法理论与社会政策如何予以应对成为重要的课题。法律需要规制什么是行为规范的问题,附加了制裁规范的行为规范才属于刑法上的行为规范,法益既不通过制裁规范实现也不是刑法的特权。是否需要动用刑罚是制裁规范的问题,现阶段刑罚的预防机能强化,但犯罪预防尚需考虑社会构造性问题,也必须考虑到刑法的第二次规范属性。造成处罚的早期化、扩大化、严厉化的社会原因主要是被害人问题与刑罚民粹主义,对于前者,需要重视被害人的地位并向修复型司法推进,对于后者,需要向市民传达具体的犯罪实像并确认刑法预防的意义与界限。今后的刑事立法需重视被害人、加害人与社区的三方关系。
一、引 言
日本刑事立法的活性化可以说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1关于刑事立法的活性化以及对此的批判性检讨,迄今为止已经有众多论稿。在此仅列举如下:井田良,“近年における刑事立法の活性化とその評価”(井田良·松原芳博编《立法学のフロンティア3―立法実践の変革》,2014,ナカニシヤ出版),97页以下(97页注1及121页的参考文献);另有松原芳博,“立法化の時代における刑法学”(井田良·松原芳博编《立法学のフロンティア3―立法実践の変革》,2014,ナカニシヤ出版),123页以下(146页的参考文献)。在此之前一直“像金字塔一般沉默”2参见松尾浩也,1986,“刑事法の課題と展望”《ジュリスト》(852):11。本文亦收录于松尾浩也《刑事法学的の地平》有斐阁,2006,48页。的立法机关,究竟为什么转向犯罪化、重罚化的方向呢?这一趋势想必今后还会持续。曾经外国评价日本犯罪少,是开展非刑罚措施的理想国。其后,由于犯罪增加或许可以说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为何即使现在犯罪在不断减少,犯罪化、重罚化的动向依旧未见衰退呢?或许是因为存在着可以称之为“时代的风气”的这一早已十分棘手的怪物吧。
配置适当刑法、处罚值得处罚之行为的立法没有任何问题,毋宁说是应当欢迎的。问题在于,是否从作为决定基准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原理出发,恰当地选择“值得处罚的行为”。确实,国内外的社会情势不断地急速变动,社会性的脱轨现象也出现了质的变化。但是,将这些现象作为犯罪,用刑罚来对付它们是对是错,是必须不断慎重探讨的问题。
但是,由于根本性的问题超越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框架,所以事态变得愈发困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框架是让个人承担责任,而非解决背后存在的社会构造性问题。也就是说,单纯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基本原理对犯罪化和重罚化加以批判是解决不了本质问题的,如果聚焦于导致犯罪的经济性社会性因素的解决对策无法揭示出来的话,就不太可能成为对犯罪化和重罚化的有效批判。为了应对犯罪,有必要创设出替代犯罪化和重罚化的手段。
本文从这两个方向,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基本原理以及解决超越这些基本原理的社会构造性问题这两个角度出发,对日本2000年之后刑事立法的现状与课题予以若干探讨。
二、2000年之后的刑事立法概览
首先,本文试图通过概览2000年之后的刑事立法及刑事关联立法,探寻这些立法的特色。
2000年,根据对犯罪被害人等的保护两法(刑事诉讼法及检察审查会法的部分改正的法律、关于为了保护犯罪被害者等的刑事程序附带措施的法律),主要是出于在公开审理阶段保护犯罪被害人的目的,引入了证人询问之际的遮蔽措施、视频连线方式的证人询问、性犯罪控诉期间限制的废除、公开审理程序中被害者等心情及其他意见的陈述、对被害者等的旁听的考虑、刑事诉讼程序中民事上争议的和解等制度。另外,对少年法进行了部分修改,故意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场合,对于16岁以上的少年,原则上必须移交给检察官,因此导入了下调反移送年龄、原则上必须反移送、被害人的意见听取制度和被害人通知制度等内容。此外,还通过了跟踪骚扰行为等规制法(关于跟踪骚扰行为等规制的法律)和关于防止儿童虐待的法律。
2001年,在对刑法的部分修改中,新设了有关支付用磁卡电磁记录的犯罪和危险驾驶致死伤罪。还制定了DV法(关于防止配偶者暴力及被害者保护的法律)和犯给法(关于犯罪被害人等给付金支付法部分修改的法律)等。
2002年,制定了大阪府的安全城市建设条例(在道路及公园禁止携带球棒、高尔夫球杆)和广岛市暴走族清除条例等。
2003年,制定了心神丧失者等医疗观察法(关于对心神丧失等状态下实施重大他害行为之人进行医疗及观察等的法律)。此外,犯罪对策会议还制定了《实现不惧犯罪的社会的行动计划》。另外,偷盗行为防止法(关于禁止持有特殊开锁用具的法律)也得以立法化。
2004年,对刑法的部分修改中,提高了有期徒刑法定刑和处断刑的上限,更改了强盗致伤罪的法定刑,新增设了集团强奸罪。通过部分修改刑事诉讼法,将杀人放火等能够判处死刑的罪名的公诉时效从15年延长至25年。此外还制定了犯罪被害人等的基本法。
2005年,对刑法进行了部分修改,新增设了人身买卖罪。对监狱法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关于刑事设施及受刑者处遇的法律》,还通过了防止虐待老人的法律。
2006年,对刑法的部分修改中,对盗窃罪、妨害执行公务罪、职务强要罪新增设了罚金刑。还将前述《关于刑事设施及受刑者处遇的法律》的名称变更为了《关于刑事收容设施及被收容者等处遇的法律》。
2007年,在刑法中新增设了机动车驾驶过失致死伤罪。通过对少年法的部分改正使得未满14岁的少年移送至少年院成为可能。此外,通过《为保护犯罪被害人等的权利利益修改刑事诉讼法等部分内容的法律》,将一定重大事件程序的被害人参与、证人的询问、对被告人的质询、作为辩论的意见陈述、关于损害赔偿刑事程序的成果利用等予以制度化。还制定了汇款诈骗被害人救济法,即《关于通过犯罪利用存款账户等资金支付被害恢复分配金的法律》。另外修改了DV法,扩充了保护命令制度,制定了更生保护法。
2008年,修改了少年法的部分内容,允许被害人旁听少年审判。将犯给法更名为《关于通过对犯罪被害人等给付金的支付等支援被害人等的法律》。犯罪对策阁僚会议还制定了《实现不惧犯罪的社会的行动计划2008》。1如后所述,必须注意的是,从2008年的行动计划开始强调犯罪人的融入。
2010年,《修改刑法及刑事诉讼法部分内容的法律》中修改了行刑时效。例如死刑就不再成为行刑时效及公诉时效的适用对象。
2011年,《为应对情报处理的高度化等修改刑法等部分内容的法律》中,创设了关于不正指令电磁记录的犯罪,对妨害强制执行罪和猥亵物散布等罪进行了修改。
2012年,对《关于禁止非法访问行为等的法律》的部分修改中,将供非法访问行为之用而取得和保管他人用户名及密码的行为也作为处罚对象。
2013年,制定了《关于处罚机动车驾驶致人死伤行为等的法律》。另外,在《改正刑法部分内容的法律及关于对犯药物使用等罪的人部分刑罚的执行犹豫的法律》中,创设了惩役或禁锢部分执行之后剩余刑期缓期执行的“部分执行犹豫制度”。
2014年,通过部分修改《关于儿童买春、儿童色情相关行为等的规制处罚以及儿童的保护等的法律》,单纯的持有、制造亦成为处罚对象。通过部分修改药事法,规制危险药品。依照《隐私性图像记录的提供被害防止法》对“复仇色情”予以处罚。
2016年,根据《修改刑事诉讼法等部分内容的法律》,提高了藏匿犯人罪、隐灭证据等罪、威迫证人等罪的法定刑。
2017年,修改了组织犯罪处罚法,增设了恐怖行为等准备罪。另外,修改了性犯罪的相关内容,包括在修改了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及法定刑的同时,也将罪名更改为强制性交等罪,将强奸罪等犯罪更改为非亲告罪,增设了监护者猥亵罪与监护者性交等罪,修改了强盗强奸罪的构成要件等。2由于近年来日本的刑事立法又有重大变化,根据原文作者的授意,对2014年的立法论述进行了删减,新增了2016年和2017年的立法论述。——译者注
概览上述的刑事立法及刑事关联立法,可以说正如指出来的那样,“处罚的早期化”“处罚的扩大化”“处罚的严厉化”这些现象基本上是存在的。这些刑事立法的倾向,大约可以分为下述三类:
第一,为了应对新型犯罪的刑事立法。例如,为了应对网络犯罪与汇款诈骗的立法即属于此。
第二,以犯罪被害人的需求为依据的刑事立法。例如,跟踪骚扰等规制法、DV法、危险驾驶致死伤罪以及机动车驾驶过失致死伤罪、被害人参与制度的创设等属于此类。
第三,以市民的安全(消解市民的不安)这一视角为依据的刑事立法。例如,广岛市暴走族清除条例、儿童买春法的部分修改等属于此类。
当然,这三类之间是重叠的,绝不是仅仅以其中某一个作为依据。问题在于,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刑罚是不是必需的呢?特别是近来有评论认为严罚化的时代已经落幕,我们已经进入了再犯的防止与恢复的时代。3参见浜井浩一,2014,“高齢者·障がい者の犯罪をめぐる変遷と課題―厳罰から再犯防止、そして立ち直りへ”《法律のひろば》67(12):4页以下。另外,浜井浩一《罪を犯した人を排除しないイタリアの挑戦―隔離から地域での自立支援へ―》現代人文社,2013,146页以下的建议也极富启示意义。亦即,从迄今的刑罚性、惩罚性的转变到非刑罚性、非惩罚性的转变就是这样的。
以下,本文将从处罚的早期化、扩大化、严厉化与非刑罚性、非惩罚性的转变这两点为中心展开探讨。
三、处罚的早期化、扩大化与行为规范
刑法上,处罚的早期化、扩大化一般来说是通过未遂犯、危险犯、预备犯等来实现的,但是近来,刑法典中的关于支付用磁卡电磁记录的犯罪以及非法访问禁止法、跟踪骚扰行为规制法、DV法等特别刑法都各自实现着处罚的早期化、扩大化。刑法上,发生法益侵害的侵害犯和结果犯是基本的犯罪形态,未遂犯、危险犯、预备犯等都是修正的犯罪形态,正因为此,可以说近来立法的特征就是这种例外的犯罪形态的增加。
关于处罚的早期化、扩大化,肯定的立场重视运用刑罚抑止犯罪,重视刑法的规范意识形成机能,赞成刑法的早期介入。而否定的立场则认为刑法的保护只能限定在诸如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等古典法益上,只有侵犯这些法益的情况下才应该使用刑罚,由此更加重视法益概念所具有的自由保障机能,自然而然反对刑法的早期介入。
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法益的扩大倾向正变得不可避免。这也意味着,除了生命、身体、财产等古典法益之外,还有对安全、环境、情报等的保护要求,在个人法益之外,系统保护以及集体法益等普遍性利益也已经出现。1对此问题的系统研究可参见Roland Hefendehl:Kollektive Rechtsgüter im Strafrecht, Köln: Carl Heymanns, 2002。原本法益本身并没有刑罚限定机能,而是往法益当中加入了物质性内容而赋予了其刑罚限定机能。然而,在刑法典当中早已存在名誉、信用、宗教感情等精神性、观念性的事物,用物质性内容加以限定是十分困难的。另外,即便是个人法益,也不能说其与集体法益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特别是将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还原为个人法益,两者的区别完全可以说只是程度问题。进一步来说,如果将法益理解为对个人的自由发展而言所必需的条件的话,那么将安全和环境包含在这些条件之中就并不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如此,法益概念从其自身当中并不会产生限定刑罚的机能,什么应当由法来保护,为了保护它们是否有必要动用刑罚这样的实质性问题则变得愈趋重要,有必要将前者作为行为规范的问题,将后者作为制裁规范的问题来予以分析。2关于此点,参见高橋則夫《規範論と刑法解釈論》成文堂,2007,1页以下;高橋則夫《刑法総論(第2版)》成文堂,2013,10页以下。
本文对带楔板/凹腔结构的燃烧室氢气喷流燃烧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 细致分析了不同进口条件下氢气喷流穿透深度、 喷口前后回流区、 掺混效率与燃烧效率等流场结构与典型流场参数的变化特性, 得到以下结论:
必须注意的是,法益保护是以行为规范而不是制裁规范为导向的。例如,在道路交通领域,遵守交通规则并不是由对制裁的畏惧所产生的,而是由对他人行动的预期和在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下对自己产生的损害的预期而产生的。诚然,从制裁规范的存在可以推导出行为规范的存在,但是被禁止行为与被允许行为的界限、被保护权利领域的确定是无法从制裁规范中得到结论的。对行为自由的限制,可以说是该行为规范在宪法上能否得以正当化的问题。亦即,法益概念背后的下述三个问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3对于此分析,可参见Ivo Apple, Rechtsgüterschutz durch Strafrecht? in: Kr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82(3), 1999, S. 284ヵ; Ivo Apple, Verfassung und Straf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8, S. 336ヵ.
第一是应当保护的价值、状态或者机能统一体的问题,这也是规制目的在宪法上是否被允许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为了保护这些东西,是否可以施以行为规制(禁止和命令)呢?如果可以,具备何种要件对法益保护来说才是合适的呢?这是行为规范的比例性这一合宪性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为了保护被行为规范所保护的价值、状态或者机能统一体,是否有必要使用刑法呢?为了达到法益保护的目的,具备何种要件施加刑罚才是合适的呢?这是刑罚施加的比例性这一合宪性问题。
如此,保护法益的是行为规范,而维持这种行为规范的就是制裁规范。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看,其与制裁规范之间属于间接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刑法定位为第二次从属的法益保护手段。此外,由于刑法是从属的保护法,虽说制裁规范通常以行为规范为前提,但是并不能反过来说对行为规范必须附加制裁规范。例如,《关于儿童虐待防止等的法律》中,第三条规定有“任何人对儿童都不得实施虐待”这样的行为规范,但是却并没有违反该规范时所能适用的罚则规定,也就是不存在刑罚这样的制裁规范。与此相反,该法第12条之4第1项的接近禁止命令则存在罚则规定(该法第17条),另外,《关于防止配偶者暴力及被害者保护的法律》(即所谓的DV法)中,保护命令(该法第10条第1项至第4项)也存在着罚则规定(该法第29条)。这些场合既存在行为规范,也存在违反该规范时所能适用的罚则规定。后者的场合,是“法益—行为规范—制裁规范”这样的形态;而前者则仅仅是“法益—行为规范”这样的形态。
当然,通过附加制裁规范,行为规范得以构成要件化为刑法上的行为规范,解释构成要件上的行为规范时,法益自然就成为解释的指针。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法益保护并不是通过制裁规范实现的。法益保护不是刑法的特权。
四、处罚的严厉化与制裁规范
如上所述,法益保护与处罚的早期化、扩大化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关联,尽管仅仅通过行为规范的设定来保护法益是可能的,但是接下来必须要追问的是,为何要施加刑罚作为制裁规范呢?
刑罚基本上具有事后处理的机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犯罪后才能对行为人处以刑罚。话虽如此,但是也不能否认通过施加刑罚,防止今后再发生新的犯罪这一预防目的的存在。通过刑罚宣告,威慑一般人令其今后不实施犯罪,通过刑罚执行,让受刑者改过向善、重新做人,令其不再犯罪等都属于此。如此,施加刑罚就能够实现一般预防以及特殊预防这一事前的机能,但是这些不过是事后处理的派生性机能,在实质内容上是空虚的。
然而问题在于,用刑罚来预防能有何种程度的效果呢?犯罪预防不必回溯到近代学派,通过对环境与素质等的实证研究弄清楚犯罪原因,以此为基础实践起来会更有效果是不言自明的。例如,为了减少少年的不正当行为,与严厉的刑罚相比,尝试对少年的人格形成与改变、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加以改造似乎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犯罪预防并不仅仅是应对个别的具体的行为,而且还要立足于社会构造性的视角进行。在此也能得出犯罪预防不是刑法的特权这样的结论。而且,在法律介入犯罪预防的场合,作为控制行为的手段,应当先由民法行政法处理,如果认为这些法律具有第一次的规范性,那么刑法就具有第二次的规范性。
以上,从刑法的规范结构(行为规范和制裁规范)出发,对处罚的早期化、扩大化、严厉化进行了讨论,接下来将对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社会原因“被害人问题”与“刑罚民粹主义”做进一步的探讨。
五、刑事司法中犯罪被害人的地位
近代的刑事司法系统是加害人关系型的,而现在犯罪被害人则走向了前台。关于此背景,乔·古迪(Jo Goodey)列举了以下十点。即:(1)职务犯罪率增长;(2)通过犯罪调查大量隐藏的犯罪被发现;(3)大众对犯罪的恐惧增高;(4)公众对日益增长的犯罪及社会失序行为的不容忍;(5)犯罪人处遇模式的失败,与被害人相关的报应司法取而代之;(6)媒体关于针对弱势受害人的犯罪及刑事司法制度对被害人的不当待遇的报道;(7)女权主义者对暴力侵害妇女及虐待儿童问题的认识与政治化;(8)公民行动团体对种族主义暴力问题的认识与政治化;(9)犯罪率增长的政治化,即政治家巧妙地利用犯罪率增加的现象,让有权者的目光集中在“法与秩序”、“镇压犯罪”、被害人问题等之上(避而不谈政治上的失败与难题),从而在选举中胜出;(10)包含被害人在内的争取市民宪章或病人权利的运动。1参见Jo Goodey, Victims and Victimology: Research,Policy and Practice, Harlow: PearsonLongman, 2005, pp. 13-14;日文译本可参见ジョー·グディ(西原春夫监译)《これからの犯罪被害者学―被害者中心的司法への険しい道》成文堂,2011,17页。
对于犯罪被害人与刑事司法的关系,维持传统刑事司法见解的立场认为,刑事司法应当贯彻国家与加害人的两造关系图式,对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应当交由民事法及其他法律负责。但是,即便采取这一立场,既然不能完全拒绝关于犯罪被害人情报与保护的需求,那么犯罪被害人和刑事司法之间的关联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与此截然相反的立场,即重视刑事司法中犯罪被害人的地位,提倡情报和保护的进一步扩大化,例如关于被害人参与,不仅是被害感情,对于创设能够表明报应感情、处罚感情、科刑意见的制度也持积极的肯定态度。根据此一见解,刑事司法的目的和作用中包含着被害人保护,犯罪被害人也被提高到了刑事司法当事人的地位。但是这种立场是以错误的形式改变了刑罚的本质和刑事司法的目的,即使是在被害人参与制度当中,也是以犯罪被害人并非刑事程序的当事人为前提的。
既然这两方立场都无法贯彻到底,那么应当成为问题的就是犯罪被害人的地位能够更具体化、个别化到何种程度才能被认可的允许范围为何。为此,有必要追溯到与刑事司法及犯罪被害人相关联的基础问题予以考察。
关于刑事司法中犯罪被害人的地位,可能成为分析视角的有如下两种。其一是“被害人权利的惩罚性模式与被害人权利的非惩罚性模式”这一对立轴,另一种是“被害人的权利模式与被害人的支援模式”这一对立轴。
刑事司法模式早前就有“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的对立,但由于欠缺了被害人的权利这一点,又有论者补充提出了两种以被害人权利为基底的新型模式。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被害人权利的惩罚性模式与被害人权利的非惩罚性模式”。1参见Kent Roach, Four Models of the Criminal Process,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 Criminology, vol. 89, no. 2, 1999,pp. 699-713;另可参见高橋則夫《対話による犯罪解決》成文堂,2007,22页以下。
被害人权利的惩罚性模式将刑事司法看作被害人权利与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对抗关系,因而重视被害人的权利。依照这一模式,被害人的权利与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具有同样的宪法地位,更加关心过去的事实,强调被害人的无辜性与加害人行为的非正当性。此外,和犯罪控制模式一样,也认为刑事立法、追诉和处罚具有抑止犯罪的效果。因此,在事前就有了刑法保护的早期化,在事后将诸如被害人影响陈述(VIS)制度化。这一模式又被称为“环滑车模式”,它单纯地指向审判、上诉与处罚,更由于正当程序诉求与被害人权利诉求之间的对抗催生了新的问题,因而整个过程更加地曲折。
与此相反,被害人权利的非惩罚性模式则更加重视被害人的实际需求而不是其本身的权利,以被害人的恢复与谅解为目标。着眼于将来,倾向于事前的犯罪预防与事后的恢复性司法,前者例如邻里监视系统与自我警戒活动等,后者例如家族集团会议与和解计划等。这一模式之所以又被称为圈形模式,是因为通过家族与社区的犯罪预防与(纯粹型的)恢复性司法,将个人包含在了社区这一圆圈当中。
如此,被害人权利的惩罚性模式与被害人权利的非惩罚性模式这一对立的范畴,前者可称之为被害人关系型的刑事司法,后者又可称之为恢复性司法(问题解决型的刑事司法)2恢复性司法又分为纯粹模式(所有与犯罪相关的当事人会于一堂,集体解决犯罪影响及其之后关联事项的过程)与最大化(扩大)模式(以修复犯罪引发的危害、实现司法正义为志向的一切活动)。刑事司法框架中的修复性司法,以后一模式为依据,又可称为问题解决型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被害人的权利模式”与“被害人的支援模式”这一对立轴。3参见Heather Strang, Repair or Revenge: Victims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2, pp. 28-33。被害者的权利模式认为被害人是好人、加害人是坏人,据此要求让被害人赢、加害人输这样的形式构想被害人问题,是“胜—负模式”(win-lose)。与此相反,被害人的支援模式则认为被害人也可能成为加害人,加害人也可能成为被害人,以此反转可能性为基础构想被害人问题,是“双赢模式”(win-win)。
是停留在被害人关系型的刑事司法,抑或是更进一步实现恢复性司法(问题解决型刑事司法)呢?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必须在这种二选一的关系中探讨。由于加害人关系型刑事司法必须作为基本予以维持,往被害人关系型刑事司法的转变,终归只是作为现阶段过渡期的一种转变,未来还需往恢复性司法(问题解决型刑事司法)方向推进。
六、从刑罚民粹主义到非刑罚性、非惩罚性转变
刑罚民粹主义(Penal Populism),又被翻译为刑事大众主义或者刑罚性惩罚性大众主义,是指以大众接受为目的推进的刑罚政策。浜井浩一教授认为,“刑罚民粹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即一方面谋求强化‘法与秩序’的市民团体、主张犯罪被害人权利的活动家以及媒体成为普通市民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司法官与刑事司法研究者的意见越来越得不到尊重。”1参见日本犯罪社会学会编《グローバル化する厳罰化とポピュリズム》現代人文社,2009,7页。
像这样的刑罚民粹主义是不是严罚化的主要原因,需要实证性的研究,例如,根据松原英世教授的调查研究,2参见松原英世《刑事制度の周縁―刑事制度のあり方を探る》成文堂,2014,46页以下。支持严罚化与“社会情况的认识”及作为其基底的“社会观”存在着关联,但与“犯罪不安”与“刑事司法无效认知”之间几乎不存在关联。也就是说,可以做如下理解:对犯罪的具体问题,例如犯罪发生率、日常生活中的不安感、刑事政策上的缺陷等,民意并不受这些问题的影响,反而是被抽象的“对社会的看法”所推动。诸如“善恶二元论”(加害人是坏人,被害人是好人)、“古典的报应论”(严惩做坏事的人是理所当然的)、假定的感情论(倘若自己就是被害人云云)等都属于这里的抽象的“对社会的看法”。由于停留在这样的社会观层面之上,所以就很容易想象得到,舍弃犯罪的社会构造性侧面,缺乏其他方面的想象力与复杂多样的问题解决方法,最终可能导致武断的严罚化。
这样的刑法民粹主义的发展是无法阻止的,类似于这样的悲观看法还是比较多的。3例如,宮澤節生“日本のポピュリズム刑事政策は後退するか?”(日本犯罪社会学会编《グローバル化する厳罰化とポピュリズム》,2009,現代人文社),183页以下。然而,如果将前面所述的“抽象的社会观”转变为“具体的社会观”是可能的话,转变刑罚民粹主义的可能性或许也是存在的。
为此,首先需要向市民准确地传达具体的现实的犯罪现象。即使如前所述,市民的严罚化倾向来源于抽象的社会观,但强调日本的犯罪论逐年减少这一事实也不为过。自1996年犯罪的认定件数突破战后最多纪录之后,数量逐年递增,2002年达到了3693928件,但自2003年开始又开始逐年减少。2013年的认定数为1917929件,这是自1981年以来时隔32年首次降低到200万件之下。犯罪人的逮捕数量于1998年超过了100万人,1999年突破战后最多纪录之后逐年增加,2004年达到了1289416人,自2005年开始转为减少,2013年数量为884540人。必须要追问的是,在这样的犯罪现象中依旧实行严罚化的意义何在。
其次,必须要讨论的问题是,作为犯罪预防的手段,用刑罚来预防的意义与界限是什么。通过严罚化,是否能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必须要进行实证验证,并且有必要研究各种预防手段。例如,如果限定在刑事司法的范围内,国外提倡在警察阶段实行修复性警务。4关于恢复性警务,可参见高橋則夫《対話による犯罪解決》成文堂,2007,105页以下。关于犯罪预防,可参见2011,“刑事政策研究会第2回「犯罪预防」”《ジュリスト》1431:108页以下。这是基于修复性司法(问题解决型刑事司法)的原理以应对犯罪的警察活动,这一方法值得研究。修复性警务将警察活动的意义从“权力”转变为了“服务”。亦即,作为“权力”的警察活动,具有反作用性、阶层性、着眼于过去、信赖传统、受规则拘束、以法律执行为导向等特点,而作为“服务”的警察活动则具有解决问题、以社区安全为导向、采用个人责任、着眼于将来、促进改革、保护被害人与加害人的权利等特点。恢复性警务在实践中以三项原理为基础。第一,将恢复性司法(问题解决型司法)的思考方式与方法应用于解决警务问题。第二,市民、社区和志愿者之间相互作用。第三,通过促进地理上机能上的分权化与决定,达成全部及部分目标,寻求损害修复以及为了被害人、加害人、社区的解决对策。
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近来能够看到从严罚到再犯防止与恢复这一“刑事政策的方向转换”,继续推进这一转换是重要的课题。1严罚化带来的后果就是监狱的收容过剩,由此导致再犯防止的处遇变得很不充分,无法断绝重复犯罪这一负面连锁反应。浜井教授指出,“从2003年开始到2008年之后的刑事政策转换,是从排斥(exclusion)犯罪人到接纳(inclusion)犯罪人的转换。”2这一动向还会进一步与嫌疑人被告人阶段的妥当支援,即所谓“入口支援”行动联动。
如上所述,从刑罚民粹主义到到非刑罚性、非惩罚性的转变,一定会给今后的刑事立法带来不小的影响。亦即,以恢复性司法(问题解决型刑事司法)、再犯防止与恢复等为关注点的刑事立法及其他法令的完善将是今后的课题。
七、结 语
正如历史所讲述的那样,“时代的氛围”可以改变,但“处罚的早期化、扩大化、严厉化”这一沉重的氛围却始终沉淀在社会之中。从共同体社会向个人孤立社会的转变导致了负面的连锁反应:催生了社会的弱者,这些人犯罪后就要被严厉惩罚,被社会排斥,又让他们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3当然,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加害与被害、加害人与被害人,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处罚的早期化、扩大化、严厉化”是很有必要的,但这应当仅限于最终的不得不用刑法应对的场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忽视刑罚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所以不断探索刑罚替代手段的可能性是很重要的。
犯罪对策必须照顾到被害人、加害人与社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刑事立法也是如此。例如,强化对被害人的经济支援与精神安抚,4充分保证对加害人社会回归、融入与复原的社会性援助,5对社区要强化为了保护市民安全所需的人与地域的联系。6充分考虑这些并以之为目标的立法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时,“司法与福祉、医疗的合作”,即执法领域、检察领域、审判领域 和矫正保护领域引入福祉医疗措施,强化各个阶段的相互合作将成为前提,因而完善这些措施的立法也将变得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