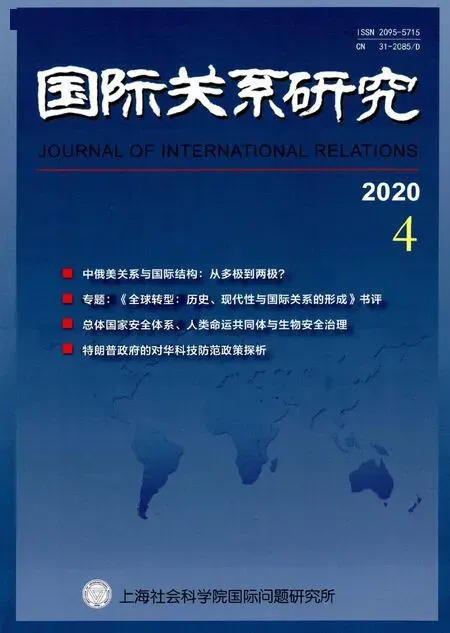作为历史学家的巴里·布赞
刘德斌
近年来,巴里·布赞的学术作品不断地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估计已有10本之多。他与历史社会学家乔治·劳森合著的《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已由崔顺姬等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巴里·布赞教授已经是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新一代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盛誉,似乎没有人把他当作历史学家来看待。但就笔者来看,他也是一位别具一格的历史学家。与西方其他杰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相比,布赞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他在理论和方法上兼收并蓄,在整合英国学派优良传统的同时又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还在于他一直专注于历史的思考和研究,形成了独到的历史眼光,从而使他成为西方学界反思和批判“欧洲中心主义”、重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性学者。在世界历史遭遇“百年变局”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在反思人类历史经验的今天,巴里·布赞对世界历史的解读尤其具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一、别具一格的历史学家
巴里·布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类”著作并不多,并且都是与人合著的,其中包括他与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杰拉德·西格尔合著的《预测未来:人类两万年的进步》(中文版被改名为《时间笔记》)、(1)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 Anticipating the Future: Twenty Millennia of Human Progress,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2000;[英]巴里·布赞和杰拉德·西盖尔著,刘淼和张鲲译:《时间笔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与理查德·利特尔合著的《世界历史中的国家体系》(2)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和与乔治·劳森合著的《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3)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当然,他的所有作品都有比较厚重的历史感,都与他对历史的解读有直接关系。如果我们把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衡量,他在这几个方面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巴里·布赞是一个有着“大历史观”的历史学家,并且构建了与众不同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他的“大历史观”首先表现在《时间笔记》中。 这是一本小书,但内容极为丰富,很遗憾没有引起太多中国学者的关注。《时间笔记》实际上构成了巴里·布赞世界史观的基础。时过境迁,不排除他对历史的认识已经超越了这本书中所阐释的观点,但作为一种对世界历史的解读方式,《时间笔记》还是值得我们品读的。它以20世纪90年代末为开端,采取了一种由近及远的“倒叙”方式,从20世纪的全球化与世界大战谈起,然后是中世纪以来欧洲的扩张,文明国家、帝国和蛮族,最后是从史前到文明的的过渡。他和西格尔认为,人类历史上唯一能与当下科技、工业、政治革命所释放的人类巨大潜力相媲美的时代只有从史前到文明这个时期。但他们认为这个转变在世界各地大不相同:从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开始的中东到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非洲。读者可能会对书中的观点持有不同看法,但难以否认世界上不同地区历史进程极大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对惯于按照欧洲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模式理解和思考世界历史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幅更为贴近历史真相的图景。在讨论“我们现在何处”这一命题的时候,布赞和西格尔认为这个西方化的世界很快就将面临人口数量和流动性无限增长的终结,人类社会与地球的关系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现在浏览这本书,读者会发现20多年前他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竟然与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倡导的“大历史”有相似之处,即把人类社会置于一个万年时空的视界中去考察。在这个视界中,人类是一个整体,人与环境的关系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其次,巴里·布赞也是一个极有创见的历史学家,他所创建的学术概念和他所构建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框架拓展了历史学的视野,开辟了一种新的世界历史解读体系。在这方面,有许多穷经皓首的专业历史学家也没能做到。他和理查德·利特尔合著的《世界历史中的国家体系》一书重新定义了“国际体系”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主线,阐释了人类如何从分散的采猎群开始,经过部落、城邦、帝国和现代国家的演化,发展到今天高度一体化的全球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历史学界研究人类不同组织形态和进程的专家有许多,但像布赞这样以此构建起一种世界历史解读体系的人似乎还没有。这本书中文版的发行量超过了英文版,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也成了许多中国历史学界专家和学者重要的参考书,它所阐发的概念也为许多中国的世界历史学者所借鉴。(4)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多家重点大学编写的《世界通史》(多卷本)中,第24卷《全球国际体系的演进》的作者李春放就采用了布赞和利特尔的“国际体系”定义及其相关概念。 参见李春放:《全球国际体系的演进》,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有学者甚至以巴里·布赞的“单位”和“解释源”为分析工具,解读先秦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变革。(5)参见杨倩如:《先秦国际体系的类型与演变》,《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1期,第96~111页。布赞和利特尔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中讨论了国际关系演进的基准时间,后来他与乔治·劳森对此作出了修正,(6)[英]巴里·布赞、乔治·劳森:《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第3~19页。对中国历史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7)赵思洋:《反思国际关系史的书写——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准时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2期,第131~150页。
第三,巴里·布赞是一位博采众长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家,他对西方历史学界非常熟悉,可以根据他在作品中的阐释逻辑,随手拈来历史学界经典和新锐作家的观点和论据作为支撑,或提出挑战和批判。在《全球转型》这本书里,我们就会发现一长串著名历史学家的名字,其中很多人也有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学界所熟悉,如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和《极端的年代》等)、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等)、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大卫·阿米蒂奇(《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约翰·达尔文(《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贾斯廷·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和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等等。阅读巴里·布赞的著作,你会发现他的文献储备非常充足,围绕每一个主题的阐释都能够展示出一整套类近于学说史方面的信息。在历史学日趋“碎片化”和“专业化”的今天,布赞的作品展示了另一番天地,也给读者传递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二、《全球转型》也是知识转型
在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为《全球转型》中文版撰写的序言里,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本关于世界历史的书”。但笔者认为,这不是或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世界历史的书,而是一本以19世纪的历史解读为基础,重构国际关系学理论基础的书。或许得益于与历史社会学家乔治·劳森的合作,这本书与布赞以前的“历史类”著作相比,要更为“立体”和丰富,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也更为“细致”。他们讲的是19世纪现代性“全球转型”的历史故事,但实际上提出了国际关系学知识转型的问题。这本书肯定会在国际关系学界引发不同意见的争论,但要想驳倒布赞和劳森的观点又很困难。这本书注定会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全球转型》的核心观点是认为19 世纪的现代性的“全球转型”重塑了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其中包含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的复杂结构。(8)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l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全球转型促成了一个完整的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同时也生成了诸多的行为体:理性民族国家、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已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全球性结构与国际行为体的变化意味着“19世纪见证了当今我们所熟悉的国际关系的诞生”。正是由于忽视了这种全球转型的整体性意义,国际关系学科的基础才“极不牢固”。两位作者强调社会之间的互动在全球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反对“现代化”是欧洲特有历史现象的观点,同时也不接受“中华中心”和“欧亚中心”的主张;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持续的不均衡的发展过程;全球转型既在不断地激化差异化发展,又在不断地强化社会之间的互动。无疑,这本书浓缩了巴里·布赞以前历史作品的观点,但引进了更多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视角和概念,并不是历史画面的平铺直叙,而是通过三个部分,十个章节的详细阐释,论证了被国际关系学所忽略的现代性全球转型条件下国际关系的形成。
作者特别指出,主流国际关系学界过于强调历史的延续性和重复性,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和过程是亘古不变的,没有意识到国际关系中的许多因素是近期历史的产物,从而把国际关系学置于与其他社会科学相“隔绝”的状态,难以进行深度的交流和对话。国际关系学需要像历史社会学家、世界历史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那样来思考19世纪。而全球现代性转型不仅为国际关系学者思考当代议程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而且还有利于将国际关系学子领域整合起来,拓展和丰富学科的知识性,从而开启与其他学科的深度交流与对话。布赞和劳森对国际关系学界“美国中心主义”和美国学界把国际关系学与政治科学绑定的做法不以为然(称之为怪癖)(9)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l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p.331.,认为重视全球转型将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去中心化趋向。布赞和劳森甚至认为国际关系学应该将自身定位为一门旨在为全球现代性提供新的叙事的“历史社会科学”。(10)Ibid., p.332.如果理解其主要关心的议题在何等程度上源于全球转型,那么国际关系学科本身也会经历一场转型,升格为一个能够也应该在社会科学内产生跨学科综合讨论的知识场域。(11)Ibid., p.333.
三、布赞的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学
作为一位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巴里·布赞一直致力于清除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弊端,即现代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呼吁非西方学者将非西方的历史经验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中来。(12)[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1页。无疑,这是一项艰苦的奋斗。但巴里·布赞一直在努力。他与乔治·劳森合作完成的《全球转型》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这之前他与阿米塔·阿查亚完成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对于这位西方学者的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我们没有办法不表示钦佩。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以对历史的解读为基础构建国际关系学说的著作有很多,如约瑟夫·奈不断再版的《理解国际冲突与合作》,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经典之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以及约翰·伊肯伯里的《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等,但是像巴里·布赞这样以国际体系的演进为主线,系统性地构建一种世界历史阐释框架,或以现代性为主线,阐释一个世纪的全球转型如何构建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大手笔”理论家并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巴里·布赞是独一无二的。
在《全球转型》中,布赞和劳森公开宣示要以全球的现代性转型为共同起点,拓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基础,使之从狭隘和僵化的知识视野和与政治学的“绑定”中摆脱出来,加入到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对话中去。这是一种非常鼓舞人心的前景。布赞的历史作品,特别是《全球转型》,实际上已经在国际关系学与其他学科,甚至在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发挥桥梁和中介的作用。我们期待国际关系学界有更多这样的作品问世。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加入到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探索中来。现代性的转型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迄今还没有一个学科能够“纵览全局”,发挥引领作用,向人们解释清楚当代世界的来龙去脉,新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或许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布赞的历史解读不仅要经得起国际关系升级换代的考验,而且很有可能还要经受其他学科的评判。如果尚有不足,我们期待巴里·布赞仍旧笔耕不辍,有新的历史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