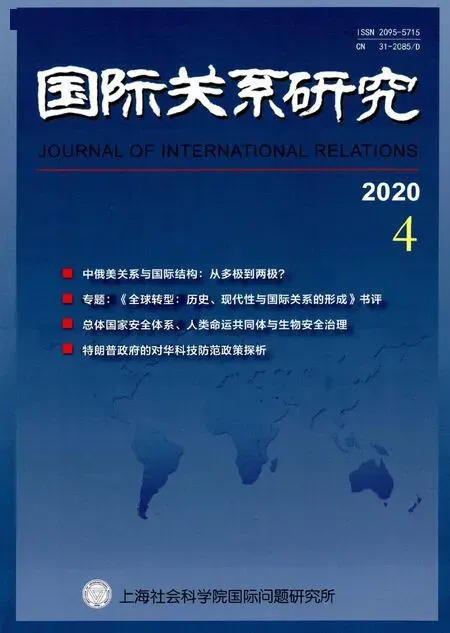反思全球转型背景下的大国责任*
崔顺姬
当今世界正经历全球秩序的大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变化趋势愈发明显,国内外学界的相关讨论也显著增多。目前全球转型的相关研究更多涉及国家实力的消长、体系主导国的扩容或更替,新兴大国是否会挑战或推翻现存国际秩序,尤其是中美之间超级大国地位的更替是否会引发危机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虽然这种争论和担忧不无道理,但过分聚焦于权力分配带来的影响,容易忽略正在兴起的全球新秩序的本质及这一过程中的大国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于2015年出版的著作《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1)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本书作为“剑桥国际关系研究”丛书之一出版后,于2016年获得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年度最佳著作”奖。为认识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全球转型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著作,它以现代性作为透视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主要切入点,选取“漫长的19世纪”检验塑造现代世界的一系列转型,这对认识当代国际关系及其转型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人有幸翻译此书,收获不小,不能一一分享,这里仅对全球转型背景下的大国责任谈一下体会。
一、如何认识全球转型
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大转型(或百年未有之变局)到底处于怎样的状态,它来自哪里又将走向何处?《全球转型》一书认为全球转型始于漫长的19世纪并延续至今,彼时建立的一系列动态因素交织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格局,这一格局重塑了国际秩序的基础,从而定义了一个新的时代。因此,19世纪所发生的全球转型是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产生及其根本特征的核心。(2)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9.作者将19世纪带来的改变总结为两大点。
一是改变了原有的权力格局,并塑造了“中心—边缘”的全球权力格局。19世纪的全球转型由三种互为关联的过程(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进步的”意识形态)互动而成。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基础,权力也在此基础上得以形成、组织和彰显。因而,形成新的格局意味着经历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显然,经历这些变革的政体比没有经历这些变革的政体拥有更大优势,而“西方”首先经历了这种变革。也就是说,19世纪的全球转型以不均衡的形式发生,并改变了原有的权力格局,从“无中心的多元世界”转向了“中心—边缘”的世界秩序,西方则是这一秩序的重心。(3)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同时,这一“中心—边缘”格局的权力鸿沟极其悬殊,也难以模仿和弥合。这是因为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权力转移,19世纪的全球转型带来的是大规模的资源集聚,即在转型过程中,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进步的”意识形态所构成的格局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权力模式”。(4)《全球转型》导入“权力模式”(mode of power)概念来解析全球转型的诸多影响,指出权力模式是权力的社会根源,其内涵要比权力分配深刻得多,它是物质与观念上的关系,这些关系生成了行为体与权力得以表现的方式。譬如,在全球转型中,三个动因(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进步的”意识形态)的结合产生了权力得以被建构、组织和表达的新基础,作者们将这种转变称为“权力模式”的转变。因而,与大部分国际关系的研究路径不同,《全球转型》认为权力模式的改变要比权力分配上的改变重要的多,因为前者影响的不仅仅是互动的结果,也是互动得以产生和被理解的基础。参见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pp.305~308。因此,《全球转型》主张,全球转型不仅标志着权力分配的转变,也改变了权力的基本来源或权力模式,刺激了全球现代性的出现。19世纪产生的全球转型从本质上“终结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5)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4.
二是改变了原有的观念结构。主导国际关系的基本观念性框架在19世纪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前的一些合法概念,如王朝统治或王权神授均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新的“进步的意识形态”,(6)此处讲的“进步的”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progress)不是特指好坏。虽然其中蕴藏着关于“进步”本身的认识,即它将科学技术上的物质进步与对“控制”自然、提高“人的境况”和改善人力资本存量(human stock)的愿望结合起来。但是,“进步”也带有黑暗面,如在19世纪,欧洲思想家开始把进步的观念和文明优越性的理念连接起来,强调了欧洲与“他者”间的明显差异以强化宗主国的优越性。相关讨论参见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98~99。本专题王江丽的文章也涉及相关讨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科学”种族主义。(7)“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是一种主张社会等级秩序可以并且应该建立在基于生物标记或基因基础之上的理论,不管这种标记是外在的(如肤色)还是根据血统(如犹太人、黑人或中国人)而定的。虽然它与其他三种意识形态都有联系,但与极端民族主义最契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标志着其影响力达到顶峰。具体参见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18~125。这些意识形态与“进步”观念密切相关,给社会关系注入了新的色彩。譬如,民族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重新定义了主权、领土权和公民权。此外,在这些意识形态驱动下,某些旧的组织(如国家)被重组,而某些(如王朝统治)则被摧毁,同时它们还催生了新的组织、行为体与制度(如移民、公民社会、股份制有限公司等)。如此,“进步的”意识形态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原则,重塑了国家建构自身身份认同和国家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并为现代国际关系的行为实践提供了新的合法性策略。(8)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97~126.
概言之,19世纪的全球转型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国际秩序的建构。当代国际体系的物质条件与意识形态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9)Ibid., p.36.同时,这一时期也孕育了国际秩序中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上的不平等,即西方是这一秩序的主导者。这些不平等依旧塑造着当代国际关系。
作者认为全球转型到目前呈现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方殖民式国际社会(自18世纪末持续到1945年)。第二个阶段是西方全球性国际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持续到21世纪的头10年)。这两个阶段所呈现的是中心化的全球主义,西方大国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进而,作者提出了全球现代性的第三个阶段,即始于2008年的被称之为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
“去中心化”意味着全球转型的格局不再只集中于一小部分国家,而是向全球扩散开来。也就是说,随着现代权力模式的扩张,19世纪形成的权力差距正不断缩小。作者认为,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此之后,全球权力的分布愈发趋于平衡。总体上,西方国家逐渐失去在国际社会中的特权地位,如新型的全球治理(例如G20)、经济形态(如金砖国家)、安全制度(如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正是这一趋势的鲜明体现。在权力逐渐趋于均衡的背景下,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将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地位,而各大国将在更加区域化的国际秩序中进行互动。(10)Ibid., pp.272~304.而去中心化的世界秩序是否可以孕育出足以有效应对共同挑战的全球管理机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一个全球无霸权的世界,国际秩序的维系与否将取决于大国的负责任行为。
二、再思大国责任及其挑战
全球转型所引发的讨论中较多的还是关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由于西方国家实力的相对衰微和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西方大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否已经停止,特别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是否将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倘若如此,中国会不会改变现存的国际规则?这类讨论将中美交替论作为最重要的议题和担忧。但是,《全球转型》认为,过分聚焦于中美超级大国地位的更替有其局限性。首先,有中心的全球秩序转向去中心的全球主义意味着全球无霸权,超级大国将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更替。未来的世界将走向更加区域化的秩序。(11)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09~293, pp.302~303;唐世平:《国际秩序的未来》,《国际观察》2019年第2期,第29~44页。其次,这类观点容易忽略全球转型不仅使得安全议题在扩大,其威胁的性质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对大国的责任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12)参见Shunji Cui and Barry Buzan, “Great Power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9, Issue 2, 2016, pp.181~210。
(一)大国责任:从管控大国战争到担当全球治理?
国际秩序大转型背景下大国应负怎样的责任?用英国学派的说法,作为国际社会首要制度的“大国管理”的内涵应如何得到改变和充实?传统意义上,大国管理的内涵主要局限在管理大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关系上,如管控大国之间的战争、危机、势力范围或权力均衡等等。(13)有关国际社会的首要制度,包括大国管理,参见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7。因此,它与国际社会的另一个首要制度“均势”有着密切关联,(14)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请参见Richard Little,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Great Power Management,” in Richard Little and John Williams eds., The Anarchical Socie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97~120。即保持大国间的权力均衡成为大国管理的主要手段,以达到防止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的目的。由此,大国间的权力分配(军备竞赛)、地位更替成为长期以来的权力政治的重要关注点。正如《全球转型》所强调,全球现代性首先引发的是大国关系的动荡,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心国家之间的军备质量竞赛,即我们所说的传统安全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大国之间的战争,甚至是获得(或失去)殖民地成了衡量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15)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40~270.然而,大国责任的这种传统认知在国际社会转向去中心的全球主义背景下暴露出至少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更多的不是由于权力分配的变化所致,而是由权力模式的变化引发。全球现代性的传播不仅限制了各类战争的成本效益,也重新定义了暴力的核心论题。由于现代武器所具有的破坏力量不断增加,且具有毁灭性,这使得20世纪前半叶那样的大国战争退出历史舞台。(16)Ibid., p.278.但与此同时,另一类安全问题,包括另一类暴力问题,则变得更加突出。譬如,自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以来,国际社会开始对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恐怖主义发起了安全化,其中最大的担忧便是极大的破坏力是否将落入少数群体、网络和个人手中。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环境问题也上升为安全议题。从某种方面看,这也是孕育了全球现代性的权力模式的结果,即现代性解放了生产力,随之给全球的环境问题带来了巨大压力。譬如,煤炭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关键要素,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则是石油与天然气,而到了19世纪末期,约有一半的世界能源是由化石燃料制成。加上其它人为原因引起的气候变化,全球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棘手的安全问题之一。(17)Ibid., p.296.除此之外,随着全球现代性的推进,21世纪我们还见证了一系列独特的非军事的安全议程,包括近几年频繁出现的难民危机、全球性流行病、网络安全等等。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不同,这些非传统安全所呈现的特性是威胁的共享性、安全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安全的全球性和跨国性。(18)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国际安全研究》 2014年第 1期,第3~34、157页;Bruce Jones, Carlo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9。这些非传统安全不是国家之间如何应对相互之间的威胁问题,而是国际社会如何作为整体来合力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问题,因而是“大家如何共同维护和改善全球公地的问题”,(19)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6~7页。也就是余潇枫所说的如何达成安全的“优态共存”。(20)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8~13页。
由此引出大国责任的传统诠释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它忽略了共同问题需要共同安全的逻辑。也就是说,过分强调权力均衡,甚至是只盯住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竞争,它忽略了“负责任大国行为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认识到共同问题的存在,并承认这些问题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21)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03.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不同于多极化,而是一种新型的结构,即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试图或者能够主导整个体系,也不是超级大国地位的更替。因此,各大国若处于“自闭症”(autism)(22)Shunji Cui and Barry Buzan, “Great Power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9, Issue 2, 2016, pp.204~206.状态,只顾本国利益而不顾体系利益,且没有意愿去承担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责任的话,对去中心的全球秩序将是个灾难性的打击。然而,国际局势发展趋势并不乐观,诚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折射出的,在全球最需要合作特别是大国间的合作的情况下,人们却发现民族主义的膨胀和民粹主义崛起。也印证了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国优先”政策给国际秩序带来的冲击。
由此看来,安全议题的这种扩展是全球现代性最重要的结果之一,给大国责任提出了新的内容和挑战。在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治理难题,大国责任的传统诠释如军事能力、权力均衡已显得力不从心。面对共同命运,国际社会需要“共生”型安全而不是传统的“对抗”型安全。在这个意义上,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的拓展不仅仅是安全议题从军事到非军事议题的扩大,和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到人或其他对象的深化,更是安全逻辑从对抗逻辑到共生逻辑的转变,因而不可避免地对国际社会的特性、国际关系的互动模式带来影响。(23)Shunji Cui, “Beyond Histor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orth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2, No.83, 2013, p.884.那么,面对新的安全挑战,在没有超级大国的去中心化的国际社会中,大国应如何管理全球事务、维系国际秩序的稳定?
(二)“资本主义大国协调”将出现?
本书提出了“资本主义大国协调”(a concert of capitalist powers)出现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在管理一体化但多样化的政治经济模式之间的竞争方面,这种大国协调可能发挥重要作用。(24)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89~301.这种“大国协调”具有19世纪“欧洲协调”的某些特性,其基本守则是,任何一个大国在没有事先尝试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或谅解的情况下,都不应该进行单边行动。同时,每个大国都有责任充分照顾到其他国家对自身防御的合法性担忧。(25)Ibid., pp.300~301.作者认为,这种“资本主义大国协调”出现的可能性大有存在。这是因为当代国际关系的运作已经与20世纪30年代大不相同。如今,大国间意识形态的差异相对减少,帝国和种族主义不再合法,核武器使大国战争丧失了合理性。而且,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相比,当今的全球经济治理已经高度制度化,且所有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治理模式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维护全球贸易、生产和金融链以保持可持续增长。
基于这样的判断,作者对未来国际秩序的运作提出了较为乐观的预测,即在这一体系中,“体系利益”的逻辑将是明显特征,且可能会出现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首先是“共生型国际社会”出现的可能性,其中不同的资本主义治理模式共处于“软性地缘经济”之下。其次是“合作型国际社会”出现的可能性,它能对国际合作项目(诸如世界贸易和大型科研项目)和集体行动难题(诸如气候变化和核扩散问题)进行有效地管控。从而作者预判,未来可能出现的多元主义秩序“并不等于把人们推向绝望的深渊”,因为在当今世界,“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已经非常小,与此同时,所有的大国都在一些重要的原则和利益上达成了共识”。(26)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00~302.
“资本主义大国协调”与“民主国家同盟”(league of democracies or concert of democracies)理念或治理路径相比较更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因而更具现实可行性。毕竟,“民主国家同盟”理念旨在维持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27)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s://world-governance.org/IMG/pdf_080_Forging_a_world_of_liberty_under_law.pdf.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由于自由主义在冷战中的胜利以及美国实力优势显著,不少西方学者开始提出以“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新文明标准”重塑国际规范体系。“民主国家同盟”理念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最大的后果是国际社会被一分为二,即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即“民主国家联盟”)和非自由主义国家,前者代表着“有序、统一、合法”,后者则被视为“非法、无序、混乱、落后、危险”。(28)Gerry Simpson, Great Powers and Outlaw States: Unequal Sovereign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大国协调”则为大国管理设想了一个有限且多元的系统。
本文对《全球转型》提出的“资本主义大国协调”的可能性与所能达到的预期(即避免硬性地缘政治或硬性地缘经济而实现软性地缘经济),及作者的谨慎乐观观点持怀疑态度。“资本主义大国协调”的提法本身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尽管作者强调多元主义特性,因而不确定这一路径能否产生广泛的凝聚力,至少对中国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路径的回答也是比较悲观的。特别是鉴于当前在全球范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还很明显,东西方之间的信任程度也很低,因而要在一个去中心的、更加区域化的全球秩序中凝聚如此多元化的行为体以应对共同的挑战,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理念,而是一个更加去意识形态化、更加包容的理念,以获得更广泛的接纳。
(三)全球转型与大国责任:中国视角
与《全球转型》的作者相比,中国学者观察全球现代性及其影响时,更多的是发现其存在的问题、探索改革的路径。譬如,柯银斌等学者已经发现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共同现代化”理念。他们指出,传统现代化理论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为视角,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或者是两者兼有的理论。它是一种民族国家本位的、国家利益优先的现代化,因而是竞争的、独享和独大的现代化。相反,共同现代化理论试图解释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它是国际共同体本位的、共同利益优先的现代化,因而是合作的、共享和共生的现代化。(29)柯银斌、乔柯:《共同现代化:一种新的理论探索》,《理论与现代化》2017年第4期,第27~35页。还有不少学者面对近年来出现的全球治理的失灵、民粹主义思潮的上涨、逆全球化等现象,对全球安全与发展前景表示出深深的担忧。认为在当今世界发生巨大的变革和转型期,在全球性挑战越来越严峻而需要有效解决方案的时候,“强起来”的中国理应承担大国责任。(30)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第1~14页。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更好维护转型中的国际秩序、构建更加健全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或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构想,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具体方案,(31)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并试图将这些理念和方案付诸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当中,意在构建开放包容的、多元协商的、合作共赢的、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32)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第1~14页。从这个意义看,中国所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似乎更符合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国际秩序的治理需求,因为它体现了共同命运意味着共同安全的逻辑。
问题是,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等新理念受到了不少国外学者和领导人的质疑,他们认为这种提法或者是没有任何新意的空洞口号,或者是掩藏着中国霸权的野心。(33)相关研究参见Shunji Cui, “China-US Climate Cooperation: Creating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Asian Perspective, Vol.42, No.2, 2018, pp.239~263。甚至有些人指出,中国想要建设的不是什么“新型的”关系,而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大国关系,其本质是人们所熟悉的势力范围概念。他们或将中国的这种努力比作当年美国的“门罗主义”,认为其意在扩大和稳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范围,并对该地区重大事态的发展拥有绝对的发言权。(34)Zachary Keck, “China’s Growing Hegemonic Bent,” https://thediplomat.com/2014/06/chinas-growing-hegemonic-bent/; Jawant Singh, “A Chinese Monroe Doctrin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jaswant-singh-believes-that-india-has-no-choice-but-to-challenge-china-s-hegemonic-ambitions-in-asia.可见,西方国家对崛起中的大国特别是对中国深怀不信任甚至敌意,这也将对中国行使其大国责任带来不少挑战。
大国崛起包括物质和理念双重层面,前者即一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大大提高,后者是一国被公认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特别是在国际规范体系的设立、调整与维护中具有领导作用,其崛起需要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与接受。国际规范体系包含了国际社会一系列基本制度和派生制度,决定着行为体在国际社会的行为标准和游戏规则,并据此界定“自我”和“他者”的身份,(35)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因此,它既制约和塑造国家的对外行为,也是国家行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事实上,自从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主导者,是国际规范的制定者、解释者和裁定者,同时也是主导其变迁的引领者。(36)张小明:《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要成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负责任大国,真正肩负起担当国际规范体系转型的“贡献者和引领者”的作用,(37)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提“两个引导”。详见《习近平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2/17/c_1120486809.htm。还要越过很多的难关来克服现有国际规范体系对崛起中的新兴国家的成见和遏制、对中国国家行为的误判与扭曲。因此,在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秩序中,大国的责任不但需要单个国家的努力,更需要面对共同挑战、建立共有认知、构建互信关系,特别是东西方之间、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等多元行为体之间广泛的信任和支持。
结 语
大国在全球大转型时代应负起怎样的责任?如今的全球转型已经不同于19世纪,这种转型不仅是权力格局上从有中心的全球秩序转向去中心的全球秩序,而且大国所面对的挑战和责任也从传统的安全议题拓展到非传统的全球治理议题。因此,大国责任的传统界定已经不能满足当今世界的合法性要求。全球转型,正将大国管理的内涵拓展至在全球和区域层面提供公共产品来满足区域和地方正义的要求,并有能力应对和解决全球治理的共同议题。(38)Shunji Cui and Barry Buzan, “Great Power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9, Issue 2, 2016, p.182.因此在21世纪如何平衡“国家利益观”与“体系利益观”以应对共同面对的挑战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只顾本国利益而不顾体系利益的“自闭症”大国将失去其合法性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所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更符合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国际秩序的现实需求,有助于中国在全球转型期为国际规范体系的设立、调整与维护发挥引领作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做到这一点,实现多元合作是关键:即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东西方之间、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都需要广泛合作。这种合作是在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世界中各大国应负有的最基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