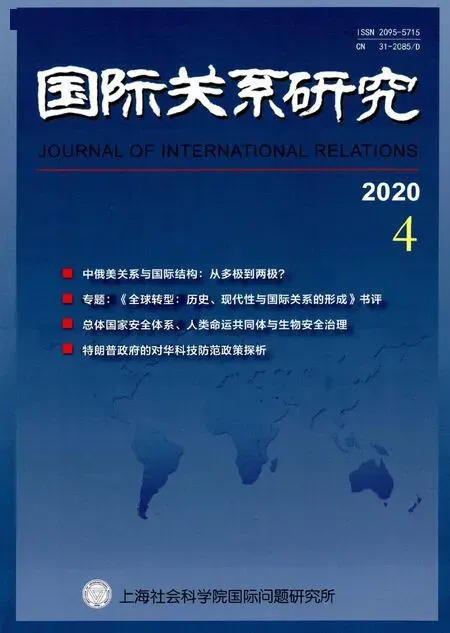全球转型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前后左右”
余潇枫
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涉及领域广泛、问题挑战不断、认知方法多样且与外交政策紧密关联的“知识场域”,也是最能体现学者全球意识、理论视野、方法论特征以及价值性偏好的“学术平台”。这一学科具有多重的二元复合性,即既年轻又古老、既理论又实践、既整体又个别、既可预判又不确定、既独享又杂合。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来说,无论从历史维度——以“前”的源起,现实维度——与“左右”学科的交叉,还是从未来维度——往“后”的走向看,近两个多世纪以来持续的“全球转型”是其最重要又最难以把握的语境。
巴里·布赞一直强调要从“人类是一个整体”的历史演进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但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忽视人类“现代性问题”和“全球转型的整体性意义”等,并造成了自身“学科基础的极不牢固”。(1)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5.为弥补这一缺失,巴里·布赞曾与理查德·利特尔合著《世界历史中的国际关系》(2)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一书来凸显国际关系的历史性与“现代性问题”,如今又与乔治·劳森合著《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以下称“《全球转型》”)(3)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一书来凸显“全球转型的整体性意义”以及对国际关系形成的特定意义。
对国际关系学科作“前后左右”分析凸显的是一种时空分析的视角。“前”是指时空的历史性回溯,探讨学科形成的历史源起,包括背景、代表性人物与文献及其经典解释;“左右”是指对某一时段进行空间结构性考察,揭示多学科互动、交叉乃至杂合的可能性。“后”是对时空的前瞻性思考,探讨学科发展的未来走向及可能形成的重要景象。
一、国际关系学科的“前”:历史维度与学科源起
历史维度的考察首先是审视任何一个学科的“逻辑起点”。约瑟夫·奈认为“国际关系不是一门实验性质的科学,历史学与其最为接近”。(4)[美]约瑟夫·奈:《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载[澳]克里斯蒂安·罗伊—斯莱特、[英]邓肯·斯尼达尔编,方芳等译:《牛津国际关系手册》,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711页。国际关系理论不能缺失“历史维度”,因为“理解过去成为重构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提”。(5)[英]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理论》,载刘德斌主编:《英国学派理论与国际关系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以世界史视角研究国际关系,并批评大多国际关系学者过于关注权力的分配,而不关注成为其支撑的权力模式;过于聚焦战争影响,而不检验引发战争的社会发展;过于重视寻找历史的“转折点”,而不把“全球转型”置于其视野的中心。为此,《全球转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正是19世纪的“全球转型”重塑了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形成了有诸多行为体(理性民族国家、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第一个“完整的全球性国际体系”(a full international system)。(6)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
《全球转型》通过六个理论假设构画出了国际关系形成的时空定位与总体语境。一是19世纪全球转型所呈现的现代性给国际关系学带来的诸多益处;二是全球转型源于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的”意识形态三者间的关联互动;三是具有“多元向量”的社会间互动建构起了全球转型中的“现代性”;四是现代化是一种持续的、不均衡的发展过程;五是全球转型特征表现为“不断激发的差异化发展”与“不断强化的社会间互动”;六是“中心—边缘”范畴解释全球转型中世界秩序的主要特征。作者主张,19世纪的全球转型重塑了国际秩序的基础,而这一秩序不仅改变了19世纪的国际关系,也奠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7)Ibid., pp.6~10.
《全球转型》的作者认为,要理清19世纪全球转型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关系重点在于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全球现代性如何引发了概念化、历史化和理论化的有意义的学科间对话?答案是,全球化导致的世界一体化的速度、强度、范围和总量以及变化的“深度”是引发学科间对话的原由;相反,如果忽视“全球转型”,那么“国际关系学科将面临两种风险:一是错判世界政治的内容与趋向;二是错失与相关学科共享话语的机会”。(8)Ibid., p.314.
第二个问题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未能认识到19世纪作为“体系”转型之源的原因是什么?答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对后来可能爆发全面战争的恐惧使国际关系学成为了一种“忙碌的经验主义”,把焦点放在战争及其解决方式上,以致忽视了这些战争在19世纪的根源。因此,如果以1919年作为国际关系学的起点,就忽视了国际关系学、种族主义和殖民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意识形态这三者所带来的权力模式的转型才促成了国际关系的真正形成。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为国际关系学科提供强大的学科基础?答案是,“从全球现代性出发,以全球现代性为依托,将为现有的国际关系学科的比较研究带来更为可靠的比较基础”。(9)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22.
在历史价值维度的分析中,巴里·布赞与乔治·劳森采用的是英国学派的理论立场,即“引人入胜的特质之一在于从国际秩序社会结构的角度,打开了研究国际关系史与世界的大门”,(10)Ba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td., 2004.形成了马丁·怀特所说的“国家体系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tates-systems)。(11)Andrew Linklater and Hidemi Suganami,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89.《全球转型》认为国际关系学常用的五大基准时间是1500、1648、1919、1945、1989,而事实是,1713、1776、1789、1815、1840、1842、1857、1859、1862、1865、1866、1869、1870、1884、1905都可作为国际关系学的基准时间。(12)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94.可见,《全球转型》的贡献在于不仅促成了19世纪作为“体系”转型之源的认知,而且把握住了国际关系的形成与根本特征是全球转型这一标志,特别是通过价值赋词如“理性的”国家、“进步的”意识形态、“利益和谐的”自由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种族主义等,凸显了历史维度中影响国际关系的要素特定价值内涵,为国际关系学科奠定了新的学科分析基础。
二、国际关系学科的“左右”:现实维度与学科聚合
《全球转型》从多学科综合,特别是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社会历史学”综合的角度,对国际关系形成进行了创造性考察,其方法论是多学科视角的运用。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通过汇聚多学科研究议程而促进了自身的自下而上的跨学科性质。成就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认识论范式最初脱胎于外交史和国际法。然而,这个新兴学科的逐渐成长应归功于和社会学、国际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哲学以及思想史的跨学科对话。”(13)[意]马里奥·泰洛著,潘忠岐、简军波、张晓通等译:《国际关系理论:欧洲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目前,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还在不断地分化与综合,或在综合中分化,或在分化中综合,它的发展好似不断地“从单一性的主流分化为一个‘三角洲’式的研究走向”。(14)[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著,余潇枫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页。
事实上,国际关系学科涉及的领域众多,参照国际研究会的分会设置名目可知国际关系大学科之下的子学科或子领域包括:国际事务、外交研究、环境研究、种族与移民研究、女权理论与性别研究、对外政策分析、全球发展、情报研究、国际教育、国际伦理学、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安全研究、和平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对国际进程的科学研究等。(15)李少军著:《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为此,国际关系学科在发展中必然会与其他学科相交叉与方法融合。
国际关系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交叉与结合有多重维度。体现哲学维度的有《基督教信仰、哲学与国际关系》(16)Simon Polinder, The Lamb and the Wolf: Christian Faith, Philosoph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iden: Brill 2019.等,军事维度的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人、国家、战争》(18)[美]肯尼思·N·华尔兹著:《人、国家、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等,政治维度的有《国家间政治》(19)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3.等,法律维度的有《国际公法与国际关系》(20)[美]吕德著,邓公玄译:《国际公法与国际关系》(影印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文化维度的有《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21)[美]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锴译:《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等,心理维度的有《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22)[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等。特别是体现经济维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支学科,直接采用跨学科的路径研究全球层面的经济与政治互动,代表性成果除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23)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外,还有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24)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苏珊·斯特兰奇的《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25)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等。
国际关系学科与自然科学结合的有数学、物理学、系统论、博弈论、医学等维度。特别是戴维·伊斯顿把“系统论”应用于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学分析,出版了《政治体系》(26)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Kropf, 1953.、《政治生活的体系分析》(27)David Easton,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1967.。莫顿·卡普兰将“体系理论”引入国际关系学,出版了《国际政治的体系和过程》(28)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57.。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的开拓者亚历山大·温特把量子物理理论引入社会科学,出版了《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29)Alexander Wendt, Quantum Mind and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等。体现医学维度的有《医学与国际关系》(30)秦倩、徐以骅:《医学与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等。
随着国际关系与众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出现了国际关系研究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跨学科交叉在促进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同时,不能不看到跨学科交叉以及形成的相应理论的“论战”又给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带来重重困境。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的学科理论总是充满着各个思想学派的争论,如代表性学派有新现实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学派间争论包含了三种危险,一是人们发现没有一个学派实际上是“充分发展的理论”;二是各学派只强调复杂现实的几个侧面如权力、安全、制度、规范和信仰,不仅相互矛盾,而且可相互替代;三是这些争论着的学派存在“会让这个学科的学生觉得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自以为是的学问”。(31)[意]马里奥·泰洛著,潘忠岐、简军波、张晓通等译:《国际关系理论:欧洲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2页。
国际关系学科左右交叉带来的困境往往是因为缺少对学科整体结构性语境的分析。苏珊·斯特兰奇提出过结构性权力的四种形态: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这均是冷战后全球新转型所产生的新型权力形态,即国际关系从支配性的“关系性权力”转向了间接影响型的“结构性权力”,并且后三种全球性结构挑战了国家的“中心性地位”,特别是知识结构性权力的形成。科学和技术积累所带来的“知识社会”的形成,有可能使企业、地方和区域性政府、超国家的权威机构都参与了知识的创造,因此知识成为了权力的新来源,“知识结构”将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未来发展的新决定性因素。(32)[意]马里奥·泰洛著,潘忠岐、简军波、张晓通等译:《国际关系理论:欧洲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6页。
基于“前后左右”的时空逻辑,我们可以理出一个学科发展的一般性轨迹,即问题形成与被提出—研究对象基本确定—准学科研究—单学科建设—多学科交叉—跨学科整合—横断学科群形成,甚至可以导致“杂合学科”出现。
三、国际关系学科的“后”:未来维度与学科杂合
要深入考察国际关系学科的未来维度,我们首先要对时间分析视角进行学理提升,运用“价值时空”理论来拓展深化对时空的认识。换言之,考察学科发展的关键是“时空坐标”不仅要考察其时空定位,而且要考察其“时间演化逻辑”与“空间结构逻辑”是否匹配与契合,以及与人类社会运动的价值关联性。在物理时空中,时间是遵循运动的“过去—现在—未来”延续而呈单维线性状的,空间则是体现运动的广延性而呈现静态分割状的。这种作为一切物质存在方式的物理时空观本质上是自在的、可拆分的、静观的。然而相对论揭示,时空特性是由物质“运动”特性决定的,并且在物质运动特性支配下,时间与空间可以互相转换。相对论将一种自在的“实体”时空转换成了一种作为非欧几里德的“关系”时空,(33)Albert Einstein, Relativity: The Special and the General Theory,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1961, pp.104~106.实现了时空观的范式革命。由此,种种按照社会运动特性建构的非自然物理时空假说被提了出来,如历史时空、经济时空、文化时空、语言时空、心理时空等,而统合这些且体现整体性、一致性与深刻性的“价值时空”理论则成为了与物理时空相对应的全新范式。
“价值时空”的自为性、总体性、发展性分别揭示出了人的“亲在”具有属人性、不可分性与实践选择性,(34)余潇枫、张彦:《人格之境:类伦理学引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9页。使人们看到一个全新的“价值世界”。以“价值时空”观来检验学科发展,会发现凡是时空逻辑不匹配与价值时空分析缺失的理论都是难以成为学科发展的支柱性理论。学者赵鼎新批评过社会科学中错对历史与时间关系的四种态度,一是“没有时间的横向历史比较”,二是“固定时间的纵向历史研究”,三是“进步时间下的历史研究”,四是“无规律性时间下的多样性历史研究”。赵鼎新提倡与价值关联的“积累型的发展时间”观和“本体型的道家时间”观,特别是道家的本体型时间观“强调阴阳之间的互含与转化,而不是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35)赵鼎新认为道家时间“就像是一幅太极图,它没有终极目标和意义、但却是有规律的和不断转化的。……道家的时间本体论很容易与社会机制结合而发展为社会科学理论,因为它背后是如下的一个涵盖性法则(covering law):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和思想,随着它变的强大,削弱它的力量的社会机制也会变的越来越重要”。《赵鼎新教授主讲“时间性、历史和智慧”》,http://www.ccpds.fudan.edu.cn/e1/12/c4581a123154/page.htm。这已涉及“价值时空”的本质性探讨,或者说道家“本体型时间”其实是“价值时空”观的一种经典的个案式表述。所以对国际关系学科进行“前后左右”的考察不仅需要按物理时空作向量表示与特征描述,而且更要按“价值时空”作复杂维度的特性揭示与超越性建构。
“价值时空”的分析视角使我们领悟到未来维度的考察不能局限于实体性的全球关系考察(尽管人类与非人类的生态关系超越了以往人类自身的全球化),还必须引入虚拟性的全球关系(人类将进入数据网络的生存方式之中)。对人类文明演化来说全球转型是史无前例的,但不能否认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比以往更为加速的“相变”之中,全球化将被“‘网’球化”所取代,这个“网”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广义数据网”,二是“广义生态网”。前者是“数字化”、“符号化”为本质特征的“信息人”世界的形成,其超越性体现在其“超时空”特征上。后者是基于“生态化”和“智能化”为生存特征的“智能体”或“超人类”社会的形成,其超越性体现在其“超人类”特征上。这两个“网”的形成与交织都是对“主权国家体系”藩篱的超越,届时“后人类国际关系”将成为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新主题。或者说决定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未来维度的最重要的跨学科影响将是以量子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以及与以新物质主义为代表的“后人类主义”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
“量子心灵”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创始人亚历山大·温特的新著《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一体化的物理与社会本体论》(36)Alexander Wendt, Quantum Mind and Social Science: Unifying Physical and Social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为量子心灵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奠定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基础。温特认为,我们解释世界并非是世界本身,而是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因而量子理论将全面挑战传统的世界观和既有的社会科学假定,如物质主义、原子主义、决定论、机械论、绝对时空论、主—客体论,将全面检讨审视问题的元解释框架、工具主义、现实主义、多重世界与多重心灵理论、理念主义等。(37)Ibid., pp.68~89.特别是以量子意识为本体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对“平行游戏”、“非定域性”和“心灵认知”的研究,将全面改变人类对理性选择的认识,改变人们对“世界社会”(38)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与“全球关系”的认识。
“后人类”国际关系。未来的人类发展,除了人类自身这一行为体,还将有更多的行为体参与进来甚至直接影响和决定人类的发展,如大量的有生命的物质、无生命的智能体、基于基因技术的新生命体、基于量子物理层面的超意识现象以及能和人类的意识、感性、知识等特征相互连结的、具有超级智慧大脑的“强人工智能”体(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39)《从AI到AGI,未来最强的人工智能是什么?》,https://www.jianshu.com/p/fb834ed79441。等。所以“后人类”国际关系学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后人类”国际关系学的主要议题是,基于复杂性理论视角下的与“后人类政治”紧密互动的“广义生态”、“社会关系”、“经济实践”和“权力转型”等。(40)Erika Cudworth and Stephen Hobden, Posthum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lexity, Ecologism and Global Politics, London: Zed Books Ltd., 2011.这就要求国际关系学科需要有更宏大的视野和更多地与其他学科“杂合”。事实上《全球转型》也关注到了全球政治中新行为体的出现与可能有的影响,未来可能性包括“所谓的‘奇点’,即出现比人类更加智能、更加长寿的实体,它可能诞生于机电技术或生物医学技术,亦或是二者的结合。虽然我们不能断言这一转型究竟会以何种面貌出现,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的发展将会改变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如果这些不可测因素中的某一个在未来几十年内真的出现,那么国际关系的发展将与本章所描述的轨迹产生天壤之别。”(41)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97.
《全球转型》一书虽强调其主要目的不是预测未来,但也探讨了全球转型的主要趋向“去中心化”将以何种方式呈现,其主要标志是作为“霸权国”的美国的式微。事实上,“美国无法稳定全球经济,也无法通过军事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的挑战;……从霸权这一概念的科学角度而言,除非是采用比喻手法或者新闻报道用语,否则已经无法再严肃地称美国为霸权国或者是美利坚帝国了。”(42)[意]马里奥·泰洛著,潘忠岐、简军波、张晓通等译:《国际关系理论:欧洲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与之相应,全球非传统安全挑战凸显,异质性冲突增加,伴随不断式微的单极化趋势,多极化、多边化、碎片化、聚合化、拓扑化趋势不断增强,成为了“去中心化”的另一现象。《全球转型》强调面临未来“去中心的全球化”,“作为一门学科,国际关系学最终要追赶和反映这些驱动力,同时学科本身也要变得更加全球化与去中心化”。(43)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31.特别是通过努力,“国际关系学将会使自身升格为一个能够也应该在社会科学内产生跨学科综合讨论的知识场域”。(44)Ibid., p.333.
结语:全球转型与国际关系学科的范式转型
《全球转型》论证了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形式与过程不是自古不变的,而其中的许多因素实质是近期的产物。同样,国际关系学科的形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非西方的发展正在改变国际关系学科的正统形态。当我们从宏观视角进行国际关系学科的“前后左右”分析时,不能忽视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在现实中的地位。“在中国,从学科上看,国际关系学科尚不属于一级学科,不少人甚至认为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边缘和交叉学科”。(45)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页。巴里·布赞也曾指出国际关系学科是令人遗憾地“碎片化”的,(46)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06.或者“国际关系学科不仅看起来是一门‘分裂的学科’,而且日益显得就是一门根本没有明确中心的学科”。(47)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页。
《全球转型》一书虽为我们揭示了全球转型导致的从“无中心的多元世界”到“中心—边缘的世界秩序”,再到“去中心的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轨迹,但作者对未来维度尚缺少阐发,甚至认为“世界上不会再有什么突破性发展可以带来与第一艘蒸汽船、第一条铁路、第一封电报和第一架远程喷气式飞机相媲美的影响力”,这多少对科学技术革命对全球国际社会带来影响的估计严重不足。事实上马斯克的“星联计划”、特斯拉的“航舰飞行”、华为的5G技术等的实施,已经证明这种突破性发展在未来不仅可能,而且对人类的影响还会更加巨大,对国际关系学科的重塑也将是不可估量的。
当然,全球转型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提出更多重塑国际关系学科的新议题:虚拟权力、非传统安全、网球化、数据结构、代际划分与算法等。或者说,权力模式将从现实政治转向知识构型,安全形态将从传统转向非传统,人类与非人类融合的“‘网球’化”将替代全球化,数据结构的主导性将替代观念结构的主导性,代际划分将替代时代划分,算法将成为真正的新历史标志。国际关系学科的未来前景可能是聚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形成一个比跨学科、交叉学科、多元学科更整合的,更能融合历史维度、现实维度与未来维度的“协同”式学科或“杂合”性学科。我们可以猜想,“国际关系学科”与“全球转型”将会形成一种“量子缠绕”式的关系,即既具有“广域关联性”又具有“超距感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