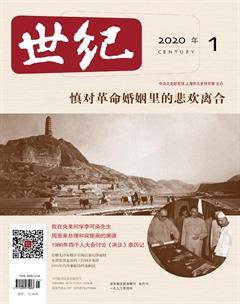关于陈望道重新入党和梅龚彬的政治身份
贺越明
陈望道先生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首译者,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成员,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还是中共建党初期历史来说,都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钱益民先生的文章《30年代陈望道与中共的关系》(载《世纪》2019年第4期),对读者了解他退党后继续为中共工作的一段经历很有助益。可是,该文截取的仅是陈望道人生的某个横断面,通篇未就他的政治归宿有所交代,容易让人误以为终其一生践行着早年退党时所说的话:“我在党外为党效劳……”,而这显然不足以反映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坚守。
据《陈望道传》(邓明以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记载,陈望道是早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人,虽然因不堪忍受总书记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退党,但还希望有朝一日回到党内。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会见陈望道时回溯往事,更使陈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共。不久,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市委随即向党中央报告。毛泽东对陈望道很了解,就此做出指示。于是,陈望道于1957年6月再度加入中共,并成为不公开身份的党员。直至1973年8月,他获选中共“十大”代表赴京出席党代会,才等于向社会公布了这一情况。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病逝。两年后的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在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为陈望道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史实说明,从1923年到1957年,这整整三十四年,陈望道身在党外,但坚定恪守“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的诺言,最终如愿回到党的组织。这正是老一辈革命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人生写照,亦是值得人们敬仰和追慕的典范。
钱益民先生的文章,有不少征引党内外知名人士回忆的文字,可以佐证陈望道的经历片段,但回忆者囿于一时一事的认知而不免有局限性。例如文中所举“第三则”之例“陈望道与《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的签名”,主要引用冯雪峰回忆录关于此一事件的记述,并称:“在此,冯雪峰把上海文化界人士分成好几类,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是一类,陈望道与任白涛是另一类,第三类是梅龚彬和胡秋原等人。在这里,陈望道的角色是中派文化人。”姑且不论视陈望道为中派文化人是否恰当,将梅龚彬和胡秋原等人简单地归为第三类,有可能使人对梅的政治身份认识模糊而产生误解。
梅龚彬原名电龙,参加过五四运动,1923年加入国民党,但很快选择笃信共产主义,于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是上海徐汇区团、党组织首任书记,曾参与领导五卅运动,又投身南昌起义。1932年改名后受潘汉年指派,以灰色文化人的面貌进入国民党内反蒋民主阵营,先后协助创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底陪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参加次年新政协和开国大典,建国后担任民革中央常委、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常委。在政治上,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梅龚彬与加入国民党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且去了台湾的胡秋原不属于一类人,尽管二人为湖北同乡且有私交。正是通过胡秋原,他结识了陈铭枢、李济深等国民党爱国将领。由于统一战线工作需要,梅龚彬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活动。受潘汉年案株连,他从1959年起被审查并劳改,1975年8月1日在流放地病故。直到1980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为梅龚彬举行追悼会,在悼辞中首度公开赞誉他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冯雪峰在1968年8月31日回忆往事时,只从梅龚彬早年的表面言行及与胡秋原的关系作出判断,似不知道他真正的政治身份。故此,借助有關资料对此略作补遗说明,冀有助于读者较多地了解这位经历不凡的职业革命家。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责任编辑 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