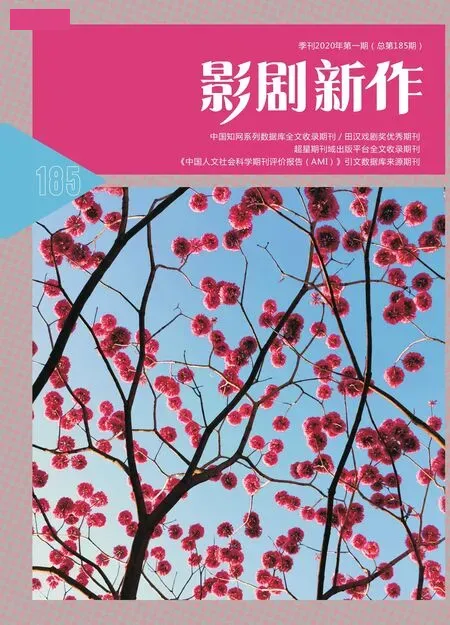东方电影的诗意表达
——谈越南电影《三太太》的符号与语言
张 帆
一、引言
当代电影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诞生了诸多流派和表现方法,电影的表现力涉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多方面要素,同时也囊括了语言学、符号学、诗学等多方面的研究。纵观当下的电影创作环境,随着电影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电影的制作手法愈发“工厂化”“好莱坞化”,千篇一律的叙事方法、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及绚丽的电脑特技和流水线一般的生产模式成了现在所谓“大片”的基本结构,这种创作方式可以适当地保证电影的产量与质量,但是也造就了观众对于电影审美需求不断降低的现状,电影艺术愈发地脱离其作为艺术创作之初的本质,转而向着工业产品的道路去发展。我们越来越难以看见极具个人特色的导演洋溢地挥洒,如当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那般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是笔者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起,大量越南导演关注到本民族的艺术文化特色,用自己的电影语言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朴素、充满反思性和人文情怀的电影世界,也违逆着西方“好莱坞式”的电影拍摄方式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情怀。越南的电影,特别是近期的新作——阮芳英导演的《三太太》在拍摄手法、视听语言、表现方式上极具东方电影的特色,诗意性的修辞和隐喻贯串了电影本体,导演运用充满东方特色的各种符号、民族特色的布景和服饰营造了唯美的叙事空间,因此笔者选取这部电影作为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寄望以此唤醒东方电影美学的创作诉求,让更多从业者去研究、发掘东方电影美学的诗意和魅力。
二、形、意、喻:诗意化的影像符号
索绪尔在语言学中提出,言语活动可以由“语言和言语”两部分组成。当电影被证实可以作为一门语言去解读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以视觉图像来模仿语言文字及一切言语活动,从而达到深层次的表意功能。相较于文字,视觉符号可以更加直观地将文字的能指转化为所指,因此可以更加形象地进行表意活动,这也是为什么语言本身具备影像时,它反而比文字语言更具有诗意的原因。越南导演非常善用具有东方特色的影像符号去进行表意。笔者认为,电影诗意的表意方式是一套“影像/声音→语义→诗意”的语言系统,在对《三太太》这部电影的语言和诗意进行研究时,笔者运用具有汉字语言文化的表现方式将电影中的镜头加以表述和分类,以“形、意、喻”三种形式囊括电影中镜头语言的能指、所指及意指,使其所具备的东方民族诗的特性更加便于理解。
在旧社会时期的越南,女人们嫁入豪门无非只是成为一个生育机器,她们无权享有爱情和自由,只有生出男婴的女性才可以在家族拥有地位。在电影中,当女主人公第一次躺在男主人家的床上时,镜头拍出了一轮圆月,同时,仆人在其身上用勺子播下了一颗生鸡蛋,鸡蛋象征着种子,以祈福播种、子孙满堂;月亮和鸡蛋两组近似镜头进行切换,利用了心理学上的“顺同化”效应,将两组镜头组成了一对蒙太奇语言,月亮与鸡蛋实则为两种符号,象征着女主人公在地主家必须多子多孙,才可圆圆满满的寓意,这里也形成了本片中的第一段诗句:月亮,在东方人民的心中代表着圆满,中华民族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也正是寄意于“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寓意,导演在这里通过东方民族对圆月和团圆的向往,隐喻了女子在家族中渴望拥有幸福的憧憬。(见图1)
除了利用景物的顺同化进行诗意的描绘,导演还利用了按照常理本不应存在的生物进行诗意的刻画:白天,女主人公正在床上缝衣服,然而镜头一转,在白色的纱帘上突然出现了一只鲜活的壁虎。(见图2)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认为,影像符号应更具有非理性的心理程式,诗意电影更加关注诗人的意象而非现实的逻辑性,符号的依据是非理性的主观抒情、记忆与梦境。我们知道壁虎昼伏夜出,一般不易在中午出现,因此笔者认为,白天出现的壁虎实则存在于电影导演的“意境”中,而不存在于电影的叙事空间内,这里实则为一组理性蒙太奇的镜头组合,壁虎是作为一段诗句中的喻体而出现的。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提出,人的一切思想都有其现实中的梦境为投影。若将壁虎这个符号进行解读,按照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壁虎象征着“性欲”,这显然与电影内该桥段想表达女主人公悲惨的身世这一思想相违背;然而在东方国家传统的民族思想中,壁虎象征着守节、守宫,也象征着女子的贞操,同时《周公解梦》一书有梦境中出现壁虎,则意味着“生活即将陷入屈辱之中”这一喻义。很显然,这里只能用东方民族特有的语境去理解才能得到正确的符号含义。导演在这里借助一只壁虎,便描绘出了少女失去贞洁这样的一系列活动,同时隐喻了少女即将陷入屈辱的生活这一主题,符号与诗意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这也是东方电影特有的诗意之美。符号学家苏珊·朗格认为:“人们会对记忆中熟悉的符号有特殊的亲切感和认同感,从而对符号产生特有的认知和情感,这种认同是具有个人和文化特色背景的。”由此我们也可知在进行电影符号的解读时,必须充分考虑导演的意图和民族文化语境,才能正确地理解其中蕴含的诗意。

图2

图3
在影片中还多次出现蚕、蚕蛹和蝴蝶的特写。(见图3)蚕这一符号在东方文化中象征着勤劳,在古代还象征着丝绸和财富,同时还有“破茧成蝶”一说,代表着人在经历过苦难和艰辛的奋斗之后,重获新生的喻义。片中导演用蚕来隐喻身处越南地主家的女人们,每日勤劳耕作,为主人家奉献自己一生的状态,只有生育出后代的女人才能破茧成蝶,不然只能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苦难。电影中的人物“雪”在自杀后,导演运用了一个蝴蝶飞走的镜头,隐喻了生命的流逝和解脱。在中国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双飞”的故事,这里用蝴蝶这一符号隐喻生命的解脱也极具东方诗意之美。在生孩子之时,导演还运用了女主人公漂浮在水面上的梦境去表现孩子从羊水中破出的那种释然和生死攸关的状态。片尾女孩子剪头发象征着对旧社会女性遭受的屈辱表现抗争和反抗的意识,意味着越南这个民族在对抗封建迷信、殖民统治社会的觉醒和新一代的越南人民已经长大的喻义。本片运用了大量诸如此类的表述手法去叙事、描绘人物心理动态以及隐射社会现象,在此不一一例举,笔者通过电影语言学将片中具备东方诗意的影像符号总结梳理如下:

?
表达电影一直是先锋派导演们孜孜不倦的追求,我们从《三太太》中也可以发现早期电影例如《一条安鲁狗》中的一些影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导演依旧在用许多东方民族的符号实验性地去做许多尝试,这种创造力和对艺术的追求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可以发现,越南导演在进行“影像→诗意”关系构建时,几乎都采用了具有东方诗意的符号去塑造,例如圆月、蚕、生鸡蛋、壁虎等符号。这些符号在西方电影中很少出现,只有东方世界的国家和民族在特定的语境下才可以理解。在东方人的美学观中,无论是美术、舞蹈还是其他艺术形式,都具有“重写意、轻写实、重表现、轻再现”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中国身为东方世界的一员,应该多借鉴、使用这些具备东方美学的元素进行创作,在好莱坞电影工业化肆意横行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自信,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民族美学思想的作品。
三、特写、画框与长镜头:诗意化的电影语言
电影是一门时间与空间并存的时空艺术,只对单一静帧符号进行解读无法真正且全面性地表现其中的诗意之美。《三太太》等越南电影在摄影、构图、运动和声音等方面的设计上,也充满了浓浓的东方诗意。
法国先锋派导演爱普斯坦认为对电影诗意追求的基础在于“现代文学和电影都必须是反戏剧的”,他主张用快速的意象更迭、暗示、比喻和感知去描绘内部世界和意象。在对人物进行刻画时,他主张“电影镜头感”,此概念泊来于摄影艺术,是刻画人物在相貌和身材上美感的途径,即使灯光消失了,但是人物的意象还是会保留下来,而特写镜头则是可以刻画人物意象感知和精神世界的一种方法。在电影中,导演多次以特写镜头对女主人公的外表进行描绘,旨在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意象和世界,产生诗的效果。类似的镜头我们还可以在陈英雄导演的《青木瓜之味》中看见,两组特写镜头从景别、景深到光圈大小极为相似,两名演员的眼神都非常清澈,长相极具黄种人的特点,她们都曾是越南封建落后社会的受害者,单纯清澈的眼神与复杂封建的社会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内在意象实为对封建社会的不满与抨击。(见图4)

图4
在镜头美学的构建上,导演还十分擅长利用“二次画框”进行构图和写意。在中国写意画中,我们讲究“重意轻形”的创作方式,采用大量留白、写意的方式对含义进行表达。而电影的画框,我们一般认为受到摄影机取景框的约束,即取景框的大小,约束了电影画布的大小。在电影《三太太》中,导演充分运用了两个画框进行二次构图。(见图5)

图5
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摄影机的画框外,导演在构图上还利用正方形的窗户创造出了三层空间。电影空间的数量也决定了叙事空间的丰满度,“二次画框”常常被认为是一种重音符号,符合巴赞的电影美学,即“完整的空间与延伸的画外空间与画外音”。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层空间是剧场空间,也就是摄影机的画框向观众延伸的空间;第二层空间是房间内的空间;第三层空间是窗外的空间。一般电影空间分为剧场空间和电影空间,而画框的引入则在电影里增加了一个叙事空间。房屋内轻薄的纱帐、木质的床板和窗户、昏黄的烛光充满了东方的诗意,房间内相当于牢笼和旧社会,窗外象征着新世界,代表着女主人公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和抵触,想要脱离这个社会以及对新世界向往的诗意。大量留白的墙面及多个正方形的构图使得整个画面非常稳定、和谐,极具视觉舒适感。
笔者还注意到,在反映整个场景空间关系及演员的调度时,导演阮芳英同样采用了类似陈英雄在《青木瓜之味》中的长镜头对其进行描绘。在诗意电影的理论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对于电影技术或者工业化的讨论,然而长镜头却在帕索里尼对于诗意电影的讨论范围之列。我们知道长镜头的魅力在于其对现实空间的描绘及其特有的反蒙太奇式的记录性,长镜头的诗意不在于其对于某种视觉符号的刻画和隐喻,而是对于整个镜头运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时间的真实流淌和空间运动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电影艺术有别于摄影艺术的一方面在于其镜头的运动性。我们可以在格利高利·丘赫莱依的《士兵之歌》中看见在麦田中奔跑的诗意,也可以在毕赣的《地球上最后一个晚上》中无人机上飞行的运动长镜头感受到梦境和意识流的诗意。中国导演贾樟柯也是一名善于拍摄诗意电影的导演,他有时也会花费与现实时间一样的等长镜头来表现一些与叙事无关紧要的场景,例如《小武》中在车站打哈欠的少年,以及不惜用近2分钟的时间来拍摄洗澡前脱衣服的过程。虽然这些镜头在整个电影叙事的结构上来看可有可无,但是却充满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诗意美学。贾樟柯本人也提到:“电影的诗意,是一种精神性和心有灵犀的东西,是一种被感染和认同的时刻,这种东西可能是音乐,也可能是语言,总之这个诗意必须是与我生活有关的。”因此,长镜头虽然不具备单一符号般语言性的诗意,却在视觉感受上产生了诗句一般行云流水的主观运动效果,或者产生了在生活中可以得到的真实感的认同,是一种宏观性的诗意。在长镜头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越南民族特有的服饰、建筑、人物、植物等等多方面的符号,这些符号汇聚在一起,通过镜头的运动快速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流露出浓浓的东方诗情画意。
影片中还有许多场景的布景、构图、灯光、摄像等方面都颇具鲜明的东方诗意。影片中时不时传来的梵音、钟声,具有民族特色的乐器等无一不致力于塑造出一个丰满的视听形象,在此不一一赘述。越南及东方民族都对诗人和诗性抱有极高的崇拜情怀,对于电影所展现出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导演阮芳英以一名具有西方电影思想的“他者”而出现,其作品带有西方“凝视”的修辞痕迹。而导演用自身具有东方民族血统的情怀,从民族的磨难、封建社会对人民的压迫等方面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是东方民族自我辩证的需要,是通过自己对家乡的无限向往而抒发出的对新世界的憧憬,是越南导演特有的一种诗意的表达。
四、结语
越南诗意电影的表达,多数充满了外乡学子对于越南当下社会的关怀。同样,我们在韩国导演金基德的电影里,也可以看见大量民族化、具有反思精神的诗意电影。他们的电影语言用诗歌的表现方式去结构化,重视作者的主体意识,淡化剧本和剧情的完整性,通常以开放式的结局作为结尾,对社会问题具有隐喻性、启示性和批判性。在当下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见大量西方世界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电影导演用“他者”的眼光凝视东方的电影文化。近年来,中国的电影也愈发朝着好莱坞式的工厂模式发展,诸如“万达影业”“腾讯影业”等互联网新媒体进入了中国电影市场,电影生产进入了流水线的工作模式,电影市场进入了高产低质的迸发期。近年来,进行艺术电影、诗意电影创作的中国导演越来越少,相反是具有浓烈好莱坞个人英雄主义特色、结构化和模块化的电影大量出现。而毕赣的诗意电影《路边野餐》《地球上最后一个夜晚》等电影票房异常惨淡,骂声一片;反而某些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照搬好莱坞的电影票房大卖,还赢得市场一片叫好。近期上映的动画电影《哪吒》虽然在画面和美术风格上大量采用了具有中国元素的影像符号,但是其在叙事方法和表现方法上还是可以看见日本漫画和美国好莱坞式的风格,大有向西方世界和中国观众兜售东方文化情怀的嫌疑。中国民族化诗意电影的复兴之路还有待努力,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大量民族化的故事素材,在电影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也应回头审视过往,建立自己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电影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