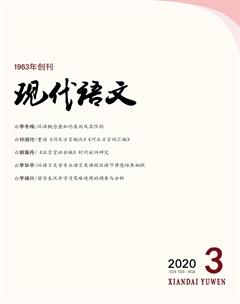人际互动话语标记“信不信”的交互主观性
顾建身
摘 要:“信不信”可以归纳为话语标记,它是具有人际互动作用的话语标记。话语标记拥有自己的核心语义功能,“信不信”的语义功能是由动词“信”和表示原始的征询意义的疑问句“信不信?”带来的。话语标记“信不信”主要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对于“预期”的判断,从而带来了一种交互主观性,并激活了对话语境。
关键词:“信不信”;凸显;预期;交互主观性
一、引言
(一)問题的提出
在现代汉语中,“(你)信不信……”或是“信不信(我)……”频繁出现在口语交际中,在不同的情况下,它所表达的意义不尽相同,有的是表达疑问,有的并不表达疑问。例如:
(1)那警察信不信你说的这些呢?(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话说天下事》,2008-01-16)
(2)你信不信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搜狐网新闻,2017-10-29)
(3)信不信我一个不开心就给你差评然后投诉!让你今天白干!(新浪微博,2017-09-14)
(4)信不信我戳瞎你双眼。(新浪微博,2012-10-24)
关于“信不信”的话语功能问题,学界讨论得并不是很多。在我们的检索范围内,专门研究“信不信”的论文仅找到一篇,即王华的《试析来源于疑问小句的话语标记“你信不信”》(2015)。此文认为,作为话语标记的“信不信”具有话轮交接功能、人际提醒功能以及铺垫和强调功能。我们的问题在于,在这三种功能之中,是否有一种核心的语义功能?这种核心语义会是什么?这些不同功能之间是否有其内在联系?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中心话题。
(二)“信不信”作为话语标记的判定
话语标记既有由词汇化得来的,也有由语用化而来的。由语用虚化而来的话语标记往往以小句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我告诉你”(董秀芳,2010)、“不是我说你”(乐耀,2011)、“谁说不是”(刘丞,2013)等。本文所要讨论的“信不信”也属于此类。
张黎(2017)认为,“语言除了具有表达讲话者的亲身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功能外,还具有表达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他对事物的推断、判断和评价的功能,这种功能称作‘人际功能”,并把具有相关功能的话语标记称为“人际互动功能标记”。“信不信”不仅表达了讲话者的态度,而且对事件做出了评价,如:“你信不信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这句话表明了说话者对听话者威胁的态度,同时具有对事件不满意的评价义。我们认为,这种类型的“信不信”应属于“人际互动功能标记”。
(三)研究目的
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基于现有材料,对各类的“信不信”进行划分。同时,从对话语境出发,分析作为话语标记的“信不信”的互动功能,以揭示其核心所在。以此为基础,我们试图解释“信不信”在主观性方面的交互性特征。本文所选用的语料大部分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媒体语言语料库(MLC),少数例句选自北京大学CCL语料库中的口语语料,还有部分语料来自录音的转写。由于全部语料都是口语语料,所以总体上口语色彩较为突出。
二、“信不信”的演变轨迹
(一)从短语到话语标记的演变
“信不信”是从一般的正反疑问句发展而来的。下面两例就是这种形式的“信不信”:
(5)那警察[信不信]你说的这些呢?(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话说天下事》,2008-01-16)
(6)康总,你[信不信]这些?(池莉《来来往往》)
这种反复式有时也会放在非疑问句中,表示两种可能性,其常见搭配还有“信不信由你”。例如:
(7)不是,你[信不信]这个事很简单吗?你试一下,拿个电源来?(中央电视台《乡约》,2012-03-29)
(8)沙奎尔·奥尼尔、何塞·卡尔德隆,[信不信]由你,这些NBA大明星穿过的鞋,你也能买到穿在自己的脚下。(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2009-10-05)
根据张伯江(1997)的分析,与一般叙事句相比,疑问句都属于一种非事件句,它不在连续叙事中发生作用,只是表明一种征询的态度。由于“信不信”来源于疑问句,它也在话语连接过程中起到征询作用。相对于叙事语体而言,话语征询这种具有交互性的行为在对话语体中更为常见。
李宗江(2010)认为,“我说”这类话语标记是由表示言说意义的“我说”演变而来的;董秀芳(2010)认为,“我告诉你”这一话语标记是从一个完整的小句结构演变而来(董文称之为“习语化”);乐耀(2011)认为,“不是我说你”这类格式已经“习语化”为一个语用层面的话语标记。根据类化或同步引申的规律来判断,“信不信”的演变途径与以上几种应该是类似的,都是由一个完整小句经过“习语化”演变而来的。“(你)信不信”或“信不信(我)”这种短语,多数放在句首,而一个话语标记“如果其初始位置是在句首,那么其中的动词一般都是及物性的,其后可以带宾语,当所带宾语为句子形式时,就有了变为话语标记的句法条件”(董秀芳,2007)。
如前所述,“信不信”来源于“信”的正反疑问形式。当“信不信”的宾语为小句时,为了突出小句的信息,说话人会在主句与小句之间有所停顿,以引起听话人注意,然后再单独说出小句宾语的内容。这样就使一个复杂的述谓结构变为两个简单的述谓结构,起到了突出小句宾语的作用(王华,2015)。“信不信”与小句的宾语关系松弛,两者的依存度降低,“信不信”就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溢出,而原来的宾语小句就会成为句子主体。在“信不信”位于句末时,它便成为附加问句。附加问句是一种特殊的语用问句,其语用意义表示就始发句的内容征求听话人的意见。依照王森(2017)关于“X不X”的四个维度(征询允准、建立互动、增强语气和话语填充)来区分,我们发现,较之一般的正反疑问句,其单纯表示疑问的程度明显降低,而征询、互动、语气等方面有了明显增强。由于征询、互动、语气等因素都包含了强烈的主观性和交互性,因此,“信不信”的语用意义增大,“信不信”的主观交互性显著提高。
(二)“信不信”的疑问句语义框架对言语标记功能的影响
“信不信”虽演变为话语标记,但“信”这个认识类动词本身所带的意义与话语标记的用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信”本身的动词意义和“信不信”的征询意义也制约了言语标记的演变方向。从正反疑问句的句子(如:“你信不信这些”)到非疑问句的句子(如:“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再到“信不信”作为话语标记的句子(如:“信不信我告你”),都有征询意义的存在。
与正反疑問句和非疑问句不同的是,“信不信”进入话语标记层次之后,产生人际互动的功能,多数含有威胁义。那么,这种威胁义是如何产生的?这是我们下面将要探究的重点。我们认为,“信不信”后面的事件往往是出乎听话者意料之外的,涉及到了对说话者及听话者对言语行为的预期的判断。
三、话语标记“信不信”对“预期”的凸显
张黎(2017)把话语标记分为话语组织功能标记、元语言功能标记和人际互动功能标记三类。“信不信”对双方的观点、态度、情感等进行了互动,因此,它应属于人际互动类的话语标记。
张旺熹(2009)指出,话语信息的传达是一个综合的信息传递过程,话语特征会以不同的方式在话语的各个侧面传递出话语的具体信息。“信不信”这种言语标记的核心语义功能就在于对“预期”的凸显。这种对“预期”的凸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威胁,一类是征询。两类凸显的依据在于说话者会话意图。下面我们分别考察其凸显情况。
(一)凸显“威胁”
在此类话语标记中,“信不信”主要位于话轮的开头,交际的意图是试图使对方相信自己的言语。例如:
(9)你[信不信]我给你(打)散在这里!(《新闻1+1》,2017-04-17)
(10)[信不信]我把孩子生下来送人!(新浪微博,2019-01-03)
(11)[信不信]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搜狐网新闻,2017-10-29)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这类话语标记的“信不信”,绝大多数都以“信不信我……”的形式出现。由此可以推断出,这类话语标记“信不信”要让对方预期判断的就是说话人下面将要进行的行为,其意图是通过使听话人相信自己的意图,从而达成说话人的实际目的。这种言语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威胁类的行为。这里我们要区分威胁行为和警告行为。威胁是由指令的言语行为和承诺言语行为构成的复合言语行为,其本质主要是说话人以威逼利诱的手段要求或禁止听话人做什么,“信不信”后面的小句所强调的是如果不按说话人所说去做所要承担的后果。而警告行为是一种指令性言语行为,其本质是提醒听话人应该做或者不做什么。警告言语行为的典型话语标记是“我告诉你”“我警告你”等这类话语标记,它主要是对当下的行为作出提醒。
这类表示威胁的言语,既可以用“信不信我……”来标记,也可以不带“信不信”。例如:
(9)我给你(打)散在这里!(《新闻1+1》,2017-4-17)
(10)我把孩子生下来送人!(新浪微博,2019-1-3)
(11)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搜狐网新闻,2017-10-29)
不带“信不信”的句子也可以表示威胁语气,不过,加上“信不信”之后,更加强化了这种威胁的语气。“信不信”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增强威胁的语气,使后面这种宣誓性的行为显得更不容置疑,让听话者更相信这种预期的真实性。
(二)凸显“征询”
此类话语标记既可以位于句首,也可以位于句尾。当它位于句尾时,多数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小句。例如:
(12)你这时候让它降下去,或者说人家涨了你不涨,你[信不信],他给你游行到地老天荒为止。(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2012-06-30)
(13)但是你[信不信],今天会有中国富豪喜欢这个款。(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2011-12-20)
(14)老子有钱,花10万块钱买你一只手,你[信不信]?(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2009-11-09)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这类话语标记的“信不信”多数会在前面加上“你”。与此同时,这类话语标记确实是在征求对方对一个客观事实的判断,而且对这类问题的回答,说话者是有一定预期的,这也就符合了会话中的合作原则。如果所陈述事实是超乎寻常的,说话者的预期回答通常是否定的。例如:
(15)主持人:没做过按摩,你[信不信]?
观众:打死我都不相信,打死你都不相信。(中央电视台《乡约》,2010-05-12)
(16)主持人:他说除此之外,其它按摩都没做过,你[信不信]?
观众:是我帮他按完以后,然后轮着他帮我按,是这样按的。(中央电视台《乡约》,2010-05-12)
(17)一个全职家教,一年能挣多少?如果我告诉你是10万,你[信不信]?《广州日报》说,为了给上初二的14岁儿子招一名全职家教,目前深圳一名高科企业的老总周先生就开除了这样的待遇:月薪7000元,包吃住,干得好还能加薪。(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2009-09-15)
在例(15)中,主持人认为他没做过按摩是不可能的,是超乎寻常的,因此,问观众信不信,而观众确实也给出了否定回答。在例(16)中,主持人问观众对“除此之外的按摩都没做过”这个事实信不信,主持人自己认为是不可能的,而观众同样给出了否定回答。在例(17)中,“一个全职家教一年挣10万”在作者看来是不可能的,其预设的答案是否定的,之后就给出了一个不寻常的答案。
四、“信不信”的交互主观性
张旺熹(2009)认为,交互主观性主要是指说话人使用一定的语言形式去关照听话人的感受,即说话人在进行说话这一言语行为时,一方面需要顾及对方的感受,另一方面也要促使对方与自己互动。我们认为,“信不信”所处的对话语境也体现了这种对听/说双方的交互关照的特征。
Searle(1979)将行事行为分为五类,我们认为,表达“威胁”凸显的“信不信”的句子应属于承诺类(comissives)中的威胁小类。Searle(1969)曾以构成性规则为理论依据,以“承诺”为例,给出了其构成言语行为的合适性条件。我们即仿照这种格式,给出“信不信”的合适性条件:
(1)正常的语言输入、输出条件成立,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输入输出条件完全符合正常情况。
(2)说话人表达了一个命题。
(3)表达命题时,发话人述说了一个将来可能会发生的行为。
(4)受话人害怕发话人去实施这个行为,说话人也相信如此受话人会害怕。
(5)说话人一般情况下不会去实施这个行为,这个条件是说话人和受话人都知晓的。
(6)说话人确实有意去实施极端行为。
(7)说话人有意通过话语去威胁受话人,警告受话人将要承担这一行为的结果。
(8)说话人想让受话人知道,说出该话之后,即意味着受话人将要承担这一行为的后果。
(9)当且仅当条件1至8成立时,话语才算是正确的、有主动意愿的。
在这些合适性条件中,条件(2)和(3)是与命题内容有关的条件。条件(4)和(5)是预备条件,其中,如果条件(4)中受话人是乐意的,那么就是“承诺”;如果受话人是害怕的,那么就是“威胁”。条件(6)是意愿条件,它将有意愿的威胁和无意愿的威胁区分开来。条件(7)是基本条件,说明威胁对发話人后来的行动具有预兆。
我们此处所说的“交互主观性”,更多地体现为受话人对发话人所说内容的态度,即是否相信。在条件(4)和(5)的预备条件作为双方的共同知识存在之后,发话人满足条件(6)和(7)的意愿,此时,说话人判断受话人是否满足其“预期”。也就是在条件(8)中,受话人通过理解话语意义识别意图之后的反应,能否达到发话人的“预期”,就是“交互主观性”的体现。
就此而言,我们认为,“信不信”最基本的话语功能就是对“预期”的凸显,它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激活对话的交互性,这样就可以使双方的互动能够正常持续下去。“信不信”这一类的问句,要求听话者必须做出回答,从而体现出说话人要求对话双方进行互动的强烈意愿,这也就是“信不信”最基本的话语功能。
综上所述,话语标记具有核心语义功能,“信不信”的语义功能是由动词“信”和原始的征询意义的疑问句“信不信?”带来的。说话人运用“信不信”这个话语标记,就自然构建起一个语义框架。在这个框架内,需要说话者和听话者对事实进行一个有预期的判断,听话人配合说话人回答,便体现出二者之间的交互主观性。简而言之,我们认为,“信不信”是体现了听话人和说话人之间的交互主观性,从而激活了对话语语境的一个话语标记成分。
参考文献:
[1]董秀芳.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J].世界汉语教学, 2007,(1).
[2]董秀芳.来源于完整小句的话语标记“我告诉你”[J].语言科学,2010,(3).
[3]李捷,何自然,霍永寿.语用学十二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李宗江.关于话语标记来源研究的两点看法——从“我说”类话语标记的来源说起[J].世界汉语教学,2010,(2).
[5]刘丞.由反问句到话语标记:话语标记的一个来源——以“谁说不是”为例[J].汉语学习,2013,(5).
[6]屈承熹.汉语篇章语法[M].潘文国等译.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
[7]王华.试析来源于疑问小句的话语标记“你信不信”[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8]王森.基于立场表达的“X不X”类附加问句的话语功能[J].汉语学习,2017,(5).
[9]乐耀.从“不是我说你”类话语标记的形成看会话中主观性范畴与语用原则的互动[J].世界汉语教学, 2011,(1).
[10]张伯江.疑问句功能琐议[J].中国语文,1997,(2).
[11]张黎.汉语口语话语标记成分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7.
[12]张旺熹,李慧敏.对话语境与副词“可”的交互主观性[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2).
[13]张旺熹.汉语口语成分的话语分析[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
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whether“xinbuxin(信不信)” can be classified as discourse markers, and holds that “xinbuxin(信不信)” is a discourse marker with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While discourse markers have their own core semantic functions, 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xinbuxin(信不信)” is the verb “xin(信)” and the original inquiry question“xinbuxin(信不信)?” Bring it.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discourse marker “xinbuxin(信不信)” mainly refers to the speaker's and hearer's judgment of “anticipation”, thus bringing about a kind of interactive subjectivity.
Key words:“xinbuxin(信不信)” ;salience; anticipation;teractive subjec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