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亦奇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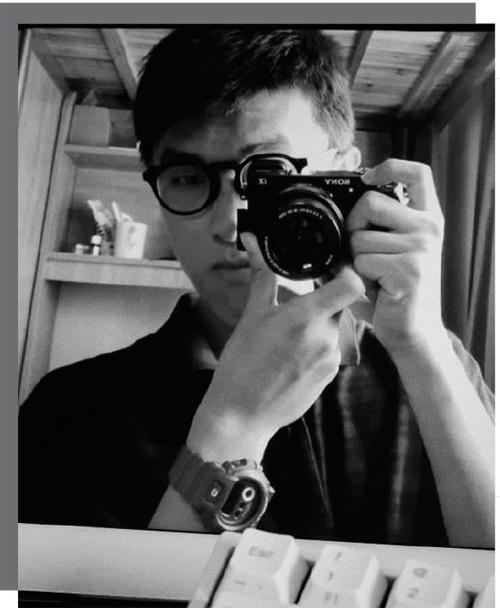
刘亦奇,1999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软件工程系2018级本科生,复旦诗社现任常务副社长。曾获江东诗歌奖。
“农忙与丰收”手册
“我的这条黑色工装裤已经穿了三年”
这不适宜作为一首诗的开头
它早就被洗得发亮:
不止于一种,介于白色和灰色
之间的颜色,或许是红色
再也没有什么新歌让我欣喜了
上课铃,牵一发而
动身,赴往又一次读写
那些更稠密的日子,攀附
高光处,气喘吁吁地安慰我
“所有的爱在畏惧中等待附身”
例如那弧度不再的腰肢
总得续上,长跑至日落
摩擦的省道。水稻田满溢
此时彼时的灾难:孟婆汤
与瓦片屋里的瞎老头,浮出
倒刺的手,我难以再握了
东海的浪潮尚未拍打至这里
这里离海很远,因此
从未有船只能够成功掉头
“西班牙国王,怠速的引擎”
月光冲泡好一阳台的游泳池水
舰队与岛屿屏气狙击
无人石砖路的暮色
四合,我甚至看清了它们的眼睛
金枪鱼摇晃两次,它
如油漆般焦灼的肚腩
就来到这远东的领土
加勒比湾侧方登陆
蒙面的戏台,欲坠如天鹅绒
洒下一满盆淋漓的大米,我就会
完成一首诗歌
赋格与复调
找点消遣
我们知道这很好
**开车**上学去
再喝**一瓶科罗娜**
因为我们游刃有余的
之前 很久之前
第一次就会了
最后一块拼图
这似乎是更有益处的
*爱!自由!旧金山!*
正驱车深入这片新大陆……
明明也不总是美的
却非要留下很多风光
爸爸 我们也都知道
学 校
这是一个,太
快乐的地方
我的朋友们来这儿放假
爱的台风为我们带来温暖
然后是套色印刷的
碧波,留不下一面白墙
这一切可以轻易地解决为
一座海边的森林,它什么都有
都是流亡而来的,会松散地于此聚拢
甚至是一种信任,架在脖子上
大笑。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
是难以赊账的(我爱她),
那就是晒不干的沙子几乎永远黏在我们的脚上
每个人都愿意,一种主义几乎
可以永远:你的夏天,52年了,居然还没结束。
日出冲浪入门
现在你还不能冲浪 饿着肚子的
潮也正开始 新学一种语言
去踩那些夜里长的苔藓 却安全得
像他们给了你养分 如果
你感到要醒了 就徒步来岸边找
人 和石缝里的螃蟹 都等着被打捞
会有柏油路潮湿地 通向你
你想起 昨天下午水波中央的
一场睡眠 也浮在橙蓝色的光里
这样便正好连续 倒影会织得更密
说明已有人仰着头游远了 他是幸福的
有的是心急的人 但更多的
只是归来的渔船 早早锚定那些轰响
直到红日竟跃起如浪 抢在
温度裹上我们之前 这一刻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同时失去重力
谁按下闪光灯 谁先回家
通關《牧场物语》
逐渐熬进我们眼眶里的
夜空,一张暗红色天鹅绒在
老公房的另一头紧张
落下的头屑,累积床头
替代郊区学校明天的星空
本可以和你说很多,梧桐叶般
不至于是秘密的俏皮话:
不至于在无人的教学楼出口
躲雨,玩《牧场物语:矿石镇的伙伴》
也不在海边沙滩的小雨中种甘蔗
没温好的甜牛奶挂着水珠
教会我一种难以加上定语的爱
重踩细沙时的晕眩,让我
忘了劳作的辛苦需要头顶承担
该如何收获?我竟无法再回想了
剧烈的困倦常常让我回到你
因此,我常常为语言干枯
而颤抖的手指落泪,它远不如
命运的手指有力,能将我紧紧
钉在扩张的版图上。去考取
一个复杂的信任,是一把
谷仓的钥匙。一次漫长的饥荒
还没开始,今年的雪就落下了
我再也交不到什么新的朋友
而他们总是试着模仿更多
短 评 DUAN PING
初读刘亦奇的诗歌,很难不被其强烈的形式自觉所吸引。亦奇这一代诗人天生有一副杂食的好胃口,能够轻松地吞噬并消化众多诗学资源,诸如赋格、复调、手册、入门,这些看似浓墨重彩的诗学方法被信手拈来用作装饰花纹。《“农忙与丰收”手册》《赋格与复调》这两首诗歌的形式意味尤其明显,看起来满布褶皱、应有尽有,暗布各种语言的“倒刺”;与之相应的是一种“气喘吁吁”的、充满摩擦和诙谐的语气,诗人似乎并不打算在诗句结尾处悬停稳当。这些诗让我想起一位我喜欢的鼓手,基斯·穆恩。“这对韵律恰当停顿的挑战,这对容纳更多意象的渴望,被叫做跨行连续。”詹姆斯·伍德曾用“跨行连续”这一诗学术语形容穆恩打鼓的风格:“是一种我一直想写出来却总也不能自信写好的句法:它是一段长长的激流,形式上有所掌控而又有狂欢的凌乱,滚滚向前推动也能随性分心旁逸,盛装出席却顶着一头乱发,小心周到同时无法无天,青红是非混为一谈。这样的句子像是一场越狱,一场逃离。”而亦奇正是这样一位擅长跨行连续,小心周到同时无法无天的诗人,同时具备蓬勃的野性和形式的智性。
但在驳杂、凌乱的活力迸发之余,亦奇有些诗句的诗意并不能持续,就像未燃尽的煤球,被置于寒冷的空气中,会过快地冷却下来,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亦奇驳杂的语言形态貌似富含经验,但似乎仍然缺乏足够的经验温度和后坐力,更像是经过风格和修辞精心过滤的产物。比如,《赋格和复调》一诗对于“赋格”和“复调”的使用还是过于轻巧。众所周知,诸如策兰的《死亡赋格》,或巴赫金对复调的描述,从来不是止于形式风格,而是指向更坚实开阔的意义。亦奇使用这些诗学资源时有些“脱序”,更多着眼于修辞技巧。亦奇的诗句,同样存在着沦为“彻底的吊诡”的危险,尽管这种晦涩难解的吊诡会引发读者,尤其是对诗不太明了的读者的“惊叹”,但起初的惊叹如何能经诗人的处理,激发“意识的极大扩展”,并“变幻为富于想象力的理解”,这是对亦奇最实在的考验。
——洛 盏
当我们打开花花绿绿的明信片(我是指,刘亦奇歪歪扭扭的诗行仿佛遵循着某种因地制宜的排版,文字被许多现成而绚烂的图片分割在纸面的这里和那里,而我们对于这类不规则的接纳如同收到遥远处朋友寄来的礼物)发现语言的快乐有时仅仅依赖于它被写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想入非非无意间是诗的局面,以及友谊的张力。而它们变现在语言的活力层面,得体感是次要的。因为漫无边际的诱惑也等于警觉的礼节,他到处感触所演进的音乐性对于“礼崩乐坏”恰恰有个“虚无”的包袱。
——李尤台
读刘亦奇的诗,总会被其中语言松散轻快的场域影响。可以说,他的诗是场域大过语言的,用一种看似低密度的语言,引发了往往音乐才能带来的情感场域。
他的诗中并没有刺绣式的缜密针脚,而具有明亮的空间感和流水般的自由节律,充盈在句与句的空隙之间。《赋格与复调》中,星号内外的文字,甚至这组诗两首之间都形成了类似赋格中采用的复调对位法,两首诗在内容上勾连,主题上也近乎同构。《学校》中既有“套色印刷的碧波”这样高明的修辞,也有“我的朋友们来这儿放假”、“一切可以轻易地解决为”……这样日常而不寻常的表述,它们在诗的逻辑中变形,叙事性和象征化的影子渐渐重合。
——李舜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