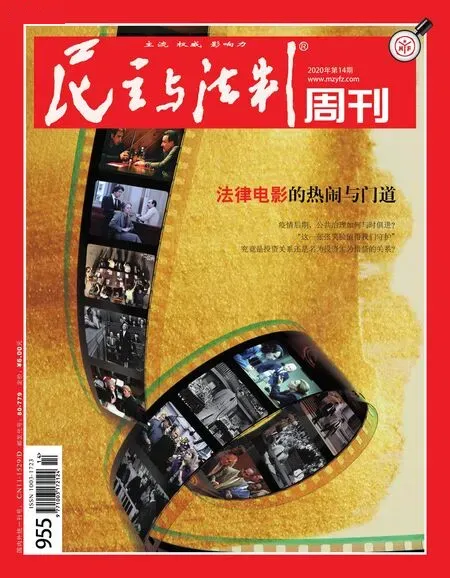看程序价值:法律电影之立意
李长城
电影是一面透镜。观影的人望向屏幕,凝视的却是自己的内心。
美国殿堂级编剧兼导演保罗·施拉德(Paul Schrader)曾说:“真正好的电影就像一枚警铃,会在你体内和你共鸣。法律题材的电影更是如此。”
作为一个从教二十余年的法学教员,正是在一部部敲响心灵的法律电影引导下,十年前笔者萌生了将法律电影作为教学资源引入法学院课堂的想法。此后,历经三年酝酿与打磨,拙作《电影中的法律》于2013年付梓。
囿于篇幅有限,这里笔者将从法律电影中程序正义的角度谈谈电影中的法律问题。
胶片上的法律叙事:拓展的案例
法律电影是法律与大众文化的交集。电影中的法律往往运用直观的手段把法学所关心的主题,诸如审判、正义、道德、人性、习俗、冲突等客观地呈现出来。而法学学者之所以需要认真地研究电影,并非仅仅是因为二者存在主题的相关性,更重要的是电影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视野。
电影不仅是一种消费品,更是一股思潮,一种对社会制度的反思,甚至扮演社会变革预告者和摇旗者的角色,从而使法学可能从中获得滋养。法学家的关注往往来源于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而不仅是法律体系内部。甚至可以说,重大的法学问题往往与社会大众对法律的质疑和思考有关。而胶片上的叙事拓展了法学关注的疆域——作为大众文化产物的电影往往反映出普通人对法律的忧思,这本身就是法学研究需要关注的命题。
从教学的角度来看,案例教学法一直是传统法学教育惯常采用的方法,且被广泛证明收效显著。使用电影作为教学资源,究其本质来说,并不是一种崭新的法学教学方法,而只是案例的一种延伸。然而,法律以其特有的方式简化了世界。
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通常只需要关心法律所确立的事实和要素。在这个体系中,当事人无非是一个个代号,人们的行为只是互相分离的代码,法律职业者们只需要套用法律的公式把行为对号入座即可完成法律的适用。因此,在我们普通的法学课堂上,案例解析的主要目的集中于培养学生的法律适用技术。
可是问题还是出现了:法律越是想简化世界,世界就越复杂。法学教育和研究如果只满足于对法律技术的传播,那么这样的教育既不深刻也不完整。因此,法学教育需要有社会伦理和公众情怀的介入。当电影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法律事件的时候,它就可能成为承载人类感情的法律案例。
正如影片《死囚越狱》和《扒手》的导演罗伯特·布烈松所言:“电影不分析,也不解释。它重组。”在跌宕起伏、情感交错的故事情节发展中,电影建构起关于案件的完整事实;当事人不再是代号,而是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行为与行为之间显现出了关联。在一种常人的感知和思考方式下,电影还原了案件的背景和情形,成为一种“扩展的案例”,为法律学人的认知提供了立体的素材。
尽管人类的认知在过去千百年间惊人地拓展着,但局限与盲点始终如影随形。不仅个体是如此,民族、国家甚至整个人类在特定的时代,都有其认知的局限性。今日为人类所广泛接受的普世价值观,也曾经历过“非主流”的历史阶段:很难想象高歌民主自由的美国,在六十年前还是一个将种族隔离制度写进法律的国家,而南非更是直到1994年才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类似情形的不断涌现启示着我们,人类目力所及受限诸多,而作为时代中的个体,我们很难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陷入盲区与认知困境不可避免。电影特殊的叙事方式恰能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这种认知的局限性。法律电影尤其如此。
通过艺术处理,电影可以轻易地在时空上全方位地展现一个法律事件,优秀的导演和演员借助电影的张力,有足够的时空跨度展现主人公的性情与生平,甚至可以还原主人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这样观众就可以超越时代局限去回归当时,对整个法律事件有更为全面的认知和思考。
就如当下影响整个世界的“新冠肺炎病毒”,人们以自身的经验为基石,很难客观评价各国所采取的防控措施及其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产生的影响。然而很多人在疫情蔓延之时,重新关注起2011年上映的美国电影《传染病》,正是因为该片呈现了同一考题下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和人性的万千侧面,令人深思,以为镜鉴。
在西方法律电影中,最激烈的冲突就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对峙与取舍。许多佳片重构了这个横亘在人类法律思想史和制度史上的价值选择难题,冲撞着我们的思绪,以致振聋发聩。

>>“辛普森杀妻案”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受公众关注的刑事审判案件之一,是“臭虫原则”的生动演绎。辛普森花1000万美元雇佣的辩护律师团被称为梦之队。 资料图
《辛普森的梦之队》:证据里的臭虫
证据法上有一个“臭虫原则”,即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中有一项是伪造的,全部的证据就都会被法庭排除。就像是,当你发现面条里有一只臭虫,你决不会耐着性子寻找第二只臭虫,而是把面整碗倒掉。
“辛普森杀妻案”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受公众关注的刑事审判案件之一,是“臭虫原则”的生动演绎,亦将人类对程序正义的追求推向了极致。依据该真实事件改编拍摄的电影纪录片《辛普森的梦之队》则真实地再现了这场“世纪审判”,重演了“律师梦之队”的主力成员助辛普森无罪释放背后的一个个精心构造的桥段。其中最为精彩和关键的一幕,莫过于“律师梦之队”揭穿警方证据漏洞,使案件走势突然折转的部分。
辩方首先指控负责办案的主要警察证人福尔曼为种族歧视者,遭到福尔曼的否认。于是,辩护律师播放了福尔曼曾数次口称“黑鬼”的录像,形成了对福尔曼不利的品格证据。这对于拥有九名黑人成员的陪审团影响巨大:福尔曼关于种族歧视的谎言就像证据里的臭虫,不仅使自己的证言被陪审团嗤之以鼻并全部排除,也使参与调查的整个警方团队深陷信任危机。
辩方继续挺进,质疑福尔曼违反规定,在未取得搜查证的情况下深夜潜入辛普森住宅的动机,逐步引导陪审团相信福尔曼的行为是制造伪证构陷辛普森。随后,辩方抓住警方未在第一时间将辛普森血样送检的违规行为以及送检血样减少等事实,令陪审团相信警方将部分血样留在了案发现场。
再结合对其他证人的询问,辩方律师不断向陪审团传递出这样的暗示:警方在取得不同血样之间未更换手套、血样,可能存在污染,最终深化了陪审团对警方办案公信力的怀疑,并使法官也认定,检方出具的所谓“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辛普森血迹”的DNA测试结果作废。
实际上,控方在当时已经证明辛普森有充分的作案动机和确凿的证据。如果警方不是为了使案件更加“铁证如山”而伪造了一双沾有辛普森及其前妻血迹的袜子,案件几乎必然走向有罪判决。
而这个关键证据被排除,最终成为整个案件翻盘的关键,也使得辩方律师约翰尼·科克伦得以笃定地说出:“如果证据不足,辛普森便无罪。”
在对审判公正的态度上,我国更加注重实体公正,而美国更加注重程序公正,因为程序正义对于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具有独特的意义。美国的证据法中包括一系列关于证据的采取、证人出庭、质证以及弹劾证人的严格规定,获得和引用的证据必须符合程序要求,实现“看得见的正义”。“臭虫”原则便是美国注重程序公正的产物。

>>左图:李长城的著作《电影中的法律》 张纯摄

>>右图:由阿尔·帕西诺和罗伯特·德尼罗两大影帝主演的影片《正当杀人》上演了一场执法者越位成为审判者兼行刑者的司法实验。 资料图
长久以来,遵守特定法律程序而实现的程序正义被肯定为输送实体正义的渠道,这种比喻形象地呈现了两种正义相亲而不相同的角色特性。对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何者居上,理论界一直存在争鸣。
主张程序正义优先的一方认为,对所谓实体正义过于追求可能使人剑走偏锋而沦为不义,正当的结果必须经由正当的手段而取得;程序正义虽不必然带来实体正义,却是通向实体正义的必由之路;若连程序正义都无法保障,实体正义必然无法期待。主张实体正义优先者则主张,程序正义只是手段,实体正义才是目的,程序正义是为实体正义服务的。若实体正义缺失而徒有程序正义,无异于画饼充饥。
如果在这个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二元对立中思考,我们似乎很难得出“两种正义”孰者居于上位的结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或许能令问题稍加明了:法律重视的是普遍意义而非个别意义,在现实社会中,多元的价值观往往就实体问题的评价莫衷一是,但规范的程序则更容易获得严格的执行和公众的认可。尊重明确而一元化的程序推导出的结论,是人们就社会生活的重大命题求得一致的最有效的方法。
在对辛普森的“世纪审判”中,陪审团和社会公众对辛普森的“无辜”不无怀疑,但“无罪”判决是一系列正当程序输送出的结果。因此,无论陪审团还是受害者家属,均理性地接受了这偏离实体正义的结果。因为人们相信,司法是社会正义的底线,而程序则是司法活动保持正当性和可预测性的底线。
正如宏观的社会秩序比微观的个案解决更重要,法律将法的安定性置于个案的正义性之上。如果为实现所谓的个案正义,突破程序的束缚,打碎司法的防线,人类的社会生活终会面临更严重的惶惑,且这种危机将无法救济。
《正当杀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实际上,法律题材的电影不乏呈现这种惶惑与危机的生动之作。由阿尔·帕西诺和罗伯特·德尼罗两大影帝主演的影片《正当杀人》就上演了一场执法者越位成为审判者兼行刑者的司法实验。
片中的“顽童”和“凤凰”是纽约警署里一对合作超过30年的搭档,对维护社会治安功不可没。但是,公诉案件“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似乎成为警察惩治犯罪的障碍。
在二人负责侦查的一起案件中,名为兰德斯的犯罪嫌疑人被指控杀死女友的幼女,却即将因为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看到被害人母亲悲痛欲绝的神情和兰德斯不以为然的样子,“顽童”感到无法袖手旁观。他在兰德斯的沙发下藏进了一把手枪,最终以非法持枪罪将其送入监狱。
然而,这种“正义”却因为掺杂了不法的因素而变得不再纯粹。更可悲的是,豁口的打开也造成了老搭档“凤凰”的信仰危机:原来他们一直以来恪守的条条框框是如此掣肘,而突破程序束缚竟可以如此轻易地实现实体正义。
内心汹涌的“凤凰”开始借助刑警的职务便利,持枪射杀那些侥幸逃脱法网的犯罪人,制造了一连串神秘的杀人案件。然而,一个膘肥体壮的俄罗斯嫌犯出人意料地扛住了枪伤,成为唯一目睹杀手真容的人。眼看即将被指认,“凤凰”以破釜沉舟的姿态终结了俄罗斯人的性命,并向“顽童”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其实,在公民与公权的对峙中,关于程序的规定往往更多地保护“人”的一方。严苛的司法程序与定罪标准看似为惩治犯罪、实现实体正义制造了巨大的困境,却在实际上调整着公民与公权的力量对比,维系着法律的节制与理性——这在克制公权肆虐与正义感行凶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知道,作为执法者的警察身份和其手中的枪支充满了强权的隐喻,若无严格制约则可能汹涌肆虐,流向另一个不义的极端。正如在影片中,“凤凰”前脚还在扮演正义的执行者,径自射杀漏网之徒,后脚便潜入医院,试图杀死大难不死的俄罗斯嫌犯灭口——由人自定义的“正义”是何等脆弱与狭隘。
2017年1月19日,海派清口演员周立波在美国驾车时,因在道路上蛇行且打手机被警察拦截搜查,当场搜获枪支和可卡因。警方以非法持有管制药品、武器、枪支和危险驾驶对周立波提起指控。
该案历经11次庭审,三易辩护律师。第三任律师斯蒂芬·斯卡林提出的关键性论点是,周立波不懂英语,所以警方不可能在征求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搜车。因此,这项搜查是不合法的,之后获取的证据也应作为毒树之果被排除。最终,斯蒂芬的观点被法庭采纳,周立波无罪释放。
这一案件与辛普森案有诸多同工之处,其结果亦在一段时间内引发诸多争议,包括对辩护律师个人的质疑。然而,我们不妨设想,如果非法搜查这一证据里的“臭虫”不被挑出来,警方在类似的情况下,都可能持枪冲进公民车里甚至家中搜查。面对全副武装的公权力和一个正义凛然的理由,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周立波。因此,程序对公权力的约束平等地保护着每一个人权利中合法的部分,无论你是守法公民还是亡命之徒。
事实上,实现实体正义所需要达到的客观真实标准,与实现程序正义需要的法律真实标准,在多数时候是具有同一性的,只是得出结论的理论依据有所分别。但是,由于人类理性与生俱来的局限以及诉讼活动回溯证明的特点,客观真实标准时常是法律真实标准难以企及的。
此时,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就可能出现分离,出现无辜者被冤入狱有罪者逍遥法外的情形。但是,这作为下位价值(个案正义)向上位价值(程序安定)妥协的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误差,亦是社会维持法律运转所必须忍耐的缺憾。
程序正义是一座不完美的桥梁,但程序的正义排除了暴力、血腥、酷刑和杀戮,为嫌疑人的人权和执法者的操守设定了底线。试图逾越程序实现正义,则陷入另一重原罪。从聂树斌到程正义,我国历史上的冤错案,几乎无一不是程序失范导致人权的侵犯和荒谬的结果。人类的理性天然存在缺陷,对于执法者和司法者同样如此。
执导犯罪片《法外之徒》的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曾说:“电影就是每秒24格的真实。”法律电影在凝缩、重组的情节里,还原着社会和人的复杂性,使观影者陷入巨大的思维与道德困境中,不得不重新思考诸如程序正义冲撞实体正义的命题。
然而,电影终究还是简化的真实。几十分钟过后,影片终结,而现实世界里关于法与社会的思索还漫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