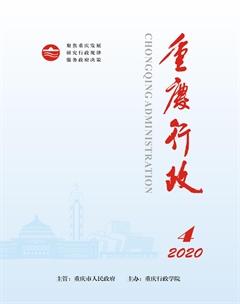信息披露监管:强制披露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在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大趋势下,信息披露制度被监管者寄予重任。2019年我国正式修订通过《证券法》,将信息披露扩充为专章,进一步扩大强制信息披露的范围。但实践中,我国证券市场仍存在着信息过载和信息披露质量不高的问题。相较于直接的政府规制,强制信息披露已是轻微的证券监管手段,但受到投资者有限理性、上市公司披露成本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监管者一味地依靠强制披露,将难以实现保护投资者的目标,还可能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因此,在证券市场中,监管主体应谨慎使用强制披露手段,防止证券监管陷入全面信息披露的困境。
一、问题的提出
在证券市场中,信息披露制度是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亦是证券监管的重要手段。早期的信息披露以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方式进行,但随着证券市场中虚假披露、证券欺诈等问题的层出不穷,各国政府纷纷建立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对证券市场实施间接规制。我国当前的信息披露法律规范要求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的内容已然很多,而实践中仍存在信息供给不足和信息过载的问题。[1]
第一,证券市场面临信息过载的问题。上市公司为履行强制信息披露义务,向市场公开了很多信息,虽符合了监管的要求,但实际上只是信息篇幅的增长,面对繁冗复杂的信息披露文件,投资者难以从中找到需要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另外,年度报告等披露文件存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进一步增加了投资者阅读理解的难度。
第二,上市公司价值相关性的信息披露供给不足,信息披露的质量不高。实践中,上市公司对于投资者真正关切的信息披露往往极少,市场上公开的财务会计信息对于投资者价值判断和市场定价机制的意义并不大,而这类信息在披露文件中占据最大的篇幅,有关公司前景预测、管理层讨论、公司社会责任等更具有价值的信息披露却流于形式,未能真正满足市场的需求。[2]
二、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客观制约因素
信息公开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强制披露的支持者们将其视为解决一切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正如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所说,公开被恰如其分地誉为医治社会及工业弊病的良方。强制披露制度通过要求信息披露者给予披露对象相关的信息,从而使披露对象能够更有效地做出投资决策,同时防范披露者滥用信息优势地位。[3]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合理性在于能够有效解决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们之间的代理成本,促进证券交易的达成,但作为证券市场的规制手段,其作用的发挥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市场参与者的影响。
(一)投资者有限理性与信息过载问题
强制披露的假设前提是信息的充分披露能够帮助投资者决策的优化,但忽略了投资者的有限理性。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市场中每个自主投资者都是冷静谨慎的行为主体,他们在被给予信息后能够评估风险投资中存在的欺诈和利弊,并由此做出理性的最优决策。但是,从行为经济学的诸多研究中可以发现,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存在着诸多认知偏差,如启发式偏差、过度自信偏差、确认偏差与锚定效应等。如哈耶克所说,将法律运用于工具性目标这一思想,容易产生福音式的错觉:假定人们能够知晓所有相关因素,能够从这些关乎特定情形的知识中建构出社会秩序。在证券市场出现新问题之后,立法者就通过扩充现有披露条款来应对公众质疑,而实际上,在面对这些大量复杂的专业信息时,人们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信息过载反而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负面的影响。
结合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趋势,政府规制在证券市场中将逐步实现前端放权,这会促使监管者越发依赖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以期保护投资者利益与证券市场秩序的维持。[4]但是,我国中小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占有很高的比例,相较于成熟的机构投资者,强制披露制度实现的信息对称,会因为投资者的非理性而被弱化,难以形成理性的市场定价机制,这就需要我们对强制信息披露进行简化,提高投资者的可阅读性,来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需求。
(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成本高昂
过多的法定披露义务会增加上市公司的信息生产成本,挤压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空间。现实中,强制披露制度只有普遍适用的标准,而不同行业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异性客观存在,因此强制披露的实施成本并不低廉。实践中,如果监管者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过于宽泛,那么公司为满足披露的合规性已耗费大量成本,那么价值相关性的披露就会因此减少,导致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实际需求相背离,信息披露的质量也难以提高。上市公司的披露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直接成本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进行信息的收集整理,并对披露信息进行审计以及将信息传递给证券市场产生的费用。这些费用可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但强制披露还会产生许多无法量化的信息生产成本,如诉讼成本、管理成本、竞争成本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人们通常低估了上市公司披露的成本,忽视了信息披露成本与披露质量的负相关性。
(三)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稱
监管者与上市公司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法定披露要求不可能事先涵盖所要的信息需求。自安然事件后,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强制披露制度试图事先涵盖所有的信息要求。尽管有这么多的信息披露要求,但仍受到“披露供给不足”的批判。其原因就是除了财务报告等可预测可核实的信息之外,对于一些软信息,如上市公司前景预测、年度经营计划、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以及相关社会责任等信息,公司客观上存在披露的自主决定空间,监管者难以对其进行事先的预测和事后的核实,强制披露在这类信息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决定了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从投资者有限理性、上市公司披露成本以及监管者的局限性来看,强制披露并非万能。立法者试图通过对上市公司施加更多的法定披露义务的方式,来实现投资者利益保护和市场秩序维持的目标也许会落空。在信息披露监管中,不仅要关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还应关注强制披露的范围是否过于宽泛。
三、强制性信息披露的优化路径
(一)披露范围的界定:以监管有效性为标准
从监管者角度看,强制披露对于不同信息的有效性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根据上市公司在披露中选择权的大小,只有可观测可核实信息是最小的,当选择的空间越小,那么外部监管措施在实际操作中就越有效。[5]因此,根据信息自身的属性与监管的有效性,强制披露的范围应当集中在公司外部人可以有效观测并核实的信息上,如上市公司的资产、现金流量等直接反映公司生产经营的财务信息,监管者可以对这类信息进行有效的监督。但对于可观测可核实之外的信息,由于其信息自身的属性决定了,即使作出强制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定,上市公司也具有很大程度的披露选择权,信息监管很难对其披露的真实完整性进行考察,将这类信息纳入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范围更为合适,譬如上市公司经营计划调整、管理层讨论分析、公司社会责任等非财务信息。信息属性的分类与监管的有效性紧密相连,将其作为划分强制披露范围的標准是行之有效的,这既防止信息规制的无限制扩张,还能保证强制披露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二)上市公司角度:解释性披露的引入
从上市公司角度看,强制信息披露给上市公司带来的信息生产成本往往被低估,过多的法定披露义务会降低信息披露的质量。不披露即解释规则的引入可以缓解强制披露的制度刚性与上市公司披露成本高昂的冲突。[6]
强制性披露转变为解释性披露,可以加强市场执行机制和契约的作用。因为在市场竞争中,信息披露质量高的公司更受投资者青睐,这是传统的自由市场中的价格与质量成正比的自然结果,上市公司基于市场竞争本就具有披露的动机。然而当公司披露成为一种强制性规范行为,此时市场竞争机制与契约的作用被削弱,上市公司的披露行为更加侧重于满足法律的要求而非市场的需求,这时就需要政策制定者以一种轻推的方式来达到政府规制与市场自由之间的平衡。具体来讲,在强制性披露规范中,首先默示上市公司需要遵循这些强制性规范,而上市公司可根据自身实际需求,明示排除适用部分条款。解释性披露是强制规范适用的例外,同时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即上市公司需要对排除适用部分条款的原因进行解释并公开其替代性措施。不披露即解释规则不再是传统的制定——遵守或违反的二元模式,而是由外生性规制转化为内生性规制[7],既没有加重投资者信息搜集阅读的成本且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关注,同时赋予了上市公司一定程度上的选择权利,有利于缓解强制披露制度与市场自由之间的对抗状态,促使上市公司由合规性披露向价值性披露转变。
(三)投资者角度:强制披露的简化
从投资者角度看,有限理性的相关研究证明了强制披露导致的信息过载问题比信息不足更加严重。实践中,强制信息披露面临着简化的需求,我们需要在信息的理解难度和投资者理解能力之间找寻一种平衡,提高上市公司披露文件的可阅读性。如前文所述,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而且各类投资者的专业素养并不相同,所以平等的信息披露并不能实现平等的保护。不论普通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他们都有着披露简化的需求,来降低信息搜集处理的成本,我们需要在专业化的基础之上对披露文本进行重新设计和调整,譬如通过浓缩报告摘要、简化报告文本的方式来提高投资者的可阅读性。[8]对于普通投资者,因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简化披露的重点在于提高文件的可理解性;对于专业能力较高的投资者,他们利用信息的程度更高,简化披露的重点在于对繁冗无效的信息进行删减,以此来提高信息处理运用的效率。
综上所述,从监管者的角度看,强制披露范围的界定除了传统的重要性原则外,还需考虑信息自身属性与监管有效性的关系;从上市公司角度看,解释性披露可有效地缓解强制披露的制度刚性与上市公司披露成本高昂的冲突;从投资者角度看,有限理性存在于各类投资者之中,要防范信息过载的问题,完善强制披露的简化工作。
四、结语
信息披露在保护投资者与维持证券市场秩序的逻辑是正确的,但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投资者的素质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强制披露并非万能,但在当前的证券监管中,相较于政府直接规制和合同主义的监管理念,强制信息披露介于二者之间,因此既要考虑其制度的优势,同时也需结合现实的制约因素,不断地进行制度的优化和调整。
参考文献:
[1]蔡奕.十字路口的中国证券法:中国证券市场法制新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6.
[2]巴曙松,郑子龙.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变迁中的上市公司责任[J].金融市场,2018(1).
[3][美]欧姆瑞.本.沙哈尔.过犹不及强制披露的失败[M].陈晓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9.
[4]陈洁,孟红.我国证券市场政府监管权与市场自治的边界探索[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
[5]王慧芳.信息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的重新界定与监管[J].宏观经济研究,2010(12).
[6]张辉.倡导性规范与上市公司治理[J].证券市场导报,2010(11).
[7]杨淦.上市公司差异化信息披露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5.
[8]李虹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立法的适度性研究[D].福州大学.2018.
作者:福州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法律硕士
责任编辑:刘小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