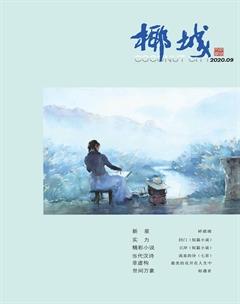相遇者
作者简介:李霞,山东诸城人。作品散见于 《散文选刊》 《小品文选刊》 《广州文艺》 《滇池》 《文学港》 《青海湖》 《福建文学》《青岛文学》 《散文诗世界》 《新国风诗刊》 《中国教师报》 等报刊。
一
邻座。上去火车找到座位号,正要把沉重的双肩包托举到行李架去,他恰好忙完转身给了我帮助,快速轻松做好了搁置事宜。这是自己所期盼的帮助。事后,我更愿意相信这种热情来自一个人好客的品性,而不仅仅出自举手之劳。好客,让那些所做多了自然。一个戴眼镜、大眼睛的高校男生。
忆起,出现他的大眼睛和开朗的笑容,仿若还生动在那列夜行火车上,呈现的是一张毫无拘束的脸。
交谈。他的目光定定地望向你,不会有丝毫闪躲,随时保持着话题的热情。他从放于脚边的纸袋里取出两个小灌装的果冻,一个自己吃,另一个分送给我。还保持着稚气未脱的用食偏好,令人切近他尚在青春的年龄。
他打开手机一档娱乐节目视频,把音量调大,置于共用的台桌间合适的位置,邀请旁边的我观看。婉言谢绝后,他便戴上耳机瞬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不时作出开心会意的情绪应和。之后在列车哐当有致的长夜中困倦,伏身沉沉睡去。醒来,搓揉几下双眼,依旧现出饱满状态,继续看手机、吃食物,包括大方品尝我邀他共享的小零食。
将近拂晓,他有一段长时间的离开。再出现,身边多了一位同龄的女伴。她从合肥上车,站票。他把座位让给她坐,自己很绅士地做护花使者。累了,便挨挨挤挤坐下。是少男少女间活泼的谈话。热衷于各自生活圈子的交往趣闻,凑在一起翻看手机,彼此取笑。——虽属于相识并不相熟的关系,一路上这样的持续并不吵嚷。男生善谈却并不琐碎的品性把控起这些,旅途因显轻松,不会过多被动接受喧扰。
对面是极其安静的男子,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工。他从临沂上车。宽大实用的条纹帆布包举推到搁物架,留下一个拉链提包和一个红色布袋置于脚边,使座椅之间的窄小空间更显局促,向前伸腿要小心绕过。他要坐32个小时到达打工之地贵阳。漫长的旅途。随后看到他为这些做好了充足准备——捎带大量的食物。一度认为他是嗜酒者,上车落定,就把便于携带的一小瓶高度酒置于台桌之上。
没有想象中的严重,只是称得上喜好而已,用作一日佐餐,打发偌久的长途时光。食物,是典型的鲁东南乡村特色。脚旁的包里塞满着这些,是至打工之地后短时间内可以一直取用的食物。
用餐。他从里面取出一张煎饼,取出大玻璃瓶里腌制的青辣椒,又取出同样玻璃瓶盛装的炸肉块。肉块被两只黧黑的手拿到煎饼里摆成条状细心裹卷,成为细细长长的卷筒。筒长超出自己先前所见,是独属一处地域的风格。伊始见到,作为山东同乡,我和大眼睛男生还是略有吃惊,随着他一下一下逶迤的裹卷不禁微露笑意。腌制不久即取出的大青辣椒,辣味依浓,作为辅菜,他大口食用,直到辣得嘴里发出哧溜哧溜的声音。这样的食物虽然简单,却足以诱人。讨教腌制的最佳方法,他很在行地一一解说。觉出是农活之余勤于持家的男人。
即使在火车上,他的一日三餐时间也按部就班进行,极为规律。除此之外便陷入沉默、睡眠或一次次于车厢口逗留,放松久坐僵直的身体。
现在忆起,是他的半身照图像,就像先前隔着台桌看到的他坐于我对面的样子。相异于开朗健谈的大眼睛男生,他惯有的沉默让我于他的面前有了理性划分,还原为旅程里彼此陌生的过客形貌,于此,凸显出与其紧密相关的那些物的呈现,比如每餐饭必有的一张阔大的煎饼。这些成为一个个象征符号,附着在他身上,让人由此而记住一个人。那位后来坐在我旁边的湖南籍邻座,当看到对面的他在用餐时间双手展开又裹拢的看上去壮观的食品,完全表现出陌生和好奇,不由侧头探询。疑惑,在那时,闪现在一个年轻的南方人眼中。
二
娄底。路的拐角,十月依然热烈的阳光里,她坐在阴凉处的台阶上在低头做一只拖鞋。拖鞋的毛线用材吸引了我。之前并没有见过用此类材料制成的拖鞋。趋近观赏,未曾想到吓到她,她眼神相迎的一瞬充满了惶恐,身体本能地往后一缩。这样的反应同时令我不安,为于她没有察觉自己靠近的冒犯。但仅仅只一瞬,她便又恢复到放松的神情,甚至欢喜起来——为有人蹲下来认真欣赏她的作品,而不是对自身造成不利的闯入者。那时也才知道,她是个聋哑人。
也许她在钩织中等待有人来买她的拖鞋,瞬间的惶恐是误以为城管前去干涉,或者只是在消闲中给自家人钩用,惶恐来自专注力在不经意间的被破坏。不能明晓。
交流。她没有像其他聋哑人那样发出“啊啊”的声音,只是用轻快的眼神和手指交流。是内秀和乐观接受既定命运的女人。她指给我看还需要加固的鞋口,然后开始一针针熟练的钩线操作。看得出她的认真和专业。毛线紫红和深绿相间,是和谐沉稳的色调。浅色鞋底垫层厚实、针脚密致,耐品且耐磨。整双拖鞋称得上精细好看,非一般的功力所能达到。
佩服这样擅于家常的女子。身体于常人的有异,这样的擅于显得格外肃重,为别人认同,同时成为自身安实的来源。一位四十岁左右、普通而安然的聋哑女人。
即将告别娄底的下午,在火车站等待时,与另外的残疾人相遇。他们在乞讨。
他们在大厅座无虚席的每排座椅间串走,获取一点讨费。没有票证,不知他们怎样进入、又为何可以毫无顾忌地讨要,缺少站内监管。现今各地火车站出于秩序维护和安全防控的需要,如此情形已几乎消失不见。这儿成为个例。乞讨者中的盲人,由他身体正常的家人引带到乘客面前站定,然后他自己开口讨要。两人都是五十岁左右的男人。而其他两人也均为男性:一位右小腿截肢柱单拐,年轻微胖;一位左腿肚静脉曲張,同样并不年长。后者把左裤腿高高挽起,便于所到之处把病患部位显而易见地呈现给他人,赚取怜悯。
微胖男子,会在讨要一圈后于一根柱子或一面墙壁前倚靠,吃点东西略作休息,等待旧乘客大批检票离去后新一批乘客的填充,减少重复索要带给乘客的厌烦。另两位似乎没有耐心,他们在每排座椅间穿梭时间不会相隔很久。被重复索要的乘客不堪其扰,会因此心急气躁抢白一句,讨要者只好麻木地离开,表情于先前并没有多大变化。
大部分乘客,处于置之不理的状态,任凭对方怎样在面前站定讨要,保持沉默一概成为回答方式,是一道无形屏障,也是对其行为的无言抵抗,彻底阻止着对方进入。
熙来攘往的候车大厅,因这些少了有序和等待的安然。
火车一再晚点。窗外渐渐散去夕照时,那些乞讨者也随之消匿了,应和着那句“日落而息”的话,不知是否也“日出而作”。他们寄生于这个候车厅,使被成为宿主的候车厅受到损害,失掉原本的光华。
聋哑女、乞讨男,他们以坐和站的影像轮廓出现于记忆中的画面,一则莹亮安谧,犹如那双灵动精致的拖鞋。一则混浊不安,仿若望见的其中一人腿上那几条变形的筋络。他们最终将这些当作讨钱的资本。
三
晚点的火车,要在两小时后才能等到。背起略重的双肩包走出车站,到来时路上经过的石马公园。相比沉闷的候车厅,碧空下绿树环绕的公园虽然同样人流众多,但显然敞亮清透许多,可以较安逸地度过等待的时间。
进门,便有优雅的乐音缭绕于公园,以为是园区音箱的播放。攀上一道斜坡,拐角,望见了乐音出处—— 一位拉小提琴的中年男子。这让自己略有惊异,为来自自然中的现场演奏。或者说是为艺术日臻成熟的练奏,而不是卖艺者。他站立在演奏之地,处于坡崖边缘,面前为坡崖下浓密的乔木灌木,这些剔除掉别人从正面望到他的可能,除非他主动回头。
的确,偶尔他会回过头来,那是他在一段练奏停顿时对来自身后声响的自然回望。——孩子怪异的尖叫声,或者旁边人影的喧哗和走动。所以背对人流,于他自己和别人都可以轻松自在,像处于两个不相干的世界。又像两件相异事物的共存,因为有了默契共识而消解压力,继而产生愉悦。这像一幅画面,画面一侧,是心无旁骛凝心演奏的男子。另一侧,是其身后不远处散落的石桌旁那些随性闲坐休憩的游人。这同时是大自然安适浪漫的生活景况。
分辨不出他演奏的曲目,听来陌生。但熟练流畅,觉出用心。面前,摆放着立式乐谱架,很郑重的练奏,让人感到专业的特质。
他有持久的耐力,长时间同一姿势站立,并不休息。艺术融入个人生命,便成为孤绝之事,于内心一次次完成朝拜,是自我成就力量的信仰,值得承担面前所对,即使困窘。它来自生命中的切实体验。艺术因这些而阔远和深厚。不知他于自然中演奏的初衷,是汲取抑或寻证什么,或者仅仅释放什么,从而完成与心灵的某种对接。艺术本身,包含了太多可能,每人所见,是各取所需的部分。
如今存留记忆的男子画面,是和自然相连一起,是融入大自然中的画面,两相和谐、唯美,彼此生动照应,同为艺术。它们盛大延展开一方天地,让观者领略到一种余味悠长的丰富所在。
同样存有的愉悦记忆,还来自一位同龄女子。是在长沙。她以追跑的身影出现。而自己那时正在稳步前行。她边跑边用力高声叫住我,回头的疑惑间,看到了她手里晃动着的手机。顿时明悟手机于她处的遗落,她在送还手机。一位米粉店店员。自己刚刚在那里用过午餐,印象极佳的餐馆。店址毗邻湖南第一师范,一家百年老店。
及时的交还,免去事后尋回的烦琐奔波。一个于一处地方短暂停留的远方客,对自己随身所用物品需细致珍视的必要,于那时得到提醒。也由此对所历印记带出鲜明观望,如同在片刻凝视一个静止或活动着的焦点。
旅途中的那些相遇者,亦是如此。